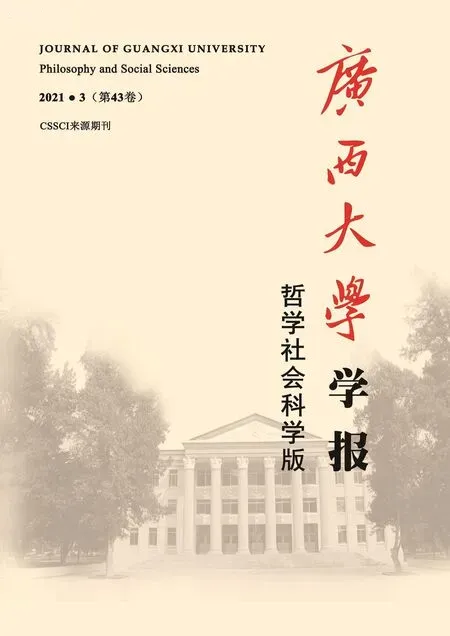朱熹注解“明德”的思路与意义
郭矩铭
《大学章句》对明德的注解包含心、性两个层面,并且没有将明德具体归于性或心,为后人留下解释的空间。学者们就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蒙培元主张“朱熹把明德说成是心之本体,它是心,又是心之理,亦即性”[1]。陈来认为明德指“本心”[2]。朱汉民、周之翔以“心性一体”[3]解释明德。吴震释明德为“心中之理”①吴震强调心和明德是“明德之在心中,心中之有明德”的关系。参见吴震.朱子思想再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21,123.。四种观点各有侧重,但都坚持从心、性两个方面理解朱熹的注文。因此,朱熹究竟如何理解明德仍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一、从《大学或问》到《大学章句》
关于朱熹如何注解“明德”,学者们的意见各不相同。这不仅是由于朱熹没有用具体概念解释,而注文又包含心、性两个层面所造成的,还因为在各类文献的记载中,朱熹对明德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其中,《大学章句》的注解最具代表性: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4]3
“人之所得乎天”指性,表示明德是从人的角度而言,其根源在于天。《孟子集注》中定义性是“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4]356。性指心中具有的理,而理又源于天。由此观之,在概念上明德包含性。天、理、性虽然相同,但有视角的差异:“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5]82朱熹点出“天”字,不仅是将天作为明德的根源,更从形而上的层面保障了明德的至善与普遍性。所以,不是部分人,而是所有人都具有明德。《孟子集注》偏重于阐释心、性、理的结构关系。《大学章句》着重从人由天而禀赋性的角度论述。
“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是言心。据《孟子集注》,心是“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4]356。两处表述相近,但有不同。“虚”表示内心没有私欲,“灵”是感觉思维能力,“不昧”指心原本湛然而不遮蔽理的状态,“虚灵不昧”是描述心的本然状态。“神明”指心的感觉思维能力,主要描述心的功能。“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指人凭借自身能感觉思维而又毫无私欲的心去具有众理,接应万事。“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旨在说明心是人能够具有道理、接应万事的原因。前者侧重于从工夫的角度描述心的状态,后者偏向于论述心的功能结构。此处的心不是发为思虑情感的已发之心,而应是未发的“心之本体”。原因有二:第一,文中称“学者当因其所发”,而“其”指明德,故心应该是未发状态;第二,朱熹用“虚灵”来描述“心之本体”[5]87。“心之本体”指心的本然状态,不涉及价值判断。朱熹点明心的含义后随即论述了明明德的工夫。“气禀”“人欲”会遮蔽明德,但明德本身不会消失。人们应该根据明德的发用而回复到它本来的样子。由此可见,《大学章句》揭示明德属心的一面与明明德工夫的展开有关。
在朱熹之前,二程就直接将“明德”解释为“道”“理”①二程并未详细阐释其中涵义。“《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22,136.,但尚未涉及心的概念。朱熹在二程解释的基础上引入心,从心、性两个方面来理解明德。这一立场早在《大学或问》中便已体现:
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6]507
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6]508
前者“虚灵洞彻,万理咸备”言心,后者“本明之体,得之于天”论性。《大学或问》和《大学章句》的思路基本一致,都从心、性两个方面解释明德,只是表述不同。《大学或问》成书于1177 年,朱熹之后虽有改写但在整体思路上应保留着成书时的原貌②“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余议论,别为《或问》一篇,诸家说已见《精义》者皆删去。”朱熹.朱子全书:第25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4680.束景南、陈来考证此信写于1177年。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85;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56–157.朱熹本人也说:“五十岁已后,觉得心力短,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学》《中庸》《语》《孟》诸文字,皆是五十岁已前做了。五十已后,长进得甚不多。”参见黎靖德.朱子语类:第7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621.可见朱熹注解的基本思路在《大学或问》成书时已确定。。
《朱子语类》对明德的解释相对丰富:
问:“《大学》注言:‘其体虚灵而不昧;其用鉴照而不遗。’此二句是说心,说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细看。”又问:“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许多道理,光明鉴照,毫发不差。”[5]265
此条语录为徐㝢所录,不早于1190 年。其中所引的“其体虚灵而不昧;其用鉴照而不遗”为朱熹的旧注。相较《大学章句》,这一解释更倾向于以心的体用来解明德。但是,当朱熹被问到“是说心,说德”时,他又强调“心、德皆在其中”。故朱熹在旧注中同样持心、性兼释明德的立场。《大学章句》较旧注更强调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和“具众理”两点,突出其属性的一面。
1194 年,朱熹为宋宁宗讲授《大学》而作《经筵讲义》。其中,“明明德”被释为: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当有以明之而复其初也。[7]
《经筵讲义》的注释与《大学章句》更为接近,应在旧注之后。《大学章句》的论述又较《经筵讲义》更严谨细致,当成书于《经筵讲义》之后。旧注侧重于言心之体用。《经筵讲义》点出“人之所得乎天”的性,并以“至明而不昧”言心。《大学章句》将“至明而不昧”改为“虚灵不昧”,并提出“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虚灵”相较“至明”突出人心毫无私欲的本然状态和感觉思维的能力。“具众理”表示心能够具有道理,是明德能兼具心、性特点的原因。“应万事”指心接应事物的能力,是明德工夫得以展开的基点。
朱熹有时直接用性解释明德:
(1)或问:“明德便是仁义礼智之性否?”曰:“便是。”[5]260
(2)或问:“所谓仁义礼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无一毫不明。”[5]260
(3)“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与我,未尝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5]262
(4)明德,是我得之于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统而言之,仁义礼智。[5]271
语录(1)(3)释明德为性。语录(2)(4)在论明德时虽涉及心,但最终还是将明德定义为性。语录(1)(2)没有明确的记载者和时间。语录(3)录于1198 年后,语录(4)的记录者为汤泳,时间在1195 年后。而1198 年左右,今本《大学》的注释已形成①“‘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禅家则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而无以具众理以下之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66–267.此条语录的记载不早于1198年。。因此,朱熹在基本确定了注文的情况下,仍强调明德属于性的特点。考虑到《语类》的语录体特点,朱熹的解释可能是根据提问的不同而有所侧重。语录(1)(2)便是例证,朱熹只是就提问人的问题而回答,所答内容自然会受限于问题。此外,《经筵讲义》之前的解释相对偏重于心,所以朱熹弟子问明德是否为性的例子自然较多。
明德与心、性究竟是何种关系?钱穆对此有一段精彩解读:“明德虚灵不昧,能具众理而应万事,此乃人心本体……由知言,则理必明于心。由行言,则理必由心流出。就其本始言,则是心与理一。就其终极言,亦是心与理一。”[8]钱穆所说的第一个“心与理一”指心与性(理)合一的本然状态,即明德,第二个“心与理一”是人经过工夫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因此,明德是在排除“气禀”“人欲”的情况下,对心与性合一的本然状态的描述。同时,明德兼具心、性的特点也符合朱熹对心、性相即不离、相互发明的理解②“此两个说著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88.。
综上,至少从《大学或问》开始,朱熹就坚持从心、性两个方面诠释明德的立场。其间,朱熹不断地打磨文字,以求更清晰地阐明其中的含义,主要有旧注、《经筵讲义》两种表述,直到1198 年左右才形成今本《大学章句》的注释。
二、明德与良心、本心
以心、性合释明德是朱熹的基本立场。那么,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还有哪些和明德相对应的概念?在《朱子语类》中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关于良心:
明德,谓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5]267
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个止处。[5]269
以上两条语录均为廖德明所录,朱熹用孟子的良知、良能、良心等概念解释明德,而此种解释相较少见。同时,两条语录均为廖德明所录,并且记录时间只能判断在1173 年以后,故不能直接断定朱熹主张明德就是良心。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判断朱熹是从以良心释明德,发展为以心、性合释明德。因为,1177年成书的《大学或问》已经表现出心、性合释明德的立场。即使两条语录记于1173 年,朱熹也不可能在成书前四年时对核心概念仍模棱两可。
“良心”(《孟子》11·8③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为据。)由孟子提出。《四书章句集注》多次提及: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故平旦未与物接,其气清明之际,良心犹必有发见者。[4]337
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4]292
良心是善心的原初状态,即孟子说的仁义之心(《孟子》11·8)。善心指人的意识活动符合道德准则,属于心的发用层面。故“本然之善心”指心之未发。“良心之发”表现为“事亲”“从兄”,那么良心就是未发。此外,朱熹将孟子所说的“仁义之心”解作性,“恻隐之心”释为情,二者对举[5]91。所以,良心是未发的,指心与性合一的本然状态,在概念上等同于明德。至于《语类》中为何仅有两次将明德解作良心的记载,下文再论。
第二条线索指向本心。在《语类》中,朱熹曾肯定过“‘明明德’,是于静中本心发见”[5]263的说法。此条文献间接地表明本心与明德相同,但我们还需要从义理上一探究竟。关于本心,《四书章句集注》载:
(1)其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也。[5]266
(2)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5]133
本心之中的德就是理④“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48.。句(1)为朱熹解“赤子匍匐将入井”(《孟子》5·5)的注文。夷子视父母为路人却厚葬父母,朱熹认为原因在于夷子的“本心之明”从未消失。而人之所以能明自身的明德,正是因为明德“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句(2)所说的是,人心之中的德性本为天理,但会被人欲毁坏,人们应该克服私欲,回复心中德性的原貌。“心之全德”即是天理,与明德“人之所得乎天”的表述相同。回复“本心之全德”的工夫也与明明德“复其初”的工夫一致。由此可见,明德即是本心。事实上,现代学者以“人心本体”“心之本体”解释明德,都是从本心的角度来理解。
前文已经论证明德就是良心、本心,而其中的差别还有待说明。朱熹对良心、明德的使用有严格限制。除《论语集注》引张敬夫的一处[4]51,良心的用法只限于《孟子集注》。在《大学章句》外,明德仅在《中庸章句》《孟子集注》中各出现一次①一次为《孟子集注》中朱熹引尹焞之文,另一次是《中庸》引《诗经》之文。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41,376.,且两次均为引文。“本心”(《孟子》11·10)也源自孟子,但在《中庸章句序》《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都曾出现[4]14,133,266,成为朱熹注解《四书》的基本概念。
综上可知,朱熹不会轻易地使用《四书》中某一文本的概念去解释另一文本的概念。因为这是注解的基本规则,否则注解只是用一个不清楚的概念去解释另一个不清楚的概念,达不到注解的目的。所以,即便朱熹常用“本心”一词,《大学章句》中也没有用本心或其他概念注释明德,而是细致地阐释了明德在心、性两方面的特点。如此方能完整地揭示明德的心性结构,并引出其工夫论的面向。
明德、良心、本心的内涵一致,但根据文本语境的不同,朱熹的解释有所侧重。因此,朱熹注解《四书》时,良心限于《孟子》,明德仅释《大学》,而本心在《四书章句集注》的注文中随处可见,显然成为朱熹哲学中重要的概念术语。由此再回顾廖德明所记的两条语录。这两条语录都提及《孟子》的文本,朱熹以良知、良能、良心解说明德实质上是用《孟子》《大学》中的概念相互发明。正是依靠这样的方式,朱熹打通了《孟子》《大学》中的核心概念,为文本思想的融会贯通提供了基础。
三、从明德到新民
尽管《语类》常强调明德属于性的一面,综合来看朱熹更重视以心、性合释明德。性保证了明德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心则是性的着落处,也是工夫的立足点。工夫具体立足于“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和“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两点展开。《语类》载:
或问:“‘明明德’,是于静中本心发见,学者因其发见处从而穷究之否?”曰:“不特是静,虽动中亦发见。孟子将孺子将入井处来明这道理。盖赤子入井,人所共见,能于此发端处推明,便是明。盖人心至灵,有什么事不知,有什么事不晓,有什么道理不具在这里。何缘有不明?为是气禀之偏,又为物欲所乱。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终是遮不得,必有时发见。便教至恶之人,亦时乎有善念之发。学者便当因其明处下工夫,一向明将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时都不知,便是昏处;然有时知得不是,这个便是明处。孟子发明赤子入井。盖赤子入井出于仓猝,人都主张不得,见之者莫不有怵惕恻隐之心。”[5]263–264
明明德工夫的展开主要基于明德“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的特征。这一特征源于心与性的关系,具体指“人心至灵”和“德本是至明物事”。明德之“德”指性,是内在于心中的先天道德准则。同时,由于性源自天,性普遍、永恒地存在于人心,从而保证每个人的明德必然能发见。如果离开性,心不仅会失去道德准则,甚至无法知觉②“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邪?’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85.,这就是“舍性又无以见心”。性超越于经验,但也蕴含在具体的实践工夫之中③“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见者。只是穷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须求,故圣人罕言性。”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83.,而心就是做工夫处④“心是做工夫处。”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94.。德之所以能“至明”是因为“人心至灵”,即拥有知晓自身所具道理的能力。当心知晓道理时,道理就显现在心中。性作为先天的道德准则要在具体的经验世界中显现就离不开心,一旦离开,它只能是纯粹的形而上之理,此即“舍心则无以见性”,故明德之“明”是从心的角度而言。基于心和性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发明的关系,明德才能从不停息,人们也方能根据明德的发见处而做工夫。
明德从不停息只是明明德的根源和依据,还不是直接做工夫处。现实中,人们做工夫是根据明德“所发而遂明之”。明德的发用主要有两个阻碍:一是“气禀所拘”,二为“人欲所蔽”。按朱熹的解释,气禀的拘束和人欲的遮蔽只能使明德暂时昏暗,而心中所具的性能确保明德从不停息。因此,明德不会一直被遮蔽,终有显现自身光明的时候,甚至最邪恶的人也会不时地心生善念。每个人在现实中都必然有明德发见之时,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做工夫处。
明德的发见有“动”“静”不同,分别指心的已发和未发。引文主要论述明德在“动”时发见的情况。“孺子将入于井”(《孟子》3·6)、“赤子匍匐将入井”(《孟子》5·5)都是孟子提出的思想实验,用来说明人皆有恻隐之心。朱熹认为,人见到小孩将要掉入井中时所产生的恻隐之心就是明德的发见之处。朱熹紧接着还谈到更为普通的情况:“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时都不知,便是昏处;然有时知得不是,这个便是明处。”当一个人做了错事而不自知时,明德的光明就被遮蔽了。如果人能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便是明德的发见。朱熹认为:“一念竦然,自觉其非,便是明之之端。”[5]261明德的发见表现为对自我意识和行为的是非判断。换句话说,明德的发见指人心对性的意识。
明德发见之处只是明明德工夫的出发点,明明德还包括其他许多具体的工夫项目:
所谓明之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阙一。若阙一,则明德有所不明。盖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无间断,使无时而不明,方得。[5]265
如此,朱熹把《大学》“八目”中的前五项归纳到明明德之中,是人充分实现自身明德的必由之路。致知、格物是知,属于认知范围,诚意、正心、修身是行,为实践领域。从一念的是非判断,到知、行都要做得分明,明明德是个一以贯之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足都无法充分地实现明德。
明明德不仅包括一系列的具体工夫,还有程度的不同。朱熹认为:“至善虽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须是止于那极至处。”[5]269明明德的最终境界是“止于至善”: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4]3
“至善”是“事理当然之极”,即事物完全符合天理。事实上,这既是明德,也是明德所来源的天。“止于至善”指人完全符合理而不改变的境界。明明德的工夫从略微符合理到完全符合天理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一个人只有做到“止于至善”才算充分实现自己的明德。这一思路正是对孟子“集义”(《孟子》3·2)思想的发挥。“止于至善”的人在认知、行为上都完全符合天理,是没有丝毫人欲的圣人。
圣人不仅要修养自身,更应该兼济天下,即新民。朱熹解释“新民”为: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4]3
朱熹据伊川的观点改“亲民”为“新民”[9]。新民旨在引导民众革除旧习,充分实现自己的明德。其中,“使之亦有”表明统治者的作用在于引导民众觉察到自身具有的明德。在朱熹看来,民众的道德培养不能完全靠自上而下的政教法度,关键在于民众的道德自觉①“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新者,则又皆非人力所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为也。”朱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509.。从道德教化的角度看,统治者对于民众主要起到模范和引导的作用。新民在本质上仍是明明德,只是将明明德的主体从个别先知先觉的人推广为天下之人。《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明亮自身的明德,即明明德,属于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使民众能自觉地明亮自身的明德,即新民,属于外王,二者的尺度都是“止于至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充分实现自身明德的人必须要新民?朱熹的回答是:
我既是明得个明德,见他人为气禀物欲所昏,自家岂不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来气禀物欲之昏而复其得之于天者。此便是“新民”。[5]271
当一个人充分实现自身的明德,一旦看到其他人的明德仍被气禀物欲遮蔽,他的明德便会发见,使其不得不想去引导他们。这种“恻然”之情根源于人心之中的天理,因而具有普遍必然性。所以,只要是充分实现自身明德的人,见到被气禀物欲遮蔽之人就必然会产生恻然之情。而充分实现明德不仅包含知,更意味着行。故充分实现明德的人有能力、也必然会将自己的恻然之情落实为具体的行动,即新民。只有个人的明德(明明德)和他人的明德(新民)都“止于至善”,才能实现平天下的最终目的。
总而言之,明德的发见是明明德工夫的落脚点,从格物到修身是明明德的具体项目,“止于至善”是明德的完全实现,新民是使民众明亮自身的明德,天下平是天下人完全实现自身的明德。朱熹用明德统摄《大学》的三纲八目,三纲八目则是明德的具体表现①“ 明德是指全体之妙,下面许多节目,皆是靠明德做去。”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61.。
四、朱熹注“明德”的哲学史意义
朱熹的注文揭示了明德的心性结构,为《大学》构建起性善论的基础,一转汉唐注疏的理解,甚至对平天下的理想提出新的解释。下文将从性善、工夫、理想社会三方面揭示其中的转变。
其一,性善论的引入。学者们对《大学》所属学派的问题观点各异。冯友兰将《大学》归于荀子一派[10],郭沫若认为《大学》属孟子一系[11],徐复观、劳思光主张《大学》立足于孟子的思想而兼取荀子[12-13]。除郭沫若,三位学者都未肯定《大学》持性善论的观点。这是因为《大学》缺乏人性论的阐述所导致。对于《大学》的作者而言,人性论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或不言自明的问题。
汉唐注疏也未论及《大学》的人性论。郑玄注“明明德”为:“显明至德也。”[14]1592孔颖达疏“明明德”作:“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14]1594郑玄、孔颖达所理解的“明德”指君主已具有的德性,是一种政治道德。“明明德”就是彰显光明的德性②“光明的德性”是形容德的纯粹和至善。这点同样适用于朱熹的解释。,“彰显”的译法是为了突显向外用工夫的面向。德性本身是否先天内在于人则无需讨论,如何不断地向外彰显德性才是关键。
对朱熹而言,人性论是否在《四书》中一以贯之,还关系到道统与《四书》体系的建构。朱熹通过注解“明德”的方式,将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引入《大学》,从而贯通《大学》《孟子》的人性论。朱熹解释“明明德”为:“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4]3“明”为明亮之意,“明明德”是明亮光明的德性。“明亮”的译法强调向内用工夫。“人之所得乎天”的性直接将人和天关联起来,保证所有的人都具有至善的明德。“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心肯定了性内在于人心,更强调人在道德修养中的主动性。因为,人的心在本质上都具有性,并有将它显现出来的能力,人们只需要察觉到它的存在,再加以工夫的修养。这种心性结构一方面为明德引入性善的基础,另一方面突出了人心的自觉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
其二,明明德工夫模式的转变。汉唐儒者认为,不必讨论人性问题,明德也可以通过《大学》中的一系列工夫实现。这是一种线性的塑造模式。虽然朱熹也认为明德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一系列工夫,但由于明德本身是至善的,并先天内在于人,工夫只是将它从潜在的状态转化为实现的常态。因此,朱熹才说明明德的目的是“复其初”,即复性的模式。这种转变正是基于朱熹对明德心性结构的阐释,即性为至善,心能具性、知性的特点。
此外,明明德的范围也有不同。在孔颖达看来,明明德是一个由诚意到平天下,通过学而不断累积的过程③“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先治其国’者,此以积学能为明德盛极之事,以渐到。”郑玄,孔颖达.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92,1594.。朱熹则认为明明德的范围是从格物到修身,齐家以后的部分属于新民。一加一减的背后是思想的变化。增加格物、致知与天理有关。程朱理学用天理统摄道德准则与自然规律时,道德准则难免会表现出知识化的倾向。因此,孔颖达虽解释格物、致知为“学习招致所知”[14]1595,但并不视其为修养明德的环节。减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于明德概念的转换。汉唐儒者所理解的明德主要指君德,所以,明德能延伸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所说的明德属于道德范畴,故明德止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归于新民。
其三,理想社会的不同。孔颖达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理解为“欲章明己之明德,使遍于天下者”[14]1594。在这一思路中,平天下是统治者使自己的明德遍及天下。故统治者始终是明明德的主体。与此相应,“亲民”被解作“亲爱于民”[14]1594,是统治者彰显自身德性的主要表现。朱熹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为“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4]3。平天下被理解为使天下人都能明亮自身的明德。明明德的主体不再限于统治者,而是扩展为天下之人。因而,朱熹将“亲民”解释为“新民”,即引导民众明亮自身的明德。
郑玄、孔颖达认为,明德的修养仅属于统治者,与普通民众无关。平天下是统治者以自己的德性来教化、感化民众,使民众思慕其统治①“圣人既有亲贤之德,其政又有乐利于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郑玄,孔颖达.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93.。朱熹既重视培养统治者的明德,使其起到引导作用,也强调民众的道德自觉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平天下就是,通过所有人都充分实现自身的德性,达到天下之人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二者都以天下人各得其所为目的,但在理论依据、实现方法、所达境界等方面都截然不同。
朱熹的注文不同于汉唐注疏,这既是程朱理学发展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儒者的普遍理想。例如,宋代盛行的家训、乡约、书院等,都是这种理想的具体表现。伊川曾将宋代在社会治理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道德教化②“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防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159.,朱熹则称赞北宋初的道德教化已远胜唐代③“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黎靖德.朱子语类:第8册[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085.。不仅宋人自我评价如此,王夫之同样给予高度的认可:“宋分教于下,而道以大明。”[15]陈寅恪评价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6]若非宋人普遍具有此种理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何来后人不断的表彰?朱熹是将宋人的普遍理想凝练为自己的哲学理论,再经由注释的方式表达出来。
相较汉唐注疏,朱熹通过援引孟子的思想,阐释明德的心性结构,将性善论引入《大学》,把明明德释为复性的工夫,勾勒出天下人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按照朱熹的理解,新民是“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明明德为“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而明德就是孟子之后所失传的“大道之要”[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