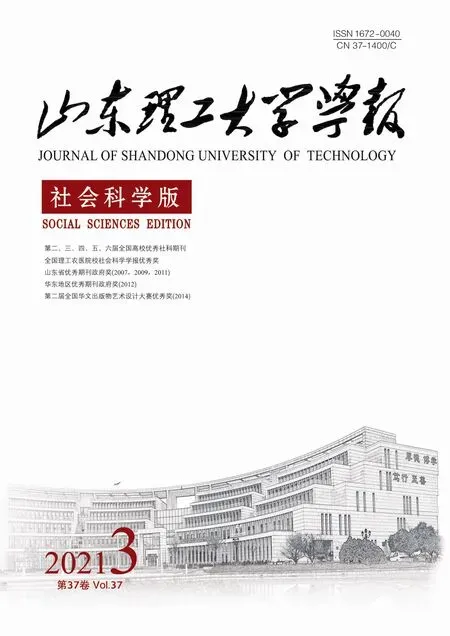徐彦《春秋公羊疏》的诠释方法
焦桂美,尚 梦
徐彦的《春秋公羊疏》,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作者时代目前尚不能确定的“疏”。关于徐彦的生活年代,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以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董逌《广川藏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持徐彦为唐人说;另一派以清代学者王鸣盛、严可均、阮元、洪颐煊、姚振宗、皮锡瑞及近现代学者潘重规、牟润孙、赵伯雄诸先生为代表,认为徐彦当为北朝人。笔者认为徐彦的《春秋公羊疏》与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杨士勋的《春秋穀梁疏》、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诠释风格不太一致,也没有唐人义疏做得繁密复杂,倾向于徐彦为北朝人之说。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南北朝经学史》中已有讨论,此不赘述。
《公羊传》在西汉今文经学昌盛的时代背景下曾独步天下,显赫一时,但自东汉古文经学兴起,包含《公羊传》在内的今文经学日渐式微。东汉末年虽有何休为《公羊传》作解诂,补弊起废,使其理论体系走向成熟,但仍无法挽救《公羊》学没落的命运。清中叶以降在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努力下,《公羊》学又呈复兴之势。在从东汉至晚清的一千多年中,研究《公羊》学者为数不多,出现的优秀著作寥寥无几。如将徐彦的《春秋公羊疏》置于《公羊》学史中考察,该书堪称《公羊》学义疏之典范。其以何休注为宗,所用诠释方法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仍有借鉴意义。此仅就其主要方法略作阐述。
一、本经互证
本经互证,就是利用本经上下文及其传、注互相证明、阐发经义的方法。这是何休注解《公羊传》的常用方法,这一方法为徐彦继承,在《春秋公羊疏》中使用最频繁,也最具特色。如隐公四年经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即公子翚,字羽父,是鲁国宗室、权臣。公子翚于鲁隐公十一年请求隐公杀桓公,以求太宰之职。隐公没有答应,并表示要还政桓公。公子翚惧其言为桓公知,故在桓公面前反谮隐公,并请弑之。此处传云不称“公子”,是因公子翚后来有弑隐公之罪故加以贬斥:“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何休注中阐释了“弑”的含义及“终隐之篇贬”公子翚的原因:“弑者,杀也,臣弑君之辞。以终隐之篇贬,知与弑公也。”[1]52何休由《公羊传》对公子翚直到鲁隐公终篇皆持贬斥态度,断定公子翚参与了弑公之事。那么,何注“终隐之篇贬”公子翚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呢?何休并未说明。徐彦将隐公十年相关经传文前置于此,为何休说注明了来源:“即此及十年‘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传云‘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是也。”[1]52由徐彦疏知,何休“终隐之篇贬”公子翚说出自隐公十年传文。徐彦在此条中通过援引本经下文疏解传注,简明易懂。
由上例可见,何休虽已使用本经互证法阐释经传,但有些引文他没有标注出处,与自己的观点浑然一体,难以切分。徐彦不但为何休所引之文明确了来源,将何休的见解与他人的观点明确分开,而且把上下文中所涉该事始末或同类例证汇聚到一起,多置于首条中疏解,便于读者对该问题的整体把握与全面理解。如隐公三年传:“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1]48意思是说:超过了礼仪规定期限的葬礼不书葬日,表明没有按时安葬。何休以隐公五年卫桓公之葬为例阐释传义:“解缓不能以时葬,‘夏,四月,葬卫桓公’是也。”[1]48卫桓公于隐公四年二月为卫州吁弑,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礼仪,理应葬在该年秋七月,实际却因卫乱直到五年四月才安葬,属于过时而葬的缓葬,不合礼仪,故不书日。但如仅看何休注,尚不知卫桓公自死至葬的具体时间,也就无从得知卫桓公“不能以时葬”究竟拖延了多长时间。徐彦运用本经互证的方法,将隐公四年相关经文补充进来,传注之义不言自明:“即下四年二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至五年‘夏,四月,葬卫桓公’是也。”[1]48
但如果仅把对某一问题的疏释置于首次出现的经传文下,下文相关条目不再做疏,对阅读、理解下文也不方便。徐彦对此当有清醒认识,故不厌其烦,前勾后连,以便观照。如上例在隐公三年传中,何休已经指出卫桓公属于“解缓不能以时葬”,且引隐公五年经文“夏,四月,葬卫桓公”为说。在隐公五年该条经文下,何休因在隐公三年中已经注过,此处不再做注。徐彦与何休的做法不同,他不因上文已作阐释此处便予减省,而是将隐公三年相关传文及何休注拿来疏解此条:
即上三年传云“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何氏云“解缓不能以时葬,‘夏,四月,葬卫桓公’是也”。然则桓公见弑在去年之春,过期乃葬,故以解缓言之[1]56。
诸如此类,徐彦通过本经上下文互相证明,往复疏解,既免去了读者翻检之功,又加深了对经义的理解。通观《春秋公羊疏》,徐彦主要采用本经上下文经、传、注互证的方法进行疏解,虽对经、传、注义发明不多,但简约征实,便于观览。下文“类聚总结”“重事略义”部分所举之例亦多为本经互证法,此不赘述。
二、援《左传》《穀梁》校释《公羊》
何休注释《公羊传》,有取《左传》《穀梁传》为说者,但数量极少,且不加标识。徐彦疏采二传之说也不多,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为何休援引的《左传》《穀梁》说标明出处。如隐公三年经“癸未,葬宋缪公”,何休注中有“礼,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徐彦指出:“皆隐元年《左传》文。”[1]47-48又,庄公元年传“曷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条,何注中有“礼,齐衰不接弁冕,仇雠不交婚姻”[1]134,徐彦指出何注源于《穀梁》说:“义取《穀梁》之文,‘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之言也。”[1]135
其二,引《左传》《穀梁》校勘文字。如昭公八年经“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孔瑗”,徐彦云“孔瑗”之“瑗”,《左传》《穀梁》作“奂”[1]561。
其三,引《左传》《穀梁》阐释《公羊》。如宣公六年传“有人荷畚”,何休注:“畚,草器,若今市所量谷者是也,齐人谓之钟。”徐彦引《左传》说释注中之“钟”:“即昭三年《左传》云‘齐旧四量:豆、区、釜、钟’是也。”[1]384又如文公六年经云:“晋杀其大夫阳处父。”阳处父实为狐射姑所杀,此云“晋杀”,何休阐明根源:“明君漏言杀之,当坐杀也。”意为阳处父被狐射姑所杀,盖因晋襄公泄言所致。晋襄公当坐,故其死不当书“葬”。但上文经云“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之所以书“葬”,徐彦引《穀梁》说释之,以为当因晋襄公葬后才发生了阳处父被杀之事,故得书“葬”。“襄公当坐,则例去其葬,而上文经书‘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襄公’者,盖谓葬讫乃相杀,不得追去葬,是以《穀梁传》曰‘襄公死,处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杀之’是也。然则此传虽连言之,仍不妨杀之在葬后,是以经书‘葬’,在杀前矣”[1]333。
由上可见,徐彦援引《左传》《穀梁》,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为何休援引《左传》《穀梁》者标注出处,二是校勘三传文字之异,三是引之解说、佐证《公羊传》。总体来看,徐彦多用《穀梁传》及范宁《集解》来疏何休说,采撷《左传》者较少,这与何休不信《左传》、徐彦疏不破注的原则密切相关。徐彦采用三传互证的方法,援引《左传》《穀梁》解说《公羊》,表明他已经具有三传综合研究的学术倾向。但他对三传的综合研究、对三传义例的总结、对三传优劣的判别较杨士勋《春秋穀梁疏》薄弱很多。
三、类聚总结
何休注往往仅释本条,就事论事。徐彦疏多将同一问题汇集到一起,于某一条目下进行总结。如隐公元年经:“冬,十有二月,蔡伯来。”传:“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1]28此条何休注仅针对事件本身,着眼于传文不称使、无事两个因素,判定蔡伯的行为是出奔:“以不称使而无事,知其奔。”[1]29徐彦则联系上下经传所载同类事件,根据不同书法,概括为无使有事、有使有事、无使无事三种情况,再针对本条具体情形申述何注:“下三年‘武氏子来求赙’,文九年‘毛伯来求金’,是无使而有事也。上文‘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之徒,皆是有使有事也。今此无使复无事,故知其正是奔也。”[1]29此条徐彦将传文所载相关情况汇集到一起,在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分析本条传注之义,宏通开阔,信实有据。
类聚总结也表现在义例上。何休阐释义例较为简单,一般仅释本条所涉义例。徐彦往往为何氏所释义例补充证据,以明传注之义。如隐公二年传“其言归何?妇人谓嫁曰归”,何注云:“内女归例月,恩录之。”[1]41徐疏为何氏此例补充三条证据,通过汇集同类事件,申明何注义例:“即此文冬十月、隐七年三月‘叔姬归于纪’,成九年‘二月,伯姬归于宋’之属是也。”[1]41
徐彦有时也将相关义例进行归纳,通过研究总体情况来分析具体问题,如庄公三年经“夏,四月,葬宋庄公”,何休注云:“庄公冯篡不见,书葬者,篡以计除,非以起他事不见也。”[1]139宋庄公因篡即位,本不该书“葬”。何休认为经文书“葬”,是因其父有让国之善,可折其篡权之过,故云“篡以计除”。单看何注,经义难明。徐彦先总结了“篡不明者”和“篡明者”书“葬”义例,认为“篡不明者,皆贬去其葬以见篡”“其篡明者,不嫌非篡,故不去葬以见篡”:
《春秋》之例,篡不明者,皆贬去其葬以见篡,即僖二十四年“晋侯夷吾卒”,注云“篡故不书葬,明当绝也”;又宣九年秋,“晋侯黑臀卒于扈”,彼注云“不书葬者,篡也”之属是也。其篡明者,不嫌非篡,故不去葬以见篡,即隐四年“卫人立晋”,桓十二年冬“卫侯晋卒”,十三年春“葬卫宣公”;又庄九年“齐小白入于齐”,至僖十七年冬“齐侯小白卒”,十八年秋“葬齐桓公”;又哀六年秋“齐阳生入于齐”,至哀十年春“齐侯阳生卒”,夏“葬齐悼公”,此等皆由其初有立、入之文,不嫌非篡,故书其葬[1]139-140。
明白了“篡不明者”和“篡明者”书“葬”通例,即可知宋庄公篡权,不当书“葬”之理。徐彦指出此传书“葬”乃因其父有让国之善,“故计其父功而除其篡罪”:
今宋公冯初篡不明,所以亦书其葬者,正以其父缪公有让国之善,故计其父功而除其篡罪,故云篡以计除也[1]140。
比较可见,此条何注仅就本传而言,徐彦则对相关义例进行了总结,是对何注的推进。但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杨士勋《春秋穀梁疏》相比,徐彦对义例的贡献还是有限的。
四、运用“功过相除计”评价人物
王光辉指出:“公羊家认为,《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在实际运用中,可依时除计,也可在不同代际间除计。”[2]104也就是说对重要人物的评价,《公羊》学家不是简单地就某一事件对人物进行褒贬,而是联系人物此前甚至前代的功过,通过综合考量确定褒贬:此前之功,可抵当下之过;此前之过,也能消当下之功。这种方法何休已经使用,徐彦则归纳为“功过相除计”,并将其上升为《公羊》学评价人物的特色方法。如庄公十三年经“夏,六月,齐人灭遂”,何休注:“不会北杏故也。不讳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恶。”[1]176此事的背景是该年齐桓公为尊天子,会诸侯于北杏。遂国因未与盟,为桓公所灭。灭人之国为大恶,按照“《春秋》为贤者讳”的通例,本不该书“灭”。此不为桓公讳而书“灭”者,何休认为是因齐桓公灭遂时,行使的是霸权,其时他的德望、功业尚未著显,却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其功不足以除恶,故书“灭”以贬。
徐彦为何休注做了进一步阐发,他遵循以“功过相除计”评价人物的方法,以庄公三十年取鄣为界,把桓公一生的功过划为两个时段予以评价:此前过大于功,取鄣以后,“以其霸功足以除恶”,功大于过。
具体到此条中,徐彦认为北杏之会虽有尊王之功,但因桓公此前有篡逆、灭谭之过,故于此处书灭以恶之:“《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桓公之立,虽有北杏之会,前有篡逆灭谭之非,论其功不足,而恶有余,故不为讳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后,功足以除恶也。”[1]176
我们看到,就该条来看,徐彦对桓公灭遂书于传文的分析较何注更为明晰,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徐彦于此正式使用“功过相除计”一词,将何休的评价方法上升为一条法则,使之具有了普适性。
徐彦不仅将这一法则运用于何休已经注解的条目中,而且对何休未及但也适用这条法则的条目做了发掘。如宣公元年经云:“六月,齐人取济西田。”[1]374宣公十年经云:“齐人归我济西田”。传云:“齐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绝于我也。曷为未绝于我?齐已言取之矣,其实未之齐也。”[1]399何休针对齐人取鲁济西田而传却称“归我”,指出两地虽为齐取,但尚属于鲁,并未归齐,“不言来者,明不从齐来,不当坐取邑”[1]399。徐彦则以传注未曾提到的功过相除法来阐释传不书齐取的原因,以《春秋》的恕道看待齐人的行为,较何注更胜一筹:“正以尔来十年仍不入已,见宣有礼,还复归之,功过相除,可以减其初恶,是以《春秋》恕之,不复书来,以除其过,故曰不当坐取邑耳。”[1]399
由以上两例可见,徐彦运用功过相除的方法评价人物,是对何休说的继承、发展与超越。前举庄公三年经云“夏,四月,葬宋庄公”条,以“篡以计除”分析宋庄公因以其父功抵过除恶,故传以无罪书葬,性质与“功过相除”同。由此可见,功过相除法确如王光辉所说不仅可用于一人的不同阶段(如上例对齐桓公的评价),亦适用于不同代际之间(如此例之父子)。
五、重事略义
《公羊传》好言灾异,何休注重阐发大义,往往以灾异附会人事。徐彦重视史实,对传注所涉微言大义、阴阳灾异等往往不加阐释或不做进一步阐释。如襄公十二年传云:“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何休注:“时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孙宿遂取郓以自益其邑。”[1]501徐彦没有阐发何注“时公微弱,政教不行”之义,而是阐释了下句季孙宿的行为,质实可感:“遂者,专事之辞。言季孙自专取郓,故言遂取郓也。知以自益其邑者,正以讨叛邑而不入国家,故知以自益其邑也。”[1]501-502
文公十四年经云:“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即彗星,传云经乃“记异也”。何休将经文所记天之异象与现实政治相附会:“孛者,邪乱之气。篲者,扫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枢机玉衡,七政所出,是时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统政,自是之后,齐、晋并争,吴、楚更谋,竞行天子之事,齐、宋、莒、鲁弑其君而立之应。”徐彦对何注由传云“记异”而阐发出的齐桓、晋文之后,“王者不能统政”的观点未作疏解,而是为注云“齐、宋、莒、鲁弑其君而立之应”之说逐一补充了史实:“即下文九月‘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八年夏五月,‘齐人弑其君商人’,是齐弑君事也。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处臼’,是宋弑其君事也。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是莒弑其君事。十八年‘冬,十月,子卒’,传云‘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者,是鲁弑其君事也。”[1]355
由以上两例,大约可以印证笔者在《南北朝经学史》中所下论断:“徐疏未将自然与人事牵合,更未对灾异作进一步发挥,但徐彦在阐明史实、少申阴阳的同时,也掩盖了其带有个性的政治倾向,从而很难看到他对时政所持的基本态度。”[3]413
六、用“时王之礼”解说何休注中文献无征者
对文献无征、古制无文的何休注,徐彦往往用何休等汉人闻见的当时的礼仪即“时王之礼”予以阐释。如宣公十二年传云:“郑伯肉袒,左执茅旌”,何休注:“茅旌,祀宗庙所用迎道神,指护祭者。断曰藉,不断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顺一,自本而畅乎末,所以通精诚,副至意。”[1]405何休所释“茅旌”,文献阙载,徐彦便以“时王之礼”疏之:“茅旌,‘祀宗庙所用’云者,皆时王之礼。正以公羊子是景帝时人,是以何氏取当时之事以解其语。”[1]406
何休注中个别内容,既有文献出处,又为当时之礼,徐彦便对二者均做说明。如宣公六年传“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何休注中有“礼,天子为三公下阶,卿前席,大夫兴席,士式几”,徐彦云此为“《春秋说》文。亦时王礼也”[1]384。
何休注中并未说明用“时王之礼”阐释经文之处,徐彦疏中明言,或沿前人之说,或出主观己见,不得而知。
由以上对《春秋公羊疏》诠释方法的总结、分析,大约可窥徐彦疏的特点和贡献。
其一,徐彦精通《公羊传》,其疏以申明何注为主,主要运用本经互证的方法,从《公羊传》本身及何休注中寻求阐释,上下贯通,往来穿穴,虽然视野不够开阔,但融贯之力超越前贤。徐疏重视阐发史实、校勘文字,学风质朴,简约明了,便于阅读。
其二,徐彦不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他将《公羊传》中的阴阳灾异、谶纬附会做了淡化处理,虽然对传注之义少有发明,但进一步凸显了其征实色彩,体现出与汉人迥然不同的关注重点,具有时代诠释特色。
其三,徐彦运用功过相除、时王之礼等方法阐释经传,在继承何休注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新贡献。
其四,徐彦关注三传文字、解说之异,具有融通三传的意识,但远没有杨士勋《春秋穀梁疏》做得自觉而有特色。
综上所述,徐彦疏虽然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公羊传》义疏的最高水平,但与其他唐人义疏相比,徐疏的细密性、总结能力、三传融通趋向相对薄弱,《崇文总目》云其“援证浅局”,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