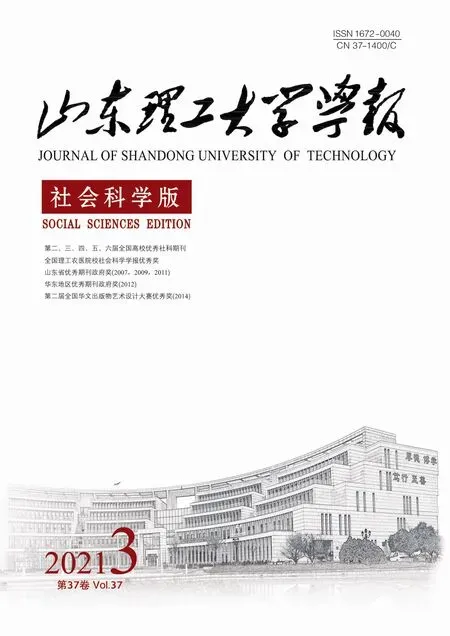论《左传》叙事的尊“国”意识
李 明 丽
国野制是周代重要的社会制度,“它是周代分封制的空间体现”[1],国野制不仅确立了周代社会的基本空间规划,也以空间为基础明晰了周代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结构,即《周礼》所谓的“体国经野”[2]。虽然春秋时期各国的赋税、兵制、地方行政区划等都逐渐出现变革,但终春秋之世,这些变革并未对国野制造成根本性冲击,社会运转依然以其为原则,人们对国、野空间的认知是较为稳定且清晰的。“国”指国都,《左传》中绝大多数的“国”皆为此意。广义的“国”包括国都城邑及郊区,狭义的“国”则仅指城邑本身。“国”是一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是政令制定之处,拥有其他城邑不可比拟的地位。这是《左传》叙事的制度背景,《左传》对春秋史的呈现与阐释自然受其影响,在叙事时带有鲜明的尊“国”意识。
一、以“国”为筑城运动重心
春秋时期,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独立性的增强,在日趋严峻的战争局势的促动下,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广泛的城邑修筑运动。据许宏统计,有关此一阶段筑城的记载有97处,涉及85座城邑(1)具体内容可参见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66-168页。这里所统计选取文本为《春秋》《左传》和古本《竹书纪年》。。我们单独对《左传》整理所得有60处记载,涉及78座城邑,《左传》通常以“城”来指称此类活动。包括周王室在内,绝大多数国家皆有“国”的整修经历:周,襄公二十四年冬“齐人城郏”。郏,“即郏鄏,又曰王城”(2)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1093、119页。本文《左传》引文均出自此版本,后文不再赘注。。定公元年,“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鲁国分别于襄公十九年、哀公四年“城西郛”。成公九年“城中城”。据《春秋》,定公六年冬鲁人亦曾“城中城”(3)中城,学界意见有二:其一,以杜注为代表。杜注:“鲁邑也,在东海厚丘县西南。”(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1905页)厚丘,当作廪丘。则中城在今江苏沭阳县,为鲁东南边邑。《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 ,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14页)、黄鸣《春秋列国地图志》(黄鸣:《春秋列国地图志》,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50页)持此观点。其二,《谷梁传》云:“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范甯注:“讥公不务德政,恃城以自固,不德能卫其人民。”(范甯、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2421页)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据此认为中城为鲁都内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贾贵荣、宋志英辑:《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96页)。从《左传》的叙事中可知,内、外之分是建立在“国”与“国”以外的空间基础上的认知,竹添光鸿谓“内城以外之民竟外之”(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巴蜀书社,2008年,1030页),范甯之注即此意。杨伯峻也认为中城即内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842页)。两种意见的区别还在于鲁国边境是否能拓展到如此程度,春秋时期各国封境尚未清晰,领土犬牙交错常有之,或有可能鲁国拓土至此,但不似东郓为鲁、莒所争,中城并未在任何边境领土之争,或边境战役中出现。而以《左传》的叙事情况来看,越是重要的城邑,其见载次数越多,也是修筑重点。因此,本文同意中城为鲁国都内城的意见。。楚国亦有两次“城郢”经历:文公十四年秋公子燮与子仪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昭公二十三年,“囊瓦为令尹,城郢”。庄公二十六年夏,晋“士蒍城绛,以深其宫”。僖公十二年春,“诸侯城卫楚丘之郛”。宣公二年春,“宋城”。襄公二十九年,“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城“国”的核心需求是巩固、提升其军事防御能力,《传》文多以对被攻伐之“惧”来揭示,如鲁城西郛因“惧齐也”。诸侯城楚丘,“惧狄难也”。曩瓦是因“今吴是惧而城于郢”。
“国”之外的大部分城邑都是为满足军事防御而修筑,作为“国”的层层防卫线拱卫“国”。这是从西周起就确立的城邑修筑观念,周天子之“国”以外的各诸侯之“国”,无一不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僖公二十四年)的实践,通过分封诸侯,周人建立了遍布四方、远近有序的防线。《左传》所载春秋时期鲁国修筑的16座城邑也是如此,形成了三级防御层次。
其一,边境防线:郎(4)鲁国有二郎,此处所提者为隐公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竹添光鸿谓此郎在“兖州府鱼台县东北八十里”(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巴蜀书社,2008年,22页),具体而言,“其地当在昭阳湖东岸今微山县留庄镇附近”(黄鸣:《春秋列国地图志》,文物出版社,2017年,39页),紧邻邾国之地,距离鲁都约有二百里之遥。、漆为鲁国南方边邑,是鲁、邾之间的防线。中丘、向、诸、防(5)鲁国有二防,此处所提者为臧氏采邑,位于“山东省费县东北四十余里”。《春秋》隐公十年六月辛巳鲁人“取防”之防为宋国之防,“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南六十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64、67页)。前者在鲁国之东,后者在鲁国之西。、郓(6)鲁国有二郓,此处所提者在“山东省沂水县东北五十里”,即东郓。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围郓”之郓,“在山东郓城县东十六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568、867页),在鲁国之西。,为鲁国东方边邑,是鲁国与齐国、莒国之间的防线。防,齐、鲁间为会、征伐多发生在此处,如“冬,公会齐侯于防”(隐公九年)。“高厚围臧纥于防”(襄公十七年)。《春秋》又载,“及齐高傒盟于防”(庄公二十二年)。防邑位置重要,是鲁国重点修筑城邑之一,庄公二十九年“城诸及防”,襄公十二年再次“城防”。郓为鲁、莒边邑,文公十二年“城诸及郓”,杜注:“莒、鲁所争者……以其远偪外国,故帅师城之。”[5]1851郿,鲁西北边邑,鲁、齐间防线。
其二,中部防线:平阳、成、输、武城(7)鲁国有二武城,此处所提者为襄公十九年所城者,此次筑城与前所提“城西郛,惧齐也”相接,是鲁人向晋人求援后的举措,“穆叔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在鲁国之西,“其地在今嘉祥县满硐乡南武山下”。邾人城翼后所经之武城、吴人伐鲁所克之武城,是鲁国东部城邑,靠近邾国,“在今山东省平邑县魏庄乡南、北武城村一带”(黄鸣:《春秋列国地图志》,文物出版社,2017年,55、52页)。。此四邑皆为齐、鲁间防线,平阳、成、输在鲁北方中部,武城则在鲁西方中部。其中成邑尤为重要,曾多次遭受齐人攻伐,襄公十五年齐人因范宣子假羽不归而背叛晋国主持的同盟,围困成邑以示不满,此事后鲁国立即“城成郛”。为处理昭公出奔一事,齐国亦以“围成”的方式向“国”中鲁人施压。鲁国堕三都时孟孙氏拒绝堕成,理由之一即“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定公十二年)。中部防线的稳定对于国家腹地的防卫十分重要,一旦失守,或失去对该城邑的掌控,修筑其附近城邑便成为有效的补救措施。成曾因孟武伯与成宰之间矛盾的激化而背叛孟氏,归顺齐国。伐成失败后,孟武伯“遂城输”(哀公十五年)。输,其地不详,但以孟氏之举来看,佗邑唯命当为成附近的城邑。“城输”既起到逼迫成的作用,也具有弥补此一阶段中部防线缺失的意义。
其三,内部防线,即郊区:郎。郎为隐公九年所城者,庄公十年齐、宋伐鲁,“师次于郎”,公子偃“自雩门窃出”与宋师交锋,雩门为鲁都南城西门,则郎在鲁都之南。据《春秋》,庄公三十一年鲁“筑台于郎”。《公羊传》文公十八年《传》文称朗台为泉台:“泉台者何?郎台也。”[11]泉,即逵泉,“在曲阜县东南五里”[4]254,则此郎为鲁都南近郊之邑。郊是国都最后一道防线,意义重大,越过郊,“国”就陷入危险之中,故而郊区防线建设一直受到重视。春秋末年,曹国曾背叛晋国同盟侵伐宋国,宋人反击,晋国未予救援,事后曹国“筑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钟、邗”(哀公七年),意在提高郊的防御能力。
及时、适时修筑城邑被当时人视作国家防护的必要举措,《左传》中有对不以时筑城、非君命筑城的如实记载(8)如“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公元年)。“夏,城中丘。书,不时也”(隐公七年)。“夏,城郎。书,不时也”(隐公九年)。,但批评意味并不严重。比较而言,《左传》更关注城邑修筑这一活动是否进行。成公八年申公巫臣前往吴国时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恶。’”但巫臣的提醒并未引起莒子的重视,莒子认为莒国僻远,不会被大国侵伐,无筑城必要。次年,楚人自陈伐莒,接连攻破渠丘、莒、郓三座城邑,《左传》假君子之评表达出对筑城的态度:“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无备”是国君的严重失职,“备之不可以已也”(成公九年)才是一国的军事常态。显然,“国”是防御的重心,莒都被迅速攻破不仅在于楚人最先攻伐的渠丘因未得到及时修筑,无法起到“国”之防线的作用,更在于莒都城郭亦未适时修缮。
二、对“大都耦国”之警惕
“国”之外城邑的修筑亦对领土扩张有重要意义,“大国的城邑则成为其对外扩张的据点”[3]128,如东阳,为齐国东南边境城邑,是齐国震慑莱国的据点。齐人分别于襄公二年、襄公五年“城东阳以偪之”,最终于襄公六年攻破莱国国都,灭掉莱国。但即便这些军事据点对于领土扩张、军事防御意义重大,《左传》还是对它们的存在与崛起保持了警惕,这种警惕主要集中于大都(9)都本义即指城邑,《左传》中的“都”有两种含义:其一指卿大夫采邑,其二指国都。但后者使用并不多,以前者为主。之上。
(一)《左传》认为要审慎大都之封
规模大、地理位置重要的城邑不宜作为公子、重卿的采邑予以分封,这一观点在《左传》开篇就已申述明白。郑庄姜偏爱共叔段,为其谋求利益最大化,郑庄公没有直接与母亲发生冲突,忍让的表象下,郑庄公将关键城邑的掌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隐公元年)制,位于今河南荥阳县。在汜水之侧,北临黄河,南接嵩岳,地势险要,岩邑即险邑。原为东虢之地,郑灭东虢后为其北方要塞,连同其附近的虎牢,在春秋时期有关郑国的战役中多次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郑国有效阻击入侵者的堡垒,如卫人、燕师伐郑,“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隐公五年),也是入侵者有效施压郑国的砝码。
会于戚,谋郑故也。孟献子曰:“请城虎牢以逼郑。”……冬,复会于戚……遂城虎牢。郑人乃成(襄公二年)。
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士鲂、魏绛戍之。……郑及晋平(襄公十年)。
比之于制,京临京水,亦有山岭依靠,《读史方舆纪要》载:“汉二年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蒯通曰:‘楚人起彭城,转斗至荥阳,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间,迫西山而不敢进’,谓此也。”[12]2200但论险要远不及制。孔颖达引《春秋释例》曰:“虎牢,郑之郊竟。”[5]1948与虎牢距离甚近的制应亦为郑郊北境之邑,对于“国”的安危意义重大(10)虎牢曾在僖公四年时被齐桓公赐与申伯,辕涛涂向郑文公谮陷申伯,讲其“美城其赐邑,将以叛也”(僖公五年),郑文公对此毫不怀疑,在齐伐郑时“杀申侯以说于齐”(僖公七年)。郑文公此举正是基于虎牢对于郑国国都的防御意义而来,要确保虎牢的掌控权。杨伯峻认为赐申伯虎牢非郑国本意,“恐亦强迫郑文公为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294页),颇有道理。由这一事例不难理解制对于郑庄公君位稳定的意义。。
郑庄公“佗邑唯命”的动因在晋国君位承继问题的叙事中得到阐述。晋献公听信骊姬、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所进谗言,令大子申生居于曲沃,闵公二年申生奉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时,狐突引辛伯之言点明晋国当前情势:“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大都耦国,乱之本也。”耦国即匹敌国都,大都被视作“国”的威胁,是形成政治动乱的原因之一。哀公十四年桓魋“请以鞍易薄”,宋景公拒绝他亦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可。薄,宗邑也。”薄,即亳,殷商旧都。
《左传》审慎大都分封的思想主要以“大都耦国”事件的叙述,及人们对此类事件的反思来体现。晋国献公卒后“五立而后平”[13]254,郑国与之相似,郑庄公卒后郑厉公与郑昭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君位之争,栎邑在其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厉公出奔蔡国后,“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桓公十五年)。栎,郑庄公封厉公之邑,今河南禹县,距离郑都九十里。杜预注:“栎,郑别都也。”[5]1758对郑国都形成严重威胁,为纪分裂一事鲁庄公意欲同郑昭公相会于滑,“郑伯辞以难”(庄公三年)。杜注:“厉公在栎故。”[5]1763厉公以栎为据点,“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庄公十四年),与傅瑕达成盟约,傅瑕杀死昭公而纳之,厉公成为最后的胜出者。萧,宋国东南部城邑。宋万弑闵公后,立子游为君,“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庄公十二年)。在萧叔大心的支持下,群公子及公族重新进入国都,杀死子游,立御说为君。萧叔大心因功获封,萧成为宋的附庸。萧邑直到春秋末年依然能够对宋国政局产生巨大影响,“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萧以叛。秋,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定公十一年)。
大都之所以成为“国”的威胁,在于大都意味着丰厚的财力、人力,强化受封(占有)者的经济、军事能力。齐襄公的继任者公孙无知被雍廩所弑即与雍廩以渠丘为采邑有关,渠丘即葵丘。杜注:“齐地临淄县西有地名葵丘。”[5]1765《水经·淄水注》:“系水又北径临淄城西门北,……系水又西径葵丘北。”系水为时水“北径西安城西,又北”时所汇入河流,“时水出齐城西北二十五里”,葵丘距齐临淄城亦应不远,如郦道元引京相璠之言:“齐西五十里有葵丘地。”[14]杨伯峻注,葵丘在“今山东淄博市西三十里”[4]1328。葵丘为齐国郊之重邑,对临淄防卫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从齐襄公曾专门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亦可见出。卫献公出奔更是权卿以采邑实力为依托,卿权碾压君权的典型事例。孙林父以戚为采邑,戚在卫国近郊,“盖其地濒河西,据中国之要枢,不独卫之重地,亦晋、郑、吴、楚之孔道也”[15],是卫近郊之重邑。孙林父凭戚邑族众便能攻入国都,之后不仅接连杀死卫献公派来的和谈使者,甚至追击离开国都的卫献公,“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襄公十四年),可见其实力之强悍。
“大都耦国”事件往往引发君位更迭这样的政治巨变,严重影响国内政局稳定,故而被视为深刻的历史教训,用以警醒当世之人。当楚灵王想封公子弃疾于蔡时,申无宇以各国故事为例,“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告知楚灵王“大城”实“害于国”(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正是对《左传》春秋初年审慎大都之封思想的总结与呼应。
(二)《左传》认为大都的发展要受到严格限制
共叔段封于京,其擅自扩充京邑的规模,在郑国臣子看来,这是对礼制的僭越:“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远超旧制,城过百雉的京邑,是“国之害也”。以祭仲、公子吕、子封为代表的“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请除之”(隐公元年)的声音不绝于郑庄公之耳。此观念贯穿于《左传》的叙事中。士蒍领晋献公之命为重耳与夷吾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诸献公,士蒍即以“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僖公五年)为自己辩解,认为筑城认真谨慎,坚固的城邑将成为“国”的威胁,是不忠之举。定公十二年鲁国堕三都,即三桓季孙氏封邑费、叔孙氏封邑郈、孟孙氏封邑成,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16]1916可知三都不仅规模堪比国都,还拥有很强的武装力量。在堕三都的过程中,费人袭鲁、围成不克的情况皆证实了大都对“国”的威胁的严重性,及控制大都发展的必要性。既将其他城邑视作“国”的军事防御屏障,亦将其中的大都视作“国”的地位威胁之因素,都说明《左传》对“国”的尊崇和维护。
三、称谓与尊“国”
《左传》叙事时为了凸显“国”的重要性和尊崇地位,通常会以国名来指称国都,尤其以战争叙事为代表。如诸侯国内部冲突事件:公子弃疾“入楚”(昭公十三年)。“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隐公元年)。“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庄公十四年)。“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定公十二年)。这些事件发生在诸侯国疆域内部,却以“侵袭+本国名”的形式来指称,显系指称其“国”。宋万之乱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等宋国公族“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庄公十二年)。杨伯峻注:宋,“宋国都也”[4]192。若战争发生于诸侯国之间,《左传》则有不同的表达,如侵、伐、袭、围、入等,皆表征讨之意,其间却有区别,竹添光鸿阐释道:
盖云伐者,声罪而来,陈兵于境,必服而后去之。不服则战,不战则守,守之固则围之,守之不固则入之。故《春秋》书伐之后,有或战或围或入之事,而书侵则无之。侵者掠其境而即去,故不鸣钟鼓……则知《春秋》书侵书伐,亦因乎事之大小、入之深浅、时之久暂、名之有无之实也[10]333。
则围、入是程度最深入的表述,入是围的结果,杨伯峻即称“入者,以兵深造其国邑”[4]22。《左传》中“围+国名”的战争即指包围其“国”。陈庆寅、庆虎与公子黄不睦,向楚国谮陷公子黄,公子黄诉诸楚人,“楚人召之。使庆乐往,杀之。庆氏以陈叛。夏,屈建从陈侯围陈”(襄公二十三年)。庆氏所据即陈之“国”,楚人所围亦是陈之“国”。除去为拓展疆土而发动的兼并战外,春秋时期多数围“国”之举或是为施压,或者令小国驯服,或者解救同盟,夹在晋楚南北两霸主之间的郑、蔡、陈、许、宋等国多有此遭遇,《左传》中记载“围郑”5次、“围陈”5次,“围蔡”“围许” “围宋”各3次(11)此处仅以《传》文明确记以“围”者作统计。若结合《传》文,则在诸次伐郑之役中,襄公九年冬十月诸侯伐郑,诸侯分别门于郑之四门,可见已形成合围之势,但下文晋令诸侯准备“围郑”,可见此时与围郑尚有些区别,故此类事例不纳入统计中。。
受到相同制度背景的影响,和《左传》相近时间的文献也多有这种表述,如《国语·吴语》越人伐吴,“三战三北,乃至于吴”[13]561。此处的吴即是吴国国都。清华简《子产》:“子产既由善用圣,班羞勿俊之行,乃聿三邦之令,以为郑令、野令,导之以教。”[17]以郑、野相对,说明子产对国、野分别有政令,《左传》对此叙述相似:“子产使都鄙有章。”(襄公三十一年)(12)鄙,在《左传》中既可指国都之外(郊外)的远地,也可指其中的城邑。春秋时期有都鄙连言,也有国鄙对言的表述:如《国语·吴语》,申胥讲吴王夫差疲敝民工,致使吴国出现饥荒,“今王既变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苏。天夺吾食,都鄙荐饥”。都鄙,韦昭注:“都,国也。鄙,边邑也。”《国语·楚语》,申无宇讲:“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君臣与都鄙对言,都鄙之意应如韦昭注。《国语·齐语》,管仲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昭注:“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542、499、219页)在这个意义上,都鄙与国鄙、国野同义。
周代的国野制从建立之初,便形成了层级式的城邑关系,以天下论,则周天子所在周之“国”是天下之“国”,居周代国野关系的第一级,其他诸侯国之“国”的第一层级地位仅针对其国内部国野关系而言。尽管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衰落,但在礼制的约束下,各国还是保持着形式上的对王室的尊敬。尊周亦是尊崇礼制的《左传》的叙事理念之一,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对周之“国”与诸侯之“国”称谓的不同。《左传》叙事多以国名指称该国国都(13)桓公六年,“冬,淳于公如曹”。淳于公即州公,州为国名,都淳于。以国都名代国名,《左传》中极少类似事例。,《传》文中言及国都城邑称谓比较多者为晋之绛、楚之郢,余者齐之临淄、鲁之曲阜、郑之新郑、陈之宛丘、曹之陶丘、吴之姑苏等,均未被提及(14)夷仪,在僖公二十五年卫灭邢之前,夷仪仅以诸侯为邢复国的新都之址的身份被记载1次。成为卫国一邑之后或作为会盟之地,或关系卫国政局变动之地被记载了9次。。周之“国”,据《史记·周本纪》,“平王立,东迁于洛邑”,《正义》曰:“即王城也。”[16]149王子猛之乱后,“(敬)天王入于成周”(昭公二十六年)。昭公三十二年诸侯城成周,说明此时周之“国”在成周。《左传》中虽亦以城邑之名称之,但同时另有“京师”一名以示尊周,京师之称贯穿于《左传》的叙事。
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僖公十一年)。
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
京师为周之“国”的专称、敬称,从《诗经》中亦可看出这种传统。《大雅·公刘》赞颂公刘在周族壮大过程中的贡献,描写公刘迁都之事,诗句云:“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据《毛诗正义》,“《笺》曰:‘山脊曰冈,绝高为之京……谓可营立都邑之处。’”[18]542此后京师之称一直被沿用,王充谓“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19]。《大雅·民劳》为“召穆公刺厉王”之作,“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18]547-548。中国,即京师,周之“国”。诗句明确道出周之“国”的政治地位:国家的中心。《齐诗》谓《曹风·下泉》“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时,忧念周京”[20]。该诗是曹人参与城成周时所作,其诗云: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萧。忾我寤叹,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忾我寤叹,念彼京师。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18]386。
孔广森以为此诗以“念彼”指成周是因敬王新迁,吕祖谦则道出春秋史的真相:“思周道之诗,独作于桧曹何也?政出天子,则强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诸侯,则征发之烦、共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国偏受其害,所以睠怀宗周为独切也。”[21]自敬王以后,诸侯不复勤王。《左传》的京师之称虽一直使用到哀公二十六年,也只为王室保留了形式上的尊严。战国时,成周与王城彻底被分化为两部分,各为一国,成周为东周,王城为西周。周天子沦落为普通诸侯,听命于强国的调遣:“秦召周君,周君难往。或为周君谓魏王曰:‘秦召周君,将以使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兵)于河南……’。”[22]周之“国”不再被尊为“京师”,而是称以“河南”。《读史方舆纪要》曰:“周室衰弱,所有者……七城而已。河南、缑氏、榖城三邑属西周,洛阳、平阴、偃师、巩四邑属东周。”[12]26河南即王城,洛阳即成周。
国野制对周代社会的空间区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中国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23]。对天子、国君所居之“国”的独尊,正是对王权精神的强调,是对以天子、国君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这与《左传》叙事中对礼制的重视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