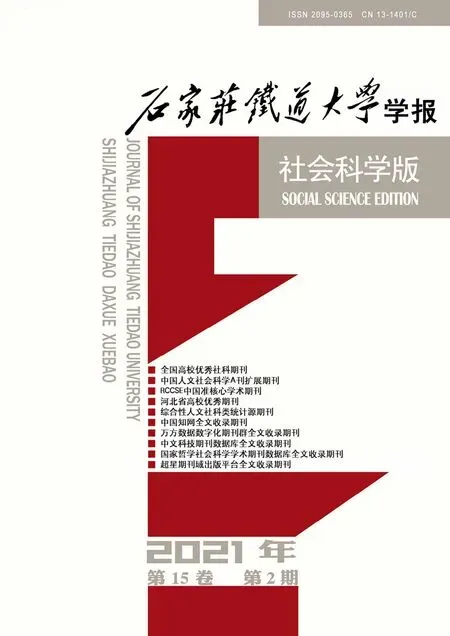论元丰官制后秘书省职官的困窘状态
王艳军, 季红艳
(1.石家庄铁道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2.武警士官学校 基础部,浙江 杭州 310000)
北宋立国,承晚唐五代之制,设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太宗年间又增设秘阁,自此馆阁真正成为北宋的国家图书收藏、管理、校勘、纂修的机构。秘书省,在北宋前期虽然存在,也有秘书监、秘书少监等职,却处于一种“虽有秘书省职官,而无秘书省图籍”[1]的尴尬状态,并不具备图籍典藏、修纂、整理的职能,可以说秘书省在北宋元丰前有名无实。北宋元丰五年,施行新官制,馆阁并入秘书省,秘书省掌管国家图籍经典的职能得以恢复。不仅如此,此后的秘书省还承继了馆阁储养人材的功能。其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正字等职事官被视为“储之英杰之地以饬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益其聪明,稍优其凛,不责以吏事,所以滋长德器,养成名卿贤相”[2]的清要职位。然而入职秘书省并非平步青云,仕途和经济的压力有时也让那些秘书省职官陷于困窘之中。
一、升迁艰难中的困窘
元丰官制后,秘书省被视为馆阁,也被看作养育人才之地,然而却难以完全复制宋初馆阁所获之优礼待遇。元丰官制后的秘书省职官与其它监司的职官一样,依循年资、考核绩效而迁升,即“岁月酬劳”,如元祐间先后作出明确规定:“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诏:‘应试中馆职者,内选人除试正字,改官、请俸等并依太学博士法。未升朝官除秘阁校理,正字供职四年除秘阁校理,仍候改寄禄官日除授。校书郎供职二年除集贤校理,秘书郎、著作佐郎比集贤、秘阁校理,著作郎比直集贤院、直秘阁。应校理以上未有兼领职事者,并于秘书省供职轮宿,依旧例给职食钱,并破御厨食。有兼领者,遇本省迎驾起居及议论事并预”[3]。“哲宗元祐二年七月四日,吏部言:‘秘书省官三年为一任,复置馆阁校勘、正字,四年成任。丞满,除秘阁校理;校书郎满,除集贤校理,并谓升朝官知县已上资序之人。余除馆阁校勘,候及上项官及资序改校理。校理已上资任依官制以前法,到馆一年与通判,一任回并到馆三年与知州,已系通判资序即二年与知州。秘书省官关升不用举主,著作郎、佐郎、秘书郎并除升朝官知县已上资序人,秘书省牒吏部施行,余如旧制。任满日,著作郎除直集贤院,佐郎、秘书郎除集贤校理。’从之。”[3]可见,朝廷对秘书省职官的迁转、改任的年资、职位做出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秘书省职官与其他省、司的职官一样,循年资升迁。
元丰厘正官制,以求名实相符,但“矫失太过,立法既峻,取人遂艰”[4]。秘书省职官循年资升迁,要求严格,选人益艰,导致虽入职秘书省,并非平步青云。虽然也有像苏辙那样未实际任职秘书省而最终升任两制、宰辅者,苏辙元丰八年八月除授秘书省校书郎,元丰八年十月在其赴京途中改为右司谏,元祐元年九月权中书舍人,元祐四年六月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元祐五年二十七日除御史中丞,元祐六年二月二日守尚书右丞,元祐七年六月守门下侍郎。苏辙由校书郎经两制而升至两府,共历时六年又十个月。元丰官制后的秘书省职官像苏辙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但绝大部分秘书省职官没有苏辙这样幸运,而是久历年资而迁延于秘书省。更有甚者如陈师道元符三年十一月(48岁)为秘书省正字,且终身止步于秘书省正字。兹举例如下:
宋匪躬,元祐二年十一月至元祐七年正月为秘书省正字,历时六年又二月。
晁补之历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元年十二月至元祐五年七月)、秘书省校书郎(元祐五年七月至元祐七年十月)、著作佐郎(元祐七年十月至绍圣元年六月),在秘书省任职十年又六月。
李昭玘历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元年十二月至元祐五年七月)、秘书省校书郎(元祐五年七月)、秘书丞(绍圣元年四月至元符二年正月),在秘书省任职八年又三月。
张耒历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元年十二月至元祐五年六月)、著作佐郎(元祐五年六月至元祐六年六月)、秘书丞(元祐六年六月至元祐六年十一月)、著作郎(元祐六年十一月至元祐八年十一月),在秘书省任职八年。
黄庭坚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元丰八年四月至元祐二年正月)、著作佐郎(元祐二年正月至元祐六年三月)、著作郎(元祐三年五月),在秘书省任职七年。
陈察历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元年十二月至元祐五年七月)、秘书省校书郎(元祐五年七月至元祐五年十二月)、秘书郎(元祐五年十二月至元祐六年二月),在秘书省任职五年又三月。
范祖禹历任秘书省正字(元丰七年十一月至元丰八年十月)、著作佐郎(元丰八年十月至元祐元年四月)、著作郎(元祐元年四月至元祐四年五月),在秘书省任职四年又七月。
司马康历任秘书省正字(元丰八年四月至元祐元年五月)、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五月至元祐三年十一月)、著作佐郎(元祐四年十月至元祐五年八月),在秘书省任职四年又五月。
孔武仲历任秘书省正字(元丰八年六月至元祐元年五月)、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五月至元祐三年九月)、著作佐郎(元祐四年四月至元祐五年三月),在秘书省任职四年又二月。
由上面几则资料可以看出,宋匪躬、李昭玘、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在秘书省任职皆超过八年。可见入职秘书省虽被视为荣途,其升迁也较为艰难。所以《容斋随笔》点评说“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反为留滞”[5]。如上面所列的张耒,在秘书省前后任职八年,《宋史》评为“居三馆八年,顾义自守,泊如也”[2]。而《石林燕语》记载了张耒与晁补之的一段轶事:“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荐士试馆职,多一时名士,在馆率论资考次迁,未有越次进用者,皆有滞留之叹。张文潜、晁无咎俱在其间。一日,二人阅朝报,见苏子由自中书舍人除户部侍郎,无咎意以为平,缓曰:‘子由此除不离核。’谓如果之粘核者。文潜遽曰:‘岂不胜汝枝头干乎?’闻者皆大笑。东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辄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谓之‘枝头干’,故云。”[6]“枝头干”乃是一种干果,因果子成熟后因未能及时摘取而干枯于枝头而得名。晁补之在秘书省任职十年又六月,张耒在秘书省任职八年。此则材料张耒是借“枝头干”来喻指他们困于秘书省、久不得升迁的现实境况。陆游也曾用“枝头干”来比喻仕途无望的遭遇:“官如枝头干,不受雨露恩。身如水上浮,泛泛宁有根。刈茆以苫屋,缚柴以为门。故人分禄米,邻父饷鱼飧。前门吏征租,后门质襦巾军。不敢谋岁月,且复支朝昏。雨余幽花坼,亦可侑清尊。吾生信已乎,终老此山村。”[7]
晁补之、张耒、秦观、黄庭坚等人在秘书省职官任上蹉跎数载,原来入职秘书省所期望的“名虽文字之选,实为将相之储”(陈师道《谢正字启》)的美好愿望很难实现,仕途上的压力让他们对秘书省及自身有了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二、经济贫乏中的困窘
元丰官制后的秘书省职官除了升迁之难,有时在经济上也颇受困扰。
北宋经济发展,太宗皇帝曾说:“国家岁入财数倍于唐”[2]。而关于宋代官员的俸禄待遇,赵翼之说颇为流行,即“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8]。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宋初之馆阁,地位优崇,然不乏馆职清贫的记载。《梦溪笔谈》记载了晏殊为馆职时因家贫不能参与臣僚宴饮的事情:“晏殊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9]晏殊关于馆职俸禄微薄的描述,并非虚言,王安石本人也有这样的体会:“以臣疵贱,谬蒙拔擢,至于馆阁之选,岂非素愿所荣。然而不愿就试,正以旧制入馆则当供职一年,臣方甚贫,势不可处。”[10]朝廷升任王安石为集贤校理,进入馆阁,但王安石拒绝赴京任职,他请辞集贤校理的原因就是家里贫穷,难以在京城呆下去。理由看似荒唐,却较为可信。
元丰官制后的秘书省,张耒在《答林学士启》中对其政治待遇、社会名望、俸禄待遇给予了客观的评价:“窃惟馆阁之选,盖待儒学之臣,既非典领之权,几于冗散,又无议论之责,少补丝毫。宜非仕者之愿居,而为一世之所尚。盖学问为君子之事,职卑而待之不轻;诗书非俗士所知,禄薄而意则甚厚。虽厌居寂寞,夸者至谓之病坊;而脱略等夷,赤尉均称于宰相。名既如此,人犹贵之。”[11]张耒眼中的秘书省,没有实权,不能议论时政,几近于冗散,却又为士人所崇尚;职务卑微,清冷寂寞,被视为病坊,却又被世人所贵;俸禄微薄而又被人寄予厚望。张耒在这段话中所描述的秘书省的矛盾状态,也在一些文人身上得到了验证。
如黄庭坚久在秘书省任职,其诗中多有生活穷困的记载。元祐三年,其《次韵答秦少章乞酒》说“颇知富贵事,势穷心亦舒。秋来献穷状,水饼嚼冰蔬”[12],此诗写出了“水饼嚼冰蔬”的“势穷”的生活状态。而元祐二年的《送刘道纯》云:“我今四壁恋微禄,知公未能长挂冠”[12]以及“虽勉素餐,已糜岁月”[12]更加直白地写出了自己家徒四壁、俸禄微薄、常年素餐的生活困窘情况。《鸡肋编》甚至记载了黄庭坚以笔墨换米的情况:“先公元祐中为尚书郎,时黄鲁直在馆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笔墨来易米。报谢积久,尺牍盈轴,目之为‘乞米帖’。”[13]这段材料写黄庭坚以公家的笔墨来换米的故事,所谓的“乞米帖”就是黄庭坚生活贫困的见证。
秦观入职秘书省,哪怕是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也有着“始觉身从天上归”[14]的感受,然而生活的情况也是他不能回避的现实。元祐六年冬,秦观《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云:“道山虽云佳,久寓有饥色”[19]。“道山”指代秘书省,但是由于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俸禄微薄,久处乃有饥寒之色,说出了秦观任职秘书省时的困窘。元祐八年春,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秦观又作《春日偶题呈上尚书丈丈》:“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19]秦观自元祐五年进京任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至今已经三年。这是秦观写给钱穆父的一首诗,说春日时节老枝绽放新花,而自己三年中屡添白发。自己此时典当春衣并非像杜甫那样喜好喝酒,而是家中贫苦已经食粥多日了。很明显秦观此诗既是述说自己的家贫,更是希望对方施以援手的求救信。钱穆父见诗后赶紧给秦观送去米二石,并附诗一首:“儒馆优贤盖取《颐》,校雠犹自困朝饥。西邻俸禄无多少,希薄才堪作淖糜。”[19]秦观受米后赋诗酬谢钱穆父,其《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云:“本欲先生一解颐, 顿烦分米慰长饥。客无贵贱皆疏饭, 惟有慈亲食肉糜。梦里光阴挽不回, 掩关独坐万缘灰。偶因问讯维摩病, 香积天中施饭来。”[19]秦观和钱穆父的诗揭示出秦观任职秘书省俸禄微薄而家贫的事实。
三、秘书省职官困窘下的外迁
晁补之在任秘书省正字三年又七月后,于元祐五年七月除授秘书省校书郎,随后晁补之请求外任,于元祐七年十月通判扬州。晁补之由秘书省请求担任外官,经济方面是重要的原因。这不乏先例。如徐度《却扫编》记载了吕大临由馆职充任外官的经过:“家贫甚,僮仆不具,多躬执贱役。一日自秣马,会例赐御书,使者及门适见之,嗟叹而去,归以白上,上大惊异。他日以语宰相,遂命知广安军。”[17]这段材料交待了外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困顿。晁补之请求外任也是如此。晁补之自己说“都城米贵斗论璧”[7],苏轼、张耒、蔡肇等人的作品中都反映了晁补之任职秘书省后生活的清贫。苏轼在《和穆父新凉》写道:“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朝来又绝倒,谀墓得霜竹。可怜先生盘,朝日照苜蓿。吾诗固云尔,可使食无肉。”[17]另外,苏轼在《戏用晁补之韵》也说:“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17]苏轼在诗中以举家食粥、食无肉、忍饥诵诗来形容晁补之的生活状况。张耒形容晁补之为“清贫学士”:“清贫学士卧陶斋,壁上墨君澹无语”[11]。元祐二年,蔡肇在《和文潜初伏大雨戏呈无咎》中说:“城中鼎食排翠釜,羊胛驼峰贱如土。青衫学士家故贫,斗米束薪炊湿雨。”[7]蔡肇之诗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京城之中富贵之家鼎食翠釜、羊胛驼峰,挥金如土,而晁补之则是家贫斗米。正因如此,所以晁补之在《次韵文潜病中作时方求补外》中明确说明自己要请求外任。
外任之后,可以大大缓解经济上的困顿。因为按照宋代俸禄之制,外官俸禄不同于京朝官,外官的俸禄由俸钱、料钱加上职田构成。尤其是职田,其收入远远大于京朝官之职钱。咸平中对职田数进行了明确规定:“咸平中,……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十顷,兵马都监押、砦主、厘务官、录事参军、判司等,比通判、幕职之数而均给之。”[2]庆历中又对职田数进行了变更:“庆历中,诏限职田,有司始申定其数。凡大藩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官四顷。凡节镇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三顷。其馀军、监长吏七顷,判官、幕官,并同防、团以下州军。”[2]但职田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官吏兼并、挤占田亩之事,于是熙宁三年,朝廷以成都府为例对职田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宋史》卷172 记载:“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以本路职田令逐州军岁以子利稻麦等拘收变钱,从本司以一路所收钱数,又纽而为斛斗价直,然后等第均给。”[2]也就是以成都府路为例,其他州府仿照,来改革职田制度的分配方式,把原来应得的职田数折换成石数,以实物的形式分配给官员。按宋制,“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江宁府,延、秦、扬、杭、潭、广州”[2],扬州与成都一样同为上州。如晁补之由校书郎通判扬州,其职田收入达到450石,收入远远大于京官校书郎的收入。所以当晁补之即将赴扬州之时,又给张耒寄诗一首,诗中不仅称赞张耒的品性,述说二人兄弟般的情谊,而且再次强调了自己之所以出任外官的家庭境遇:“小人奉慈亲,皆尝小人羹。寒衣妇补绽,学绩女娉婷。日欲江海去,心期杨柳青。”[7]“皆尝小人羹”语出《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於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18]是说颖考叔在与郑庄公吃饭时,把饭菜中的肉都留下准备带走,郑庄公看到后就问他问什么这样做,颖考叔说家里有老母亲,从来没有吃过君王您的肉,所以要带回家给母亲吃。晁补之引用这段话是说自己要奉养母亲以尽孝道,可是现在妻子要亲自缝补寒衣,家里的女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学习绩麻织布。正是这样穷困的家庭,所以希望能够远赴江海,也就是将要赴扬州任职了。晁补之最终赴扬州赴任,但他的内心是矛盾的。晁补之在到任后写的《扬州谢执政启》中说“囊空坐小,辄倾将母之诚;钧播无私,偶遂佐州之请”[7],表达了对朝廷体谅自己家庭困难、让自己出任外官,从而得以实现侍亲愿望的感激之情。但同时,“意虽甘于远外,迹终涉于摩伏”[7],是说自己虽愿意离京外出任职,但远离秘书省,对自己的仕途也有着较大的影响。
尽管有升迁中的困难以及生活上的困窘,秘书省“非独使之寻文字、窥笔墨也,盖将以观太下之材,而备大臣之选”[19]的养育人才的政治功能,使秘书省依然成为文人们的向往之地。如上文所提到的苏辙由校书郎升任右司谏并最终升至两府,苏辙却说“仕宦不由天禄阁,坐曹终日漫皇皇”(苏辙《次韵张去华院中感怀》),以不入秘书省而深以为恨。“名既如此,人犹贵之”[11],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