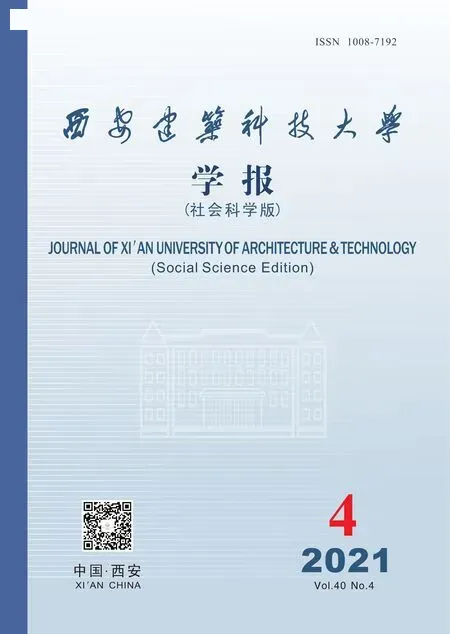论朱熹理学经典诠释法
——以《论语》“亲亲相隐”为例
魏子钦,黄 熹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1]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这样做的。朱子通过诠释“四书”,试图建立儒家的人间秩序与价值信仰,一方面在彰显儒家“元典性”,另一方面也为儒学发展空间的延展提供可能。不过,这里面似乎存在着一定问题,就好像是同郭象《庄子注》般,是“庄子注解郭象”,还是“郭象注解庄子”,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朱熹面对汉宋之学是如何择选,又是如何诠释经典呢。鉴于此,以朱子《论语集注》中对“亲亲相隐”的诠释为例,拉长时间线,将其纳入儒家经典诠释史中,从汉宋诠释与朱熹诠释主张与设计角度,进一步体会朱子经典诠释思想,期望对朱子理学经典诠释法的理解有所推进。
一、“亲亲相隐”的诠释流衍
对于《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解读,历来是学者们思索之关键,由其诠释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经典诠释法也不尽相同。如先圣孔子取认“六经”,欲通过“亲亲相隐”等言使“周文生命化”[2]53。至于如何诠释“六经”,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为之作注:“述,传旧而已……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3]93可以说,孔子“亲亲相隐”等言之“述”是深入三代的诠释法。
自孔子后理学家出现前的一批学者们,大体上对《论语》的诠释研究呈现出“训诂”与“考据”两类。要么是从“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4]2的训诂出发,对上古不同时期、地域的语言进行梳理。要么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何乎?是以论其世也”[5]193的对古代名物制度和历史事件的考据法。而且,关于考据法,宋明儒家多有所偏向。回顾“训诂”与“考据”下对《论语》“亲亲相隐”的文字疏解,汉时古文经学儒学力求“知人论世”对抗今文学家的“古为今用”,而魏晋南北朝之期的集解与义疏,可说是汉代古文经训诂法的又一发展与推进;宋明时期虽有理学的超克,引起文字训诂研究方法论,由汉唐重语义词源转向宋明理学视域下重义理发挥,然宋明学者亦不废小学之功,虽重考据,但指归义理;而清儒见长于考据,有重返汉唐之气,亦是对宋风后期流于空疏的拨乱反正。总之,这批儒者是站在汉学的角度,谈论文字原始意与风情掌故的历史还原与文化再现,似乎忘记了孔子欲使“周文生命化”的生命文化意识,忽略了其“斯文在兹”的历史文化情怀,缺少了一定义理思想的现世关怀。
“其实汉儒于义理亦有精胜之处,宋儒于训诂未必一无可取也。”[6]4章太炎也讲:“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吕思勉评曰:“大抵一种学问,有其利必有其弊。”[7]78其实,重视“考据”“训诂”这批儒者,其实是共享一种相似理念:他们以“历史主义态度”诠释经典,试图建立一种诠释边界。期以训诂考据,达到对历史文化的明澈体察,落实到知人论世之追体验,但经典诠释活动始终都需要人的参与。一方面,典籍词句的基本解释,只能让读者对于经典的理解变得简单机械;另一方面,仅以此法辟仙派佛,儒家难取优势。面对此种诠释之弊,须回重义理的阐发突围原有束缚,适用于经学梳理的“训诂”“考据”必然转向新演进。当依循这样的观点,从义理角度出发,来审视“亲亲相隐”时,就会发现其中的闪光处,已经超越了训诂与考据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理学大儒朱熹开启宋代经典诠释的新天地,其经典诠释法有别于以往儒者。
二、朱熹的诠释主张:“训诂考据”与“心性义理”的并举
章太炎讲:“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7]92陆九渊批朱熹不重“血脉”(《象山全集》卷35),但朱熹并不这样认为:
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至追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述,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8]3640。
朱熹指出两个症结:一是秦汉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使儒家经典损坏、散佚,汉学学者仅以训诂章句求解,于圣心天道上少有言明;二是宋明儒者以“明性命之归”为鹄的,依向上之文化意识与向内之生命体验来重塑儒家精神,以克服汉学的疏解之失,但宋儒矫枉过正,使后学门人不知深求经典,亦不讲训诂考据。
朱熹也指出汉晋治学之别,“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9]1675。朱子大致肯定汉儒而批评晋人解经文学,其中含有对魏晋玄学解经之思想基础(老庄思想)的贬斥意味。
朱子在批评汉宋之弊的基础上,对汉宋之学多有吸取:“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9]191
一方面,朱熹肯认“汉学”,要求学者“一一认得”;另一方面,朱子也讲“向上透处”,在理解经典与感悟人生中,追求自我的觉醒、发展、完成,以言“性与天道”[1]。在以往研究中,学界对朱熹的义理研究已是充分,但对其训诂考据研究关注略有不足,以下将对朱子“训诂考据”的经典诠释研究着重论述。
朱子认为文字训释是解经之始事。解经应从“解字”始,“先释字义,次释文义”(《晦庵集》卷31)只有先行解字,才能发明“义理”。在对经典考据方面,朱熹通过稽考相关资料以通训诂。一方面,训释辞书。如《论语·乡党》中,“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侃侃”“訚訚”,古注“和乐与中正貌”[3]117,朱熹采《说文》训:“侃侃,刚直也。訚訚,和悦而诤也。”[9]1001另一方面,考辩正文。朱熹注“过位,色勃如也”、《论语·乡党》言“位,谓门屏之间,人君宁立之处”[3]118。理由为:“古者朝会,君臣皆立,故《史记》谓‘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君立于门屏之间。”[9]999朱熹通过钩考《史记·商君列传》“古者朝会,君臣皆立”的典制,对“位”一字精确注释。
朱熹将训诂考据与义理并举,并在注解“四书”过程中,用力颇深。朱熹解“亲亲相隐”言:“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盗曰攘。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去声。……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3]146
朱子在此处虽涉及一定训诂,但更多偏向天理人情的义理讨论。如果将其放大至《论语集注》中,便会发现一些与本章相关的考据训诂工作,一方面,朱子关于叶公及叶的讨论。《论语·子路》言:“叶公问孔子于子路。”朱子注:“叶,舒涉反。叶公,楚叶县尹沈诸梁,字子高,僭称公也。”[3]97另外,关于叶公的问题,朱子也有明确考据,因在上文已经论述,此处略论。另一方面,朱熹关于“亲亲相隐”之“直”的讨论,他把《论语》中的“直”多解读为“正直”,此处的“亲亲相隐”亦取这一含义。“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朱熹把这种“直”与“仁”“知”“信”“勇”“刚”称为美德。“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3]98不过,也有例外。“古之愚也直”,朱熹说“直,谓径行自遂”,《论语·阳货》[9]此“直”为“直率”义。
朱熹站在高于汉宋之学的立场,对汉宋之学进行取舍。不过,若从义理角度辨识,则会发现朱子对“亲亲相隐”背后的思想解读已是剔透分明。在《论孟精义》中,朱子牵引诸家,并作阐明:
范曰:“父为子隐则慈,子为父隐则孝,父慈子孝,天下之直也。夫隐有似乎不直,至于父子天性,则以隐为直也。……隐与直反,然而父子必隐乃为直。”
谢曰:“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矽卡岩型矿围岩蚀变主要为矽卡岩化,形成钙铝石榴石及透辉石矽卡岩、透辉石榴矽卡岩等,呈条带状分布于岩体外接触带上,同时伴有碳酸盐化,与铜矿体关系密切,并伴有磁铁矿化、孔雀石化。
杨曰:“父子相隐,人之情也,若其情,则直在其中矣。子证其父,岂人情也哉!逆而为之,曲孰甚焉。”又曰:“父子之真情,岂欲相暴其恶哉!行其真情,乃所谓直,反情以为直,则失其所以直矣。”
侯曰:“父子相隐,直也,岂有反天理而为直哉?故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尹曰:“顺理为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所以直在其中矣。”[10]459-460
对于这些言论,朱熹说:“杨氏之说本乎情,谢、侯氏、尹氏之说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试以身处之,则所谓情者,可体而易见;所谓理者,近于泛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见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则人情之或邪或正,初无准则,若之何必顺此而皆可以为直也邪?”[11]817-818朱熹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角度讲“亲亲相隐”,强调“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既肯定父子相隐是合情合理,又认为此合情合理是形下形上的贯通。在朱熹看来,要想清楚地理解“亲亲相隐”问题,既要像杨时从人情出发;又要像谢良佐、侯仲良、尹焞从天理而言,并将两者结合,使天人、礼法、情理贯通。
话至此处,可对前文所提的朱熹面对汉宋之学是如何择选,又是如何诠释经典呢?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给出明确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不能机械地“非此即彼”地回答。一方面,朱子是在继承“四书”基础上而形成,且朱子对“四书”充满认同感。故此,他必不会以穿凿之机代替儒家先贤的圣心道理,这一点也可以从朱子的生平和学履历程看出来。另一方面,朱熹所处的时代难免不受佛老影响,加之朱熹个人气质与学脉继承关系,他所诠释的经典必会打上个人和时代“文化烙印”。所以,朱子所著之《四书集注》是“六经注我”,亦是“我注六经”。其中,就《论语集注》看,既是“朱子注孔子”,也是“孔子注朱子”。不过,朱子并未止步于汉宋之学,而是对经典诠释的工作进一步展开,即在经典诠释过程中融入了文化与生命融合的体知。朱子诠释经典以“训诂考据”“心性义理”“生命体知”三重诠释法来完成,实现了儒家经典诠释的“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
三、朱熹的诠释设计:生命与文化融合的体知进路
朱熹依“训诂考据”与“心性义理”并举法,拓展、深化了四书学,“甚至在一定范围之内转换了解释向度,建构了一个形而上的体系”[12]19。但朱子并未离开儒家根本,其目的是学以成人,成贤成圣,即追求天人合一的气象境界。蒙培元先生的讲法大致不错,如将其说法进一步展开,则可说儒家所讲的根本,在于生命文化意识的体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达至圣人境界的天人合一,也是为了追求合外内之道,实现知识与价值的统一。
朱子《四书集注》与原本“四书”相比,在很多地方已发生变化,这在理论形态上有着更多显现。当然,朱子经典诠释的形成与佛老义理冲击有很大关系。但是,朱子《四书集注》中儒学基本问题和核心价值,并没有就此偏向佛老,它还是继续讲儒家圣言,即天人外内,成己成物,生命体知。从这一点看,朱子经典诠释做到“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这种思想在其《四书集注》中有着明确体现。
朱子在对《论语》“亲亲相隐”的注解中,并没有将圣贤的话当作客观的知识去对待,而是主张人们把外在的知识和个人的生活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进入生活世界切实体会生生不已的真生命之价值,即体会天理人情、亲亲之仁、儒家生命的真诚与实敬。孔子重在言仁,指出了仁是人的真实生命,是诸德之本、价值之源。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命是有根源的,无根则无生命。而人之根在于“孝弟”,是以“亲亲”养教以日成,人通过下学践仁行孝,便可上达契悟天道,体证无限价值。
仁是生生之理,但其表现在气化活动中,便有渐次过程,如四时流行,“渐”是生的秘密。在朱熹眼里,生命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润物细无声”。譬如嫩芽初如针,假以时日,抽枝生叶,开花结实。而在人的生命中实现,必有程序,其实现有一发端处,孝弟便是仁的发端。人之生命力量含蕴“亲亲仁爱”的积蓄。孝弟亲情是这么自然,悄无声息。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在与凡动静语默间,世事流转,但惟致此事一念之孝弟,颠扑不破。在亲亲相隐的仁孝之间,万物生命是整体贯通的有机体。“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宇宙是天地、万物、人相关联、相依赖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生命不是独存的,而是互依相关的。朱子所流露出来的生命的体知思想,不仅共同构成了生命整体之流,也蕴育、支撑着“天理人情”的真生命。在这一过程中,生命、生生、生的意义通过“天理人情”而一语化出。
那么,如何理解朱子理解“天理人情”之真生命。朱子之学更多地聚焦于理解和安顿生命。这里所讲的生命,不是生物学的生命,也不是抽象上的生命,而是日常生活的生命。这种生命的文化与力量在“孝弟慈”中升达,在“天地之心”处生发,“亲亲仁人”,直见本心,调适上遂,直通天人。就生命本体而言,一个生命的历程就是生命文化的体知历程。体知不是另有一个外在化的过程,更没有脱离生命本身的独立形式,而是和生命本体的存有状态融洽如一,生命文化的融合就是体知。生命遵循本体原则,生生不已,发用流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进入超越物我,主体生命与本体世界浑然一体的生命境界。这不仅是朱熹对生命与文化融合意识的体知体验,也是朱子诠释“四书”的最高目的,归至“性与天道”的真实用意。一如朱子训门人曰:
世间只是这个道理,譬如昼日当空,一念之间台着这道理,则皎款明白,更无纤毫窒磚,故曰“天命之谓性”。不只是这处有,处处皆有。只是寻时先从自家身上寻起……千人万人,一切万物,无不是这道理[9]2787-2788。
体知是人生的万般阅历,特别是一种道德实践的工夫,朱子明确了生命体验需内外结合的道理,使得知与行工夫的重要意义不断上升,在经典诠释中不断强化个人的生命意识。最后,生命的体知也是一个证实过程,将已有知识放到实际生活中去检验,化“亲亲相隐”理论为“亲亲相隐”德行。经过不断体证后,将书本知识化为自己生命,这样也就接近或者达到了圣人所描绘的境地。
人的生命存在及人的生命意识始终是朱熹经典诠释思想的焦点。人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历史和文化的存在。人的自然的现实生命意识、亲亲的生活生命意识和人文的文化生命意识,三者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文化形态。朱子之学是生命智慧之学,也是亲身践行之学,它关涉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与意义,具有强烈的“成己成物”的践行性、生命性与体验性。朱子之学注重个体生命体验与现实生活的开拓,是以生命与实践来贯通天人。不过,在朱熹的时代,他的这种诠释方法并非所有人都接受。“朱谓陆为空疏,陆谓朱为支离,二家异同,其要点在此”[10]460,朱陆主张不同,彼此辩论,互不相服。章太炎称:“古人之学也,即以是义贵其人,又何争于文字语言之末也哉!”[7]92按梁启超先生言,则是“平心而论,两派各走各路,各有好处,都不失为治学的一种好方法”[13]58-59。
四、结 语
朱熹经典诠释法立足于汉宋之学基础上,而行训诂考据与义理之法并举。这种方法打破汉宋学者之藩篱,汉宋学者未有涉及,实超二学,开出新路。朱熹讲“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又讲“父子相隐,本非直,而‘直在其中’”,既肯定“父子相隐”是儒家讲究天理人情的合理选择,又认为“父子相隐”本非直,需要在对父母的达变劝谏中展现出正直。所以,仅以“训诂”“考据”静态地解读“亲亲相隐”,只是研究的出发点,若是纠缠于此,便会损伤经典文化血脉。只有发掘圣人微言大义,建立起历史、文化、生命(训诂考据、心性义理、生命体知)的血脉桥梁,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典深刻含义,继往开来,老树发新枝。
朱熹经典诠释法将生命的学问(成己)与学问的生命(成物)相连。朱子哲学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生命体知的智慧思想,提醒人们须明白求学不能仅满足知识积累,还要体察涵泳,调适上遂,以实现成己成物,追求参赞天地之境界。熊十力先生曾言:“朱子是注重修养的,也是注重知识的,他的主张,恰适用于今日。”[14]10在21世纪的今天,为何读书、如何治学?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又要如何安顿身心?这些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难题。面对这些问题,回看朱熹理学经典诠释法,可从中寻找到一定朱子思想的心声解答。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
——以“亲亲相隐”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