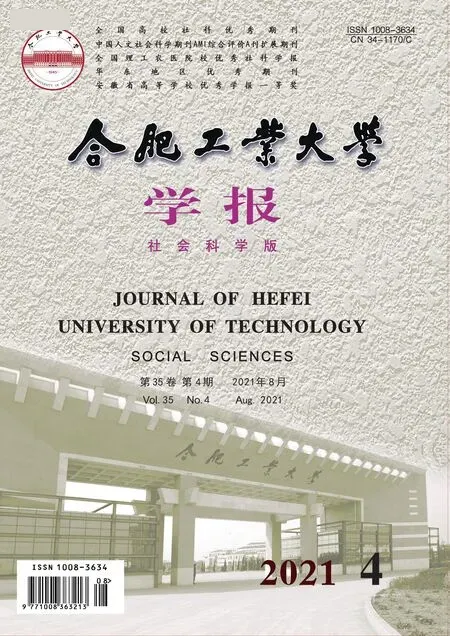狡诈的能指
——论《已知的世界》中摩西的欲望运作
师彦灵, 郑可欣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兰州 730000)
《已知的世界》(TheKnownWorld,2003)是当代美国非裔作家爱德华·P·琼斯(Edward Paul Jones,1950-)的一部新奴隶叙事(neo-slave narratives)力作,故事聚焦于美国内战前夕黑人奴隶主的奇特史实。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将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小说奖以及都柏林文学奖(IMPAC)等多项大奖收入囊中。不少评论家均对琼斯关注的独特视角大加称赞,“《达拉斯晨报》、《波士顿全球报》等评论认为《已知的世界》是‘与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相媲美的关于奴隶制的最佳小说之一’。”[1]传统的奴隶叙事着重塑造黑人与白人之间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通过描绘黑人的屈辱与白人的残酷为废除奴隶制奔走呼号,而新奴隶叙事关注的是当代美国非裔对奴隶制历史的内化,希望他们将被奴役的创伤记忆整合为力量之源,以此对抗当代生活中深化的种族矛盾[2]。《已知的世界》这部优秀的新奴隶叙事作品,通过刻画黑人奴隶主的形象来揭示蓄奴制问题的复杂性,超越了单纯的种族对立,以更深刻的人文关怀探索非人道的社会制度、阶级间的权利冲突以及人类自身的道德复杂性。
《已知的世界》采用的是多线并行的非线性叙事策略。小说首先对种植园主非裔美国人亨利·汤森(Henry Townsend)的种植园监工头黑奴摩西(Moses)进行了刻画,由此引出亨利短暂的一生以及几十位身份各异的人物的故事,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叙事关系网络。摩西本是西方文化两大源头之一《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逃离法老奴役、前往富饶之地的先知领袖,但在《已知的世界》中,琼斯却将这个名字安在沦为奴隶制牺牲品的监工头身上,并以其作为小说的开端和结尾,这种安排在这本复杂精妙的宏大小说里自然是作者故意为之。琼斯在访谈中指出:“奴隶制侵害了每一个人,有的人能够超越……而有的人却被压垮了。”[3]402摩西就是琼斯所言被奴隶制压垮的悲剧人物。亨利去世之后,摩西一直妄想成为下一个亨利,下一个黑人奴隶主。他曾几度靠近其目标,但最终他的苦心经营还是以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的社会性死亡而结束。本文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欲望理论入手,剖析摩西这一欲望主体进行的身份建构尝试,分析其失败成因,阐释文本所暗示的黑人救赎之路。虽然奴隶制早已被废除,但其影响却根深蒂固,当代语境下的非裔美国人仍处于话语权严重缺失的边缘地位,对新奴隶叙事中身份建构的分析可以为生活在当代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的非裔美国人提供生存启示。
一、对象ɑ最初对摩西的诱导
象征界中主体性的建构是其不断被象征秩序阉割(castration)的过程,但是该阉割不是彻底的,总有来自实在界的一小部分作为阉割的剩余物(remainder)抵制着象征化,成为象征界的创伤性内核,这一部分即是对象ɑ。“对象ɑ”(objet petit a, 读作“对象小ɑ”)是拉康理论中含义最为复杂晦涩的一个概念,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对此这样评价:“在拉康的著作中,很少有概念有如此多的变体:小他者、小神像(agalma)、黄金数字、原质(the Freudian Thing)、实在界(the real)、异形(the anomaly)、欲望之因、剩余享乐(surplus jouissance)、语言的物质性、分析者的欲望、逻辑一致性、大他者的欲望、类像/赝品、失落之物等等。”[4]本文所采用的是对象ɑ最常见的定义,即欲望的对象-原因(object-cause of desire);自我的欲望对象是不安分的对象ɑ不断投射到象征界能指链条上的替代能指,是阉割的剩余对主体一次次运作的结果,但由于在社会法则支撑下的象征界中并不能找寻到真正的归属于实在界的对象ɑ这一客体,所以正是出于将神秘的对象ɑ确定下来的尝试,主体才产生了欲望。
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亨利并非自出生起就注定了其成为黑人奴隶主的命运,一开始他只是白人威廉·罗宾斯(William Robbins)种植园里的一名奴隶,不到十岁时,他父母相继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但是很久之后他才赎回自由。二十岁时,亨利在罗宾斯手里买下了第一片土地和第一个奴隶摩西。摩西最初来到曼彻斯特县是由于他被罗宾斯买了下来,当时罗宾斯只看中了摩西,却没看中他的情人贝茜。贝茜腿脚不好,对奴隶主而言不是一件值得拥有的财产。摩西一遍遍地求情,只求不要把他们分开,但是奴隶主丝毫不为所动。在奴隶制社会,象征界法则(Law)这一大他者——即奴隶制的运行——赋予了奴隶主们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是父之名(Name-of-the-Father)的人格化。而摩西不过是象征网络中一枚符号而已。在二者的交锋过程中,摩西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父法之名的绝对威严与冷酷,他遭遇到了大他者毫不留情的阉割,进而承认了自己菲勒斯(phallus)的缺失。
摩西第二次被父法阉割发生在亨利着手建造种植园之初。摩西是亨利买回来的第一个奴隶,亨利是摩西服侍的第一个黑人奴隶主。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甚至合住在一起。但是这样的相处状态让罗宾斯担忧亨利作为奴隶主的威慑力不足,于是他义正辞严地将奴隶制的运行规则灌输给亨利。由于亨利的亲生父亲一直不在身边,罗宾斯对亨利而言就是父亲的化身,所以即便身为黑人,他所认同的也是以罗宾斯为代表的白人的象征秩序。于是亨利将奴隶主的威严内化,逐渐地在能指链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为大他者背书,在自己与奴隶之间画上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他扇摩西耳光,称呼摩西为“黑鬼”,向他下达严苛的劳作命令,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摩西深刻地感知到自己身为奴隶的身份,感觉“自己快要瘫软在地上了”[3]134。
经过这两次突如其来的与象征法则的正面遭遇,摩西越来越远离自己想象的菲勒斯,也意识到了自己主体性建构的缺失与匮乏(lack)。由于象征界的阉割并不是彻底的,总会留下切割的剩余物——对象ɑ。对象ɑ的存在诱导主体急于填补自己的匮乏,不自觉地走向他者。在《研讨班第Ⅹ册:焦虑,1962-1963》中,拉康阐释了对象ɑ与欲望的关系,“我一直在讲要把欲望与切割/阉割的功能相结合,并将欲望与剩余的功能相联系。剩余维持着欲望并赋予其活力……”[5]在象征界阉割法则的运作下,主体经常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但也正是在这种匮乏之中,主体有机会窥见到真实自我的存在。可是摩西却选择掩盖这种匮乏,设法获得对象ɑ,继续建构象征界承认的主体性。
拉康给出的象征界运作的幻象公式是$◇ɑ,即幻象是被阉割的主体($)对对象ɑ的追逐(◇)。对象ɑ首先体现为让亨利满意的监工头这一身份。只有满足了大他者的话语,主体才能在大他者的秩序内找到自己的位置。亨利作为奴隶主讲述的就是大他者的话语,作为奴隶的摩西只能投靠亨利。然而,虽然“对象ɑ被束缚在能指链上,也不可分割地与现实中的欲望对象相结合,但它还同时存在于别的地方”[6]。所以对象ɑ是不可能完全被捕获的,欲望也只能从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摩西十年以来都是监工头,没有能指身份的变化,这不是因为他填补了自己的匮乏,满足了欲望,而是象征界没有给他机会去寻找新的能指。在亨利去世之后,摩西发现了象征网络中的符号性空缺,在此处对象ɑ得以安置,所以摩西对奴隶主这一身份有了欲望。摩西要想跃升为奴隶主,现行的唯一办法就是象征界的符号性委任(symbolic mandate),即卡尔朵妮亚·汤森(Caldonia Townsend)的肯定。所以摩西为了安置自己的对象ɑ,开始追求卡尔朵妮亚。
但是无论对象ɑ将自己安置到什么能指上,主体的匮乏仍然存在。通过回溯,拉康将这种匮乏追忆到主体离开母亲子宫,呱呱坠地的时刻,这是主体与统一性相分离的原初创伤,是其存在的缺失(lack of being)。潜意识中所体会到的原初匮乏总会促使主体弥补自己的缺失,而这可以清楚地解释摩西时不时躺在树林里自渎和吞食泥土的怪异行为。正如精神分析学说代表人物荣格所言:“很多激发虔诚或者敬畏感的东西,比如教会、大学、城市或者乡村、天空、大地、森林,还有任何静水、物体偶数(matter even)、地狱以及月亮,都可以成为母亲象征。”[7]在树林里,整个过程似乎有一种神圣的色彩。他会脱掉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地上。“他吃泥土,不只是为了知道这块农田是肥沃还是贫瘠,而且是因为这个举动把他和在他那小小的世界里,意义几乎相当于他的生命的唯一一种东西连接在了一起。”[3]4他一丝不挂地躺在树林的土地上,就像躺在母亲的怀中,更像回到了在母亲子宫里的状态;他吞食泥土,好像如此便能和母亲合二为一,弥补自己的原初创伤。在这两种行为中,摩西都看到了自己的原初匮乏,并试图满足这种匮乏,为自我营造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幻象。
匮乏持续存在,对象ɑ的驱使也不会止息。主体一直被对象ɑ这一实在界的神秘小客体所诱惑,妄想在象征界中找到其欲望能指,掩盖创伤性内核的匮乏本质,自欺欺人且风生水起地活在象征界的询唤之下。
二、他者欲望催生的侵凌性对摩西幻象的加固
拉康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是对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的阐释:八至十六个月的婴儿通过认同自己在镜子中的整体性形象而产生理想自我(ideal-I),即自我原型(Urbild)。但由于现实中,该阶段的婴儿尚无法控制自己支离破碎的身体,所以理想自我的产生不过是婴儿对镜中格式塔形象(Gestalt)这一小他者的自恋性误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镜子阶段……的内在冲劲从不足匮乏奔向预见先定……一直达到建立起异化着的个体的强固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将影响整个精神发展。”[8]换言之,虽然镜像阶段只发生在婴儿身上,但主体与其形象之间的动态关系会引导主体穷尽一生追寻理想自我,也即对他者形象的追求。
“‘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这句格言可以说是拉康欲望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他的欲望辩证法的第一法则。”[9]亨利是摩西接触到的第一个黑人奴隶主,他“用了两个多礼拜才弄明白,一个不是跟他开玩笑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比他还要黑两倍的黑人,成了他和他可能生养的所有黑鬼的主人。”[3]11对奴隶们而言,背靠奴隶制这一象征法则的奴隶主往往是威严、冷酷的,对他们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大他者。但是亨利不是这样。刚被象征界符号性委任为奴隶主的亨利一开始并没有完全适应奴隶主这一身份能指,不具备和奴隶制度一样坚不可摧的属于大他者的威严。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他和摩西睡在同一间棚屋里,他们更像是朋友。而且他俩同为黑人,身材、年龄都差不多,因此出于对理想自我的自恋性追寻,摩西将亨利视为自我欲望投注的小他者,是他所欲望的自我理想。
亨利在世之时,他的形象就是摩西追逐的欲望对象;在他去世之后,其在象征秩序中能指符号位置的空缺使得该能指变得更加淫荡,不断诱惑着摩西去锚定、去填充。卡尔朵妮亚不仅是亨利的欲望,其与亨利亲密的符号关系(夫妻)还可以保障亨利身为奴隶主的能指符号在象征网络中的运作。因此亨利去世之后,摩西对其遗孀的追求既想满足自己对他者欲望的追求,又想无限接近小他者而取代亨利的符号性地位。因此他为得到卡尔朵妮亚的芳心可谓是绞尽脑汁。其一,亨利去世不久,卡尔朵妮亚就要求作为监工头的摩西每天给她汇报种植园的相关情况。一开始的汇报只持续几分钟,但后来摩西发现卡尔朵妮亚需要听他讲话,他就把汇报时间逐渐延长到了一小时,哪怕是编也要编出些投其所好的事情来讲。其二,他在进大宅子汇报之前,会一反常态地专门洗澡。妻子多嘴问了一句,就被打了耳光。其三,他知道卡尔朵妮亚喜欢听亨利的事情,于是就编造了“最有想象力的故事,来讲述亨利·汤森怎样开垦荒地,给未来的新娘建造了这个家园”[3]284。其四,为了扫清所有障碍,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骗走。以上所有这些行为的动机都不是爱情。他讨好她,只是“因为他需要得到不用敲门就能径直从后门走进宅子的权力”[3]333,只是因为这是朝向他者的欲望,是他者欲望的欲望。
对他者形象的误认以及对他者欲望的追逐均源于自恋心理。“在理想形象对身体的控制和儿童身体实际的支离破碎的状态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一致,也正是这种不一致导致了侵凌性的出现。”[10]换言之,自我拒绝接受破碎和异化的真相,帮助镜中他者将尚未有机会形成的真实自我这一概念扼杀在萌芽状态。也即出于维护幻象中自我的他者形象主体和对他者欲望满足的保证,主体才产生了侵凌性。正如对理想自我的追寻存在于主体的每个阶段,出于对幻想中自我形象的维护而产生的侵凌性也存在于主体的每个阶段。
在摩西意识到艾丽斯(Alice)撞破了自己在小树林自渎时,他最大限度地展露了自己的侵凌性特质,“他起了念头,要跟踪她,把她干掉”[3]279。艾丽斯对该秘密的发现标志着摩西在大他者凝视下的自我理想的幻象出现了裂痕。他要取代亨利的符号性地位成为奴隶主,而在摩西的认知中,在小树林中自渎这种隐私不符合于借大他者之口发声的奴隶主形象。更重要的原因是,摩西一丝不挂地躺在树林里是为了弥补自己的原初性匮乏,摩西潜意识中认为艾丽斯撞破这一行为时似乎也透视了自己匮乏的秘密。因此,只要艾丽斯不泄露他的秘密、不撕破他辛苦建立的主体性整体幻象,他还能以一个自欺欺人的完美的他者形象存在,一个能被其他奴隶和女主人认同并承认的他者形象,一个能够匹配自己所锚定的欲望对象的他者形象。但是他不允许自己被说三道四,不允许自己的幻象身份构建中有一丝一毫的裂痕存在,尤其是在他认为即将要和女主人结婚的这个关键时刻。而且艾丽斯的疯癫、不稳定的特质就像实在界的血盆大口,他对她的举动没有任何预期,这种不确定性威胁着一切脆弱的幻象,威胁着象征秩序本身的稳定。在摩西为了维护自己幻象中的完美与威严所做的杀死艾丽斯的决定中,我们清楚地感知到自恋对侵凌的催生和侵凌对主体行为的塑造。
摩西在小说中还对埃利亚斯(Elias)展示出了侵凌性倾向,他在埃利亚斯逃跑被抓身负重伤的时候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嘲笑和厌恶。虽然埃利亚斯有二十天左右的时间身体不佳,干活跟不上大家的速度。除了这件事,摩西与埃利亚斯再无过节,他对自己同伴逃跑被抓似乎表现得过于冷酷与残忍。这是因为摩西所认同的自我理想的他者形象是亨利,认同的最佳结果便是获得欲望对象的承认,但是欲望对象不会明确地告诉摩西他要如何做才能获得自己的承认,摩西只能依靠猜测进行判断。为了这一目的,他会站在他者的角度思考,他者究竟想要自己干什么,他者究竟想要在自己这里得到什么。这一有关主体间性的疑问涉及摩西在象征界这一结构性网络中所占据的能指符号。摩西对亨利的价值在于其奴隶监工头的地位,而埃利亚斯拖后腿的行为威胁到了亨利对摩西在象征秩序网络中的承认,威胁到了摩西对他者欲望的满足。除此以外,埃利亚斯还试图逃出种植园,挑战了亨利作为奴隶主这一符号性身份的权威,损害了其利益。亨利作为摩西认同的欲望对象,挑战其权威也就意味着暴露了他者形象的缺失,有损于摩西为欲望他者精心编织的支撑主体符号性身份的幻象。因此,出于对自我形象和他者幻象的维护,摩西对埃利亚斯展现出了侵凌性。
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一方面意味着人的欲望是朝向他人的欲望,而另一方面则同时蕴含着侵凌性,以保证幻象的完满和欲望的满足。摩西将亨利视为其自我认知的他者形象,其实体现了对真实自我的否定。他所展现出的侵凌性也都是为了保持象征界所暗示他的对自我认知的幻象,但实际上这一幻象在起源上就偏离了真实主体的道路。
三、原乐悖论对摩西满足欲望的阻止与诱惑
在拉康那里,“Jouissance”(原乐/享乐)的含义常与欲望的享用、死亡驱力、对父法的僭越等命题联系在一起。虽然客体ɑ是欲望的原因及对象,但是严格说来,“欲望是没有对象的。在本质上,欲望只是对某种东西的不断追求,不存在一种能满足欲望的对象。”[4]90既然如此,对欲望的追求便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运动,主体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快感来源于“欲求过程中的快乐/原乐”。
原乐是在追求神秘的小客体对象ɑ这一永恒的丢失之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是企图回到实在界,抵制象征化和超越快乐原则的冲动。之前摩西心满意足地躺在树林里不只是为了回归到母亲的怀抱,营造整体性的幻象,同时还体现了摩西对俄狄浦斯欲望的悖论性企图。法则存在的根本性前提就是“企图打破并僭越法则的欲望”[11],比如父法最初的目的就是禁止人类最原始的俄狄浦斯欲望,但是对欲望的禁止与压抑只会激发主体产生更强烈的欲望,以求获得更大的享乐。有次他去树林的时候赶上下雨,“那次,他被一种极其强烈的快感攫住,曾经哈哈地大笑,在地上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又一圈。”[3]6这种强烈的快感正是回归实在界创伤的原乐。
虽然对象ɑ是极具诱惑力的实在界的内核,但是因为其朦胧的特质,主体只能不断地在象征界中寻求对象ɑ这一终极欲望的代替能指。在能指链上持续前进的主体,由于幻象的支撑,会产生一种越来越接近终极欲望的错觉。在大他者对亨利的询唤过程中,摩西亲眼见证了亨利从奴隶到奴隶主这一获取权力的过程,对于摩西来说,这是关于权力的间接训诫。因此,在蓄奴制这一社会背景下,摩西试图用亨利这种手握权力的奴隶主的身份能指填补自己终极欲望的空缺。
但是对对象ɑ的过分接近意味着享乐的终止,焦虑也就随之产生。享乐总是想要“再来一次”(Encore),总是驱力性、强迫性的满足,因此主体在过分焦虑的情况下反而会将终极欲望推离自身。摩西对卡尔朵妮亚的追求经过了不露痕迹地讨好、送走妻孩、结合等复杂过程之后,总算与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此时的摩西却一反常态。十年监工头的经历本来让他养成了内敛、狠心的性格,此刻的他却十分莽撞,在和卡尔朵妮亚第一次结合之后就谈到了自由文书的事情,这种过分着急正是焦虑的体现。这就是原乐的悖论:一方面促使摩西苦苦追逐欲望,一方面又阻止他过分接近欲望。所以他一边陷在欲求的循环之中不可自拔,又一边担心享乐的终止,潜意识地远离欲望对象。
计划进行到最后,摩西觉得一切都超出了自己的控制,逃离了种植园,暂时藏身在亨利亲生父母的家中。亨利的父母一直不肯接受亨利成为奴隶主奴役奴隶的事实,去到亨利家也不住在大宅子里,只是栖身于旁边为奴隶准备的屋子中。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并不认同这一不公正的象征秩序,他们的意识像实在界一样抵制被象征化。摩西藏身其中,和亨利父母在一起的行为似乎也体现了他对象征界的疏离,对象征界伪欲望的抵抗,对他者欲望的抗拒,以及对真实自我的靠近。
但是对摩西而言,他者原乐的诱惑力量最终还是胜过了其阻止力量。治安官猜到了摩西藏在亨利父母家中的可能性,却没有找到他。他本可以一直藏下去,直到遇到合适的机会再像艾丽斯那样悄无声息地远远地逃走,但他却在最后关头主动现身。他没有勇气逃离这个地方,他没有勇气去重新建构一个主体身份,他的现身是他遵从象征法则的体现,是他屈服于象征界的体现。原乐极具诱惑的一面彻底胜利了。作为奴隶,作为卡尔朵妮娅的财产,她不会以死亡为代价作为惩罚,甚至如果她念及旧情都不会责罚他,所以他把象征法则作为盔甲,为异化的自我保驾护航。至此,摩西的主体性身份构建的尝试全盘失败,他回到亨利种植园后浑浑噩噩了此残生。
四、结 语
摩西的一生是作为欲望主体的一生,但欲望的狡诈在于每一步都在诱惑主体远离自我,走向他者。对象ɑ向摩西揭示了存在的缺失,但是摩西急于掩盖这种匮乏,于是在象征秩序的询唤下不断追寻着他者的欲望,竭力维护自己在符号界虚幻的完满幻象。即使原乐对欲望满足的阻止作用促使摩西轻微地僭越了象征法则,他却没有持续与之抗衡的勇气,只能以屈服于原乐与大他者的姿态告终。摩西的悲剧并不仅仅是由大他者不合情理地约束造成的,更是因为作为欲望主体的摩西对这一大他者的潜意识认同,因为其对他者欲望的盲目追逐以及对真实自我的彻底远离。
作为生活在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企图与白人社会同化来获得救赎绝对不是一条可行之路。摩西就是鲜活的例子,他对象征秩序的盲目认同、对他者欲望的盲目追逐,并不能帮助他构建出自己满意的主体形象。相反,非裔美国人要正视自己被边缘化、被奴役的创伤经历,提炼出属于自己族群的精神力量,就像亨利的亲生父母,不认同奴隶制,用自己的姿态抵抗着奴隶制对黑人种族的侵害;就像成功逃向北方的艾丽斯,用绘画的形式将自己的创伤经历展现出来,为更多的非裔美国人提供精神支持。
当代美国社会种族冲突、阶级冲突并没有减弱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本就在大他者那里没有绝对话语权的非裔边缘群体更不应该一味认同于、依附于他者的欲望,而是要对象征界所谓父法的权威持质疑态度,抵制一切压迫。要想早日改变现状,非洲族裔群体更要直面自己的创伤,找到真实的自我,挖掘自己种族的价值,为构建非洲族裔共同体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