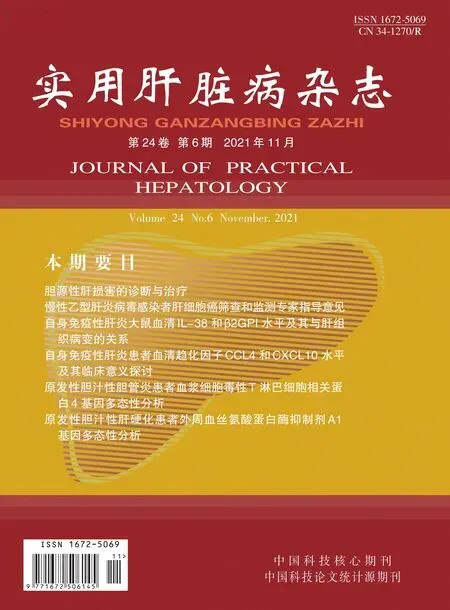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药物治疗新进展*
吕 艳,杨益大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是一种主要发生于中年女性的慢性进行性胆汁淤积性肝病,其特征是非化脓性炎症和小叶间胆管破坏,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与遗传和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异常自身免疫反应有关。乏力和瘙痒是PBC患者常见的症状,晚期可出现肝硬化相关表现,也可因胆汁淤积而发生高脂血症、脂溶性维生素缺乏和骨质疏松等。此外,多数PBC患者可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以干燥综合症最为常见。若满足下列标准中的2项即可诊断为PBC:(1)存在胆汁淤积的生物化学指标,主要是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γ-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升高;(2)血清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AMA)阳性或AMA-2阳性;(3)肝组织学检查提示非化脓性胆管炎和小叶间胆管破坏[1]。熊去氧胆酸(ursodesoxycholic acid,UDCA)和奥贝胆酸(obeticholic,OCA)是目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用于PBC治疗的一线药物,但仍有近半数患者应答不良[1-3]。
近年来,PBC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临床现有治疗药物较少,部分患者对药物治疗不应答或不完全应答,因此当前急需寻求新的药物靶点,开发新型治疗药物。胆汁淤积、炎症反应和肝脏硬化是PBC进展或预后不良的三大关键因素,因而如何有效地减少胆汁淤积、降低胆汁酸毒性、进行免疫调节和抗纤维化治疗是未来有效的治疗方向。本文针对上述靶点,对最新的药物研究进展进行了介绍,为PBC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诊疗新思路。
1 疏通胆汁淤积
胆汁淤积在PBC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胆汁酸是胆汁的重要成分,其中脱氧胆汁酸和鹅脱氧胆汁酸具有表面活性,对脂质有极好的亲和性,能溶解细胞膜上的卵磷脂和胆固醇微胶粒,引起膜损伤,从而继发性引起肝损伤[4]。胆汁酸在体内的肠肝循环过程中存在多个关键调节靶点,如法尼酯衍生物 X 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er-activated receptor, PPAR)和顶端钠依赖性胆酸转运体(apical sodium-dependent bile acid transporter, ASBT)等,这些靶点可通过不同途径达到治疗或改善PBC的作用,是目前最有潜力的药物靶点。
1.1 UDCA UDCA是美国肝病研究学会 (AASLD)和欧洲肝病学会(EASL)推荐的抗胆汁淤积的主要药物,需长期维持治疗[5,6]。UDCA是天然存在的亲水性胆汁酸,其抗胆汁淤积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如通过增加亲水性与疏水性胆汁酸的比例来刺激胆汁流动,稳定碳酸氢盐伞以降低胆汁酸毒性和抗胆汁淤积作用,通过干扰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的呈现以及对巨噬细胞的抗炎作用发挥免疫调节作用,通过上调胆汁酸转运和减少胆汁酸合成来增强肝细胞适应性等[7,8]。长期使用UDCA可延缓疾病的进展,有效改善患者肝脏生化学异常,提高患者生存率。但在PBC患者,仍有25%~50%对UDCA应答不完全应答或无应答[9]。
1.2 非熊去氧胆酸 (non-UDCA) non-UDCA为一种侧链缩短的熊去氧胆酸,缩短的侧链可防止其与甘氨酸或牛磺酸发生酰胺化反应,以增加胆汁酸和碳酸氢盐的分泌,减少胆汁淤积造成的细胞毒性[10]。一项对159例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PSC)患者进行为期12周的安慰剂对照及500 mg、1000 mg和1500 mg non-UDCA治疗研究发现,血清ALP水平呈剂量依赖性下降,试验组分别下降了12.3%、17.3%和26.0%,而安慰剂组则升高了1.2%[11]。四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大致相同,患者原有瘙痒症状均无明显改善。目前,暂无non-UDCA用于治疗PBC的相关报道,因而是否能作为PBC的潜在治疗药物仍待验证。
1.3 FXR激动剂 法尼酯衍生物 X 受体(FXR)是一种核受体,鹅去氧胆酸是其最有效的内源性配体,其被激活后,可有效降低胆汁酸水平。OCA是天然鹅去氧胆酸的半合成衍生物,对FXR的亲和力是鹅去氧胆酸的100倍[12],可通过上调 FXR 蛋白及其基因表达来抑制 CYP7A1 的活性,抑制胆汁酸的合成,缓解胆汁淤积的临床症状,减缓肝纤维化的发展[13]。2016 年 5 月 FDA 批准OCA用于临床治疗对UDCA 应答不充分或不能耐受的PBC患者[14]。研究证明,接受 OCA 治疗12 个月的患者,其血清碱性磷酸酶和总胆汁酸水平与安慰剂组相比显著改善[15]。OCA最常见的副作用为剂量依赖性瘙痒和高密度脂蛋白含量减少或低密度脂蛋白含量增加,因而在使用过程中应对患者的药物耐受性和血脂进行监测[16]。
除OCA外,其他新型FXR激动剂,如Tropifexor(LJN452)、Cilofexor(GS-9674)在动物实验结果表明两者对于减少胆汁淤积、改善肝脏生化学指标、抑制组织炎性细胞浸润和纤维化等方面均有较好的效果[17]。Tropifexor 治疗 PBC 患者临床试验数据(NCT02516605)表明其改善GGT水平疗效显著[18]。 Cilofexor 治疗PSC患者的II期临床试验(NCT02943460)表明其可显著改善胆汁淤积和肝脏生化学指标,Cilofexor 治疗PBC患者的临床试验也在进行中,但结果尚未公布[19]。
1.4 FGF-19类似物:NGM282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9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19,FGF-19)是一种由回肠上皮细胞分泌的调节蛋白,通过c-Jun N末端激酶依赖性途径抑制胆固醇7α-羟化酶的表达,下调胆汁酸合成[20]。一项关于NGM282治疗对UDCA应答不完全的PBC患者研究结果表明,其改善肝脏生化学指标有较好的疗效。该试验纳入了45例对UDCA应答不完全的PBC患者,在使用UDCA的基础上,随机分配接受0.3 mg和3.0 mg NGM282以及安慰剂,持续治疗4周,结果显示3组血清GGT分别下降了15.2%、19.2%和1.2%。由此说明,NGM282对改善生化指标水平确有疗效,目前其延长试验已经完成,但试验结果尚未公布[21]。
1.5 PPAR激动剂:贝特类药物和其他PPAR激动剂 PPAR是核激素受体超家族的配体激活受体,包括三种亚型:PPARα、PPARγ和PPARδ。PPAR参与多种肝脏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且不同亚型的生物学作用不同。PPARα通过抑制胆汁酸的摄取和合成,增加肝细胞分泌磷脂等多种途径缓解胆汁淤积。PPARγ在调节糖代谢、脂代谢、炎症和免疫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PPARδ在肝脏的多种细胞类型中均有表达,研究表明其对调控胆汁酸合成、炎症、纤维化过程的多种因子有调节作用。PPAR激动剂对各种亚型有不同的亲和力,例如,苯扎贝特与3种PPAR亚型均可结合,而菲诺贝特和seladelpar仅可分别特异性结合PPARα和PPARδ亚型[22]。
1.5.1 贝特类 贝特类药物是特异性PPAR-α激动剂。PPAR-α主要在肝细胞中表达,其激动剂可增加多药耐药蛋白3(multidrug resistance protein 3,MDR3)的表达,刺激胆汁磷脂分泌并降低胆汁的侵袭性,从而发挥减少胆汁酸合成、降低胆汁酸毒性和抗炎作用,以达到保护胆管细胞和肝细胞的目的[23]。一项对UDCA无应答患者应用苯扎贝特的前瞻性试验表明,与安慰剂相比,苯扎贝特组中有67%患者实现了血清ALP复常[23]。此外,苯扎贝特可显著降低PBC患者发生瘙痒和肝纤维化的几率,但由于样本量较小,药物的临床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1.5.2 其他PPAR激动剂 seladelpar是特异性PPAR-δ激动剂。PPAR-δ在胆管细胞、星状细胞、库普夫细胞和巨噬细胞中均有表达,具有减少胆汁合成、抗炎和利胆作用。一项对UDCA无应答的PBC患者使用Seladelpar的II期试验结果显示,seladelpar使所有患者的ALP水平有复常的倾向,但因3例患者出现转氨酶升高而导致研究提前终止。Elafibranor(GFT505)是一种双重PPAR-α、δ激动剂,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有较好的效果,目前正在对PBC患者使用效果进行评估(NCT03124108)。
1.6 TGR5激动剂:INT- 767 和 INT- 777 跨膜G蛋白偶联受体5(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5,TGR5)是一种细胞表面受体,其与胆汁酸的特异性结合可激活cAMP信号和其他级联信号,抑制NF- kB途径,从而发挥抗炎作用。在胆管上皮细胞,TGR5还通过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CFTR)介导碳酸氢盐分泌增加,从而减少胆汁酸的细胞毒性。TGR5的广泛活性使其成为治疗胆汁淤积潜在的药物靶点,目前正在研究的药物包括INT- 767 和INT- 777。INT- 767是OCA的23-硫酸酯衍生物,是FXR和TGR5的激动剂,已被证明可减少胆汁酸的合成,增加碳酸氢盐的排泄,并抑制NF-kB途径。INT-777是α-乙基- 23(S)-甲基胆酸,对TGR5具有特异性,同样在动物实验证明其治疗PBC的有效性。
1.7 顶端钠依赖性胆汁酸转运体(ASBT)抑制剂 ASBT主要在回肠壁腔侧膜上表达,负责肠道中绝大部分胆汁酸的重吸收,参与肠肝循环,是胆汁酸代谢的重要环节。通过抑制ASBT可以减少胆汁酸的重吸收,加速胆汁酸的代谢,减轻胆汁淤积。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胆汁淤积的ASBT抑制剂包括GSK2330672和 Odevixibat(A4250)[24]。一项GSK2330672治疗伴有瘙痒的PBC患者的IIa期临床试验表明,其在减少胆汁酸水平和缓解瘙痒两方面有效,但易导致腹泻;另一项Odevixibat(A4250)治疗PBC患者的II期临床试验(NCT02360852)表明其能有效缓解瘙痒,但对肝脏生化指标水平无明显改善。
2 免疫疗法
PBC患者肝组织学检查显示肝组织有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等诸多免疫细胞浸润。免疫细胞能释放多种抗炎和促炎介质,这些介质均受胆汁酸的影响,例如疏水性胆汁酸的积累可以减弱炎症因子的细胞反应,抑制淋巴细胞增殖并损害凋亡胆管细胞的清除等。常用的免疫抑制性药物如泼尼松龙、甲氨蝶呤、硫唑嘌呤、环孢菌素或霉酚酸酯、抗CD20抗体-利妥昔单抗等治疗PBC患者均未显示其有效性。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免疫抑制药物主要有Ustekinumab、Abatacept和FFP104等。对PBC患者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白细胞介素12(IL-12)与信号转导子和转录激活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STAT) 4信号通路之间存在显著关联。Ustekinumab是一种针对IL12/23的单克隆抗体,已经被批准用于治疗克罗恩病和银屑病,但一项对UDCA无应答的PBC患者进行的II期临床试验未能显示Ustekinumab治疗的有效性,因而仍需扩大试验范围。Abatacept是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的融合蛋白,可结合抗原呈递细胞上的信号分子CD80/CD86,并减少效应T细胞和B细胞活化。然而,一项对UDCA无应答的PBC患者进行的III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其改善肝脏生化指标方面无效[25]。CD4+辅助性T淋巴细胞和B细胞的相互作用是PBC特异性抗体反应所必需的。FFP104可阻断T细胞与B细胞之间的CD40/CD40L相互作用,从而抑制免疫反应。但关于FFP104的I期和II期试验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26]。
3 抗纤维化疗法
虽然对PBC患者进行抗纤维化治疗不能避免免疫介导带来的肝损伤,但在晚期患者,抗纤维化治疗可降低需要肝移植的风险。氧化酶样赖氨酸-2(lysyl oxidase-like 2,LOXL2)是一种铜依赖性胺氧化酶,通过催化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的交联在纤维化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西妥珠单抗是一种针对LOXL2的IgG4单克隆抗体。在一项纳入234例PBC患者的II期临床试验,约50%存在肝纤维化或肝硬化,分别给予为期96周的安慰剂、75 mg和125 mg西妥珠单抗治疗,结果显示西妥珠单抗组与安慰组在血清肝纤维化指标、肝组织纤维化分期和血清ALP水平改善等方面无显著差异[27],因而应用西妥珠单抗治疗PBC患者的有效性还有待印证。胆汁淤积和肝细胞凋亡能触发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的活化和增殖,从而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奥贝胆酸可减少胆汁淤积和抑制HSCs活化和增殖,但不能抑制肝细胞凋亡。研究表明,奥贝胆酸与较低剂量的凋亡抑制剂(IDN-6556)联合使用既能更好地降低血清ALP水平,又能抑制HSC活化,发挥良好的抗纤维化作用[28]。
4 结论
虽然新诊断的PBC病例不断增多,但用于临床治疗的有效药物却较少。随着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不断阐明胆汁酸代谢相关的病理生理、核受体、表面受体和转运蛋白等在PBC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新药在研发。FXR激动剂、FGF-19类似物、PPAR激动剂、TGR5激动剂、ASBT抑制剂等均在不同的临床试验中显示其有效性,提示针对PBC患者的抗胆汁淤积治疗是多方面多靶点的,亦是目前最有潜力的治疗方法。此外,在疾病早期的免疫调节和晚期的抗纤维化治疗以及不同作用机制和靶点药物的联合应用可能是未来改善胆汁淤积性肝病治疗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