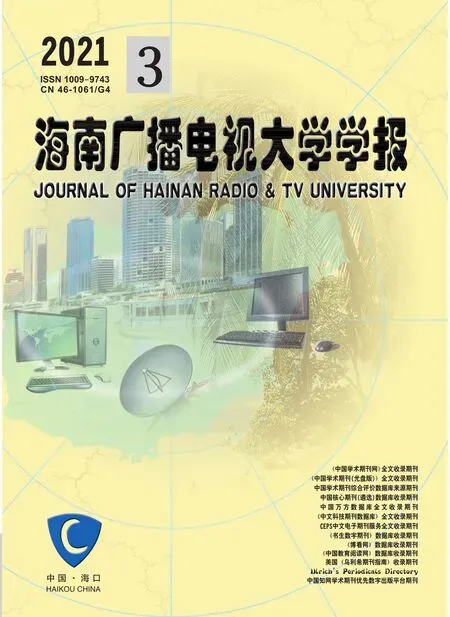上海公共租界苦役制度考察
李一枝
(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 审判管理办公室,浙江 龙游 324400)
一、问题的提出
上海公共租界发展过程中,由西方引入的制度如苦役等不仅在租界内得到良好实行,而且能由租界及华界,进而推动了上海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法制近代化发展。一般来说,从西方引进的制度尽管不能完全“拿来主义”,但进行本土化改造后都能得到长久的应用。但苦役制度实施了一段时间即告废止,这一现象令人费解。苦役制度到底是何种刑罚?与中国古代劳役制是否存在联系?若存在联系,则其具备了思想上和制度上的适用基础,但为何仍受到排斥?若完全相异,则为何引入租界,又为何施行一段时间后消失?
针对公共租界内苦役制度的施行这一专题,在往常租界法制研究中并不占很大比重,就笔者查阅到的内容来看,散见于各类著作。
曾任会审公廨陪审官的郭泰纳夫在其《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中谈论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受案范围和处罚权时对苦役有所提及,夸赞了苦役在惩罚和预防犯罪方面的良好作用,通过英国副领事阿查理(Chaloner Alabaster)的备忘录以及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对苦役的存废过程有简单阐述。杨湘钧的《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将苦役作为阐述华洋司法权力及权力关系的变化的面向之一进行了简单讨论,紧接着在谈及权力关系变迁部分时对与苦役制度紧密相关的戴中其案件的始末进行了介绍,整理了案件争议点并进行了评析。洪佳期在其著作《上海会审公廨审判研究》中论及戴中其案件时也对苦役有所涉及。姚远在其著作《上海租界与租界法权》中以戴中其案为切入点谈租界内法权争夺问题。可以看出,尽管苦役是戴中其案件的重点,但对此案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借此反映理事衙门时期公共租界司法运行情况:中外之间的冲突一直未停止,在权力博弈之下,松散的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不能处理日益复杂的情况,从而推动了会审公廨的诞生。其他的例如:马长林的《上海的租界》、蒯世勋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记载上海租界情况的书籍中也会在写到理事衙门或会审公廨时提及苦役,但篇幅不长。较之其他著作,史梅定主编的《上海租界志》对苦役的介绍更加详细,但未对苦役制度进行十分完整的梳理。专文对苦役制度进行研究的是马长林的《1864-1870年间上海公共租界苦役制考察》,其在文中理清了苦役制度发展的脉络,对其废止原因从经济、人道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但通篇侧重于社会史角度,并未从法律史角度阐述。
本文拟通过对租界内苦役制度的发展过程进行考察,了解其存废的原因及其价值,从中能窥探公共租界内华洋势力博弈情状以及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
二、西方苦役制度的引入
公共租界从一隅之地发展为一块“飞地”,为保证其管理,无论是在各项设施建设上还是制度构建方面都更倾向于直接引入西方已经发展成熟并长期适用的内容,苦役制度亦是如此。
(一)公共租界内引入苦役的原因
1845年《土地章程》签订以后,外国人在上海有了独立的居住区,但是租界初始规模较小,即使有华人,大多数也是“守份之农民,自不至于领团以重大之困难,即或有紧要案件,华人直接入城,向上海县署控告,以求昭雪,而领团毫不知情,亦在意中。”(1)夏晋麟编著:《上海租界问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7-38页。换言之,在租界内的华人仍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未有所例外。因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及太平军的几次战事影响,为逃避战祸,华人大量涌入租界,短期内租界内人数骤增,打破了以往华洋分居的局面,华洋杂居逐渐显现规模。华洋藩篱解体一方面为租界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华人入居租界,各类案件迭起,使得租界内秩序混乱,治安日趋复杂。纠纷不仅存在于华人之间,还存在于华洋之间。如何惩治租界内华人犯罪,用何种手段方式才能行之有效等问题成了租界内外方管理人员所要慎重思量的内容。
外方将苦役制引入公共租界内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租界“市政”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租界从“华洋分居”逐步走向“华洋共居”、“华洋杂居”,此时上海的市政建设也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近代上海英租界内的工部局,设立之初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租界内的道路建设。1852年,英租界内道路用地面积占租界总面积的14.2%;随着租界面积扩大,租界当局加紧修筑道路,到1866年,新形成的公共租界内道路用地面积迅速上升,占到了总面积的23%。(2)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73页。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租界道路已经发展到开埠初的两倍以上。道路建设除了需要资金外,劳力必不可少。而工部局最初支持推行苦役制度,就是希望通过利用苦役犯的体力价值,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1862年工部局道路检查员汇报了他的工作并声称,“他无法取得足够的苦力以继续开展手头上的公共工程”。于是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对目前付给苦力的工资额进行一次调查,并查明通过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否可取得足够的苦力人数”。(3)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这就说明当时工部局工程建设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而苦役犯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失。
2.理事衙门的有限处罚权问题。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最大的处罚权是笞杖一百下,枷十四天以下,不超过十四天的苦役,监禁,罚金和驱逐。阿查理备忘录中指出“如果审理中的案件表明,罪行应予以重判,这个衙门就要将之移送给知县审判。未经知县二审,理事衙门无权判处一天的监禁,而且,囚犯还必须投入中国监狱”。(4)[俄]郭泰纳夫:《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朱华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62-63页。在刑事案件方面,理事衙门只能就判罚苦役自行决定,而其他的“只能就应处的刑罚提出建议,判决须经知县的二审才能生效”(5)[俄]郭泰纳夫:《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朱华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加之外方一直对笞杖、枷刑的非人道主义颇有微词,判罚苦役等在处罚权范围内进行囚犯管理的操作在说法上更让人无可指摘,这或也是促进理事衙门判罚苦役的原因之一。
3.维护租界治安的现实考虑。阿查理毫不掩饰对苦役的夸赞,“它的遏制效力最为明显”(6)[俄]郭泰纳夫:《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朱华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相较于其他刑罚,苦役能“让罪犯在同伙前丢人现眼,从而使他们不敢步其后尘”,因为罪犯“对被送往城里受笞杖满不在乎,他们确信,即使不能以贿赂得免,给行刑者一点小费总能让行刑变成一场闹剧”,但是他们“害怕这个大庭广众下的处罚和被逐离租界”。华人仆役一旦被判处苦役,就很有可能“离开他供职之处”。(7)[俄]郭泰纳夫:《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朱华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这些看法或许是基于推广苦役适用的初衷而有些夸大其辞,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苦役的施行明确性和不可转圜,在对传统官府威势的恐惧之外,租界内的华人对法津,或者说更多的是对西方法律文化有了具象的认知。自从苦役施行以后,租界内华人对法律的服从不仅仅只是威吓下的敬畏,相反逐渐地产生了福柯所构想的“规训”力量。
(二)租界内苦役历史追溯
因公共租界机构设置沿用英国模式,主事人员也多为英国人,而苦役制度的适用也是在英方主导下推动的,故而在讨论租界内苦役概念界定时主要与英国相关刑罚进行比较分析。
劳役刑(penal servitude)与苦役名称最为相近,也是在各类研究中被提及最多的。在西方刑罚史中,劳役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优士丁尼时期的劳役刑主要为三种,按其刑罚由轻到重分别是公共劳役、矿场劳役与矿坑苦役。公共劳役分为有期限的劳役与永久劳役。矿场劳役与矿坑苦役都是无期刑,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镣铐。(8)张瑜毅:《罗马帝政时期刑罚体系初探》,《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26页。这一时期的劳役刑是剥夺自由,使其沦为奴役状态的一种处罚,带有强烈的奴隶社会的印记。起初,在英国并不存在劳役刑,1776年议会通过法案授权政府对那些原来处以流放的犯人实行劳动惩罚,主要是在泰晤士河航道上从事清洁与修理工作。(9)程汉大,李培锋:《英国司法制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0页。这就是后来说的囚船制度。这一制度虽于1857年被废止,但使得人们逐渐习惯劳役式监禁是一种恰当的犯罪惩罚方式。劳役刑正式被引入英国是在1853年,它可以由有权机关决定在任何地点执行,其刑期与流刑刑期有关,但短于流刑的刑期,最低刑期为3年,且不得赦免。1857年的法令使劳役刑的适用更为明确:在监狱里隔离囚禁;监狱工场集体劳动;凭特许证予以释放。
然而,与“苦役”中文名称意思相近的另一刑罚:服劳役(impressment),即社区服务刑的雏形,在英国出现的更早。这种刑罚措施最早见诸于1597年的《伊丽莎白流浪条例》(the Elizabethan Vagabonds Act)(10)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在17世纪,作为罚金违约拘禁刑(default detention)被引入后,逐渐成为死刑、流放刑、监禁刑的替代刑。现今的社会服务刑与过去的服劳役或“强制劳动”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即二者的适用都须得到被定罪人的同意。(11)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根据《上海新报》所记载的案例来看,租界内所适用的苦役(hard labor)(12)英译参考杨湘钧在书中的介绍,具体见杨湘钧:《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在未有确定的管理章程前,服刑时间至多为一月,与传统劳役刑(penal servitude)甚至是近代以后在英国适用的劳役刑相比时间都更短。尽管就服刑时间而言,租界内苦役刑与服劳役(impressment)最为相近,但在租界内适用苦役刑并不需要得到被定罪人的同意。故而笔者更倾向于认定租界内所适用的苦役刑是在西方劳役刑基础上减轻惩罚力度的一种强制劳动类刑罚,可以由有权机关决定在任何地点执行,但多被罚做租界内市政工程劳务。同时,与英国劳役刑不同的是,租界内苦役犯人并不由监狱进行管理,而是受工部局监管。(13)据1872年6月17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中对监狱划为工部局管理的问题讨论可知,此时工部局与监狱仍是独立的两个机构,由此笔者推断之前两者也是平行独立的两个机构。具体参见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53页。
此外,笔者在查阅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的过程中发现在1872年以后会议记录中也出现过“苦役”一词,但这里的“苦役”是否依旧是之前施行的苦役制仍待商榷。从官方通报中看,苦役制度在1870年3月被废除了(14)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尽管在后两年内时而被提及,但始终未能重新恢复使用。而从刑罚实际施行的情形来看,1872年后所记载的“苦役”囚犯是有工资的(15)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40页。,但之前被判服苦役的囚犯只是提供衣食,并未有额外工资记录。加之1872年以后的“苦役”囚犯是在监狱内强制劳动,这一点也与以前的苦役犯是进行市政建设方面的强制劳动,且是在室外服刑,不拘于监狱中的情况不同,因此笔者认为两者应属于不同刑罚。
由此可知,本文所要讨论的苦役刑是在西方传统劳役刑基础上进行调整后才在租界内使用的一种刑罚,其实施监管机构为工部局,公共租界的监狱并不参与苦役犯人的收押与监管。至于其存在的时间段大致在1865年至1872年间,1872年之后“苦役”并不包含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三)苦役制度的确立
据英国外交公报记载,仅1855年,由英国领事署审处的华人案件就达500余起。1856年,驻沪领事团规定,在租界中被捕,在英美领事法庭或法国违警罪裁判所预审时查有确切证据的华人,均须送交上海地方官府审判。(16)《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如果按照这个规定,将华人罪犯移交给上海知县,那么在此之前就需要准备好相关材料文本,而英美领事馆和工部局一直以来就存在人手不够的问题,这些机关并无充足的时间和人员进行文书工作,承包给第三方又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但是,对这些违法行为又必须进行处罚,于是才有了罗伯逊“判处或轻或重的筑路劳动”(17)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89页。的建议。
尽管这种针对华人罪犯的处罚方式已得到知县的同意,在实际上罗伯逊及其后任可能也作出了一些这样的判决,但在此时苦役作为一项新的处罚方式还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只能看作是华洋双方的一种临时性约定。(18)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9页。
1864年5月1日由上海道台应宝时委派同知陈宝渠为首任审判官,与英国领事组成混合法庭,这一混合法庭即之后所称的“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根据之前的商议内容,理事衙门专门处理公共租界内以英、美等国侨民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民刑事案件。参考《上海新报》所载案例,其开始刊登会审案例是在第333期,第337期有罚苦工的记录,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载判决刑罚多为笞杖、警告训诫(报上用语为“斥释”)和罚款,苦工(苦役)并不常见。
1964年10月初,工部局董事会会议首次作出决议:“允许雇佣被理事衙门判处服苦役的华人囚犯在巡捕的监督下从事公共工程。”(19)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88页。1865年7月,工部局又提出将囚犯判处苦役的主张。9月,工部局警备委员会建议,理事衙门的外国陪审官将交由华官讯办的华籍犯人拘押在租界服苦役,对此,工部局、上海知县和上海道台都表示同意。(20)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此后,《上海新报》所载案例中较为频繁地出现了“罚苦工”的字眼。首次出现囚犯服苦役的书面记载是在1865年10月10日召开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中:“苦役犯 根据警备委员会的建议,已开始尝试利用这种劳动力,但迄今为止,试验尚未十分成功。”(21)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18页。综上可知,1864年底至1865年底这段时间内苦役尚处于初始试用阶段。
三、苦役的实施
一般来说,一项新制度想要留存必然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和适应。而直接从西方引入的苦役制度因为有别于中国传统,加之租界内各方势力的碰撞对抗,其本土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一)苦役规范化
起初判罚苦役并无明确的条件限制,只是明确表明其只适用于租界内的华人。从1865年9月在押犯报表(22)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 519页。中可以看出除了盗窃、行为不端、酗酒等罪行之外,砍伤、伤害与殴打等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也会被判服苦役,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被判做苦工的大多是那些轻度的、不太容易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23)参考马长林在《1864-1870年间上海公共租界苦役制考察》中通过对《上海新报》刊登的案例进行整理得出此结论。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3-34页。此外,判罚苦役的时间并不确定。最初理事衙门判处的罚工,多是一天、两天,甚至有罚做苦工一个小时的,如1864年5月11日一名叫徐和尚的华人因酗酒游荡被理事衙门判罚小工一点钟。(24)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4页。后来罚做苦工的时间有所延长,可是为何延长时间、延长标准等尚无定数。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苦役制度只是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并不存在正式的文件章程对其进行规范,其真正步入正轨是在戴中其案件(25)大致案情始末:1865年10月26日,华人戴中其与高福唐收买了工部局董事汉璧礼所有的五把门锁赃物,因此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判服两个月的苦役。在服苦役的期间,两人双双罹病,戴中其疑因身体虚弱,加上受巡捕凌虐,虽经送医治疗,仍告不治。之后,高福唐和戴中其之子戴昌富一起投诉至上海县衙。围绕案件的争议点主要是理事衙门的管辖权和刑罚执行问题以及苦役的合法性、残酷与否的问题。具体情况参见《1865年11月8日道台致领事函》,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页。发生之后。1865年11月4日,英国领事温思达、副领事阿查理、美国总领事西华、道台应宝时及翻译秦右就苦役问题进行了协商,确定了制度规定的相应重点。(26)具体内容参见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31页。不久之后,正式规则顺利出台。关于规范苦役制度的文本,笔者查看了1865年12月中旬英美领事和道台批准的《苦工章程》以及工部局于1866年1月制定《苦役犯人惩处规则》两版,就内容来说二者并无二致,只因记录主体以及留存情况而在名称和时间上有所出入。中外方协商制定了相关章程以明确苦役制度的具体内容,即大致在1866年以后苦役制度有了可以参照遵循的章程规范,而不像之前全赖法官裁量性判决以及刑罚执行者的好恶实施,至少在明面上看来更加规范化。
苦役的适用范围及限制如下:
1.苦役适用对象
只适用于华人罪犯。凡18岁以下、45岁以上的男犯及女犯不得处以苦役。如在1866年5月3日审理的一起非法勒索的案件中,因为两个被告均年龄过大不适合被判处苦役,最后一个被判处监禁14天,一个被判处笞刑100下并枷号14天。(27)具体案件情形参见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560页。
2.苦役适用案件
犯有抢劫、偷盗、窝赃、勒索等罪行的犯人才可处以苦役,其他罪行判处苦役应首先经过上海道台同意;所有苦役犯人的情况应随时向上海道台呈报,上海道台有权要求会审公廨改判其他惩罚。(28)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后半句是在上海道台的坚持下添加的,但多数时候沦为一纸空文。
3.苦役服刑时间及相关管理
服苦役的时间为三日至三个月,初犯者判处苦役的时间不得超过14天。(29)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这一规定将之前判罚时间较为随意的现象加以明确制止。对如何管理苦役犯人也有所规定:工部局卫生官每天对苦役犯人进行检查,未经许可不得判处苦役;犯人劳动时间为夏季上午6~10时,下午4~6时,冬季为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天气极端恶劣时不得服苦役;雇佣华人巡士在外人监督下看管犯人,巡士不得殴打虐待犯人等。规则还对苦役犯人的伙食、衣被和卧具标准作出具体规定。(30)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303页。例如“各犯每日给予三餐,早间给煮熟米饭四两,小菜一两,午间给米饭半斤,小菜二两,夜间给米饭四两,小菜一两,间加给鱼肉各二两,随时有淡茶疗渴”(31)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9页。等。
(三)苦役适用情况
鉴于相关史料中只记载了租界内道路修缮情况,并未涉及苦役犯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故在此部分仅谈论适用苦役后租界内社会治安情况。
为更加明显地展示苦役适用的效果,笔者将从租界巡捕房拘捕情况出发进行分析。但由于资料限制,笔者只摘录整理了1865年6月至1868年3月的情况(见表1)。就1865年11月而言比同年前一个月拘捕总人数减少了44人。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中,委员会也指出这一现象“不得不认为这部分是由于害怕被判用铁链锁在一起服苦役之故”。(32)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9页。

表1 1865年6月-1868年3月拘捕人数、判服苦役人数统计表(33) 根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及1865年10月-1867年2月华人罪犯拘押和判处苦役情况表(马长林:《1864-1870年间上海公共租界苦役制考察》,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2页。)数据整理校正所得。
此外,在对苦役有连续、明确书面记载的1866-1868年两年内,拘捕华人人数和拘捕总人数有所下降(见表2),虽然不能将犯罪率降低与苦役的施行完全划上等号,但也不能忽视苦役在这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表2 1866-1867年与1867-1868年拘捕华人和总人数对比表(34) 根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及1865年10月-1867年2月华人罪犯拘押和判处苦役情况表(马长林:《1864-1870年间上海公共租界苦役制考察》,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2页。)数据整理校正所得。
尽管苦役在惩治犯罪、维护治安方面有所效用,但也可发现施行苦役后犯罪率并无大幅度的下降趋势,苦役的效果并不如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以及相关外方人员备忘录中夸赞的那样完美。而且从实际案件判罚和执行来看,苦役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按照章程文本规定实施,制度规定和司法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罅隙。
四、苦役的争议与废止
中外双方对苦役制度始终持不同意见,但未有官方层面的直接交涉,直到1865年戴中其案件产生,双方才开始重新正视苦役制的存废问题。
中方对苦役抵制的声音主要是从官方层面发出的,民间层面对强制劳动这一点并未有太过激烈的反抗,只是对“施行苦役制损害了道义和民族自尊”这一点颇有微词。据《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如果是中国人之间产生纠纷,就应由中国地方当局来解决,对华人的一切惩罚也应该由中国官厅执行。但现在“所有华人囚犯都被外国官员判服苦役,而且案情从不报告知县。在中国的法典中没有像苦役这样的惩罚,并且用外国法典中国的惩罚办法来惩罚人,这也不符合条约的精神。因此,应该永远停止让华人服英国的苦役刑法,假如要受惩罚的话,应送交知县衙门实施。”(35)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页。看得出来,中方抵制苦役制度时给出的主要原因是其认为苦役是一种外来刑罚,不包含在中国刑罚体系内。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基本上是以肉体刑为主的刑事处罚,即使某种处罚中也带有劳役的内容,但劳役并未成为主刑之一。因此在租界内出现的苦役制相对于《大清律例》中所记载的刑事处罚(36)《大清律例》规定的刑罚种类:笞、杖、徒、流、死。来说的确是一种新的处罚方式。
刑罚方式是否存在与其是否能被接受并不完全等同,并且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服刑”一说也并不只是对自由的剥夺。《唐六典》中就有对判徒刑的犯人同时需要其进行劳作的操作。这些规定延续到清代,在《大清律例》中也可查。可见在传统律法中尽管不存在将强制劳动作为主刑或附加刑的情况,但强制囚犯进行劳动的做法早已有之,中方政府“苦役刑不是中国固有刑罚所以不能继续适用”的说法就有些立不住脚。这一理由背后实际潜藏着中方对租界内审判及刑罚执行权的争夺,但这是否仅仅只是司法主权争夺的问题呢?尽管有条约限制,对于外方的越界,中方政府是否真的无法与之颉颃?笔者认为不尽然。上海恰逢战乱之时,司法被忽略了,必要的警察管制是由条约各国的领事像警官那样施行的。(37)[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继英国在管辖上的延伸,美国领事也扩展了其管辖权。因中方无暇管理,对华人管辖权的攫取似乎事出有因,但在中方政府恢复对司法的控制之后,外方依旧保持原状,甚至做法更为出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政府依旧对管辖权有所退让和放弃,可见其逃避和消极怠工的心理,那么为何却紧抓住苦役这一点不放?
与以往历朝历代一样,官员贪贿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但清代存在“陋规”收费一说。清代地方政府靠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灰暗的“陋规”方式建立其财政岁入,州县官和衙门职员们也多以“陋规”方式取得薪水,这些途径都是私人的、非正式的途径。“陋规”与贿赂或其他形式的贪污不同,因为陋规是在法律的默许之内的,而贪贿是法律禁止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政府对陋规收费的容忍及制度上缺乏控制,意味着整个陋规收费之事几乎都是由州县官们自己安排。(38)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怎样算贪贿,怎样算陋规,不过是看地方官员如何进行自我包装。至于现实中租界内犯罪的华人通过行贿减轻惩罚的情况屡见不鲜,“收赃者对被送往城里受笞杖满不在乎,他们确信,即使不能以贿赂得免,给行刑者一点小费总能让行刑变成一场闹剧。”(39)[俄]郭泰纳夫:《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朱华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由此可知,对苦役废止的坚持,不仅是“中国大员”对华人管辖权的争夺,更多的是“他们的走卒”对保留小费收入的努力。
外方决定放弃施行苦役制度,也并非“上海道台应宝时与英领事温思达多次交涉,外国领事和工部局不得不让步”(40)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的结果。推行苦役制除了特定的条件之外,需要大量成本,具体来说,就是在罪犯的待遇以及劳动强度方面都必须考虑维持罪犯的人道尊严,否则就等于完全恢复西方奴隶社会时期的苦役制,这当然也非罗伯逊等人的初衷。(41)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3页。在协商过程中出台的有关苦役犯管理的章程足以说明这一点。为强化管理,自然是要支出一大笔费用。委员会多次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中对苦役费用问题进行讨论,在商讨理事衙门所得罚金是否可转为苦役犯管理及生活费用以外,还寄希望于华方政府仍能提供资金支持,毕竟被判服苦役的全是华人。但这些诉求都未得到满足。所以在震慑犯罪、获取劳力和节省开支各方权衡中,工部局最终倾向于节省开支,由此直接导致了苦役制的取消。
五、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工作布局、重点任务,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就是要对相关立法、司法中不合时宜的制度进行有效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必然要借鉴国外优秀治理经验,而近代上海租界内情况虽与现今相差甚多,但从租界内对苦役这一外来制度的相关处理方式中我们也能得到一定的启示。
首先,不能强硬推行。苦役制度由引入实施到最终被废止这一过程历时较短,个中缘由不能简单论之,但一项制度的存废不是某一方自说自话、强硬推动即可,公共租界内苦役制的发展变化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要综合考量多方因素。通过具体的审判及刑罚执行情况可以看出中方对理事衙门权力的不满和外籍陪审官企图扩展权力等矛盾冲突。而除了各方势力博弈之外,废止苦役制度更是对此项制度实施的成本因素的考量。虽然现在并无中外方之间的权力博弈,但各个部门之间、财政预算情况等也需要进行均衡考察,不能顾此失彼。
最后,需结合实际国情进行改造。苦役作为从西方引入租界的一项刑罚制度,并未完全照搬西方奴隶社会时期所施行的苦役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自行调整刑罚的时间、惩罚力度、实施方式,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所以苦役在解决上海租界市政建设的劳力缺失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租界内的社会稳定。
总之,外来制度的本土化之路任重道远,单纯的“拿来主义”并不能一劳永逸,需要对其进行有效改造才能使其发挥最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