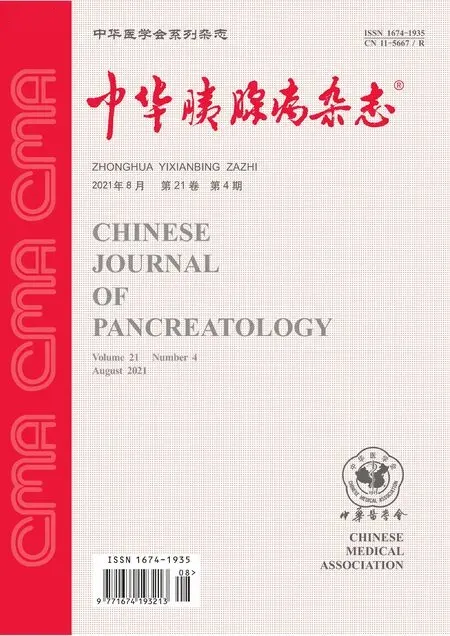重症急性胰腺炎第二个“死亡高峰”救治一例
白亦焘 马郖 阿永俊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一病区,昆明 650301
【提要】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发病急骤、病情危重、病理生理过程复杂,从而导致治疗决策困难。SPA前期以器官支持治疗为主,后期探索最佳手术时机。第二个“死亡高峰”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挑战,选择对其进行外科干预的时机以及方式尤为重要,尽管创伤递进式理论为基础治疗方式已经广泛应用,但SAP病死率仍高,本文通过总结分析一例SAP患者的治疗经过,旨在讨论外科干预时机的选择及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重要性。
患者女性,70岁。因“高脂饮食后出现脐周及右上腹胀痛,并向左肩及腰背部放射”,于当地医院急诊住院治疗。入院检查:血淀粉酶2 902 U/L,尿淀粉酶11 092 U/L,血钙1.67 mmol/L。腹部超声及CT提示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2 d后患者出现呼之不应,经急诊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后转入ICU行常规抗感染、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等治疗。多次复查CT提示胰腺周围脓肿形成,多次行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术(PCD),但引流效果欠佳。引流液培养为屎肠球菌,更换抗生素万古霉素+泰能,但感染控制欠佳,2个月后转入我院进一步治疗。入院体检:体温 38.9℃,脉搏 118次/min,呼吸 34次/min,血压 94/47 mmHg(1 mmHg=0.133kPa)。营养差,神志清,无黄染、皮疹及皮下瘀点瘀斑,呼吸急促,腹部高度膨隆,全腹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左右侧腹部可见两根腹腔引流管,引流出浑浊棕褐色液体共约70 ml,双下肢可见凹性水肿。实验室检查:WBC 19.2×109/L,Hb 91 g/L,PLT 74×109/L,ALT 212 U/L,AST 165 U/L,TBil 42.2 μmol/L,ABL 22.5 g/L,PCT>100 μg/L,Cr 271 mmol/L。腹部CT提示SAP并发坏死物包裹(WOPN);胆囊结石合并急性胆囊炎;双侧胸腔积液合并肺部感染。入院诊断:(1)SAP;(2)MODS;(3)高脂血症;(4)低蛋白血症;(5)急性胆囊炎并胆囊结石;(6)肺部感染;(7)胸腔积液。
患者转入ICU给予强化治疗,即给予液体复苏、器官功能保护、积极肠内营养、呼吸机辅助呼吸及CRRT等。入院第1~7天高热,体温39.1~40.5℃,膀胱测压正常,腹部膨隆,以中上腹部为主,考虑局部腹腔间隔室综合征。予B超引导下更换双腔套管持续冲洗及负压引流。引流液培养检出鲍曼不动杆菌、洋葱博克霍尔德菌,予头孢哌酮舒巴坦钠+左氧氟沙星+多黏菌素B治疗后体温降至38.6℃。入院第8~14天,每日腹泻10余次,经胃管注入蒙脱石散+肠道菌群制剂后改善;痰培养检出白假丝酵母菌,停多粘菌素B改为氟康唑+替加环素,间断予局麻下行纤维支气管镜气道内肺泡灌洗、吸引,以改善ICU获得性肌无力。第15天行胰胃间隙包裹性积液穿刺引流,引出黄绿色液体1 500 ml,考虑上消化道瘘,予通畅引流的同时继续加强肠内高营养治疗。第16~29天,引流液培养检出大肠埃希菌+全耐鲍曼不动杆菌,停替加环素改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在体温连续正常5 d后脱呼吸机改面罩氧疗。第30天,患者频繁呕吐咖啡渣样液体500 ml,伴血氧饱和度(SpO2)下降,无法排除消化道瘘所致出血或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故予更换中心静脉导管(CVC)为外周静脉植入的中心静脉导管(PICC),停用低分子量肝素,输血液制品,予氨甲环酸抗纤溶治疗,并给予呼吸机辅助呼吸,抑酸、止血、抑酶等治疗。第31~39天,上消化道出血症状改善;体温降至37.9℃,3次尿培养均阴性,停氟康唑。第40~45天体温复升至39.2℃,引流液培养检出对阿米卡星敏感的阴沟肠杆菌亚种,予加用阿米卡星。第46~61天,血气分析示原发性代谢性碱中毒,遂行胃液充分过滤后经鼻肠管回输;间断进行系统床旁康复治疗。第67天,患者再次呕吐数次后SpO2降至70%,合并误吸并伴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频发室性早搏,予呼吸机辅助,去甲肾上腺素、艾司洛尔、胺碘酮泵注后情况趋于稳定。第68~72天,体温峰值至38.7℃,因引流效果不佳,增加每日双腔套管更换次数,引流液培养检出屎肠球菌,加用万古霉素,体温峰值降至38.0℃。第73~78天体温峰值达39.1℃,痰培养见奇异变形杆菌及全耐鲍曼,停万古霉素改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第79~84天发生感染中毒性休克,予右美托咪定镇静,西地兰、多巴胺强心,艾司洛尔控制心率、减轻应激;引流液培养检出嗜麦芽窄食假单孢菌及对替加环素敏感的鲍曼不动杆菌,予加左氧氟沙星及替加环素。第85~90天脱呼吸机改面罩吸氧,停血管活性及强心药物;血培养检出G-杆菌,但体温低于38.5℃,停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改为复方新诺明,并拔除双侧结肠旁沟双腔套管。第90~100天体温低于38.1℃,气管切开套囊间断放气锻炼呼吸功能;血培养检出溶血葡萄球菌、嗜麦芽窄食假单孢菌,痰培养检出肺炎克雷伯菌亚种,尿培养检出白假丝酵母菌,考虑定植菌且无明显感染发热征象,停全部抗生素。第101~107天拔除鼻肠管后改为能全力口服并辅以流质饮食,拔除气管插管,口服氟西丁、曲唑酮改善情绪障碍,加强床旁康复,包括训练平衡功能、偏瘫肢体综合能力、肌松弛、中低频脉冲电治疗等。CRE筛查提示泛耐药肺炎克雷伯杆菌亚种,继续予持续床旁隔离。第107~130天,双腔套管引流量逐步减少后拔除,血、尿、痰培养连续复检3次均阴性,患者解除隔离。第131~135天复查CT,提示胰腺周围假性囊肿,未见明确混杂密度影。第136天出院。
讨论SAP占AP的15%~20%[1],急性期以SIRS及MOF为主要表现,构成第一个“死亡高峰”,其治疗以加强重症监护、保护器官功能为主;感染期以胰周坏死组织继发感染为主要表现,构成第二个“死亡高峰”,其治疗以控制感染及其相关并发症为主。尽管随着ICU技术的进步,起病初期由SIRS以及MODS导致的病死率已经明显下降,但后期仍高达43%[2],甚至达到总死亡率的70%[3],主要原因为AP后期坏死组织继发感染所致的脓毒血症、消化道瘘以及腹腔相关血管性并发症,如门静脉系统栓塞等[4]。第二个“死亡高峰”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挑战,选择对其进行外科干预的时机以及方式尤为重要。
经过对该患者在外院治疗过程的追溯,明确了该患者患病后即在当地医院进行了系统强化的ICU治疗,包括多器官功能实时监测与保护、腹腔间隔室综合征的监测、SIRS中的液体复苏、呼吸机替代治疗以及CRRT等。也正是由于这些早期技术的应用,使患者平稳地度过了第一个“死亡高峰”,即由SIRS逐渐转变发展为MODS以致于MOF的过程[5]。王春友等[6]研究提示,SAP早期急性胰周液体积聚时,超声引导下腹腔穿刺引流甚至常规手术都将极大增加感染的概率。而胰腺坏死组织引发感染多发生在发病后4周左右,外科手术干预的窗口期为发病后4周,最佳手术时机为发病后4~6周,此期以后手术病死率随发病时间的延长而急剧上升。患者转入我院ICU时已经出现脓毒血症以及MODS,距离发病已两月余,外科手术干预时机已过,贸然行急诊手术清除胰周坏死组织很可能造成“二次打击”,导致术后死亡。因此笔者团队并没有机械地套用升阶梯治疗措施,在给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措施时重点放在每次患者病情趋于稳定时便予积极的生理储备,但均在拟升阶梯治疗时发生意外,进而重返ICU。
然而,笔者发现PCD管形成的窦道孔径随着混杂有胰液的坏死组织溢出的同时逐步被腐蚀扩大,进而为更换更粗型号的PCD管甚至双腔套管创造了条件。同时,笔者摒弃原有单纯依赖PCD管消极引流的弊端,予患者留置双腔套管持续对胰周坏死感染的积聚组织进行冲洗引流。尽管堵管情况时有发生,但凭借良好的团队合作及协作精神,通过改进引流管与窦道的接触角度、调整引流管侧孔的大小以及引流管与腹壁的固定方式,降低了堵管、换管的次数,改善了胰周坏死腔道感染物积聚的局部环境,部分或全部达到了升阶梯治疗中微创手术清除胰周坏死组织的效果。虽然在诊治过程中持续予患者监测膀胱内压力的变化,但因该患者表现为局限性腹腔内高压,即上腹部以及腹膜后高压而下腹部压力升高不明显,从实践中认识到膀胱内压正常时不能彻底排除腹腔间隔室综合征,故在治疗方式选择上,笔者以退为进,积极采取非手术方式治疗,包括反复PCD、镇静镇痛,改善腹壁顺应性,避免在患者全身情况不稳定时手术。
笔者认为,外科治疗SA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SAP后期对感染性并发症的处理。当感染性坏死充分液化并覆以完整包裹时,以PCD为首选;若引流效果不佳,则以外科清创为主进一步干预。近年来,以PCD为首选的创伤递进式治疗理念已得到各大版本指南的认同及推广,但PCD的时机尤为需要关注。不同机构的统计显示PCD的平均建立时间为SAP发病后的9~55 d,差异较大,且对无明显压迫症状及感染倾向的急性胰周液体积聚早期行PCD亦可能加速炎性病灶蔓延[7]。笔者团队通过临床实践,总结出PCD治疗WOPN的适应证为:(1)局限于胰周及小网膜囊的坏死物积聚;(2)腹膜后范围局限的单腔坏死物积聚及脓肿;(3)术后局限的残余脓肿。笔者统计的PCD中位置管时间为SAP发病后22 d。
此外,该患者并发上消化道瘘,可能为胰周感染性坏死组织混杂高浓度胰液后导致引流不畅造成邻近胃肠道腐蚀,或由于感染区域血管栓塞而引起缺血性胃肠壁全层坏死。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多数感染性胰腺坏死引起的上消化道瘘可自然愈合。该患者经过系统评估,考虑到已有鼻空肠管可以进行充分的肠内营养,故在加强营养支持的同时,持续冲洗及负压引流,上消化道瘘经非手术治疗痊愈。该患者病程中肉眼可见的腹腔引流管出血4次、呕血2次、黑便3次,考虑原因多为坏死物脱落所致创面感染性血管破裂渗血、胰胃间隙包裹性坏死所致区域性门脉高压性胃病以及应激性溃疡所致。该患者经过抗凝抗纤溶、腹腔包块穿刺置管引流以及系统性消化性溃疡治疗后,连续出血天数均少于4 d,而每次出血发生前均应用肝素,包括CVC的肝素封管以及抗深静脉血栓形成所用的低分子量肝素皮下注射,且患者血小板在出血前亦有降低趋势,出现是否与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IT)有关仍值得临床探究。
通过相关病例报道以及文献的学习[8-11],结合该病例治疗过程的分析总结,笔者了解到在以创伤递进式理论为基础治疗SAP过程中,单纯PCD可治愈约1/3的感染性胰腺坏死患者,而其他均需在引流基础上行外科清创或直接外科清创方可治愈。笔者团队自2019年10月开始针对收治的SAP患者进行详尽的疾病严重程度、BISAP评分、MCTSI评分系统评估,于急性期遵循目标导向性的治疗原则进行开放性和限制性液体复苏,于演进期进行积极的营养支持和生理储备,对不适宜行PCD的患者于起病后4~6周(中位时间39.6 d)行小切口(脐上正中长5~7 cm切口)剖腹清创置管联合延期灌洗引流术;且“清创”并非单纯将全部坏死组织清除,而是为了防止坏死灶内枯枝样血管结构的破坏以致大出血,处理的关键在于针对感染性积聚坏死物的松动及引流;在坏死腔内放置双腔套管,自术后第4天开始经双腔套管的滴水端缓慢注入生理盐水,引流端接负压吸引,冲洗坏死灶的同时防止引流液播散感染腹腔,也可有效减少局部有毒物质和炎性递质的释放及吸收,之后逐步增加冲洗量直至痊愈。依据现有的统计数据,笔者发现该项术式可以明显缩短患者病程,不仅简化了常规剖腹行胰周坏死组织清除术的步骤,也是升阶梯治疗的重要补充。但当前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由于样本量小、缺乏对照组研究,有待进一步行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对照研究来验证治疗效果。
伴随着“损伤控制”理念的普及,探索实施的创伤递进式手术策略治疗SAP逐步实现了疗效突破。坏死组织的清除技术包括多种视频辅助清创(VAD)手段[12],但手术时机的选择对治疗成功更具里程碑式意义。因此,SAP的治疗,理念大于技术,治疗不可一概而论,亦不可盲目跟风,适时的外科干预应是建立在以MDT为依托、各学科摒弃嫌隙、通力合作的基础上,以期改善SAP的整体治愈情况。鉴于SAP病情的复杂性、个体间的差异性,手术与否以及手术时机的正确把握,对提高SAP治疗效果的地位不容置疑。所以在治疗过程中,遵循个体化治疗原则,把握合适的手术干预时机仍然需要系统、客观的分析及评价[13-14],机械的套用升阶梯治疗理论是不可取的。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