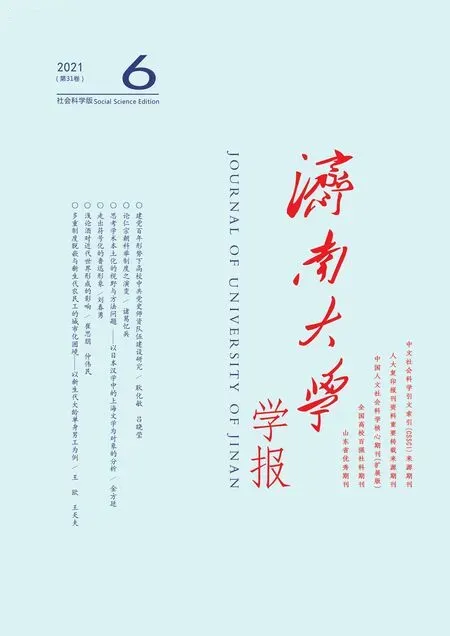韩国的上海文学研究及其“本土化”启示
狄霞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对于韩国而言,上海是一座意义非凡的中国城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成立于上海且得以维持了27年之久,与沪上中国人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1)[韩]李寿成:《透过韩国独立运动看韩中关系与东亚的将来》,《韩国研究论丛》,2000年卷,第111-115页。。上海也是韩人留学的热门城市,涌现了不少作家。据统计,现代来华留学的14位韩人作家中,在上海留学的有9位之多,占总人数的64%。上海是韩国现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都市空间,1920-30年代韩国文学中与上海有关的文章就有90篇之多(2)韩晓:《民国时期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跨体验与文学书写》,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25-67页。。
新世纪以来,韩国学界的上海文学研究渐成热点。近来,韩国汉学家林春城编选了《韩国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一书,收录了闵正基、金良守、金顺珍等十位韩国汉学家的上海文学研究成果,关注的作家主要有韩庆邦、茅盾、张爱玲、蒋光慈、穆时英、师陀、周而复、王安忆、卫慧等,作品有《海上花列传》《子夜》《结婚》《红玫瑰与白玫瑰》《上海的早晨》《长恨歌》《富萍》《上海宝贝》等。林春城对“文学上海”的概念作了拓展与延伸:“文学上海”不仅指通过文学来观看上海,还提示了一种把上海文学作为上海民族志研究文本的可能性。在人类学家看来,民族志是把世界保留在纸面上的一种书写;林春城则指出民族志与文学作品有相似之处,民族志从文学中汲取了讲故事的能力。他以民族志的方法来研究上海文学,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率先展开了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探索。对于韩国学者而言,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上海文学文本,既是一种文学研究,又符合外国人通过文学文本来理解中国的需要。
韩国汉学家的上海文学研究特点鲜明,注重对上海作家及作品的分析,善于文本细读与文化解读。他们对上海文学的研究有一种介于陌生与熟悉、外部与内部之间的独特视角:一方面是外国人,研究上海文学时投入了一种陌生化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用一种外部的眼光来重新观察上海文学;另一方面又普遍具备较高的汉文学素养,以一种亲邻的目光来看待上海文学。他们在材料、视野、方法等方面往往都有创新,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在研究对象方面,韩国汉学家所关注的上海文学作品大都可以作为上海民族志来阅读,体现了韩国学者通过文学研究来深入了解现当代中国的普遍兴趣,也呼应了林春城“文学上海”的理念。从晚清画报、《海上花列传》中呈现的近代上海,到左翼、新感觉派、京派、海派作家所书写的现代上海,再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上海的《上海的早晨》,书写上海外来移民生活的《富萍》与表现上海70后年轻人生活的《上海宝贝》,都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将这些文学文本作为上海民族志来阅读,也为发掘它们的价值提供了新思路。由此可以观察到,韩国汉学家研究上海文学,不仅是为了研究文学,也是为了研究上海、理解中国。他们选择的上海文学研究文本,大多可以成为研究上海民族志的文本。既研究文学,又研究上海乃至中国,这种文化研究的自觉意识也使得他们的上海文学研究自成一家。
在研究视野方面,韩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经常会与韩国、日本的情况作比较,将中国文学纳入整个东亚汉学乃至世界的整体性视野中来研究,往往会有独到的发现。例如,林春城提出了“东亚近现代(East Asian modern)”的概念,认为东亚国家在近现代大都遭遇了西方挑战,但各国的国情不同,选择的道路也不同(3)林春城,刘世钟,高允实,高明;《“民族志”视野与“作为方法的东亚”——林春城、刘世钟教授访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39页。。他从“东亚文化流动”的视角来看中国小说,为解读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金良守通过对韩国作家中国背景小说的深入解读,为我们对过去所知甚少的中韩文人交往发掘了新的史料;朴敏镐在研究中国革命作家蒋光慈时注重分析他与苏俄、朝韩、日本的关系,提示了一种在世界主义的视野下重新认识蒋光慈的可能性。韩国汉学家强烈的东亚意识、开阔的比较视野,值得中国学者学习。
在研究方法方面,韩国汉学家往往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选择一两种最为贴切的理论来加以解读。例如,闵正基用视觉翻译理论来分析晚清画报,金顺珍用女/母性主义理论分析张爱玲小说,林春城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文本中上海“民族志”的书写等,都展现了韩国学人理论联系文本的实力。他们的理论并非直接从欧美借用而来,经过了韩国学人的消化、吸收与提炼,因此解读并不空洞、牵强,往往能够配合文本的解读推陈出新。
不过,一枚硬币总有两面。韩国学人的上海文学研究有鲜明的优点,但毕竟起步较晚,还有精益求精的空间。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如果韩国汉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能注意到以下两点,或许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其一,冷战时期四十多年的隔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国学者的立场、态度与观点,对中国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社会与政治体制较为陌生,认知难免会出现偏差,有时也存在想象的成分。误解源于隔阂,中韩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还需进一步扩大与深化。其二,过去韩国学者受到欧美及日本汉学家的影响较大,主体意识不够强。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反思西方现代性、重估中华文明价值的声音,但仍然比较微弱。
作为中韩交流的先行者,韩国汉学家已经在反思西方现代性、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东亚乃至世界性价值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深受儒家文明熏陶的韩国学者更能理解中国重视和谐与安定的和平主义性质。尽管已经有韩国汉学家指出未来中国在世界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韩国应该积极面对这一趋势,但这样的声音还不够强烈,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之中显得十分微弱。以他们的实力与规模,完全可以形成汉学研究的韩国学派,在国际汉学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东亚各国也应该更加重视自己古代文明的遗产,在文化自信、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当代国际话语体系被欧美国家强势主导,中国话语体系的突围,不仅需要自我主体性的建构,还需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生态和国际公众心理,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优势找到合适的途径。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与海外汉学具有相似之处。前者是中国主动向外部世界言说自我,后者在于海外学人主动来研究中国。两者存在诸多共性,值得深度合作。海外汉学可以就此更了解中国,而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者也可以学习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声音更好地被理解与传播。如果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时不注重中外文化交流,不开放吸收国外优秀的文明成果,这一话语体系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封闭的自说自话,容易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淖。
在近年来的文论反思中,学界已经意识到了过于依赖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发展现实脱节的问题。当代文论研究中存在本土经验总结不够、表达不足、不充分的问题,泛泛之论多于言之有物的中国经验的总结与表达,至今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文学研究的本土化正是对症良药,近年来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文学研究的本土化有助于“避免对异域理论的‘机械使用’和脱离中国问题的‘理论演绎’,加强文学研究对中国现实问题、文学问题的阐释能力,激发文学研究的活力。”(4)王光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研究中国文学既不能盲从于西方理论话语,又要找到一套既适合于解读中国文学文本、能够顺利海外传播的言说方式。在这一意义下,文学研究的本土化亟需与海外汉学对话。与西方以外的海外汉学合作,也是一种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尝试。在韩国汉学家的上海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重视线的交织:西方、韩国、中国的视线交织之下,上海文学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推而言之,韩国汉学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带来的启示主要在以下方面。
其一,韩国汉学启示我们如何应对西方话语体系的霸权。随着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扩张,西方的价值观念与理论话语支配着全世界,形成了文化霸权。在以西方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中,东方处于弱势与边缘的地位,近代东亚各国都不得不学习西方。韩国汉学家虽然以研究中国为主,但也无法拒绝西方话语,这是无需避讳的事实。在西方学术话语、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今天,韩国学者也借鉴了西方的视觉图像、女性主义、文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理论,但他们在理论应用时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注重对文本的细读,文本高于理论。他们研究上海文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通过文学观看上海与中国,将文本置于第一位,在此基础上寻找合适的理论来解读。二是在选择理论的时候,往往并非直接引用某种现成的西方理论,而是综合几种理论并加以融会贯通之后再加以使用。他们对西方理论的化用并不生硬,在实际使用中注意将其转化成为更适用于中国语境的理论,西方色彩较为淡薄。在韩国学者的论文中很少会看到外国人名和理论的堆积,显示了对中国文学文本的尊重。韩国汉学让我们看到,使用外国理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妄自菲薄,忽略自身文化的价值。
其二,韩国学者的研究提醒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有文学的价值,也有人类学的价值;不仅对于中国人有价值,对于外国人也有价值。那些受到外国学者重视,被视为文学人类学文本来研究上海民族志的作品,正是书写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成功之作。通过韩国的学术研究,我们理应反思如何进一步确立“学术本土化话语”的思路和方法等问题。
近邻的便利、文化的相通使得韩国汉学家拥有研究优势,而这种优势正在随着国际学术格局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引人瞩目。新世纪以来,韩国的汉学研究更为开放,更加多样化,研究对象也有所扩大。他们引进了民族主义、“东亚视角”“现代性”反思等,展现了独立自主的研究风格。林春城、闵正基等韩国学者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提示了一种从中国来观看世界的可能性。韩国汉学家的这一尝试也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带来了信心。
不过,海外汉学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关注点往往有其本国背景,中国学者应该注意区分,不可盲目追随、随意套用。在与韩国汉学家合作的同时也应该注意:韩国毕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历史与国情使得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陌生感。与韩国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注重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在与海外汉学的合作中,也应继续保持自己的学术本色。
无论是“井底之蛙”还是“盲人摸象”,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提醒着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理解上海文学,也同样需要来自于外部的眼光与声音。研究中国不仅要从内部出发,也要通过不同的域外文化来观照,多面“镜子”才能照清楚自身。以他者立场思考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自己。韩国学者对上海文学的研究,不仅是一种上海民族志的研究,也是在透过上海看中国,透过中国看世界。韩国汉学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带来了启示:中国文学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理论话语,但更要注重“拿来”之后的吸收与转化;中国学者有史料的优势,也有传统理论的发掘与现代转化方面的不足;与亚洲汉学的合作有助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也有利于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开启新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