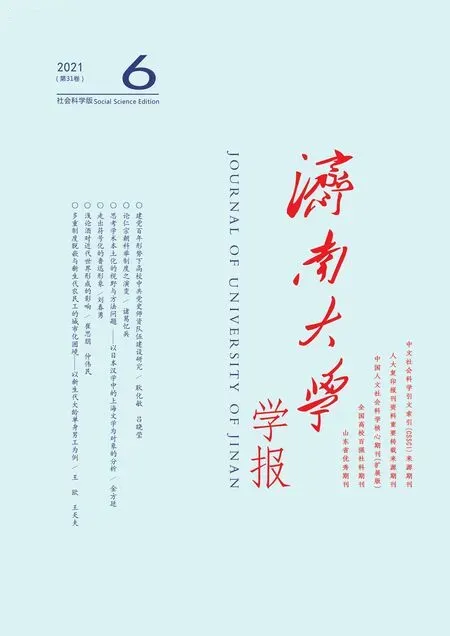思考学术本土化的视野与方法问题
——以日本汉学中的上海文学为对象的分析
金方廷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在世界各地的汉学研究中,日本汉学以其深厚的学术传统和鲜明的学术特色,一直颇受推崇,日本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不仅极富日本特色,且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那么,在今天中国学术面临“本土化”转型的进程中,他国汉学研究能够为我们探索学术主体意识、挖掘本土学术特质带来怎样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来自邻国日本的学术经验不失为一个值得考察和分析的对象,日本的文艺创作对中国都市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1)参看宋波、张璋:《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都市形象研究述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其学术研究在这一方面亦当有胜境。
本文将观察一问题的视线进一步聚焦于“上海文学”这一研究领域,试图从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上海作家与作品和知人论世的实证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讨论日本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说明日本学界在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建构和把握学术主体意识的方法、路径与得失,以此为镜鉴,在比较视野中进一步思考中国学术本土化的视野与方法问题。
围绕上海的研究时常徘徊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之间: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也是一座华洋杂处的“现代化”城市,上海既可以是“中国的上海”,也可以用“世界的上海”来对之加以阐释。这组矛盾在日本汉学家探讨上海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通常日本学者很少将上海文学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他们更倾向于把上海文学视作“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由此构成了日本学者进入上海文学研究时的基本视野。必须承认,日本学者在讨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时具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因为以日本学者的身份研究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为中国文学赋予了一种“世界”的眼光。一方面日本学者善于考察上海文学中源自西方、日本的外来元素,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倾向于从一种更为全球化的、综合的视野来解释上海文学中的作品、作家及现象。
在这类的研究中,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作家和文本频繁成为日本学者尤其关注的对象,上海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被阐释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正如藤井省三所言:“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时,仅停留于国内的一国文学史观是不够充分的,因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往往亦是比较文学研究”(2)藤井省三:《浅谈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与沈杏培博士商榷》,《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从这种带有比较视野的前提出发,对于像陶晶孙、鲁迅、柳雨生、刘呐鸥等与日本有着深入渊源的作家,日本学者不仅挖掘出了大量珍贵的日文文献,他们还时常能给出视角独特的评价。例如,擅长“借助时代语境解决人物的思想源流问题”的北冈正子(3)刘奎:《鲁迅有关国民性思想的起源》,《读书》,2019年第4期。,对鲁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回忆录作了细致的文献整理工作(4)[日]北冈正子,邱香凝:《有关〈上海日报〉记载须藤五百三的“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日本学界还尤为关注经典上海作家对日本文化的接受,此处以鲁迅和张爱玲的相关研究为例,藤井省三就以《呐喊》为例比较了鲁迅与芥川龙之介的写作异同,池上贞子也从张爱玲散文中尝试复原张爱玲对日本文化的阅读与接受(5)参见[日]藤井省三:《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2期;池上贞子:《张爱玲和日本—谈谈她的散文中的几个事实》,《四海》,1997年第1期。;而研究的另一面,则是去观察日本文坛与近代中国文学的关系(6)这方面的研究可举例[日]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上述这一系列研究不仅拓宽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地域和文化边界,也使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中被“边缘化”的作家、作品得到了重新的发现和评价。
在此之外,日本学者对西方文本在中国近代的接受研究或许更值得关注,因为在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中,日本历来是中、西之间重要的“中转站”。众所周知,周氏兄弟的文学译介工作就始自日本时期的留学经历。然而有趣的是,对于西方文学文本在中国本土发生的引介和改编,多位日本研究者却经常给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其中的关键案例是1914年前后在上海市民阶层中广受欢迎的文明戏。由于文明戏的创作者不少人曾留学日本,且许多文明戏剧本也有着自日本转译的文化背景,这种短暂兴盛过的新型戏剧形式由此得到了日本学者的重视。饭塚容的研究通过追溯文明戏从西方源头被译介、转译而后改编为戏剧和电影的过程,详述了文明戏的剧本创作和改写无异于是一种使西方故事“本土化”的过程;但在濑户宏探讨莎士比亚戏剧的中国早期接受问题时,文明戏对西方文本的改编却不被其认可,他更关注西方文本是否得到了准确的引介,因而认为“以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来改编的剧本,不仅无视原作且荒诞滑稽”(7)[日]饭塚容,赵晖:《被搬上银幕的文明戏》,《戏剧艺术》,2006年第1期;[日]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陈凌虹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
可以看到,在日本学者所构筑的“世界文学”视野下,日本经常作为西方文明得以进入上海的某种“中介”出现,但是日本学者对于发生在上海地区的中外文化交流状况,却没有形成确定而统一的价值评价立场,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又尤为敏感于中国的读者、观众如何看待日本—尤其是经过西方“凝视”之后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和展现的日本形象,此处值得一提的典型便是《蝴蝶夫人》。《蝴蝶夫人》是一个具有浓郁东方主义色彩的文本,中村翠的研究从好莱坞电影在上海30年代电影市场的投放情况入手,透过上海观众对日本女性既嘲笑又憧憬的“男性视线”,揭示了中国近代对日本抱有的复杂感情,由此反观施蛰存和穆时英如何以改编的方式拓展了这个文本既有的接受和阐释空间(8)[日]中村翠:《〈蝴蝶夫人〉:从好莱坞电影到施蛰存与穆时英的小说》,《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可见,日本学者的研究力图在一种比较的、世界的视野中去解释中国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由此便揭示了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都市舞台上,上海文学也必然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的“全球”文化语境中生发出来的。这种研究视野暴露出日本学者理解“自我”与“他者”、思考“本土”与“世界”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日本学者将中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时展现出了极强的学术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将日本视作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之“中介”的定位,可在这种明确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定位背后却时常缺乏一种确定的文化价值立场。于是日本学者经常纠结于如何评价西方文本在中国本土的改编和转译问题,究竟是以遵循西方原著为评判的标准,还是应当接纳西方作品在中国遭遇的各种乖离原著的改编?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世界”的视野未必能提供一种确定的价值立场,只是对上海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性”加以考证和描述,仍不足以勾勒出上海文学自身的精神特质。
在研究方法的整体取向上,日本学者尤其擅长文学文献的考索,也更强调将文学文本和作者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来阐释,由此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知人论世”的实证研究方法。正如丸山昇在总结日本鲁迅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取向本身反映着日本汉学对“来自于对中国和日本的距离的自觉”,而回归文学诞生的一手文献及史料,从文本层面完整厘清文学发生时期的材料与状况,这种实证研究的结果势必演变为“不断解明着这些被战后中国的正式文学史评价所忽略的史实”(9)④[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 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第348-349页,第349页。。
必须承认,日本学者所采用的这套以“知人论世”为目的的实证研究方法,确实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且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例,原本日本的鲁迅研究就是日本汉学中积淀颇深的一环,而在几代日本学者的挖掘下,“鲁迅”已经成为与日本战后思想界发生深刻共鸣的精神肖像,生动地反映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汲取外来资源重建主体性的努力。但如果将日本鲁迅研究与上海文学研究相重叠,便会看到,一旦透过“上海”这个限定词来观察日本的鲁迅研究,便出现了大量通过史料考订、文献阐释展开的“实证”研究,其内容和特点大体丸山昇所言,包括了“围绕鲁迅的诸事件,到鲁迅周边的文学家,进而到与鲁迅对立的作家们”④,以上诸种研究内容皆可相应举例言之:丸山昇本人通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细读,为这桩历史公案提供了别样的解读(10)[日]丸山升,孙歌:《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谈晚年鲁迅与冯雪峰》,《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1期。;藤井省三透过缜密的史料考证,复原了鲁迅与刘呐鸥围绕《獾山艳史》、《春蚕》两部电影的隐秘论争(11)[日]藤井省三,燕璐:《鲁迅与刘呐鸥:“战间期”在上海的〈猺山艳史〉〈春蚕〉电影论争》,《现代中文学刊》,2013第1期。;秋吉收的《成仿吾与鲁迅《野草》》一文结合鲁迅与成仿吾在文坛的多次“交手”,证明了鲁迅将最初的新诗冠以“野草”之名,是对“成仿吾的以‘野草’嘲笑拙劣诗作”的回应(12)[日]秋吉收,李慧:《成仿吾与鲁迅〈野草〉》,《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从中可知,日本学者往往试图还原鲁迅在上海时期创作活动的历史语境,来考察鲁迅在上海期间的文学活动,而作为历史语境的“上海”差不多就如鲁迅自己在书信中描述的那样:“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来”(13)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 《书信1927-193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第84页。。显然上海地区的文学场域为鲁迅创作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是将鲁迅研究的时段局限于居住上海时期,又将对鲁迅文学活动的观察限定在上海这个地域范围之内,透过日本学者知人论世的考察方法,揭示了日本“鲁迅像”塑造的另一面:一个时刻处于上海地区复杂文学生产与流通场域中心位置的鲁迅。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及其文学实践并不总是表现为个体在“遭遇”民族困境、异国见闻、时代风波时生成的精神产物,至少在上海这样一个文学生产、出版、流通和评论的中心地带,鲁迅的一系列思想的形成尤其是杂文的撰写,正是在与不同文学派别、文学刊物、文学人士发生“往来”之中被激发出来的,由此展示了一个积极投身世俗生活的、具有鲜明爱恨情仇的鲁迅。其中代田智明的《1934:作为媒介者的鲁迅》可谓其中的代表作(14)[日]代田智明:《1934:作为媒介者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期。,文章将鲁迅在文学刊物编辑、出版和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描述,证明了在上海时“一面是不能动弹……一面又琐事多得很”的鲁迅(15)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1927-193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化身媒介者“有力地介入和撬动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化政治运动和板块构造”(16)李国华:《鲁迅的上海研究与杂文写作》,《文艺研究》,2021年第7期。。
尽管知人论世的实证研究为日本学者所长,但是,“实证”绝不等于纯粹面向“事实”的研究,“实证”的方法恰恰构成了日本学者建立学术自觉意识的起点,也即,从文献考索和材料搜集这些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从头开始梳理出一条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学术路径。至少从上面提到的鲁迅研究的例子来看,日本学者的研究非但使得上海地区作家的个人形象更为丰满,也为今日理解上海文学场域的形成开辟了一条进路。然而,这种研究方法的偏好同样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于“文学”和“历史”的独到理解:文学研究关注的不是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某种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而是通过还原文学诞生的语境,来为某个文本或是某位作者在某一时间内的写作活动提供另一种文学阐释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学者展露出了考证文献、精研史料的专长,而尤为注重与文本细节、作者生活环境有关的文学“外部”信息。在这方面铃木将久的《上海:媒介与语境——读〈子夜〉》一文颇为典型,文章挖掘了小说文本背后的时代语境,阐明了上海作为文学语境的特有现代性景观;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山口守的《巴金与西班牙内战》,这篇论文从“中国文艺界如何看待西班牙内战”一事出发,在一系列围绕国际事件的论争中,探讨了巴金思想转变的前因后果。对日本学者而言,文学阐释的基础更多是“历史”和“外部”的,而不是“理论”或“内部”的。
综上所述,日本学者聚焦上海文学的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都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点。从宏观层面捕捉到的两国在展开上海文学研究时所表现出的无法忽视的差异,或许也可作为探寻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本土化问题的起点。
首先日本学者将上海文学阐释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可在这种开放的、面向世界的视野背后,日本学者却未能就权衡“本土”和“世界”的关系建立起确定的价值指向,徘徊于东、西之间的研究视野反而走向了价值判断的暧昧。因此在处理学术话语本土化的问题情境中,当看到日本学者利用地缘和文化优势积极地开辟出了一种面向“世界”的问题场域和学术话语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如何在一种包容而开放的学术话语生态中,持续地为本土化的学术话语赋予鲜明的文化和价值立场,也即追求开放的视野与坚定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统一,在时刻保持与“他者”交流的开放心态的同时,不断突出“本土”学术的价值寻求和意义坚守。
此外,中、日两国在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上也呈现出颇有意味的差异,且以前文提到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例,尽管中国学者也时常提出“回到历史”的主张,但中国学者更强调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精神传承。中国本土的中国文学研究历来被看作是一种高度“切己”的学问,学者们必须将自己置身于一条确定的文脉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研究无非是对中国文学之精神和思想传统的赓续。于是中国学者习惯采取的实证研究很少纯粹追求一种纯粹客观的、事实性的“历史”,而是需要透过作家的生平、作品、思想,去还原一个具有深厚现实关切的、具有时代精神气格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者在“触摸历史”的同时,更为深入地阐发、继承一种具有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历史”。因而实证研究在中国的学术意义在于挖掘和展现一个能够将研究者自身“参与”其中的、富含精神特质的传统。显然,同样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中、日两国学者在对实证所试图表现的“历史”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
面对像上海文学这样自身包含了丰富外来文化元素的研究对象而言,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不可能仅仅聚焦和突出一种纯粹的“本土”,而是必须在一种能够容纳“世界”的视野中展开,而所谓的“本土性”更多时候指向了问题意识的原点和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同时,透过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比较和剖析可以看到,不同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思想路径,中国本土的上海文学研究始终体现着现代中国学术的精神向度,也是对现代学术文脉的赓续与传承,这是中国学者面向自身文明时所应具备的文化担当。由此可见,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只有当立足于本土的价值取向、文化担当同不拘于本土的世界视野共同达成的一种有机的结合,才能进而缔造出一种开放而有坚守、包容而有传承的本土学术话语——这或许正是借助上海文学研究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去观察日本汉学研究之余,对今日反思、推进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启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