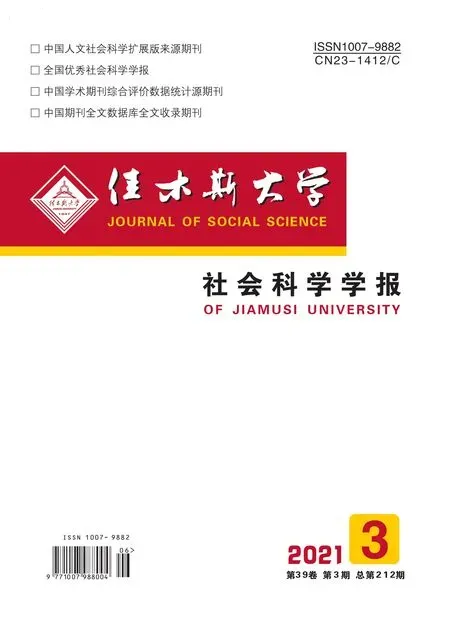迟子建《炖马靴》的叙事艺术*
许青青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作为当代文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一直都保持在高产且高质的水准。她在201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炖马靴》荣获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奖、“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奖,并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度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榜。这部小说在思想意蕴上延续着迟子建对人性光辉的热情赞美,在叙事艺术上的特色也因其短小精悍的形式显得尤为突出。作者将个人的生存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中,在人与人、人与物的牵扯中将“父亲”绝境中的瞬间命运通过小故事的形式缓缓讲述,既不失趣味,又能感人至深。
一、叙述者的双重转换
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提出:“任何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即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这是叙事作品区别于其他艺术和文学种类的最基本的特征”[1]158。《炖马靴》最直观的一个特色,也是该小说整体架构的一个基础,就在于作者对小说叙述者的设计。她综合运用了双重叙述者,一是故事的讲述者——父亲,二是听故事的人同时也是小说文本的叙述者——我。双层嵌套的叙述者“父亲”和“我”属于不同的叙事视角,从而达到了不同的叙事效果。
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把叙事视角分为三种形态:“全知视角(零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2]60。小说《炖马靴》的叙事虽然具有历史节点,但它不着眼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反而将叙事视角转向平凡的个人,以讲故事与听故事两种视角相互转换铺开,通篇以“父亲说”展开回忆性叙述,父亲是讲故事的人也是故事的经历者,这是一种内视角,“我”作为听故事的人,是一种外视角。而小说文本则由“我”转述“父亲”的故事,所以,便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父亲”以内视角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作者包括读者只能根据父亲的口述内容知晓故事局部面貌。这在小说文本中多处可见:文本中一开始就表明故事时间不明;父亲的抗联部队番号不明;后来在与日本兵的周旋过程中,父亲不以“敌人”反而以“敌手”相称;父亲不解释用手帕给敌手蒙面的具体原因;“再说狼得了吃的,就不会过来吃人。他说的吃人,是否包括敌手呢?这个话题我始终没敢问他,直到他辞世”;父亲点篝火,“是不是火葬了敌手?父亲给出的答案总是模棱两可的。”这种内视角的设置便产生了很大的叙事留白,作者和读者都可以根据父亲的叙述展开不同的想象与解读。由此便产生了三种叙事效果:一是作者的想象以其外视角展开叙事,作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与体会展开文本的叙述,这就是小说整体呈现出的叙事效果;二是读者根据父亲的叙述展开自我想象填充,不受作者叙述介入的影响;三是读者根据主观设定后的叙述进行空白填充。小说中“父亲自诩枪法不错,用它打过野猪和狍子,为支队改善伙食”,对此作者加入了自己的猜想“我一直怀疑他有吹嘘的成分,因为在我童年时,看他参加武装部的运动会,父亲投掷的铁饼和铅球,都是不听话的孩子,落脚点不在规定范围内,没一次成绩有效的。”所以根据不同视角的叙述,在此呈现出三种相应的叙事效果,一是认同父亲的说法,父亲作为一名火头军神勇无比的形象再一次拔高;二是相信作者的叙述,父亲的故事加入了自我渲染的成分,也许枪法确实一般般所以才被委任火头军;三是读者根据文本自我解读,或许父亲枪法不差但也不算好,偶有一次打过野猪和狍子,枪法也在退伍后有所生疏,才会出现作者童年时看到的情景。文本中很多作者主观上产生的疑问与情感倾向,都可以产生多重解读效果。产生这种效果的前提是,正由于文本中的两种叙事视角的转换,打破了全知视角的无所不知的确定性限制,阅读期待在文本的无限阅读过程中形成多层次的叙事效果。
二、叙事空间的巧妙设置
“小说空间形式”理论是由美国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最早提出的,他强调以空间干预时间,形成小说空间形式,特征是“事件的前因后果集逻辑顺序被取消。”[3]71-77故事被拆解、破坏,通过拼贴、并置的方式重新组合。国内的空间叙事研究学者龙迪勇认为“小说家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4]15-22空间要素在小说叙事功能中占有重要地位。
迟子建的小说研究中“乡土”要素一直以来都是热议的话题,这是因为她的小说背景基本都设置在北国大地,这便是一个整体上的空间范围,河流森林、雪乡冻土、东北风俗人情都成为这一特殊空间的具体表现。而短篇小说就像一个舞者在精小的圆桌上起舞,空间感常常要胜于时间长度,《炖马靴》作为短篇小说,它的叙事空间感更为显著。小说一开始便弱化了时间感,强化空间感,对于故事发生的时间“父亲记得并不是很清楚,他说年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令,寒冬腊月,祭灶的日子。”这里的时令并不是侧重于时间,反而指向东北雪国大的空间,相较于南方,北方对于寒冬腊月的触感更为强烈。紧接着就将故事发生的空间地点锁定于四道岭小黑山,在此父亲所在的抗联部队与日本守备军进行了激烈交火,故事后半部的空间地点是父亲在雪地森林里与日本兵周旋、战斗。不同于迟子建以往长篇小说广阔的空间,《炖马靴》将人物设置在一个封闭式的雪地森林中,故事的开展、高潮、结束都离不开这个封闭式的空间。这种相对狭小空间的设置,推动了整个叙事进程。正是空间距离小,所以在本来已是优势的交战中,日本兵突然返回,“父亲说他们受到了前后夹击,优势立刻转为劣势。”这样便转入了下一个叙事,也就是“父亲、日本兵、瞎眼狼”之间炖马靴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故事的叙述也离不开这样封闭式的空间,正是因为父亲所在的支队基本活动于头道岭附近的森林中,所以父亲才有机会多次喂养并偶遇瞎眼狼,最后被其所救。在这样封闭式的空间中,环境愈是恶劣,愈是能凸显置身其中的人物心理,父亲身处黑暗雪夜中被追击,对于生的渴望的心理被极度放大,这是人类在绝境中生命意志的极致体现;敌手在同样雪夜森林中,战斗意志由强到弱,最后放弃挣扎,却仍求得最后一点生命的尊严,这同样也是对生命的尊重的一种体现。
除此以外,小说空间叙事也体现了约瑟夫·弗兰克所说的“故事被拆解、破坏,通过拼贴、并置的方式重新组合”的特征。《炖马靴》若以简约的一句话概括,就是父亲讲述的一个抗战故事,但却是一个由“我”转述故事,整个文本时间的长度整体拉长,并且打破了正常的故事时间,以碎片化式的拼接进行叙事。《炖马靴》很明显是由三个故事组成,一个是父亲的抗联支队夜袭日本守备军行动失败,一个是父亲被一个日本军追击,一个是父亲瞎眼狼之间的故事。这三个故事之间本是相互联系牵扯,但是在小说文本叙述中,作者多次加入自己的旁白、想象、回忆中断故事时间,例如父亲在缴了日本兵的枪后,作者随之加入这个小马盖子枪成为父亲俘获母亲芳心的后续。或者将故事中某些问题的原由后置,例如,袭击行动那天日本兵为何突然返回?失败后最终几人从虎口脱险?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并不存在于故事时间中,而是后来抗战胜利之后才知道。也正是这样封闭式的叙事空间才有了将故事进行拆解、拼接的可能性,因为它集中于故事发生的冲突点,不会涉及太多无关的人或物,造成叙事线性混乱。
三、叙事意象的别具匠心
叙事意象是杨义先生首次提炼出的中国叙事学的独特范畴。所谓叙事意象,就是指在叙事作品中承担叙事功能的、浸润着创作主体主观情感,能够引发接受者的审美想象和审美情感,具有一定文化意蕴的特殊的艺术形象。笔者通过文本细读发现《炖马靴》中有两个反复出现的意象——“狼”和“火”。这两个意象,在叙事与审美功能上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含义。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经常能见到诸多动物意象,而且作者信仰万物有灵,所以她笔下动物不只是单纯的动物,常常寄托了作者的思想和愿望。《炖马靴》中“狼”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动物意象,甚至是小说的主角之一。瞎眼狼在故事中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它是故事进展的线索之一,同时也是后半程故事的光环所在。“狼”在一般人心目中往往是“恶”和“背叛”的象征,但是这部小说中的瞎眼狼反而是知恩图报的存在,作者通过瞎眼狼与“父亲”之间的互动,传达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从自然环境角度看,“父亲”不因惯常的偏见“狼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喂不熟的”就对瞎眼狼置之不理,反而“实在心疼”,所以一次次给它投喂骨头,后来“父亲”陷入险境,也是多亏瞎眼狼相救。在这里,“父亲”与“瞎眼狼”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是互救的盟友。在此,迟子建想传达的就是一种朴素的自然观,人只要善待大自然,也会被大自然所善待。正如小说结尾父亲的慨叹:“人呐,得想着给自己的后路,留点骨头!”
“火”也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意象,父亲是一名火头军,行军途中常备火柴,这是部队陷入被动时的救生索。小说中对于火的多次精致描述主要体现在“篝火”上。父亲用“篝火”来烧水、取暖、判断敌手距离、炖马靴充饥。在父亲的逃生之路上,“篝火”在某种意义上对父亲而言是活着,是希望,是光明。所以“父亲说那夜的篝火太美了,将它周围的雪花,映照得像一群金翅的蝴蝶!”对于敌手而言,他希望能葬于篝火,而非被狼吃掉,“篝火”是他保全生命最后一丝尊严的寄托。对敌手而言,“篝火”何尝不也是一种希望与愿景。《炖马靴》延续了迟子建一贯以来温情地展示人性闪耀的创作主题,“狼”与“火”两个意象对于连接叙事和深化主题产生了重要意义。
四、叙事伦理的引人深思
叙事伦理,在西方是伴随各种伦理研究而兴起的一门属于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正式使用“叙事伦理” 这一专业术语的是亚当·桑查瑞·纽顿,他在其著作《叙事伦理》中从两方面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阐述,“一方面指叙事话语的伦理形态:另一方面指使叙事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更加本质和合乎文法的叙事形式。”[5]8-17在国内最早使用“叙事伦理”这一术语的是学者刘小枫,他认为,伦理学有两种,一种是“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从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和培育,从而符合这些理则。而另一种伦理学则是“叙事伦理学”,它不探究一般的伦理法则,而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生命的感觉,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6]3在汉语语境的文学研究中,刘小枫的二元分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视角来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叙事伦理,理性伦理学关注道德的普遍情况,叙事伦理学关注道德的特殊状况,而文学常常就是从特殊叙事中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境况。同时著名人文学者徐岱从美学的角度,在《审美正义论 伦理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中从广义角度阐述了“叙事伦理中的‘叙事’主要包括新闻叙事、历史叙事和艺术叙事三大类,通常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伦理要求。”[7]183前两类可以用真实性和客观化来要求,但是涉及艺术叙事则是更为复杂,徐岱最后给予的观点是“叙事中所谓的‘伦理’,概括地讲也就是一种德性之‘善’的体现。”[7]188但是他存在机械切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界限的嫌疑,因为如若以“叙事功能”来看待文学与历史,二者之间很难是泾渭分明的分割。在涉及历史小说题材时,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关系常常都是论述的重点,祝亚峰认为中国当代历史小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叙事特征,从文学叙述的角度可以将之界定为轻逸与沉重,“沉重是从‘真’的角度看取历史,力主‘真相’的浮现,轻逸则是从‘思’的维面,探寻历史是怎样的和可能呈现的面相。”[8]83
从叙事伦理角度来看待《炖马靴》,它侧重从“轻逸”一面探寻人性在那段特殊历史中可能呈现的面貌。小说讲故事的手法是双重叠加的,父亲讲述他年轻时经历的一次战役,再由“我”转述父亲的故事。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本身就削弱了那段历史的沉重感,甚至在“我”的转述中,对于父亲反复讲述的那场偷袭行动失败被追逐的经历提出质疑和不确定性,甚至最后逐渐厌倦了,也是在模糊历史的“真”。但是对于后半程故事“总能在我心底搅起波澜。我对后半程的故事永不厌倦,就像对一首喜欢的乐曲,不管循环播放多少次,依然爱听。”也就是父亲所经历的“再遇瞎眼狼”、“炖马靴”这两段故事,在这里“我”以及隐藏于后的作者的情感态度乃至小说本身的价值取向才有所显露。父亲是否最后真的如敌手之愿火葬了他,“父亲给出的答案总是模棱两可的。”因为站在民族国家的角度,给敌手最后人间的温暖,让他死得其所,是对战争中死去的战友的背叛。这是民族情感的一种伦理冲突。而在“我”看来最接近答案真相的一次,是父亲说:“唉,让他和那个姑娘的相片一起化成灰,他做鬼也值了吧。”这里没有对于日本兵的痛恨与控诉,原本中日战争时期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与对立,原本沉重特殊的伦理情感在这里融化为对于人性善意的展现。父亲保留了敌手最后生命的尊严,这是父亲对于生命的尊重,是个人的一种超越民族的道德选择。迟子建小说中以中日战争时期为背景的叙事有很多,最典型的是《伪满洲国》,她一方面以客观冷峻的笔墨展示日军侵华给中国底层民众造成的苦难生活,另一方面侧重于战争时期具体的个人经历,所体现的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善恶抉择、道德选择。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之间也是有着伦理诉求——万物有灵且平等。父亲与瞎眼狼互救的故事也是父亲最开始的善意行为带来的善果。且不论现实生活中狼性是善还是恶,但是作为小说叙事故事中的主角之一,作者想讲述的是,即使人类与动物之间有着物种意义上的差别,但是“至善”这一伦理道德却是能够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限制,成为自然界伦理道德中的首选。
抛开宏大的历史背景,《炖马靴》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生命体验,父亲所经历的一次战役,对于日本兵的复杂情感态度,与瞎眼狼之间的互帮互助这段经历不仅让父亲也让“我”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所在。正如刘小枫“叙事伦理学”所说,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生命的感觉,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炖马靴》的文本叙事着眼于父亲年轻时的一次战役经历,父亲所在连队偷袭日军是叙事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承载作者情感价值表达的一部分,而是后半部分父亲与日本兵、瞎眼狼之间的牵连才是文本的主体,同时也是作者思想情感表达的载体,父亲与日本兵之间的民族情感伦理的道德选择,与瞎眼狼之间的善意互救,在这种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营构的背后,体现的是迟子建个人的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也就是一种人性之善的选择,与徐岱的叙事伦理“德性之善”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契合。这种叙事看似围绕个人命运,实际上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民族国家之间,应该以怎样的情感态度面对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又应该以怎样的原则和谐相处?迟子建通过这部短篇小说传递出她的情感态度,即万物有灵且平等,需善待生命。
短篇小说就像一个舞者在小小的圆桌上翩翩起舞,跳好很难。迟子建笔下的《炖马靴》则是通过叙述者、叙事空间、叙事意象、叙事伦理四个支撑点,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时间上遥远却又发人深省的故事。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它一方面体现了迟子建作为一个小说家在短篇上日臻成熟的创作艺术,另一方面也延续着迟子建一直以来的文学理念,即绝境中不失希望与温情,万物有灵且平等的人道主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