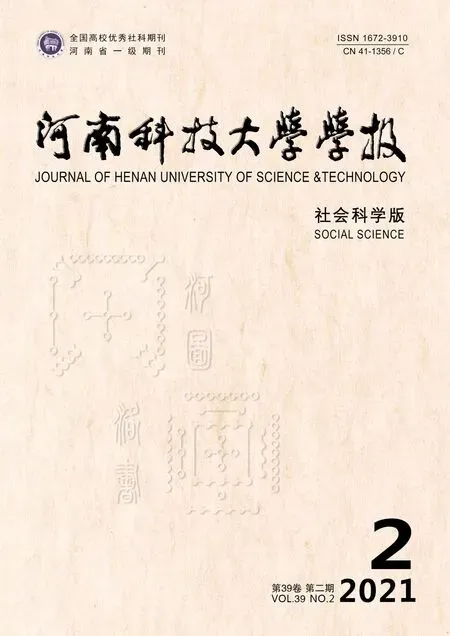论冯沅君“爱史”写作的叙事特点
——以《隔绝》《隔绝之后》《旅行》为中心
金方廷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一篇恋人絮语就是由欲望、想象和心迹表白所交织成的。”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
与其漫长的学术生涯相比,冯沅君的文学创作生涯不可谓不短暂。其创作年代主要集中在1923—1926年期间,五四运动之后,她便退出文坛,与丈夫陆侃如潜心于学术研究。[1]冯沅君小说的内容,一般局限于展现“五四”青年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主题。据文学史家考证,这些爱情小说主要取材自冯沅君表姐的情感遭遇[2],甚至早有研究者指出,冯沅君以自己目睹的现实题材,杂糅进文学创作当中,“将之转换成一个完整的‘五四’式爱情故事”,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五四’青年爱史三部曲”[2]。
如果说《隔绝》《隔绝之后》和《旅行》这几部小说构成了所谓的“爱史三部曲”,那么这也是一个读来并不让人愉悦的爱情故事:它以男女主人公突破传统伦理的大胆求爱开始,期间二人还曾惊世骇俗地单独去郑州旅居数日,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彰显了自由恋爱之纯粹,然而这段感情遭遇了来自家庭、社会的各方阻挠,最终以殉情告终。所以,冯沅君这几部题材、主题几乎雷同的小说不过是以不同的口吻和视角描绘了“同一件事”[3-5]。鲁迅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部分提到:“(《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的精粹名文。”尤其是《旅行》一篇暗示旅行的终点位于郑州,而《隔绝》当中也提到了两人在“郑州旅馆中的最神圣的一夜晚”,这种巧合更能说明几部小说实则在写“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也就是说,这几部小说的故事原型只有一个,却被作者分别“拆写”为三部小说,这种写作使得几部小说从整体上读起来构成了一种针对“‘五四’时期自由恋爱”的“现象学展示”。
本文聚焦冯沅君这几篇展现同一故事原型的爱情小说,在分析其爱情小说创作之叙事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小说的思想主旨。与其认为冯沅君的这几部爱情小说是一类赞颂自由恋爱的“赞歌”,毋宁说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一系列带有“反讽”意味的创作。通过这种笔法,表面上看小说描绘了五四时期青年演绎自由恋爱时的内心状态[6],事实上“反讽”创作使这些小说反映的“自由恋爱”主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一
“一切喧嚣的声音,都被摒在别个世界了。”[7]
除却《隔绝之后》,冯沅君的小说均采用了第一人称自述的口吻,描绘了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情事。这几部小说不仅在小说题材、内容和情节上高度相似,写法上的相近之处亦不容忽视。从叙事层面看,三部小说展现的都是一种由女性叙事者讲述的单向度的“叙事声音”:《旅行》是一对青年男女旅行十日之后,女性叙事者回顾旅行的一篇游记式创作,叙事之中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隔绝》甚至纯粹就是一封书信,是处于“隔绝”状态的女主人公请求爱人前去营救她的求救信,即便如此,作者仍要在书信中以回忆往昔的方式顺带讲述两人相处的过往。而即便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写就的《隔绝之后》,非但整体上借用了目睹殉情的女性亲属的视角,表达了自己作为旁观者对整个事件的观察和态度,其中也通过书信体的方式穿插了一段当事人的自述。相比之下,这几部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是“孱弱和无为的”,“他们或者隐匿在女性的背后,或者在精神上深受女性的影响,基本停留在一个空洞的名字之上,成为在场的缺席者”[8]。
在这个意义上,《隔绝》中镶嵌的一首小诗中的一句话“一切喧嚣的声音,都被摒在别个世界了”就不单单是恋爱青年的内心呈现,也是小说试图营造的隔绝的叙事空间。作者在观察和描摹“自由恋爱”的故事时尤为强调由女性一方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直白而炽烈,突出放大了当事者的感知和心理活动,于是便能最大程度地凸显恋爱中女性的切身感受。但同时,隔绝的叙事空间和单向度的叙事声音却尽可能屏蔽掉了其他外在的声音。除却小说中的女性叙事者,观众便无从知晓两人世界之外究竟是怎样一副情境——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全都经过叙事人用言辞进行“过滤”“加工”之后才得以出现在故事当中。
由此看,冯沅君笔下的“爱史”小说本质上都是用女性单方面言辞建构出来的恋爱故事,于是“现实”与“叙事”之间的断裂便不可避免。这种基于“现实”与“叙事”之间的差异、矛盾在文中比比皆是。例如,此前的研究者就已经注意到,小说的称谓往往采用“我们”而非“我”,表明女性叙事者试图将女性个人的“我”的行为合理化[9],由此表现了“两人共有一个主体共同向旧传统进行挑战、抗争”[1]。进而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用依附于男性中心主义权力话语来肯定女性自我行为的叙述模式。”[9]无论怎么解释冯沅君小说中的这种特殊现象,从这个细节可以透露出,小说叙事使用的称谓存在着“名”“实”不符的情形:分明故事自始至终都以女性叙事者来讲述,却采用了与叙述者身份并不相符的称谓。
小说中存在着的这重“现实”与“叙事”的断裂、“名”与“实”的挣扎远不止称谓这一个细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叙事效果,一切的前提在于冯沅君笔下的自由恋爱故事只提供了由女性叙事者发出的单向度的声音。作为读者,我们可以从女性叙事者的描述中窥得事件的大约面目,却永远不可能捕捉到客观世界的真相。解读这一系列小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观察女性叙事者怎样讲述和演绎她的爱情故事。
二
我们关于这一系列“爱史”写作的第一个观点是:叙事者的感受和态度以及她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永远在故事的“前场”,然而作者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却未必与笔下的人物(包括故事的叙事者)分享着同样的观点和立场。
冯沅君的女性叙事者往往以一种辩护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小说所描绘的恋爱故事无一例外均面临着重重困难。男女主人公一个已婚、一个身负婚约,却大胆地追求违背当时道德观念的自由恋情,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来自家庭、朋辈和社会周遭的重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陷入爱情的女性如果仍想要诉说自己的爱情故事,则势必会演变成一整套替爱情“申辩”的说辞。
于是便触及到小说另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这个由女性叙述的故事中,“他人”的目光、评论时隐时现地在小说中作为背景出现,显然作者并不打算彻底泯灭这些质疑自由恋爱的声音,作者让这些声音存在,且是通过女主人公之口诉说出来,不仅为了说明叙事人很清楚这场爱情将要遭遇什么,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断地让这些声音与叙事者自己的观点发生碰撞。这种介于“他人”看法和叙事者观点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前文提到的“现实”与“叙事”的断裂,而且明显可以注意到,小说中两股观点针锋相对的交锋中,即便叙事者的口吻和语气总是相当强硬,女性叙事者在整个叙事当中却始终处于守势。
且拿《旅行》这篇小说来论。在小说叙事开端,女性叙事者并没有直接开始叙述故事,而是从一个关于“价值”的讨论开始了她的讲述。她说:“人们作的事,没有所谓经济的和不经济的。二者的区别全在于批评的观察点是怎样。”在这里女性叙事者表露出一种典型的价值相对主义的态度。将这句话放在开头,等若从故事的开始就奠定了一块抽离了价值评判的真空地带。这话仿佛申明了,既然“批评的观察点”决定了评论的最终走向,那么之后由女性叙事者讲述的故事就不应当从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出发去评判。
然而叙事者也没有真地安于在一片“价值真空”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反而恰恰由于叙事者的立场太过明确、太过富有争议,才必须利用这种价值相对主义来为自己赢得一些可供辩护的空间,并且她想要拿来辩护的事情便是题目所说的“旅行”。据她所言,这场旅行将要付出的代价是旷课、费钱,但同旅行者对于这场旅行的看法相比,“一两个礼拜的光阴,和几十块钱”的代价简直不值一提。小说是这样说的:“但就他方面想——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这一个多礼拜的生活,在我们生命之流中,是怎样伟大的波澜,在我们生活之火中,是怎样灿烂的火花!拿一两个礼拜的光阴,和几十块钱,作这样贵重的东西的代价,可以说是天下再没有的便宜事。”[10]叙事者将这次旅行称为生命中“伟大的波澜”和“灿烂的火花”,是超越时间和金钱的东西。往下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这次旅行的质疑,也会看到叙事者对“旅行”作出的各种层面上的辩护。又如在记叙两人在火车上的段落,女性叙事者特别留意地提起了火车上的搭客,从而有意识地让“他人”的观点和“声音”出现在叙事之中。这一段描写是冯沅君小说中最有名的段落之一[11],其中提到了作为“界碑”放置在两人中间的行李,特意提到富于暗示意味的、充当了“界碑”的行李,由此映衬出“搭客们的注意”和“他人”的目光在火车旅行途中从来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可是面对这种注意和目光,女性叙事者说:“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10]与其说是其他旅客的注目使得两人格格不入,不如说是女性叙事者对他人的关注,以及关心“他人”是否在关注自己的那种刻意的态度,才是造成“我们”与“他者”对立的主要原因。尔后,女性叙事者甚至还对那些搭客们评头论足,以贬低他人的方式反衬出自身举动的高尚:“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阔气的,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他们所要求的世界是要黄金铺地玉作梁的。我们所要求的世界是要清明的月儿与灿烂的星斗作盖,而莲馨花满地的。”[10]
他人的旅行是为了名利而不得不做的旅行,反观“我们”的旅行,是为了超越世俗名利而自由选择的旅行。在下文中女性叙事者反复地使用了类似的论证,用来表明这次旅行的动机是为了超越世俗利益的爱情,因而是一次值得且高尚的旅行。但有意思的是,尽管在此叙事者略带夸张地贬低了车厢中“注意”和观察着自己的人们,并且有可能这些人未必真的在注意着这对男女,“他人”在她的叙述中却不可或缺。因为“如果不是他们这样粗俗,也需要注意我们的行动,恐怕我们连相视而笑的自由也被剥夺了”[10]。这说明在女性叙事者看到的“旅行”活动中,纵使她一味想要营造一种道德的、价值的真空来讲述旅行的故事,“他人”在这场旅行中始终存在着,而且是作为不可缺少的叙事元素反复在故事中出现。这表明女性叙事者怀揣着的强烈的价值导向恰好站在了这些“他人”的价值观的对立面。“他人”的多次登场暗示着“他人”所秉持的那种价值观始终在场,即便“他人”没有在注视他们,“他人”所持的价值立场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人”由此代表了一种主流的看法和普遍的态度。直到二人在旅店居住数日之后,这种主流的、普遍的价值观已然开始侵犯他们的二人世界:“在我们将走的前一两天,已有好多人注意我们同住这回事了,并不是我多心。他们每问我在什么地方住的时候,辞意中都含着讥笑的神气。”[10]“他人”所代表的那种来自周遭社会的主流声音一步步渗透进男女主人公的世界之中,不断地侵犯着女性叙事者发出的单向度的声音。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和“他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而女性叙事者的多番辩护正是想在叙述的层面上泯灭、消弭这种冲突。尽管她在小说开始有意营造了“价值的真空”,但这么做无非是想让自己发出的那股单向度的声音,成为这片“价值真空地带”之中唯一的声音。
与之相比,小说《隔绝》不仅是一篇女性向爱人发出的爱的呼救,同样也可以将它理解为女性在幽闭“惩罚”的境遇中为自己写下的长篇辩护。只不过与《旅行》相比,辩护所针对的“他人”有了更加明确的范围,那便是女主人公的家人。如果说《旅行》中不过模模糊糊地暗示了女性与原生家庭的冲突,那么在《隔绝》中,这种冲突更加激烈地爆发了出来。女性叙事者在故事开始不惜将阻挠恋情的家人称之为“反动的势力”,她不满地说到自己和家人在观念上无可挽救的矛盾:“怎的爱情在我们看来是神圣的,高尚的,纯洁的,而他们却看得这样卑鄙污浊!”[7]叙事者的恋人青霭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于我不爱的人非教我亲近不可,而对于我的爱人略亲近点,他们就视为大逆不道?……”[7]这场恋情中的男女双方都无法理解周遭人们的观点。女性叙事者的家人无法接受她的恋情,而她的恋人显然也遭遇到了旁人的压力。这种来自“他人”的质疑和否定时常在冯沅君的一系列“爱史”小说中轮番登场,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爱情故事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事实上正是这些否定和质疑这场恋情的“他人的声音”,在不断地间接推动叙事者继续讲述着这场故事。
于是冯沅君这几篇小说的结构大体上由“质疑—辩护—再质疑—再辩护”的模式构成。整个故事可以视作女性叙事者面对各方面的质疑所给出的一条又一条的自我辩护,尤其是《旅行》。看起来《旅行》以旅行过程中的先后发展顺序写就,可小说对旅行中的大量事件作了模糊处理,突出的却是阻挠、妨碍旅行的各种观点和声音:从在火车上可能迎来的搭客的注意,到旅行途中不甚令人愉快的气候,再到旅行中注意到伴侣的紧张和压力,以及两人关系实质违背道德伦理的事实,还有因为这次旅行招致的他人的讥讽和批评,等等。事实上对旅行中出现的任何细小的“不尽如意”的地方,女性叙事者都在大费周章地给予辩护,似乎唯有这样才能证明“旅行”的崇高性。
三
既然谈到了冯沅君的“爱史”写作几乎都呈现为女性主人公的“辩护”呈辞,那么就不得不考虑下一个问题:她在为谁辩护?——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女性叙事者必须为自己辩护。《隔绝之后》提到,她的书信文字终归落入家人手中,给家人带来了无穷的苦楚,可也由此赢得了一丝家人的同情。《隔绝之后》的叙事者也即《隔绝》中女主人公的表妹,她在引用了死者写给家人的遗书之后表示“万箭攒心”。尔后又详细地描述了其他家人阅读遗书之后的表现,并且在男主人公士轸到来之后,充当了叙事者的表妹说道:“大家——尤其是我的姑妈——都被爱神的魔力镇摄着了;望着这对不幸的爱人只是泪珠满面,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敢哼出干涉的字眼。”[12]
这番描述似乎暗示着死亡让此前关于“自由恋爱”的辩驳即刻生效了。由于《隔绝》《隔绝之后》这组作品主要将自由恋爱的矛盾放置在青年男女及其家人之间,这种安排使得矛盾在极短的时间——三天和极狭隘的空间——家中得以激化,于是《隔绝》中的女性叙事者便能够迫于情势写下这封书信,从而在书信中力陈自身观点和立场的正当性。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小说《隔绝》中,除了对自由恋爱这件事作了辩护之外,这位女性甚至还有意为“自杀”这件事辩护。她说:“我又屡次说道: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走去看海去。”[7]“世界原是个大牢狱,人生的途中又偏生许多荆棘,我们还留恋些什么。况且万一有了什么意外的变动,你是必殉情的,那末我怎能独生!我所以不在我母亲捉我回来的时候,就往火车轨道中一跳,只待车轮子一动我就和这个恶浊世界长别的原因,就是这样。……假如爱神怜我们的至诚,保佑我们成功,则我们日后或逃往这个世界的别个空间,或逃往别个世界去,仍然是相互搀扶着。”[7]
小说的女主人公原本就期望着与恋人一同殉情。特别当矛盾的双方变成了“我们”与“家人”时,价值观念的冲突就会变得难以调和,而当冲突无可调和时,自杀便成为了无可选择的选择。如果说《旅行》中的女性叙事者姑且可以用不计较乃至蔑视的态度应对外面世界对她的质疑,那么来自家人的极力反对显然深深地挫伤了《隔绝》中的这位女性。她无法处理好“男女之爱”和“母子之爱”的矛盾[1]。在这种情形下,自杀看似是用回避的方式化解了冲突,却也未尝不是冲突无法解决之时的下策。可偏偏叙事者巧妙地将殉情、死亡也编织进了这个自由恋爱的神话当中,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女性叙事者变得愤世嫉俗,甚至声称这个世界本质上都不值得留恋,以此证成了自杀一事的正当性。尽管现实中的死亡使得叙事者为恋情作出的辩护得到了家人的认可,但她还想要进一步证明这种惊世骇俗的赴死行为也是正确的。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到,“爱史”三部曲中的女性叙事者在“辩护”这件事上做到了极致。相比之下,《旅行》在“辩护”一事上同样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叙述旅行的过程中充满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但即便是再细小的不顺意,女性辩护人也要用言辞去补救这种现实中的不顺意。这一点极为清楚地体现在描写火车沿途所见景物的段落中。在这一段里,女性叙事者先提到自己曾在沿途见过很好的景致,然而这次两人出行时,却“因为天气不很好,他的话都未被证实”。本来是件在旅行过程中令人扫兴的事,之后却在女性叙事者口中摇身一变成了一幅良辰美景:“可是又因为微阴的缘故,在浮云稀薄处露出的淡黄色的阳光,及空气中所含的水气把火车的烟筒中喷出的烟,作成了弹熟的棉花似的,白而且轻的气体。……那种飘忽、氤氲、若即若离的状态,我想只有人们幻想中的穿雾般冰绡的女神,在怕惊醒了她的爱人的安眠而轻轻走脱时的样儿可以仿佛一二呵。它是怎样的魅力呵,怎样的轻软呵!如果我们的生活也像这样,那是多么好呵。”[10]
这是全文描写最美的段落,同样也是最空洞的一段。或许言语中描绘的那种水气缭绕、云烟弥漫的状态大可以比拟小说中的这段爱情:它美丽而空洞,如果强行要将它描述成美好的恋情,则势必要动用谎言。这段话中固然有自我开解的意味。不过往更深一层想,女性叙事者为眼前所见到的景色辩护,其根本原因在于她想要为恋人辩护,而之所以要这样百般替那个“他”解释乃至圆谎,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在这场爱情关系当中,女性叙事者已然将恋人视作“爱情”——这个难以言说又无可具形之物——的化身和实体。于是《旅行》小说后半段可以看到大量叙事者为恋人辩护的说辞。前面提到,《旅行》中建构了小说中的“我们”和“他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小说叙事当中“现实”与“叙述”之反差的体现,前文也揭示了这种对立主要发生在价值观念的层面,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叙事者讲述整个故事的状态。这种来自外界的、现实世界的和“他人”的影响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层层推进、愈发浓烈。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写到两人在旅馆中同居的片段时,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却仍是一个时常外出、需要不断接触“他人”的人,这一点与小说中的女性叙事者很不一样。小说中的男性是一个在旅行过程中仍要参与社会交往的人,这意味着男性势必承担了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当时始终寓居在旅店的女性叙事者却没法真切地体会到这种压力。文中对这种压力有着相当直接的表达,并且就发生在二人遭到他人直接批评之后:“万一各方面的压力过大了,我们不能抵抗时,我们就向无垠的海洋沉下去,在此时我们还是彼此拥抱着。‘爱的人儿!’(此时他在床上横着睡下,我在床沿上坐着,彼此紧紧的拉着手。)‘要是将来他们把我诽谤得不为人所齿,你怎样呢?’”[10]这段话体现出这位男性不断地将来自外部世界的表现和反映带到他们的“二人世界”之中,这就使得女性叙事者在讲到这段经历时,她不仅要为她自己和“我们”这个小型共同体辩护,她还必须为自己的恋人辩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男性所说的话中只说到“他人”对“我”的诽谤,这种表达与女性叙事者动辄称“我们”形成了反差;之后的那句疑问句“你怎样呢”则更是将自己和女性叙事者的立场作了一定的切割。显然在这句疑问句中,这位男性并没有将自己和女性叙事者视作一体,也不认为他们需要共同承担未来的命运。但细看女性叙事者如何理解他的伴侣所说的这几句话呢?她说:“他有什么地方开罪他们,他们现在拼命的骂他,不是为了我吗?”[10]她认为恋人遭遇的压力和困境来源于自己,她不愿意将自己与恋人进行“切割”。而她对上面那句“你怎样呢”的实际回答,也仍旧使用了复数的人称代词“我们”:“我们是永久相爱的。”[10]与此同时女性叙事者也说:“我似觉得大难已经临头了,各面的压力已经挟了崩山倒海的势力来征服我们了。”但紧接着女性叙事者却更为“用力”地陈述了自己对爱情的观点,并且将一切责任推给“不良的婚姻制度”,这种决然的态度恐怕是“他”所不能具备的:
我想到了如山如陵的洪涛巨波是怎样雄伟,黄昏淡月中,碧水静静的流着的景色是怎样神秘幽妙,我们相抱着向里面另寻实现绝对的爱的世界的行为是怎样悲壮神圣,我不怕,一点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艺术化的,天下最光荣的事,还有过于殉爱的使命嘛?总而言之,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我总不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荒谬的。退一步说,纵然我们这行为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结果,我们头可断,不可负,也不敢负这样的责任。[10]
唯有在这个段落当中,女性叙事者为爱情献祭的想法被清楚地提了出来。假如我们回顾前文中女性叙事者对这次旅行的“说解”,不难看到在最初的时候她所定义的“旅行”并没有那么崇高且悲壮。可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个使命则被进一步定义成了“殉爱的使命”。这也意味着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女性叙事者的心态一再发生着变化:从一开始并没有这么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旅行会给两人在舆论上造成何种压力,直到慢慢明了了这种压力之后不惜与这种压力相抗争,甚至最终为此怀着为爱牺牲的觉悟。她一步步将自己抛掷进这个危险的赌局,直到将自己的所有名誉都压了上去,即便如此她仍一再地告诉自己这次旅行是正当的。所以《旅行》这部小说中的女性叙事者可谓不择手段地用言辞从各个方面为旅行辩护,可是这种辩护的逻辑终点却是女性叙事者的自我牺牲。
因而女性叙事者对旅行中一切不甚顺心的事情都极为敏感,然而这种敏感本身就是反常的。在小说所描述的这场关系中,唯有她一人是两人关系的承担者,因为她所关心、爱护着的“他”在思考两人关系之大是大非问题时反而将自己同自己的恋人作了切割,换言之他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不应该为这个女孩负责。反观女性叙事者,她在这段关系中将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她为了为恋人、爱情和“旅行”辩护,不得不变成了一个满口谎言的人,她不仅对“平素相信我的人”撒谎,她也背弃了生养自己的家庭,不得不对自己的表妹和母亲撒谎。唯有在想起自己的母亲时,她才感到愧疚,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和痛苦:“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想到他的家庭的情况,别人知道了这回事要怎样批评,我的母亲听见了这批评怎样的伤心,我哭了,抽抽噎噎地哭,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好像独立在黑洞洞的广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来保护我,因而对于他的拥抱,也没有拒绝的勇气。”[10]最终女性叙事者又说服自己把这些本真的悲哀和痛苦给一并抛诸脑后了:
一切,一切,世间的一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的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房中——我们的小世界——的空气,已为爱所充满了,我们只知道相偎依时的微笑,……我的旗子上写些什么也是不足轻重的。读书也只是用以点缀的世界中的景色,别人对于我们这样的行为要说闲话,要说贬损我们人格的闲话,我们的家庭知道了要视为大逆不道,我们统统想得到,然而我们只当他们是道旁的荆棘,虽说是能将我们的衣服挂破些,可是不能阻止我们的进行的。[10]
当这位女性叙事者对爱情的献身达到巅峰时,她的整个谎言也随之开始和盘托出。小说中的前后矛盾之处随处可见,而所有这些前后矛盾之间的张力均存在于小说关于“现实”的记录和女性叙事者的“叙述”之间。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很难善终的爱情,但女性叙事者却自始至终都想要用言辞挽救这段无比艰险的爱情之旅。
所以在冯沅君所写下的“爱史”写作中,女性叙事者不仅想要为她自己辩护、为爱情辩护、为爱人辩护,甚至这种充满“辩护”意味的言辞拓展到了叙述的方方面面,包括旅途所见的风景和最终对自杀一事的选择。但由此也暴露出这种由“辩护”构筑的言辞本质上是一种欺骗和自我欺骗的言说。也就是说,女性叙事者牺牲了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诚实,用辩护的言辞“制造”了这场恋情的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冯沅君“爱史”写作中的女性叙事者越是“能言善辩”,越是表明这场恋情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外部均密布阴云;当一场属于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越是不够顺意,越是需要用巧言令辞来“包装”这场恋情。
综上所述,冯沅君通过《旅行》《隔绝》和《隔绝之后》这几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爱史”叙事,这一系列“爱史”写作采用的叙事手法非常相似,均为女性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恋爱故事,且故事的题材和情节也多有雷同。在小说中作为叙事者身份出现的女性在讲述爱情故事的同时也是自由恋爱的忠实维护者。她选择以辩护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通过为自己、恋人和爱情辩护,对抗着来自家庭、周遭和社会的压力,用自己的能言善辩塑造了一则自由恋爱的“神话”,而这则本质上脆弱不堪“神话”反映出的却是女性在五四时期进退两难的尴尬[1]。在这个意义上,冯沅君的“爱史”写作是一系列充满反讽的文学建构。从表层看,这个“爱史”的故事是女性演绎自由恋爱的叙事,也是用言辞搭建出来的关于自由恋爱的乌托邦。但这种演绎的叙事行为本身也足够耐人寻味。显然这一系列小说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在于小说借助女性叙述者之口“说了什么”,而在于女性叙事者如何费尽心力去言说恋爱故事的行为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冯沅君的“爱史”写作,便会注意到潜藏在叙事之下的诸多隐瞒、欺骗和自我欺骗。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冯沅君从侧面表现出“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恋爱”的困境所在:真正的困难或许未必在于社会对青年的不理解,或许也不能把矛盾的根源悉数归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反而当青年想要用“新”的观念伦理实践自己的生活,他们必须给自己一个关乎伦理和道德的“证明”。因而冯沅君创作的“爱史”故事就是女性叙事者“讲述”给“他人”和自己的关乎伦理和道德的“证明”,这些文字不仅向众人诉说着自由恋爱的正当性,也在安抚着叙事者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从冯沅君的这几部小说写作还可以看到,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有意地造成了叙事人和作者的割裂,这种写作手法使得小说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13]。同样的故事如果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不仅难以深入地描绘人物的内心状态,势必也无法呈现出如此复杂的阅读层次,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展现五四时期青年人的“缠绵悱恻之情”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