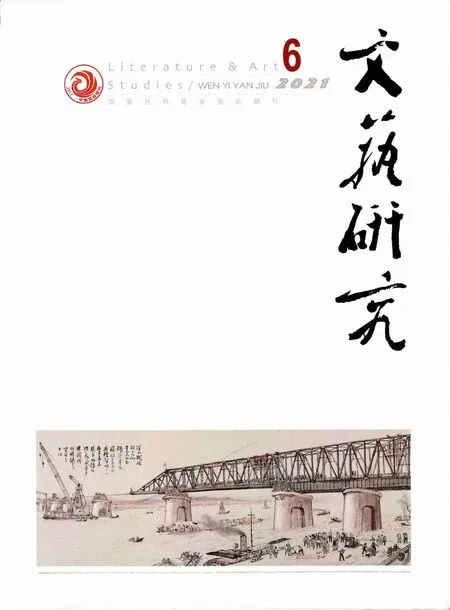诗剧形式与异端主题
——论穆旦对拜伦的创造性偏离
王东东
仅以体量而论, 拜伦是穆旦翻译得最多的英语诗人。 学界较多注意英语现代主义诗歌( 如艾略特、 奥登) 对穆旦的影响, 对穆旦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关系近来虽也有所发现, 但多持一种轻视态度。 其实, 在对穆旦的启发上, 拜伦的作用可能并不弱于艾略特和奥登, 后两位带来的更多是现代主义技法, 而拜伦不仅为穆旦带来诗剧的形式——穆旦的几篇长诗都采用诗剧形式, 毫无疑问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穆旦的文学品格和精神结构。
一、“奇迹剧”:文本的晦涩与翻译的选择
穆旦对英诗的了解, 有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 穆旦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浪漫主义诗人进行翻译, 固然有时代背景方面的原因, 然而, 同时也有可能是对曾经影响自己的浪漫主义诗人进行诗学回顾。 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 拜伦小传》中, 穆旦特别引用了1972年版的牛津《 英国文学简史》 : “ 只在纯抒情诗上, 他次于最优; 因此读者不应在诗选中去了解拜伦。 仅仅《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 审判的幻境》 和《 唐璜》 就足以使任何能感应的人相信: 拜伦在其最好的作品中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而且是世界上总会需要的一种诗人, 以嘲笑其较卑劣的、 并鼓舞其较崇高的行动。”①穆旦显然赞同这个看法。 在某种程度上, 拜伦的讽刺与穆旦有精神相通之处, 有研究者指出: “ 在拜伦讽刺的对象中, 上层社会的虚伪与狡诈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在穆旦的诗作中, 对上层社会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的讽刺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②穆旦认为卞之琳翻译的拜伦“ 笔调不合”③, 恐怕是觉得自己才是和拜伦“ 笔调相合” 的诗人。 他晚年在润色讽刺史诗《 唐璜》 的译稿时, 也偷偷写了一首讽刺时事的“ 八行体” 长诗《 父与女》 ( 长达648行) , 但从未发表④。 其实, 这应该不是穆旦第一次受拜伦影响而写诗, 拜伦的诗剧《 该隐》 对于穆旦有更大的意义, 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艾略特的《荒原》 《四个四重奏》 或奥登的《战时十四行诗》。
穆旦开始翻译拜伦并非只是缘于50年代平明出版社的约稿, 而应该和他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有很大关系。 从萧珊1953年9月8日给巴金的信中也可以看出: “ 他们说平明可以出‘ 题目’, 来些整套什么, 但出题目主要得有人, 光出题目, 没有人来完成也是徒然, 所以我还是让他们自己出题目。”⑤然而, 具体选择哪些篇目进行翻译, 却需要深入分析。 穆旦没有翻译拜伦的诗剧, 虽然他在罗列篇目时对这些作品如数家珍:“ 在诗剧方面, 有历史悲剧《 曼弗瑞德》 (1817) , 《 马里诺·法列罗》 (1820) , 《 福斯卡里父子》 (1821), 《撒旦那帕拉》 (1821); 有奇迹剧《该隐》 (1821) 和《 天和地》 (1824) , 还有诗剧《 维诺》 (1822) , 《 变形的畸形者》 (1822) 。”⑥这是耐人寻味的。 其实, 拜伦诗剧《 该隐》 对穆旦一生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如果不联系拜伦的《 该隐》 , 穆旦写于西南联大求学时期的《 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 ( 以下简称《蛇的诱惑》, 1940) 就不能被充分认知。 《蛇的诱惑》 有一个较长的引言:
创世以后,人住在伊甸乐园里,而撒旦变成了一条蛇来对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么?
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就被放逐到地上来。
无数年来,我们还是住在这块地上。可是在我们生人群中,为什么有些人不见了呢?在惊异中,我就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
这条蛇诱惑我们。有些人就要被放逐到这贫苦的土地以外去了。
正文也出现了相关的诗行:
自从撒旦歌唱的日子起,
我只想园当中那个智慧的果子:
阿谀,倾轧,慈善事业,
这是可喜爱的,如果我吃下,
我会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里游览,
带上遮阳光的墨镜,在雪天,
穿一件轻羊毛衫围着火炉,
用巴黎香水,培植着暖房的花朵。
那时候我就会离开了亚当后代的宿命地,
贫穷,卑贱,粗野,无穷的劳役和痛苦……
但是为什么在我看去的时候,
我总看见二次被逐的人们中,
另外一条鞭子在我们的身上扬起:
……生命树被剑守住了,
人们渐渐离开它,绕着圈子走。⑦
值得注意的是, 引言和正文都运用了基督教神话或隐喻。 《 蛇的诱惑》 中出现了两种人群, 抒情主体或抒情主人公( 应该是德明太太的朋友) 和德明太太乘汽车穿过城市街道, 一路上看到流离失所的人们, 并最终来到了“ 一个廿世纪的哥伦布” “ 探寻的墓地” ( 即目的地百货公司) , 但他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在街上看到的“ 垂死人”。 两类人群分别处在室外空间( 街道) 和室内空间( 车内、 百货公司) , 但抒情主人公将两种空间联系在一起, “ 我会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里游览”, 同时也意识到可以返回“ 亚当后代的宿命地”。 《 蛇的诱惑》 展示了战时中国城市两极化的社会图景, 并体现出对上层社会的讽刺和对下层社会的同情。 然而, 即使可以了解这首诗的意旨, 它的形式层面和文学隐喻仍然晦涩难解。 至少有两个问题: 一是为何穆旦会写下“ 第二次蛇的出现” 这样的表述? 二是这首诗的基督教意象与作品主题是否脱节?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 就必须联系到《 圣经·创世记》 第四节中该隐杀弟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 他们的儿子该隐种地, 亚伯牧羊。 兄弟二人向耶和华献祭, 耶和华更喜欢亚伯的血祭, 该隐就将弟弟亚伯杀害。 从此, 该隐开始了流离飘荡的命运。 这个兄弟阋墙的故事是圣经的第一桩谋杀案, 引发后世的无穷联想,自然也少不了文学家的附会。 中国诗人穆旦的作品也远远地与《 圣经》 产生关联,《蛇的诱惑》 不仅利用了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 同时也利用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兄弟二人在穆旦笔下变成了两个阶层, 后者看似没有直接表现为对抗或谋杀,但其中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对立非常明显,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对两个阶层都投以同情的目光, 体验着他们各自的痛苦:
“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
为什么?”
为了第二条鞭子的抽击。
墙上有播音机,异域的乐声,
扣着脚步的节奏向着被逐的
“吉普西”,唱出了他们流荡的不幸。
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
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⑧
这首诗的副标题是“ 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题: 自己到底属于哪个阶层, 抑或要投身于哪个阶层? 选择街道上的下层社会, 其结果是生存痛苦直至死亡; 选择室内的上层社会, 则又会体验精神痛苦甚至虚无。 而且,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负有责任, 至少是一种精神上的责任, 这是抒情主人公异常清楚的。 上层社会要承受的“ 流荡的不幸” 是一种精神不幸, 类似于该隐的“ 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⑨, 而下层社会却要付出生命, 正如“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⑩。总之, 《 蛇的诱惑》 本身即包含了两套符码: 一套是深层的《 圣经》 符码, 不仅是《创世记》 第三节中的伊甸园故事, 还包括了第四节该隐杀弟的故事; 另一套是表层的阶层符码。 如果对第一套符码不够了解, 势必无法理解这首诗的深层意涵。 穆旦的高明之处是, 他在正文中只字不提该隐的名字, 只涉及《 创世记》 第三节, 但在引言中又以“ 第二次蛇的出现” 暗示了《 创世记》 第四节。 毕竟中国读者更熟悉人类始祖被逐伊甸园, 而非该隐杀弟的故事, 穆旦必须考虑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和转化问题。 《 蛇的诱惑》 中圣经符码的潜文本即是《 创世记》 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但在诗歌意象和隐喻的实际运用上更多从第四节向第三节靠拢, 甚至停留在第四节和第三节之间。 也就是说, 穆旦更多以第三节的隐喻和符号系统替换甚至覆盖了第四节, 但又在引言中做了提示。 如果穆旦直接将第四节的意象符号引入正文, 整首诗虽然变得没有那么晦涩,但魅力恐怕会大减。
然而, 第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解, 为何穆旦会使用“ 第二次蛇的出现” 这样的表述? 结合诗题、 引言和正文可知, 蛇的第二次出现正是为了第二次诱惑人类, 使人类“ 二次被逐”, 承受“ 第二条鞭子的抽击”: 如果说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之果是人类的第一次堕落, 那么该隐杀弟则是人类的第二次堕落。 两次都由于魔鬼的引诱, 正如穆旦诗中所说, “ 自从撒旦歌唱的日子起”。 但是在《 创世记》 第四节中, 撒旦并未出现,只有上帝和该隐的对话。 穆旦是从何处得到撒旦重现的灵感, 即魔鬼化为蛇, 又一次引诱了人类( 该隐) 呢? 如果说穆旦从传教士话语中——魔鬼无处不在, 人类若不加以提防就会犯罪——得到了这一点, 那么就显得太过宽泛, 不仅不能求证, 而且这样一个“ 通俗” 的解释也将问题庸俗化了: 正因为魔鬼会诱惑一切人类犯罪, 诱惑的对象也就不必是该隐。 其实, 这个令人敬畏的文学灵感正是来自拜伦的《 该隐》 : 要知道, 魔鬼化成蛇第二次诱惑人类犯罪这个惊人的文学想象并不是通俗、 宽泛的传道,如果撒旦第二次出现的话, 诱惑的对象一定是该隐而不是其他人。 该隐杀弟的题材来自《 圣经》 , 但其表现方式——蛇第二次出现——则一定是来自拜伦的《 该隐》 , 这个表现方式是拜伦的文学独创⑪。 乔治·斯坦纳说: “ 他是自弥尔顿以来的英国大诗人中第一个想到圣经戏剧的。”⑫拜伦自己则说: “ 在整个作品中并无教义或我个人的假说:但我不得不使该隐和卢西弗的谈话相协调, 当然这在诗歌中一直是允许的。”⑬弥尔顿《失乐园》 以神圣情怀改写《创世记》 第三节, 拜伦《 该隐》 则以撒旦精神改写《 创世记》 第四节。 鲁迅也注意到《 该隐》 和《 失乐园》 的巨大反差⑭, 他舍弃弥尔顿而奉拜伦为反抗的摩罗诗人, 良有以也。 该隐杀弟的圣经隐喻在欧洲浪漫主义作家那里引起巨大回响, “ 这是因为到了19世纪, 圣经在其神圣的语境或身份之外, 已开始被当作一部艺术性作品来欣赏”⑮。 经由拜伦, 穆旦对此也做出了回应。
可以看到, 《 蛇的诱惑》 中的抒情主人公以该隐( 穆旦以亚当写该隐, 以《 创世记》 第三节写第四节) 自居, 表示“ 我只想园当中那个智慧的果子: /阿谀, 倾轧, 慈善事业, /这是可喜爱的, 如果我吃下, /我会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里游览”。 细究其义, 这个口吻也是模仿该隐而非亚当, 果然, 后面接着就说: “ 那时候我就会离开了亚当后代的宿命地, /贫穷, 卑贱, 粗野, 无穷的劳役和痛苦……” 该隐——经由他的父亲亚当的目光——向伊甸园的回望, 也可以在拜伦的《 该隐》 中看到, 只不过后者中的该隐猛烈批评亚当对上帝的信仰。 拜伦《 该隐》 的渎神, 诚如王佐良所说, “ 是反对宗教的, 利用了《 圣经》 中该隐杀弟的故事, 但剧中的该隐不仅不感到有罪, 反而嘲笑上帝, 认为人既有了理智, 就应理智到底, 为了扩充知识, 应去了解死亡。 这当中有启蒙思想的彻底的理性主义精神。 剧本发表之后立即遭到英国教会人士的猛烈攻击”⑯。 而在穆旦的《 蛇的诱惑》 中, 该隐的形象变得中性化了, 他也要面临一个“ 阴暗的生的命题”, 在文学表现上, 则将亚当和夏娃、 该隐和亚伯这两次堕落叠加在了一起。
穆旦在1953—1955年翻译拜伦只选择了抒情诗, 最主要的原因是, 《该隐》 在1950年已有汉译本问世, 由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杜秉正翻译, 距离穆旦开始翻译拜伦不过三四年之久, 穆旦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译本。 在当时的语境下, 该隐作为反抗者的形象被大加颂扬⑰。 按照当时出版业的惯例, 穆旦不需要再翻译《 该隐》 。 与《 该隐》 情调最为接近的诗剧《 曼弗雷德》 在1949年也有了译本⑱。 于是, 穆旦与拜伦这两部最出色的诗剧无翻译之缘了, 但他仍不忘在写于70年代的《 穆旦小传》 中将这两部作品分列“ 奇迹剧” 和“ 历史悲剧” 的首位。 称《 该隐》 为“ 奇迹剧”, 不仅是对其宗教题材的指认, 同时也可见穆旦对中国读者可能产生的文化隔膜的担心, 后者也可能是他落实政策后(1972—1976) 仍然没有翻译《 该隐》 的原因。 以穆旦的诚实, 也没有必要特意回避拜伦的诗剧, 何况, 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对拜伦诗剧进行了“ 创造性偏离”。 这个概念是布鲁姆从卢克莱修“ 原子偏离” 那里借来的, 指称一种“ 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这在诗人本身的诗篇里体现为一种矫正运动。 这种矫正似乎在说: 前驱的诗方向不偏不倚地到达了某一点, 但到了这一点之后本应‘ 偏移’, 恰恰应沿着新诗作运行的方向偏移”⑲。 这使《蛇的诱惑》 与《 该隐》 的联系变得隐晦、 不易觉察。 拜伦影响了穆旦, 但似乎没有形成影响的焦虑, 这不是因为穆旦创造力太低, 而恰是因为他作为汉语诗人的独特创造力偏离了拜伦和英诗的模式。
二、“人的活动的图画”:诗剧、“诗的戏剧化”与剧诗
然而, 与拜伦的《 该隐》 不同, 穆旦的《 蛇的诱惑》 并没有采取诗剧的形式, 而是一种具有戏剧性或戏剧化的诗。 究其原因, 在于《 蛇的诱惑》 中的抒情主人公在两个阶层之间犹疑不决, 并在自身内部留下了张力和矛盾, 因而实际上呈现为一种自我的分裂状态, 具有十足的现代主义风格。 抑或, 在诗歌技法或表达上, 穆旦进行了一种激进化操作, 由浪漫主义迅速过渡到现代主义。 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
在二十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为艾略特(T. S. Eliot) 所带来的,一阵十七十八世纪的风吹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wit) 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摆伦和雪莱的诗今日不但没有人摩(摹) 仿着写,而且没有人再肯以他们的诗当鉴赏的标准了。我们知道,在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中,诗人们是不得不抱怨他们所处在的土壤的贫瘠的,因为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物质享受的疯狂的激进,已经逼使着那些中产阶级掉进一个没有精神理想的深渊里了。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加速自己血液的激荡,自然不得不以锋利的机智,在一片“荒原”上苦苦地垦殖。⑳
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中国, 这种时髦的文艺风尚也获得了穆旦的推崇。 上面的引文体现出穆旦对现代主义诗歌技艺和精神的双重理解。 这里的荒原意识或“ 没有精神理想的深渊”, 与《 蛇的诱惑》 中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完全相合, 后者表现的原本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 所谓“ 小资产阶级的手势”。 穆旦在这里对浪漫主义诗人的挑剔, 其实更多是出于诗歌技艺的原因, 也有“ 主智” 与“ 主情” 的分别。 此外, 《 蛇的诱惑》 汲取了《 该隐》 《 曼弗雷德》 以及《 天和地》 的撒旦色彩, 但并没有导向拜伦式的撒旦崇拜, 而保留为一种相对隐晦的二元论的结构模式, 其实是一种“ 神魔相争” 的二元结构。 这种二元论在后来的诗剧《 神魔之争》(1941、 1947) 和《 神的变形》 (1976) 中表现得最明显, 在《 隐现》 (1943、 1947、1948) 中则相对隐晦。 这几部作品从主题到形式都打上了拜伦《 该隐》 的痕迹。 而诗剧《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1945) 中的“ 森林” 意味着一种对人形成威胁的邪恶的( 超) 自然力量, “ 魅” 离“ 魔” 并不远, 相较于英灵, 只能处于下风,正如诗中所写的, “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㉑。 这可能是穆旦对拜伦偏离和修正程度最大的一首诗。 穆旦已佚失的晚期诗作《 神塔》《魔影》㉒, 从标题来看, 也有可能与“ 神魔之争” 的主题有关。
穆旦的《 蛇的诱惑》 并未采取诗剧的形式, 而是采用戏剧化的技巧, 提高了诗歌和语言表达的效率。 从诗剧体裁到戏剧化的诗, 诗的感兴并未减少, 诗的浓度反而提高了, 这也是一种创造性偏离。 同时也必须意识到, 《 蛇的诱惑》 的题材可能更适合诗的戏剧化, 它更多是一场心理剧, 表现了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活动: 这个戏剧化的抒情主人公揣摩着他人的肉体和精神存在, 但显然对自我更感兴趣, 虽然他的移情能力、 对两种人群的注意造成了自我的分裂。 在诗歌的主题和精神层面,《蛇的诱惑》 受到拜伦《 该隐》 《 曼弗雷德》 的影响, 而在诗歌的技艺和形式层面, 则受惠于艾略特的《 J. 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 荒原》 等现代主义诗歌。 也就是说, 诗中充满了抒情主人公大量的内心独白, 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自己想象为该隐, 并幻想与撒旦、 亚当、 亚伯对话, 但同时又看着现实中两个阶层的分裂。 这表明抒情主人公脑子里本就装着一部诗剧, 如果穆旦再以诗剧的方式表现他, 那么展现他与周围的现实人物、 想象中的人物的对话, 势必会变得叠床架屋, 难以实现。
新诗戏剧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追求之一, 在“ 九叶派” 诗人那里尤为显著, 他们的理论代言人袁可嘉就总结说: “ 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诉( 述) 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 戏剧效果的第一个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㉓这和穆旦后来对戏剧性的定义正好呼应: “ 戏剧的方法, 即不用叙述人, 让客观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自己呈现。”㉔袁可嘉提炼了新诗戏剧化的三种方法:里尔克的内倾型戏剧、 奥登的外向型戏剧以及现代诗剧。 穆旦《 蛇的诱惑》 的戏剧化方式更接近袁可嘉所说的外向型戏剧: “ 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 利用诗人的机智, 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活栩如生, 而诗人对处理对象的同情, 厌恶, 仇恨, 讽刺都只从语气及比喻得着部分表现, 而从不袒然赤裸。”㉕袁可嘉以西方诗人为例指出: “ 里尔克代表沉潜的, 深厚的, 静止的雕像美, 奥登则是活泼的, 广泛的, 机动的流体美的最好样本, 前者有深度, 后者则有广度。”㉖在中国新诗中, 前者以冯至为代表, 后者则以穆旦为典型。 穆旦的抒情短诗就特具一种“ 机动的流体美”。
在谈及文学体裁时, 穆旦认为应该按照亚里士多德式的三分法( 抒情、 叙事、 戏剧) , 而非通行的文学概论中的四分法( 小说、 诗歌、 散文、 戏剧) , 用他自己的表述就是“ ( 一) 主观剖解、 ( 二) 客观叙述、 ( 三) 戏剧表现”。 这些意见虽发表于50年代, 但应该是他一贯的主张。 穆旦还特意提及作家可以综合运用不同的文学体裁:“ 我们说它们是人类塑造形象的基本方法, 这是因为它们可以单独被使用, 也可以综合使用, 犹如化学元素可以单独呈现, 也可以与其他元素化合而形成新的物质一样。 虽是新的物质, 但基本上还是由那既定的元素形成的。” 因此, 抒情和戏剧可以结合为诗剧: “ 戏剧亦然, 它包括凡是采用戏剧方法来反映现实的作品, 不管它用的是诗的语言还是散文的语言。” “ 甚至同是在诗剧中, 因为诗有各种格式, 也可以按照其不同的格式更详细地予以区分。”㉗如果我们按照穆旦的思路分析就可以发现, 穆旦的诗剧《神魔之争》 《 隐现》 和《 神的变形》 更多是抒情诗剧, 《 蛇的诱惑》 虽不是诗剧, 却是戏剧化的抒情诗, 而拜伦的《该隐》 和《曼弗雷德》 则是叙事诗剧。
袁可嘉认为现代诗剧较难实现: “ 诗剧的突趋活跃完全基于技术上的理由。 我们一再说过现代诗的主潮是追求一个现实, 象征, 玄学的综合传统, 而诗剧正配合这个要求, 一方面因为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内涵强烈的社会意义, 而诗剧形式给予作者在处理题材时空间, 时间, 广度, 深度诸方面的自由与弹性都远比其他诗的体裁为多,以诗剧为媒介, 现代诗人的社会意识才可得到充分表现, 而争取现实倾向的效果, 另一方面诗剧又利用历史做背景, 使作者面对现实时有一不可或缺的透视或距离, 使它有象征的功用, 不至粘于现实世界, 而产生过度的现实写法(Overdone Realism) ……诗剧的创作既包含诗与剧的双重才能, 自更较诗的创作为难。”㉘其实, 穆旦的诗剧也更多偏向于诗而非剧, 就如拜伦对《 曼弗雷德》 的文体说明——“ 一篇剧诗” ( a dramatic poem)㉙。 无论是《 曼弗雷德》 还是《 该隐》 , 都是难以上演的剧。 雪莱的诗剧实际上也是剧诗, 正如鲁迅所说: “ 至其杰作, 尤在剧诗; 尤伟者二, 一曰《 解放之普洛美迢斯》 (Prometheus Unbound) , 一曰《 煔希》 (The Cenci) 。 前者事本希腊神话, 意近裴伦之《 凯因》 。”㉚对穆旦这几部作品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 剧诗”, 只是习惯上一般称作诗剧。 我们可以承认穆旦是一位很好的戏剧诗人, 却不能说他是一个戏剧家。 相对于袁可嘉所说的现代诗剧更能满足现代主义诗歌“ 现实, 象征, 玄学的综合传统”, 穆旦的诗剧也有自己的特色, 例如在《 神魔之争》 《 隐现》 《 神的变形》中, 他其实更多偏向于象征、 玄学而非现实。 也就是说, 穆旦的诗剧要更为抽象, 它直接运用神魔相争的喻体或象征结构完成了对于现实的指涉, 而绝少涉及现实情节。
三、异端主题:“摩罗诗力”与中国的“反基督”
拜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首先是一种“ 摩罗诗力”。 鲁迅在1907年论及拜伦诗剧《 该隐》 时就说: “ 亚当夏娃既去乐园, 乃举二子, 长曰亚伯, 次曰凯因。 亚伯牧羊,凯因耕植是事, 尝出所有以献神。 神喜脂膏而恶果实, 斥凯因献不视; 以是, 凯因渐与亚伯争, 终杀之。 神则诅凯因, 使不获地力, 流于殊方。 裴伦取其事作传奇, 于神多所诘难。 教徒皆怒, 谓为渎圣害俗, 张皇灵魂有尽之诗, 攻之至力。 迄今日评骘之士, 亦尚有以是难裴伦者。”㉛对鲁迅来说, 以拜伦为首的这一批“ 立意在反抗, 指归在动作”㉜的浪漫主义诗人, 代表了一种“ 摩罗诗力”。 可以看到, 其中既有启蒙精神与浪漫主义的张力, 也有启蒙与反抗的张力, 后来的左翼诗人更是在这一思路下理解拜伦。 然而, 穆旦对拜伦的接受却颇为不同, 也可能更为接近拜伦的本质( 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怀疑主义精神和尼采式的“ 反基督”) 。 穆旦的精神融入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之中。
在穆旦的《 神魔之争》 里, 时时传来魔鬼或罗锡福( 即卢西弗) 针对上帝的抗辩之声, 有的甚至能在拜伦的《该隐》 中找到相似的段落:
他们有什么?那些轮回的
牛,马,和虫豸。我看见
空茫,一如在被你放逐的
凶险的海上,在那无法的
眼里,被你抛弃的渣滓,
他们枉然,向海上的波涛
倾泻着疯狂。O我有什么!
无言的机械按在你脚下,
充塞着煤烟,烈火,听从你
当毁灭每一天贪婪的等待,
他们是铁钉,木板。相互
磨出来你的营养。
O,天!
不,这样的呼喊有什么用?
因为就是在你的奖励下,
他们得到的,是耻辱,灭亡。㉝
罗锡福:是灵魂,敢利用它们的不朽——
是灵魂,敢面对全能的暴君,
看着他永恒的脸孔,告诉他
他的恶不是善!假使他创造了,
像他说的——这我不知道,也不相信——
但是,如果他创造我们——他就不能毁灭:
我们是永生的!——不,他要毁灭我们,
好使我们受苦——让他去吧!他伟大——
……
灵物和人类,至少我们互相同情——
因为我们共受患难,使我们的痛苦
虽不可计数,但是更能忍受,
由于我们全体中间无限的契合!
但是“他”啊,高高在上,如此不幸,
在他不幸中又如此不安,势必
创造,再创造——㉞
神创造, 但同时毁灭, 这在魔的眼中是难以理解的。 诚然, 《 该隐》 中的上帝和魔鬼并未直接对话, 神魔之争更多通过魔鬼与该隐、 魔鬼与亚德( 该隐虔信上帝的妹妹)的对话表现出来。 倒是亚当与该隐的对话, 有如上帝与魔鬼的争论, 他们分别是上帝和魔鬼的信仰者: “‘ 你’ 为什么不幸? 为什么万物存在? /即他, 创造我们的, 亦必如此, 因他是/不幸事物的创造者! 制造毁灭/当然决不能是欢乐的工作, /可是我的父亲说他是全能的: /那么为什么是恶——他既是善? 我向/我的父亲请教这个问题; 而他说, /因为只有这个恶是到善的道路。”㉟在穆旦的《 神魔之争》 中, 神的创造物正在被神毁灭, 魔在代替他们抗议, 并向神描绘出一幅毁灭的场景, 此时有趣的是, 就连高高在上的神也开始自我怀疑: “ 我错了吗? 当暴力, 混乱, 罪恶, /要来充塞时间的河流。 一切/光辉的再不能流过, 就是小草/也将在你的统治下呻吟。 /我错了吗? 所有的荣誉, 法律, 美丽的传统, 回答我!”㊱这样的穆旦式幽默其实有一个现实指向, 即人类陷入战争的历史事实, 具体来说是“ 二战”、 抗战和内战。 战争环境也许是穆旦同类题材最大的现实隐喻, 这是穆旦“ 神魔之争” 的题材书写完全不同于拜伦的原因。穆旦的作品试图探讨对人类来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但同时也有其现实指向, 而拜伦写作的主要动力则是和正统基督教抗辩。
值得注意的还有穆旦的形式创新。 穆旦在神魔激辩之前设置了东风的讲话, 这是一首25行的抒情诗, 也可以看作诗剧的序诗, 东风最后说: “ O旋转! 虽然人类在毁灭/他们从腐烂得来的生命: /我愿站在年幼的风景前, /一个老人看着他的儿孙争闹, /憩息着, 轻拂着枝叶微笑。” 这就将神魔之争的超自然力量纳入一种东方的自然力量, 从自然崇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穆旦同样完成了对西方基督教的天堂和东方的地狱的衔接或拼贴, 试看魔的发言: “ 那些在乐园里/豢养的猫狗, 鹦鹉, 八哥, /为什么我不是? 娱乐自己, /他们就得到了权力的恩宠。” 这是将中国式的宠物塞入了西方的伊甸园。 而魔接下来的发言则完全是中国本土带有佛教气息的地狱情景: “ 当刀山, 沸油,绝望, 压出来/我终日终年的叹息, 还有什么/我能期望的? 天庭的和谐/关我在外面。”这些都是穆旦对神魔之争模式的中国化。 当然, 东风同时是诗剧中的一个人物, 也参与诗剧情节的发展。 临近《 神魔之争》 的结尾, 东风又出现了, 为它催生的万物哀悼:“ 在至高的理想隐藏着/彼此的杀伤。 你所渴望的, /远不能来临。 你只有死亡, /我的孩子, 你只有死亡。”㊲拜伦的诗中绝无这样的宿命论的哀悼, 有的只是抗议: “ 造物——称他/什么随你的便; 他创造只为了毁灭。”㊳这些都在精神上体现出穆旦对拜伦的创造性偏离。
在穆旦晚年的《 神的变形》 中, 可以更明显地看到拜伦的影响。 较之《 神魔之争》, 《神的变形》 更为完整地呈现了神、 魔与人的关系, 增加了魔诱惑人的情节, 从而与拜伦的《该隐》 更为相似, 请看下面的对比。 穆旦的《神的变形》:
魔
人呵,别顾你的真理,别犹疑!
只要看你们现在受谁的束缚!
我是在你们心里生长和培育,
我的形象可以任由你们雕塑。
只要推翻了神的统治,请看吧:
我们之间的关系将异常谐和。
我是代表未来和你们的理想,
难道你们甘心忍受神的压迫?
人
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谁推翻了神谁就进入天堂。
权力
而我,不见的幽灵,躲在他身后,
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宝座,
我有种种幻术越过他的誓言,
以我的腐蚀剂伸入各个角落;
不管是多么美丽的形象,
最后……人已多次体会了那苦果。㊴
拜伦的《该隐》:
罗锡福:好的,有一个条件。
该 隐:你说。
罗锡福:那就是
你跪下来,而且崇拜我——你的主。
该 隐:你不是我父亲崇拜的神。
罗锡福:不。
该 隐:他的同辈?
罗锡福:不;——我没有什么和他相同!
也不愿如此:什么都可以,天上——地下——
只要不是他权力的分享者,或是
他权力的奴隶。我分开住,但我伟大:——
如今有许多人崇拜我,将有
更多的人——你就算第一个吧。㊵
《 神的变形》 写于1976年, 显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指涉, 从“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出, 这句话在诗剧中由人说出, 并天衣无缝地衔接了魔所说的“ 神的压迫”, 但却造成了一种反讽效果。 果然, 穆旦在神、 魔、 人之外又引入了“ 权力”, 试图揭穿神魔之争的实质。 由于“ 权力” 的出现, 神魔之争成了对社会现实的指证。 在这个意义上, 《神的变形》 与拜伦借基督教话语进行的“ 形而上学的反叛”㊶不同, 是一首批判极左政治的诗歌甚至政治讽刺诗, 虽然二者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拜伦在《该隐》 中就这样表现魔鬼:
罗锡福:不!天啊,由“他”掌握,
但是深渊啊,和世界与生命的
无极啊,由我和他一道掌握——不!
我有一个胜利者——真的;但没有上司。
他从万物获得崇敬——但没有从我:
我和他作战,我攻打过他
在最高的天庭。经过一切永恒,
……
作为一个征服者他会叫被征服者
为“恶”;但什么将是他所给的“善”?
假使我胜利,“他的”工作将视为
唯一的恶物。而你们,你们新生的
和未生的人类啊,他给予了
你们什么,在你们的小世界中?㊷
穆旦《 神的变形》 指涉的对象是权力的异化。 可以说, 在穆旦此类诗作中始终包含着双重话语, 在表面的基督教话语之下隐藏着诗人对中国历史的批判, 其诗作也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一种“ 包含‘ 隐晦教诲’ 的‘ 显白写作’”㊸。 《 神的变形》 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可以表明拜伦对穆旦的影响: 《 神的变形》 与40年代的《 神魔之争》 具有主题和精神上的连续性, 只不过前者主要指涉权力, 后者主要指涉战争。 《 神的变形》结尾写道: “ 最后……人已多次体会了那苦果。” 而穆旦在1948年为自己编定的《 穆旦诗集》 即出现了“ 第四部: 苦果(1947—1948) ”㊹这样的标题, 这里的“ 苦果” 显然就是《蛇的诱惑》 里“ 园当中那个智慧的果子”。
总体上讲, 正是拜伦的《 该隐》 , 为穆旦提供了一整套观察人类和中国历史的话语体系, 而且在基督教意象系统中包含了特定的精神视野。 只有经由拜伦的诗性中介,圣经才真正对穆旦发生作用,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 “ 对他而言, 《 圣经》 及其故事、教义是值得赞美的事物, 其中的文学性、 美学性和道德性价值不仅对整个犹太教与基督教世界而且对整个中国来说, 都是一种补充。”㊺拜伦为穆旦准备了运用圣经故事的诗性方法和感受力模式, 以及从基督教信仰下降或落实到世俗关注的人文主义视野。拜伦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 除了其诗性才能, 也和英国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 正如诺思洛普·弗莱所说, 英国浪漫主义文化传统“ 曾受过新教的影响。 由此形成的倾向, 将天启神喻的幻觉纳入个人的直接体验之中, 它不是神圣戒律的产物, 而是反复地想象才形成的”㊻。 而当穆旦像拜伦那样写作, 他的表现则类似拜伦的先辈弥尔顿,“ 从处理源出圣经的材料的方法上……表现他的人文主义思想。 他认为这些材料可按个人的认识加以解释并自由地、 大胆地、 富于想象力地去处理”㊼。 只不过弥尔顿更推崇上帝的创造力, 哪怕《 失乐园》 中最有魅力的人物可能正是撒旦, 而穆旦则和拜伦一样欣赏撒旦。 在穆旦这里, “ 摩罗诗力” 最终带来的是一种异端主题。
由于穆旦为拜伦《 该隐》 中撒旦具有反叛色彩的诗性力量所吸引, 这一方面使他无法认同基督教观念, 而成为宗教的异端, 另一方面也使穆旦远离目的论的现代性叙事, 以一种神魔之争的主题远远地平行于革命主题, 虽然不至于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也并不简单地附和, 而是保留了一种含混的异质性。 拜伦的《 该隐》 并非宗教文学,正如艾略特所说, 宗教文学是“ 一种特殊的宗教意识的产物”, 是“ 以宗教的或虔诚的天才所表现出特殊的和有局限性意识的那些诗人或作品”㊽。 海伦·加德纳甚至反对在“ 虚无” 的标题下将拜伦诗剧编入一本宗教文学选集, 并称拜伦思想为一种“ 孩童似的无神论思想”㊾。 而对于受到拜伦影响的穆旦, 王佐良评述得好: “ 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 照我看, 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 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 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 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就眼前说, 我们必须抗议穆旦的宗教是消极的。他懂得受难, 却不知至善之乐。 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他今年还只二十八岁。 他的心还在探索着。 这种流动, 就中国的新写作而言, 也许比完全的虔诚要更有用些。 他最后所达到的上帝也可能不是上帝, 而是魔鬼本身。”㊾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往往被忽略, 其实,恰好说中了穆旦诗剧真正的诗学灵感和来源, 不是上帝而是撒旦。 试图借镜于基督教来观照所处的社会, 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一幅现代的异端场景: 由于偏离了正统信仰而难以获救。 这也许是穆旦诗歌中精神痛苦的一部分。 即使是在最为“ 虔诚”、 积极的《隐现》 中, 在《爱情的发见》 一节里也出现了摩登男女模仿人类始祖的堕落图景, 并且暗示了魔鬼的再次出现, 然而也由于撒旦的诗性力量表现得不够, 这首诗的魅力多少有一些弱, 相对于《蛇的诱惑》 《神魔之争》 和《神的变形》 来说更是如此。
而更为重要的是, 穆旦从《 该隐》 中发展出了一种有关历史的异端主题, 拜伦的异端色彩是相对于基督教而言的, 而穆旦的异端色彩则更多是相对于中国现代历史而言的, 穆旦的后半生也暴露出作为异端的境遇和命运。 该隐形象原本蕴含了革命化解读的可能, 正如本雅明评价波德莱尔的《 亚伯和该隐》 时所说: “ 该隐这个被剥夺者的先祖被表现成一个种族的始祖, 这个种族不是别的什么, 就是无产阶级。”[51]穆旦拒绝对该隐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化解读, 没有走向三四十年代日趋激进的左翼浪漫主义。他对该隐的兴趣也许与其崇尚个性不无关系, 更着意探索人类精神痛苦的深度, 这一点他受英国文学影响甚大, 正如弗莱所说: “ 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与新教传统及激进主义传统之崇尚个性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述三种传统的倾向都将个人而不是社会利益作为其活动的主要范围或领域, 这种倾向不一定就是利己主义的, 正如与之相反的倾向未必就是利他主义一样。”[52]崇尚个性为穆旦带来的最大后果, 是与对拜伦式英雄的革命化解读拉开了距离。
结 语
穆旦的长诗和诗剧在形貌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拜伦《 该隐》 的启发。 在20世纪40年代, 《 蛇的诱惑》 已带有“ 奇迹剧” 的色彩, 试图以神秘的宗教痛苦转化和升华阶层或阶级对立; 《 神魔之争》 中的战争书写则从整体上纳入了魔鬼与上帝斗法的视野,而严重偏离了正统基督教, 以至出现了《 隐现》 对上帝软弱无力的呼唤, 二者对战争的否定态度都严饰以一层宗教外衣。 70年代的《 神的变形》 则反省了革命的激进化实践, 再一次回到历史的异端主题。 总体上看, 穆旦在英语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 以一种神秘的异教观念理解历史, 远离了历史目的论, 而倾向于历史循环论。 在穆旦那里, 拜伦式的摩罗诗力最终变成一种历史的异端主题, 没有像大多数中国的拜伦接受者那样, 导向“ 立意在反抗, 指归在动作” 的革命诗学。
① 转引自穆旦: 《 拜伦小传》 , 《 穆旦译文集》 第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8页。
② 高秀芹、 徐立钱: 《 穆旦: 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 , 文津出版社2007年版, 第35—36页。
③ 穆旦: 《 致陈蕴珍( 萧珊)》 , 《 穆旦诗文集》 第2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57页。
④ 易彬: 《 “ 秘密” 的写作——穆旦形象考察(1958—1977) 的一条线索》 , 张炯、 白烨编: 《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卷》 ,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214—225页。
⑤ 李小林编: 《 家书: 巴金萧珊书信集》 ,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第133页。
⑥ 穆旦: 《 拜伦小传》 , 《 穆旦译文集》 第3卷, 第6页。
⑦⑧ 穆旦: 《 蛇的诱惑》 , ( 香港) 《 大公报·文艺》 1940年5月4日。
⑨⑩ 《 圣经》 ( 和合本) ,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年版, 第6页, 第6页。
⑪ 参见梁工: 《 简论该隐形象在欧洲文学中的演变》 , 《 国外文学》 1997年第3期。
⑫ 乔治·斯坦纳: 《 悲剧之死》 , 陈军、 昀侠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150页。
⑬ 拜伦: 《 论〈 该隐〉》 , 《 地狱的布道者——拜伦书信选》 , 张建理、 施晓伟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68页。
⑭㉚㉛㉜ 鲁迅: 《 摩罗诗力说》 , 《 鲁迅大全集》 第1卷, 李新宇、 周海婴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第61页, 第53页, 第47页。
⑮ 彼得·S. 霍金斯: 《 作为文学和神圣文本的圣经》 , 《 圣经文学研究》 第15辑, 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
⑯ 王佐良: 《 英国诗史》 , 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第288页。
⑰ 杜秉正: 《〈 该隐〉 译后》 , 拜伦: 《 该隐》 , 杜秉正译, 文化工作社1950年版, 第13—21页。 参见杜秉正: 《 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 , 《 北京大学学报》 1956年第3期。
⑱ 拜伦: 《 曼弗雷德》 , 刘让言译, 光华出版社1949年版。 此书尚有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 在已有杜秉正译《 该隐》 的情况下, 平明出版社也不好再邀请穆旦重译《 该隐》 。 穆旦翻译的《 拜伦抒情诗选》 由平明出版社1955年推出, 译者署名梁真。
⑲ 哈罗德·布鲁姆: 《 诗人与诗歌》 , 张屏瑾译, 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第98页。
⑳ 穆旦: 《〈 慰劳信集〉 ——从〈 鱼目集〉 说起》 , ( 香港) 《 大公报·综合》 1940年4月28日。
㉑ 穆旦: 《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 《 穆旦诗集1939—1945》 , 1947年自印本, 第177页。
㉒ 《 穆旦晚期诗作遗目》 , 《 穆旦诗文集》 第1册, 第406页。
㉓㉕㉖㉘ 袁可嘉: 《 新诗戏剧化》 , 《 诗创造》 第12期, 1948年6月。
㉔㉗ 穆旦: 《 评几本文艺学概论中的文学的分类》 , 《 文学研究》 1957年第4期。
㉙ Lord Byron,Manfred, A Dramatic Poem,inThe Works of Lord Byron,Vol. IV, London: Thomas Davison,Whitefriars, 1829, p. 1.
㉝㊱㊲ 穆旦: 《 神魔之争》 , 《 穆旦诗集1939—1945》 , 第182—183页, 第185页, 第180—197页。
㉞㉟㊳㊷ 拜伦: 《 该隐》 , 第40—42页, 第123—124页, 第51页, 第137—138页。
㊴ 穆旦: 《 神的变形》 , 《 穆旦诗文集》 第1册, 第362—363页。
㊵ 拜伦: 《 该隐》 , 第54—55页。 这一段话鲁迅在《 摩罗诗力说》 中以文言翻译过。
㊶ 加缪: 《 反抗者》 , 《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选》 , 杜小真、 顾嘉琛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48—51页。
㊸ 姚丹: 《 “ 压抑” 与“ 写作”: 穆旦翻译的诗歌史意义》 , 《 文艺争鸣》 2018年第11期。
㊹ 《 穆旦自选诗集存目》 , 《 穆旦诗文集》 第1册, 第405页。
㊺ 马立安·高利克: 《〈 圣经〉 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 从周作人到海子》 , 刘燕编译: 《 翻译与影响: 〈 圣经〉 与中国现代文学》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第156页。
㊻[52] 诺思洛普·弗莱: 《 两百年后回顾布莱克》 , 傅俊译, 吴持哲编: 《 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366页, 第371页。
㊼ 伯克哈特: 《 约翰·弥尔顿的〈 失乐园〉 及其他著作》 , 徐克容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第345页。
㊽ 艾略特: 《 宗教和文学》 , 《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 , 李赋宁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第241页。
㊾ 海伦·加德纳: 《 宗教与文学》 , 江先春、 沈弘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47页。
㊾ 王佐良: 《 一个中国新诗人》 , 《 文学杂志》 第2卷第2期, 1947年7月。
[51] 本雅明: 《 巴黎, 19世纪的首都》 , 刘北成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