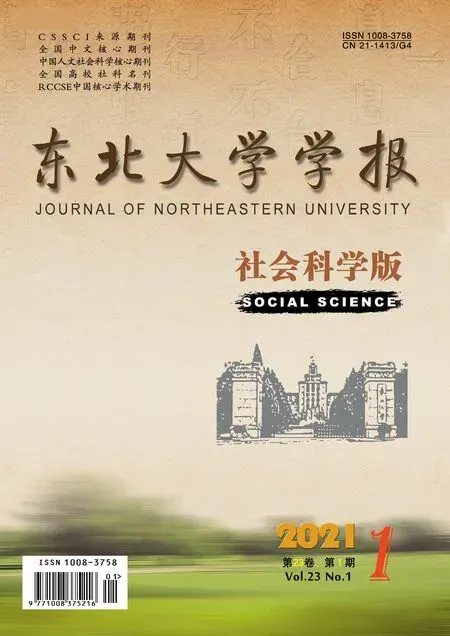《被掩埋的巨人》与电影《潜行者》联动的双重叙事进程
沈 安 妮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在《被掩埋的巨人》(TheBuriedGiant, 2015)中,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者,这成为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是石黑作品中最失败的一部。托比·利希蒂格(Toby Lichtig)将小说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第三人称叙述的使用,称故事的叙述者好像是一位处于当下某一时刻的说书人,“其奇怪而呆板的风格再也无法取得石黑之前的第一人称叙述所营造的那种出色效果”[1]。另一些批评却反驳以上针对小说语言风格的观点,认为小说的微妙之处恰是第三人称叙述者平淡且不加缀饰的叙述话语,以及看似波澜不惊地将一切不加干涉地尽收眼底的陈述,因为这些常被认为是琐碎而无效的、包含大量无用细节的叙述,才是小说深度的隐藏地[2]。
笔者认为, 石黑一雄用了一种与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潜行者》(Stalker, 1979)互文的神话方法和双重叙事手法, 在《被掩埋的巨人》的表面情节中制造了一种以非个性化的客观性为特点的叙事基调,而在隐性进程中则颠覆了这种上帝视角的可靠性----叙述者实际上是来自地狱的摆渡人, 读者被赋予了同鬼魂平行的视野,窥视着这个伊甸般的原初世界。 通过这种一明一暗的、一个徜视一个窥探、一个自天堂一个自地狱的双轨叙事进程在同一种疏离的、看似权威的、非个性化的客观性基调上的统一, 小说展现出颠覆其表面情节所表现的权威性叙述的重要隐含意义, 表达了一种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以及看似客观可靠的现实性的质疑。
一、 与电影《潜行者》互文的神话方法
布莱恩·谢佛尔(Brain Shaffer)注意到,石黑一雄早在处女作《远山淡影》中就用古希腊神话的冥河(Styx)及同名女神,构建出小说中的地貌特征及神秘的鬼女人形象[3]。石黑似乎对希腊神话中的这个冥界与尘世的交界之地充满兴趣。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他再次用希腊神话中与冥河紧密相关的人物(掌管冥河的摆渡人卡隆)来塑造叙述者的形象。借用古老的神话传说和被人熟知的原型人物及历史故事的框架结构来做叙事和情节的基础,从而让小说既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故事,又与远古的诸多原型形成互文关联----这种做法被艾略特(T.S.Eliot)称为“神话方法”(mythical method)[4]。它是被20世纪初以降的许多现代主义者用以建构文本的多重意义的一种便利形式,因为这种方法让现实不再是一系列意义匮乏的无序事件,而使现实与某个被塑形为永恒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产生联系,从而凸显出永恒性的深度。在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看来,现代主义者可以用神话将相互类似又不同的两种意识、两种现实加以并置,而意义恰恰产生于这两者之间的疏通和交流过程[5]。
石黑一雄成为继承现代主义的神话方法的后辈之一。石黑认为,理解并重组神话,进而把它用到创作中,是他身为小说家的一个重要使命[6]。他更在宣传《被掩埋的巨人》期间透露,这部小说有某些西方神话和电影的影子[7]。石黑实际上在小说中融入了一种带有古希腊卡隆神话特点的叙述眼光,营造了一种隐蔽在看似客观、中性的叙述目光背后的可疑性,以此来建构起小说表面情节发展背后的另一层隐性表意轨道和隐含意义。卡隆的名字,在希腊文里与“charopós”一词同源,原意为“敏锐的目光”(keen gaze)。但丁在《地狱》(Inferno)的第三章,将卡隆描绘为一位拥有“愤怒中流露出火焰般凶光的眼睛”[8]并留着胡子的白发老人。这样的卡隆形象被诸多文学及绘画作品采用至今。卡隆的希腊文字面意义就这样逐渐地被延伸为一种对卡隆易怒且不稳定性情特征的指涉。与以往的现代主义小说相比,《被掩埋的巨人》对神话方法的继承与重组的独到之处在于,石黑将卡隆希腊名字中的“敏锐的目光”的意思,回归到其带有视觉性特点的原意中,在小说中展现了一种具有渐入式颠覆性的、介于永恒和瞬时之间的、非个性化及中性的叙述方式。
石黑在小说中将神话中作为人和神之间过渡媒介的摆渡人卡隆,用作一种叙述目光的承载体(即叙述者),并同时赋予这个叙述目光两种表现形式。《被掩埋的巨人》的叙事载体,既是客观的、非个性化的、在故事外记录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又是出现于故事发展的三个关键处的、与埃克索夫妇产生交集的摆渡人。故事中不露声色的神秘第三人称叙述者,具有一种卡隆的“敏锐目光”中所隐含的潜在破坏力和颠覆性。他似乎渐渐地从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的外部潜入到故事里----在小说最后一章突然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摆渡人的身份出现。读者和埃克索夫妇一样,直到最后才意识到,这个看似超脱于世俗的、具有某种永恒性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同时也是主人公在现实中近距离接触到的摆渡人。摆渡人是死神的象征,他的出现打破了夫妇俩原先以为他们的爱情能赢得死神的特赦的幻想[9],也使埃克索直面其过去对妻子的不忠。这也让读者意识到,叙述者先前的缺席,其实是一种伪装。因为随着情节发展的深入,我们发现,看似在故事外的叙述者在故事中有着一个具象的附身----埃克索夫妇前后三次遇到的摆渡人。摆渡人作为一个不引人注目的陌路人,潜伏在主人公的周围,适时地出现。他在随时在场记录的同时,又从形象到观念上隐藏着自己,从而体现出一种有距离的、存在于即时即地的永恒性。
这种利用卡隆神话中隐含的独特视觉性内涵来建立双重叙事的方法,早在备受石黑一雄崇敬的20世纪70年代的欧陆“新电影”导演[10]塔可夫斯基的代表作《潜行者》中就有表现。鉴于石黑曾坦露他在创作《被掩埋的巨人》期间观看了塔可夫斯基的所有电影并深受启发这一事实[11],我们或许能猜测这部新作与《潜行者》在重组卡隆神话上的互文和共鸣,并非偶然。《潜行者》是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根据斯特鲁伽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的科幻小说《路边野餐》(RoadsidePicnic, 1971)改编的电影。石黑的小说虽然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在情节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用了卡隆神话原意中特有的渐近式和颠覆性的“敏锐目光”,来塑造叙述者的双重性。与《被掩埋的巨人》故事内外相互对应的摆渡人叙述者相似,《潜行者》里的叙事载体,既是画面外渐渐逼近但始终与故事人物保持距离的摄影机,又是画面内类似卡隆神话中的摆渡人的潜行者。潜行者一方面是具体参与到现实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另一方面也是具有某种永恒性和非介入性存在意义的电影摄像机。作为主人公的潜行者出现在影片的内部:作为被观察的对象,他是卡隆式的引路人,引渡人们到达理想中的目的地;同时,他也是在镜头视线外部的一个匿名的偷窥者,其目光与摄影机保持一致,引导着观众的观看节奏和思考方式。塔可夫斯基电影中特有的慢镜头,承担着观众目光的向导,它既是叙述者的语言,也是一种在隐秘与渐进中,对他人的精神进行不明用意地侵越和透视的行为。这个视觉的引导者,躲在门廊外面,藏在各种自然的屏障物后面,隐藏着自己;他用缓慢到几乎不能察觉的速度,逼近门内所观察的对象。影片过半,观众才意识到“潜行者”也指涉着存在于故事之外的、在静默中的、不介入也不可见的、同时又与观众视野平行的观察者。我们所看见的故事里的潜行者,则变成了这个隐藏的记录者在画面中的镜像反照和替身。世俗与永恒、被记录者与记录者,于是在主人公潜行者身上得到了微妙的统一。
石黑一雄采用了与《潜行者》类似的方法,一方面将小说故事外全知、永恒的目光,与来自故事内的、即时的、源自极易被忽视的他者的目光交汇统一了起来,另一方面还在故事的表面情节发展中构建起常见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以“不介入、非个性化”为特点的客观性叙述姿态和立场。《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叙述者,在小说大部分的时间中,就像塔可夫斯基的镜头一样,敏锐地将其所见为我们记录在案,但本身却躲在摄影机之外不被人看见。这个叙述者一度被我们认为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永恒性目光的载体。这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小说中颇为常见----叙述者超脱于故事之上,有着上帝般的客观视角。强调情感的零度介入是现代主义小说中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显著特点----叙述者几乎成了一个没有个人倾向性的“非个性体”[12]。与之相似,《被掩埋的巨人》的叙述者在表面上像是一个摄影机式的“中性”记录媒介,展现出一种被艾略特以“非个性化”来定义的、保持着情感距离的现代主义式叙述态度[13]。然而恰是在这种表面上确信无疑的客观权威性视野下,却隐藏着另一层有待被发掘的意义。
二、 小说与电影的共鸣及隐性进程的建构
《被掩埋的巨人》与电影《潜行者》的互文性解读,有助于发现石黑的小说不仅在表面的情节发展中赋予了第三人称叙述一种非个性化的“客观”性叙述基调,还在隐性层面凸显出一种能在文学与电影之间产生共鸣的“中性”美学特点。后者构成了小说中的隐性叙述基调的重要特质。这里的“中性”是指,意义的表现在任何艺术中都应是符合自然现实进程的。即使意义是被人创造出来的,艺术家也应尽可能少地表现意义经由主观意识的加工被刻意地制造出来的痕迹。与其说是意义在艺术中被创造,不如说意义总是隐藏在现实本身所具有的暧昧性当中,而艺术家只需把捉这种自然的、复杂的暧昧性即可。这种“中性”特质,在电影美学家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看来是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以降的现代电影同现代主义小说共享的一种重要的现代审美性特点,它为电影和小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潜在式隐喻”(potential metaphor)[14]。在这种隐喻形式中,艺术家选取的一切意义和细节都与周围的自然连接在一起,并把其试图表现的所有意义以一种中性的、不加干涉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意味着,一部分意义随着自然的进程被观众把捉到,而另一部分意义则被隐藏在这种自然的进程中,需要经过复查才能被人后知后觉地认识。达德利·安德鲁(Dudley Andrew)指出,巴赞的电影“中性”美学看似是通过提倡一种反对象征和抽象的叙事方法,来表现他对那些被单一意义统治的本文的抵制,但其实他是在以另一种方式重建并诠释意义[15]。巴赞一方面反对蓄意的象征(即表面情节发展中的比喻),另一方面又允许(内在和外在的)合乎自然的“交流”(correspondences)与隐喻(即隐性情节中的深意)。
申丹在她的一系列研究[16-18]中提出并不断形成的“隐性叙事进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与巴赞“反对蓄意象征,但又允许内外交流”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观点相呼应的文学文本分析策略。“隐性进程”这个术语本身指示了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的表意轨迹:意义被隐藏了起来,但隐含意义没有出现在叙事的某个特定的局部,而是通过零散的、不起眼的细节来形成贯穿文本始终的另一层叙事流,它与文本显而易见的情节线索并行。“如果说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互为补充时,忽略后者会导致对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片面理解和部分误解,那么当这两种叙事进程皆然对立、互相排斥时,忽略隐性进程则可能会导致对作品和作者创作意图的完全误解。”[19]“隐性进程”的提出,为我们将文学与电影的关联这种文本外的相关内容,再次应用到文本阐释中来提供了一种默许的途径,因为隐性进程的发现,要求读者在反复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作者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与其他影视、文学作品间的互文性等文本外的知识,综合地对文本进行分析。
巴赞和申丹,分别从电影和文学领域,通过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和隐性叙事进程理论,提出了对学术性读者的一种新的预期----期望我们将自传性、跨媒介性、互文性等涉及各种领域的文本外知识带入阐释过程中来,以发现文本中的新意。本文将《被掩埋的巨人》与《潜行者》中混合了神话的叙述特点相比较,不仅能发现石黑小说与电影在运用神话方法以及在建构双重叙事上的互文性关联,还能揭示出石黑小说中隐藏的、与表面情节发展轨道所奠定的基本叙事基调相悖的另一层隐性表意轨道及主旨。无论小说中的叙述眼光聚焦在哪个角色上,它总能以一种置身事外的疏离感与敏锐的精确度,不加批评地记录角色视角周围的一切;它允许事件不紧不慢地自然展开,不仅给读者一种情节与事件紧密联系的感觉,而且还在符合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同时,显现出平时不易被察觉的事实。在小说的表面情节发展轨道上,这个叙述目光里透露着一种在价值判断上无私公正且有意保持客观中立的倾向----叙述者以一种宏大叙事式的、对聚焦人物不施评判不予褒贬的客观立场,来记录自然事件本身;而在小说的隐性表意轨道上,这个目光在跟文本外部的电影的互文及共鸣中也透露着,与读者所认识的故事表面意义相对立的深层反讽意义。
三、 双重叙述目光中的反讽意义
叙述者目光的这种双重特质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以“目光”做引导的开篇段中就有体现。此处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以一种疏离的眼光和去个性化的语言,记录着这个看似充满奇幻色彩的中古世界:“目之所及,尽是荒无人烟的土地;山岩嶙峋,黄叶萧瑟,偶尔会有人工开凿的粗糙小路。罗马人留下来的大道,那时候大多已经损毁,或者长满杂草野树,没入了荒野。河流沼泽上,压着冰冷的雾气,正适合仍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食人兽”[20]3。詹姆斯·沃尔顿(James Walton)认为,这段描写展现了作者惊人的笔上功力。叙述者平静的、祛饰化的语言中蕴藏着与小说的主题相应和的匠心,突显了这个在我们眼前的异样世界,在生活于其中的人看来是多么的平常[21]。除此之外,这段描写的一个更为核心的要义在于,石黑自故事的开始就为其匿名的叙述者植入了一种卡隆目光所特有的“潜在颠覆性”特质。这种特质与“观念域”话语的双重性颇为相似。“观念域”(ideosphere)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根据“观念形态”(ideology)所造的术语,即一套隐含观念形态的话语类型,同时它又是一个论说域(logosphere),尤其强调语言氛围在传递意义中的重要性[22]。这种话语本身,在传达某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能隐藏这种意图,造成一种中性、零度介入的表象。也就是说,这种话语内部隐含着一种无形的统治,它不单纯地属于个人的习惯用语,而隐藏着一种被社群所接受的定见和固有看法。在小说的开头描述中,叙述者也是用这样一种话语,制造出一种权威可靠的、非个性化的客观氛围,邀请读者加入到其背后隐藏的世界观中。我们不知不觉地被这种“虚假”的引导性目光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所同化。
如前所述,之所以说这种目光有“潜在的颠覆性”,是因为石黑用了与《潜行者》类似的重组卡隆神话的方法,在故事的隐性表意轨道上向读者逐渐揭露出,与小说开篇段所奠定的“由上帝权威性视角”引导的叙述基调相反的,另一种像是“与魔鬼一同在暗中窥视”的叙述基调。我们慢慢发现,这个赋予读者视界的全知性目光实际上来自地狱的摆渡人,而读者则像神话里由卡隆负责引渡的鬼魂们一样,窥视着这个伊甸园般的原初世界。石黑督促着读者去发现,上帝与魔鬼的视野在“客观、疏离、权威”特征上竟有着惊人的统一,以此引导读者去思考一个贯穿于他所有作品的主旨问题----“真正能认识生活中的善与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历史常常慢慢地揭露出那些被你深信的价值不过是假象、虚空甚至是邪恶之物,而你所在的社会随时改变着价值取向。被历史留下的你,突然意识到:‘啊,我的生活竟是建立在‘虚无’之上,甚至是‘恶’之上’”[23]。如此,石黑提醒着读者,人们常常不能即时地、清楚地认清眼前事情的本质,唯有通过回忆和自省,才能领会那些曾经被错过和忽略的要义。
从表面上看,《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叙述者站在一个俯瞰的高度记录着事情,但实际上,这个高度并不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上帝般的全息性认知,也不是来自于他的雄辩或修辞的逻辑----他仿佛是通过一种类似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所说的来自盲众的“匿名的专横”(anonymous tyranny),试图让其听众产生对某种“一致性观念的迷信”(the fetish of uniformity)[24]。也就是说,这个叙述眼光,似乎不是源自某个具象化的人身上,它似乎不依附任何特定的肉身存在;它隐身于人群当中,象征着某种集体性的存在和意识。我们可以从石黑一雄本人对小说中被称为“你”的隐含读者的解释中,找到答案。石黑一雄说:
当我小说中的叙述者用“你”来称呼听众时,他永远不是在与读者说话,而是与他的一个同胞说话----史蒂文斯在向另一个仆人讲故事,而凯茜在向另一个克隆人讲故事。读者更像是因为和他们坐在同一个咖啡馆里,而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们与他们的世界有部分重合。《被掩埋的巨人》的叙述者同样用“你”来称呼听众。这个“你”也不是指读者,但这跟以前的作品略有不同。我的想法是,他的听众是复数的“你们”。我想让读者通过一些微小的细节渐渐发现,叙述者所说的“你们”其实是那些在战争中被屠杀的孩子们的鬼魂。而当写到小说的最后,我却因为担心这些会过于抢风头而最终未能完全将其表现,但是我仍然把充足的提示性线索保留在书中。如果大家没有看出来,那也不全怪你们。[25]
如果像作者所说,叙述者是对鬼魂们讲故事,那他一定也来自鬼魂的世界。石黑似乎为建构围绕“卡隆和鬼”展开的隐性叙事线索做足了功课。因为和故事所在的历史背景相关的史料表明,公元5世纪时的古希腊人所描绘的卡隆和鬼的关系,与小说中的描绘类似:卡隆呈现出一副施助者的样子,而“鬼”则好像被其照顾的孩子[26]。这恰与《被掩埋的巨人》的叙述者于表面情节中在埃克索和比阿特丽斯面前扮演的摆渡人角色以及他于隐性进程中在读者面前扮演的“为鬼孩子们讲故事”的角色相符合。读者作为与鬼孩子们一起听摆渡人讲故事的听众中的一员,也被带入到了鬼魅的虚无视野中,而不是从上帝的视角来俯瞰这个世界。另外,被石黑保留下来的提示着故事隐性进程的线索,也出现在接近故事的结尾处----比阿特丽斯对埃克索说:“你从来不去池水的边缘,只忙着与骑士说话,从来没有朝那冰冷的水下看”[20]371。往水下看的比阿特丽斯凝视着无数死去的孩子的面孔。这不仅代表了比阿特丽斯对现实世界本源的感知,还象征了她与正听着摆渡人讲故事的亡灵听众们,实现跨越文本界限的交流时刻。仿佛只有在跟死亡无限接近的过程中(此时的比阿特丽斯因病虚弱不堪),人们才能接近世界的本质。人物与其世界的本源、小说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在冥河的内外互为镜像,无限地交织和联系。
石黑一雄在之前的小说中,通过像《浮世画家》(AnArtistoftheFloatingWorld, 1986)中的小野(Ono)、《长日留痕》(TheRemainsoftheDay, 1989)中的史蒂文斯(Stevens)这样的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表达了人们常由于缺乏深刻的洞见和全局思辨力,而不知不觉地变成将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战乱中“错”与“恶”的方向的社会与个人生活中的失败者。然而在《被掩埋的巨人》中,石黑首次启用第三人称叙述者,并以同一个看似客观和权威性的眼光,平行地传达出两种截然相悖的叙事立场和意义的方式,将同样的问题更便利、更尖锐地抛向了读者:试问我们是否也常常不知不觉地犯着与其角色所犯同样的错误?是否也会因为思维范式的束缚,错过了摆在眼前的意义,而与魔魂同行却不自知?如此,石黑一雄既邀请又挫败着我们对故事中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所赋予的视野的认同力,使我们开始质疑一切所见之物。
四、 结 语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人物与其所在的世界看似存在确实无疑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常在最后被揭示为一种幻觉。在这个幻觉中,也确实如瑞典学院秘书长萨拉·达纽斯(Sara Danius)所言,隐藏着一道引人沉思的深渊[27]。其实,《被掩埋的巨人》中对现实的揭示,不如现实如何被伪装起来显得重要,因为在现实的表面下,小说更强调的是深一层被掩埋起来的、对看似客观可靠的现实及权威性宏大叙事的质疑。笔者认为,这一切通过小说中一明一暗的双重叙事进程得以实现,而这部小说独特地融入了神话方法的双重叙事特点,又跟电影有着跨媒介的互文性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