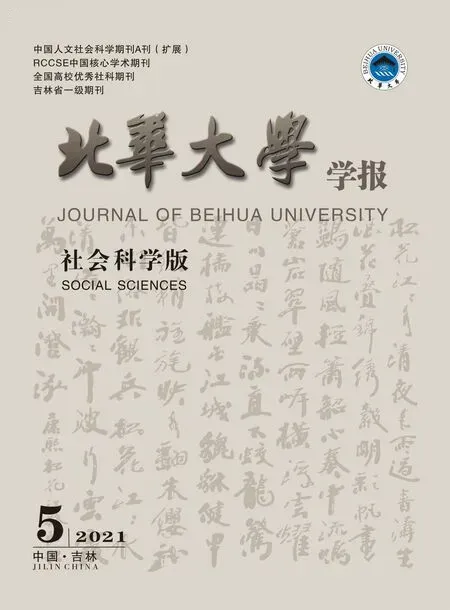甲午战前日本陆军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活动
刘豫杰
引 言
近代日本帝国的“满洲”殖民野心并非是一时战胜的偶发之物,明治维新以来,尽管政军中枢在组织人事上均历经更迭,但“满洲”始终是日本对中国情报活动的核心区域。而从“问题空间”至“调查空间”再到“经营空间”[1]的逻辑递进来看,就更加凸显出近代日本对“满”活动的长期性与一贯性。目前,中日学界对此一问题在宏观上的探讨已可谓汗牛充栋,但鲜以明治时期或情报活动为限定展开论述。(1)如关诚(均省略敬称)虽对甲午战前明治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的情报活动有详尽梳理,但对明治日本的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并无特别涉及,许多在此活动者都未收录其中。佐藤守男和小谷贤的论著则分别集中在日俄战争前后和昭和时期。国内方面,许金生几乎对整个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有着系统性梳理,堪称填补空白之作,只是在明治时代和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两方面着笔较少。张光直的专著也是几乎横跨整个近代,较多涉及军事学和情报学方面的理论。分别参见関誠『日清戦争前夜における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明治前期の軍事情報活動と外交政策—』(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佐藤守男『情報戦争と参謀本部—日露戦争と辛亥革命—』(芙蓉書房出版,2011);小谷賢『日本軍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 なぜ情報が活かされないのか』(講談社,2007);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张光新《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研究》(时事出版社,2018)。因此,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对甲午战争以前明治日本尤其是以陆军为中心的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加以检讨。
一、明治日本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的发起与高峰
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1861年,武田成章就率龟田丸沿黑龙江溯流而上航至尼古拉耶夫斯克。[2]38鉴于其随后入仕陆军,因而似可将此划作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活动的先声。维新后的明治五年,在西乡隆盛与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的商议下,将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秘密派往“满洲”地区,进行地理、政治、兵备、财政和风俗等方面的考察。[3]由于在三人次第归国之际发生了明治六年政变,他们的情报活动及其报告即使对西乡等人的决策产生过影响,恐怕也并不容于尔后的大久保政权,但这无疑是明治日本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的开始。需要强调的是,由池上和彭城提交的《“满州”视察复命书》应当被看作是近代以来日本陆军制作的有关中国东北的第一份秘密调查资料。不过,由于通常将壬午兵变和甲申事变以前的明治日本的假想敌国看作是俄国,[2]28因此,明治初对中国东北的情报活动就被置于北地(通常指北海道和桦台等地)威胁背景当中,考虑到日本在1874年即有台湾侵略与战争准备,在时间线上早于“千岛换约”,那么有关明治初期日本对“满州”情报活动问题的探讨需要再定位。
由于日本陆军在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日本陆军在制度和指导方面的变化自然会投射到情报活动当中。1871年2月,明治政府以萨长土三藩献兵设御亲兵,是为中央陆军之始,而后渐次改组为近卫兵和近卫师团;翌年,在废除兵部省后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4]中央军制初步成型。其中,萨藩构成了陆军中的最大势力,前述由西乡主导的对外派遣既出于此,亲赴一线的情报人员中萨藩出身者更不在少数。1873年政变以后,陆军中的萨土势力自动退出,长派开始掌握主导权,陆军省内先后设立的参谋局和第六局,包括“台湾出兵”是年设立的省外参谋局,担任其领导职务者均为长派军人。如先后执掌第六局和省外参谋局的是鸟尾小弥太,到参谋本部成立之前,海外派遣基本多有他的参与。1873年到1875年间便已达数人规模,指导他们的则是分别与政治情报、军备情报和地志情报有关的甲乙丙三类训令。[5]115-116这种长派独大的趋势在西南战争后被进一步强化:桂太郎在山县的庇护下迅速升迁,大山岩和川上操六虽名属萨派,却无意于自身的派阀势力建设,西乡从道和黑田清隆尽管长期保留军阶,但事实上也是委身在长派势力之下。军令方面,省外参谋局的情报职能已经大于作战职能,[6]但参谋本部的设立才是情报活动得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标志。随着参谋本部的成立,又经欧洲军制视察、内阁制导入、陆军纷议和月曜会事件,由陆军主流派中坚桂太郎和川上操六主导的对清情报活动基本奠定了甲午战前明治日本的对外情报格局。其中,在新建参谋本部的同时便下设管东局和管西局,(2)两局的设立本身是分地域统合作战和情报,此后经过局改部,除了从1896年到1903年改第三部专管情报外,期间基本都延续了最初两局的统合框架。1908年又改第二部专管情报,此后直到战败,情报部门始终在组织上保持独立地位。参见有賀傳『日本陸海軍の情報機構とその活動』(近代文藝社1994年版第23-49頁)。需要提及的是,福岛安正担任专管情报的部长正是在上述第三部期间,因此大江志乃夫的相关叙述有误,见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第84頁)。负责后者工作的便是桂太郎,继建议派遣公使馆附武官后,他又提出《管理将校规则》《清国派遣将校在兵略侦查上规则》和《清国派遣将校规则》[7]3份文件,逐步构筑出与派遣相关的内在框架。而高居次长职位的川上操六也与众多一线情报校尉有着直接联系,其对荒尾精和福岛安正的大力支持正是典型。[8-9]可以认为,甲午战前日本陆军的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无疑得益于相对健全的制度安排和相对稳定的指导体系,而一以贯之的“大陆政策”即覆盖政军指导层上下的共同的战略认识恰是塑造这一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具体到对中国东北情报人员的派遣,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岛弘毅。作为近代以来日本陆军首批“留学”清国的八名“学生”之一,他于1873年12月首次来华,翌年年末返日。在此期间,其经历虽相对单一,主要以语言学习为主,但同行的益满邦介却通过购买获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由英法等西洋人士绘制的京津地区的地图,二人还与同批来华的向郁在天津附近核查地图上的地名。[10]251874年,参谋局再次派遣七名陆军军人赴清,1875年,岛弘毅及向郁等再度受命渡清。岛弘毅在第二次派遣期间的1877年4月开始了“满洲”旅行,因前次池上之踏查主要在沈阳附近,首任驻清公使馆附武官福原和胜便希望能够开展小规模且仅涉及关外风物的侦查活动。最终,岛费时7个月完成了对“满洲”地区主要城市和干路的调查,还通过涉猎《盛京通志》、《圣武记》和《东华录》等文献资料以期相对深入地观察地方情势,更在实地经验上对以往地图的纰漏进行了订正,最后在十一年向当局提交了2卷《“满洲”纪行》,[5]121-123这一资料正是《“满洲”地志》的直接来源。[11]1879年,岛弘毅第三次被派往中国天津,伊集院兼雄则被派往“满洲”地区的牛庄,其余十人散布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和厦门等地,这也是参谋本部成立后的第一次派遣活动。其中,伊集院在驻扎牛庄期间不仅专注于汉语学习,还进行了盛京省内的地理侦查,[5]227为三年之后制作《盛京省东部图》和《盛京省西中部图》,以及参与制作《盛京省南部图》积累起了足够情报和经验。同年7月,时任管西局长的桂太郎为搜集直隶决战的相关情报也亲率校尉渡清,因颇觉不足,第二年又派遣小川又次赴清调查,与小川同行的山根武亮在完成预定任务以外,也对辽东半岛的金州湾和大连湾进行了情报搜集,同时还调查了威海卫在“有事”之际作为“中央屯兵所”的可能性。[10]84紧接着在1881年,前一年刚被任命为驻华武官的梶山鼎介携玉井曨虎前往“满洲”地区进行情报活动,9月在连山关与前文提及的伊集院兼雄相遇,[10]82-83值得一提的是,后文将要述及的酒匂景信也曾在1882年与伊集院兼雄在“满洲”相遇,这类“偶遇”不仅说明了此一时期日本陆军对中国情报活动的高频次,更凸显出陆军指导层对“满洲”地区的重视程度。另外,梶山所述《鸭绿江纪行》同岛弘毅之《“满州”纪行拔书》都曾刊载于《东京地学协会报告》,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1883年至1885年,栗栖亮、仓辻靖二郎、菊地节藏和铃木信分别受命赴满侦查,其中,栗栖从营口出发对辽河的交通和渤海沿海的状况进行了实地侦查,[5]306仓辻因剃发变装潜入宁古塔周边而被捕,[10]84菊地在《“满洲”纪行》中留有甲丁两卷,[10]112-113铃木则是在驻牛庄时一方面搜集“满洲”相关的兵要地志,另一方面对辽河水运进行了精密度调查,[5]460可谓皆有所获。而在陆军以外,职务上分属海军省和外务省的曾根俊虎与町田实一也有在中国东北实施情报活动的经历,此不赘言。通过上述情报活动可知:第一,参谋本部甫一设立,明治日本尤其是陆军的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便随即迎来高峰,且高峰不仅体现在派遣密度上,也反映在所取得的成果中。第二,此期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基本涵盖了“满洲”全域,如伊集院的活动范围大致是在东南部和中部,小川又次和山根武亮是在西部,而酒匂景信则是在偏东部,几近延伸至清朝边境地带。第三,从仓辻的被捕经历可以想见,清政府对日本方面的情报活动并非是丝毫不察无动于衷,不过与日本方面的高峰迭起相比,其应对实在只能说是平平。或许,在19世纪80年代初的“情报攻防”中,甲午战争时的第一军的捷报频频就已经被隐然设定。
二、酒匂景信和柴五郎的情报活动
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陆军的对华情报活动在国内外两方面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换期。国外方面,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在这一时期的变动与英帝国在东亚地区的强力显现“冻结”了日清围绕朝鲜展开的矛盾和竞争,[12]换言之,从壬午兵变、甲申事变到所谓天津条约体系,这些表象上的妥协实际上都有着更为宏观的国际背景。国内方面,在政治上是内阁制的导入和长派势力的强化,在军事上则是松方财政框架下的陆海军扩,以及第二局长小川又次的情报格局再部署,[13]概言之就是在对华情报活动已经达到一定积累的前提下,开始加强对英、俄的情报活动。此后,参谋本部虽仍有小规模的派遣将校渡清,但活动主体已经逐渐转移至由荒尾精领导负责的半官半民组织。当然,这其中未必不存在清政府军备增长和防谍强化的影响。
酒匂景信与柴五郎正是在这种“不振”的大环境下涌现出的情报人员。酒匂景信,1850年生人,旧岛津藩士,幼时曾就学于藩校,有汉学造诣。戊辰之际转战奥羽各地,随后作为御亲兵上京,有教导团和陆士的学习经历,西南战争时亦有战功。1880年与玉井曨虎一道受命来华,此后4年长期活动在北京及牛庄,是继岛弘毅和伊集院兼雄之后又一位专以搜集调查中国北方和“满洲”兵要地志资料为主的情报人员。1884年返国,尔后虽有升迁,但逝年与遗族情形不详。[5]237有资料涉及酒匂与其他派遣人员的联系,但客观来说并没有清晰呈现出其在清侦查的活动轨迹及其调查成果。目前,通过小林茂及其团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调查可知,酒匂的活动范围基本涵盖了北至东北、南至苏北的沿海区域,其情报成果包括:《北京近傍图》、《旅行图一 从江苏省江宁府至山东省兖州府路上图》、《旅行图二 从山东省烟台经黄县莱州胶州安邱县沂州等至江苏省宿迁县渔沟路上图》、《旅行图三 从北京至牛庄旅行图》和《旅行图四 “满洲”东部旅行图》,其中,旅行图三和图四的比例尺分别为二十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图四之中又包括“满洲”东部之图一至四以及“满洲”南郭之图合计共五图。[10]173从前文对比来看,酒匂的情报成果较为集中地体现为地图绘制,少有的文字记录也较为紧凑地书写在地图某一角。以旅行图三[14]为例,该图实际上又分为三份小图,在“三页之内一”中,从右至左依次绘有附带等高线的马兰关、马兰峪和黄崖阁等,比例尺为二万分之一,其间还标有八旗营和米仓的具体位置,左部注记方格内书有数十排类纪行文字,既说明了活动时间和移动地点,也对图中信息有相应说明,而且在指出英制地图中存在的经纬度纰漏后,还将道路景况、村落和人口贫富列入调查条项。在“三页之内二”中,既有桃林口的城池图,也绘出了城外山峰上的瞭望台,比例尺为一万分之一,以当时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手段来看已经称得上精确。“三页之内三”则主要是义州城的城池图,对城内的县衙、城守尉衙、庙、塔、十字楼和米仓的具体位置有着清晰标记,显然有经过实地确认,对于城墙的正面和横阶断面也有特别说明,比例尺为二十万分之一。如果说从上图所获信息仍无法确定该图的指向性,那么《“满洲”东部之图 第四》[15]注记中的“野炮道及小市街”“山炮道及小村落”和“骑马道及散在村落”,包括“城郭”与“兵营”等,还有手绘出的山间密集小道、河网、矿石资源以及渡口和桥梁等,无一不提示出这一系列秘密手绘图的军事用途。需要指出的是,日军在甲午战争期间广泛使用的是比例尺为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而这份地图则是十万分之一。
相较而言,柴五郎的人生轨迹便曲折许多。他于1859年出生在会津若松,十岁时即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次战败,虽是中士家庭出身,少时却饱尝冷暖,直至考入陆军幼年学校才得以改变命运。升至士官学校后,主属特科的炮兵科。[16]在士官学校就学期间,柴五郎就曾拜访有横穿西伯利亚经历的旧幕臣榎本武扬,并向其表露欲前往中国活动的志向。毕业后在近卫大队勤务期间,也曾恳请参谋本部的杉山矢一助其前往中国。尔后,柴既未听取桂太郎的建议报考陆军大学校,也未采纳兄长的意见,终于在1884年来华并驻于福州。[17]244-245驻闽期间,柴在前述乐善堂的门道以外,由自己垫资帮助亲戚开设了一家名为“庐山轩”的照相馆,日常经营以外正可以作为情报人员的一个秘密据点。事实上,化名为武富春的海军情报人员安原金次就曾在1886年伪装成照相师的助手,从而得以公然进入到船政局。[18]之后,柴在例行侦查旅行中被临时调拨与青木一道至北京进行兵要地志尤其是地图的调查,青木在任务完成后随即返国,而柴则在再三请求下终于被许可经“满洲”朝鲜由陆路回国。1888年1月24日,柴从天津出发,渡白河,过芦台,经唐山,到开平城,白天在马车上观察绘图,夜晚则记录和整理,在开平时还登上城东北方二十米高的小丘俯瞰,此间的工作便是他情报活动的常态。过滦州城到秦皇岛后,经观察,他认为秦皇岛周边是攻略北京时的绝佳上路地点。在山海关时,对兵营、炮台和城墙也进行了考察。2月1日出关,三日后抵达锦州城,经大虎山、新民屯和大石桥后,于2月11日至奉天城,与在山海关时一样在城内进行了侦查。13日向南到辽阳,登西向名为首山堡的高地观察地形,随后16日抵营口。20日,从营口出发,经凤凰城向九连城方向移动。[17]295-304至此,柴五郎的“满洲”情报活动大致结束,进入朝鲜后的经历虽不在探讨范围之内,但需要指出的是,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位跨过中朝边境的日本人。从上述过程来看,柴五郎在中国东北的活动时间只有区区一个月,而且就成果来看,目前尚未发现由他绘制的相关地图,仅凭流水账般的移动轨迹,似乎很难查证其情报活动的真实价值。不过,有两点事实应当能够对这个疑问进行解答。第一,柴五郎在起初提出请求时虽未获参谋本部批准,但是得到了身在北京、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局第一课长的山本清坚的认可,既然山本在1897年的来华是为了制定与直隶决战相关的作战计划,那么柴五郎的“满鲜”旅行之所以最终获许,其缘由不言自明。第二,柴在幼年学校和士官学校就读时曾接受过法国教官关于近代地图测量方面的知识,他的测量能力也多次被传记作者村上兵卫称道,而《轻井泽迅速测图》正是由柴领导负责完成,[19]可以认为,柴并不欠缺在此次情报活动中实现产出的能力。另外,酒匂景信曾在请愿书中希望能从“满洲”地区穿过朝鲜回国,终未获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柴五郎的朝鲜之行是一场迟到了五年的情报活动。
从酒匂景信和柴五郎的情报活动历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日本陆军虽然缩小了情报活动的组织规模,但目的和地域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也就是说,地理情报和“满洲”地区仍然是重中之重。而且,军事方面的考量始终贯穿其间,这一点应当是确凿无疑,就连分别适合山炮和野炮的道路都有特别标注,细致至此不得不令人惊愕。事实上日方在甲午战争初始阶段派出的第五师团就早早放弃了运输野炮而临时改为山炮编制,[20]这也能够说明情报搜集在战争中的实际作用。在柴五郎的个人案例中,明显还有两点值得重视:接受过较为专业的近代测量技能培养,有十分强烈的情报活动意愿。不过讽刺的是,同时期日本国内的全国测量和地图制作却进展迟缓,由于人员和经费被大量倾斜到“外邦图”的制作,直到1925年才终于完成了国内方面的五万分之一图。[21]在高度水准的外邦图和制作低劣的国内图的对比中,明治日本的帝国蓝图就此现出原形。
三、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中明治日本的对华认识
芝原拓自认为,若是在“对外观”形成过程中存在知识或情报的不足或者偏颇,那么对外观就只能呈现出与“实像”相对立的“印象”。大谷正在芝原思考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从“情报接收”到“情报加工”再到“世界观的形成”最后到“对外政策或态度的决定”的连锁过程,而且这一过程的结果还会以“反馈”的形式再次参与到新世界观的形成。[22-23]显然,有关对外观或对外认识的考察,很难与其背后的情报或者说是信息相割裂。不过,实际情形还要复杂许多,就本文所探讨的情报活动来看,首先就很难对情报人员的既有认识进行有效分割,其次,情报接收者在情报量上的优势也可能影响其判断取舍,此外,情报活动既然是在持续进行中,那么活动者与接收者的认识未必不会有应时而变的一面。由此来看,在日本陆军的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中探寻其对华认识,至少需要分出两类主体展开论述。
以情报人员福岛安正为例。1879年8月,福岛安正首次渡清,1880年时编成《邻邦兵备略》,同年经山县有朋上呈给明治天皇,十五年和二十二年时还曾刊行第二、三版。1882年再度赴清,与杉山直矢一道在中国沿海进行情报搜集,对各地兵力防卫和风土民情等都有广泛考察。正是在实地见证了清国的腐朽无力后,福岛的信函中开始出现蔑视词汇:豚尾和豚儿。[24]换句话说,至少从1882年起,福岛个人就已经对中国产生蔑视情绪。恰是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福岛在单骑横穿西伯利亚的过程于,于1893年进入到中国东北地区。3月下旬越过俄国国界进入瑷珲,不出所料的是“污物”和“不洁”等印象,当然,他也对驻扎当地的八旗部队有所评估,自然是“军律混乱”。继续行路时,当他看到醉倒在马背上的蒙古骑兵,不由感慨他们的“自甘堕落”。3月27日在墨尔根城外驿站见到齐齐哈尔将军的外出阵仗时,从其规模推测出当地“治安的不良”。在宜拉哈站修整时,又发现负责护送他的士兵们吸食鸦片,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被‘支那’文化同化”后的恶果。进齐齐哈尔城后,照例对当地八旗驻军和城墙进行了侦查,同样也对市街留下了“污物”和“不洁”的评价。在特穆德黑站宿营时恰好遇到一桩诉讼审判,对其“幼稚的裁判方式感到震惊”。出黑龙江省后沿着嫩江向东南进发,在岸边观察了岛上的镇边军水师营。到达法特哈站后,福岛突发高烧,在此期间虽极度不适,却也十分留意周边民情,当看到路过此处的瑷珲副都统之正妻的采买队伍时,认为“‘满洲’的政治已经完全死亡”。5月9日,抵达吉林城,对城中的机器局和弹药制造所有所侦查,还通过与定居本地的英国医师交谈,推测出英国的情报网已延伸至此。出吉林城向宁古塔行进时,从护卫的士官处了解到士兵们普遍有吸食鸦片的恶习,并由此认为清政府的军队已经是“由内而外腐败至极,这将是其自我崩解的主要原因”。当时,宁古塔周边马贼横行治安不靖,福岛一方面对宁古塔的城墙进行侦查,另一方面也留心于马贼相关的信息搜集。随后连过数站,入珲春城,对城内的电报局和靖边军亦有所侦查,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福岛与珲春副都统一见如故,后者在日俄战争时似乎对花田仲之助的活动有所帮助,从这里既可以看出福岛为何对马贼颇有关注,也可以看到尔后日本陆军展开的诸多所谓谋略工作的原型。[25]对比来看,福岛的对华观在1882年至1893年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无论军事还是社会层面,福岛的观察结果始终是以否定性言说为主,这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何福岛会在翌年坚决主战。
作为一线情报人员的福岛自然只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但福岛情报的接收者势必会有更多考量,即后者的对华认识将更为复杂。事实上,在福岛归国的同年10月,山县有朋就提出了一改往昔诸多“谨慎”意见的《军备意见书》。其中,山县在突出强调俄国威胁的同时,认为清政府几无保护蒙古与“满洲”领土的实力,因此当西伯利亚铁路通车之际,即是俄国侵夺蒙古一举进入清政府内地之日。当此之时,法英等国也对清国虎视眈眈,而清政府不仅兵制衰退,军队亦为鸦片所害,全然不知东洋已危机重重。因此,日本只有扩军造舰以期独立,进而改正条约以期对峙于万国。[26]山县在意见书中不仅屡次提及福岛的情报成果,而且从对华认识来的类型来看,也几乎与福岛一致。显然,福岛的西伯利亚和“满洲”之旅是该意见书的一大来源。不过,山县的强硬言论在陆海军指导层中并非孤例,而且从时间线来看也相当“迟滞”。比如在甲申事变后,当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出于现实主义主张谈判妥协之际,桂太郎不仅反对同时撤兵,力陈以大兵先发制人,其间还使用对中国人的蔑称“ちんちん”(音为钦钦)。[27]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早在福岛第二次渡清进行情报活动期间,桂就高度评价过福岛的情报成果,并支援了他的特别侦查费申请。[28]日后与桂太郎并立的山本权兵卫也在两年后的一封书翰中使用了“豚尾先生”和“豚尾海”[29]这样极具诬蔑性的词汇。由此可见,在甲午战争前一年这个关键节点,山县的上述言论恰如高桥秀直所说:“因为山县的转换,陆军实现了对清强硬路线的统一。”[30]毫无疑问,这种广泛强硬论的背后即是对华蔑视的扩散,而强硬论也是山县此前各种态度变化间的唯一出口。
从福岛安正的情报活动经历来看,山县有朋、桂太郎和川上操六这三位明治时期最为重要的陆军指导者都对其有大力支持,而福岛的情报成果本身正是他们政策制定和认识形成的重要来源。尤其是1893年的“满洲”侦查,不仅促动了陆军内部强硬论的统一,也最终确立起清政府不堪一击的孱弱形象,即使这并非甲午开战的直接原因,但至少使日本陆军指导层在战争前夕拥有了战胜自信。仅此一点,也足以说明此次对中国东北的情报活动的重大意义。另外,在福岛和山县的认识中,“满蒙”地区在俄国威胁下被呈现出与中国相分离的态势,换言之,“满蒙”在他们的对华认识框架中更接近于一种“无主”的存在,如果再注意到宇都宫太郎正是福岛安正的门人,那么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也可以在这次侦查中搜寻到某种线索。还需要补充的是,福岛在情报活动中充分留意马贼势力,这种对民间势力的重视既是尔后日俄战争胜利的原因之一,也是辛亥革命以来日本陆军与中国军阀密切交织的预演,更是此后各种所谓谋略工作的原型。[32]
结 语
在黑川雄三给战前日本国防,尤其是国防方针和军事战略归纳出的三点要素当中,第三点就是作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政策”。[31]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中国东北地区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区域。具体而言,明治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关注几乎与明治维新同步,这一阶段对该地区的情报活动虽屡屡有之,但暂未具备制度性保证,在形式上也表现出应对俄国威胁的虚构一面。
参谋本部的成立标志着明治日本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第二阶段的开始,仅从派遣密度来看,在此后的数年间,情报活动就立刻迎来高峰,活动区域不仅覆盖东北大部,也有充分的情报“成果”产出。此一阶段的“地毯式侦查”与“军事性前瞻”充分暴露出情报活动的本来性质。参谋本部在天津条约后的主动调整则是明治日本对中国东北情报活动的又一阶段,此时的派遣规模虽然缩小许多,但从“成果”方面来看却丝毫不逊色,到福岛安正在1893年对中国东北的侦查,日本陆军已经掌握了从军事到社会、从气候到风土的全方位“满洲”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