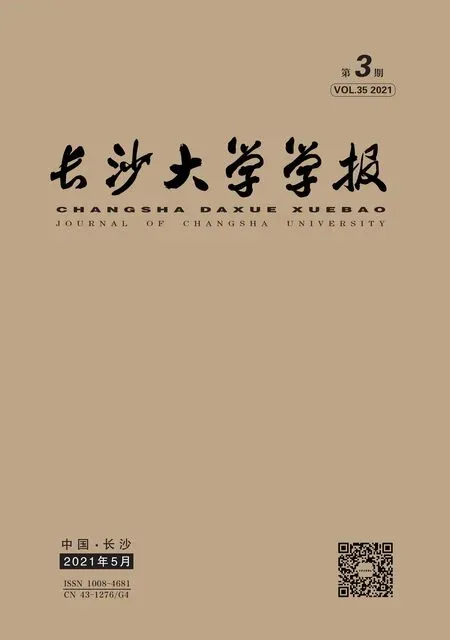文化记忆的展演与地方认同
——以长沙博物馆为例
邓 庄
(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南 衡阳 421002)
地方博物馆是一个包含着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元素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就是运用文化的象征、想象、隐喻等手段,对空间进行文化编码组构,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意义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过程,地方博物馆在此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地方历史文化传播、传承与地方认同的作用。而在文化与科技日益走向深度融合与渗透的当下,地方博物馆还需要借助数字化、影像化、互动化、故事化的表达,进行文化传播的当代性转化,增强公众的体验感,提升文化遗产的社会融入度。
一 地方博物馆、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
德国文化学者阿斯曼认为,文化是一种记忆。文化即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的体系,也表现为一个对各个集体而言统一的价值体系[1]22。这种集体记忆能够被理解为该群体成员的共同生活的文化框架,它建造了单个个体之间的具有群体特色的行为和关系的社会基础,使得他们塑造文化共同性成为可能,并且能够将过往文化的共同知识加以传承。学校、图书馆、博物馆这类文化设施就是建构和传播集体记忆,赋予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公共机构。博物馆将特定的文化物品挑选、保存、展示并传承后世,这些物品关系到特定的文化身份认同,并受到社会或政治的承认与支持[2]7。作为文化和教育机构的博物馆因此具备了保存特定的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从而维护他们的身份认同的职能。
(一)集体文化记忆汇聚地
文化记忆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纪念碑、博物馆、仪式等形式创建,是摆脱了日常并超越了个体间交流的记忆,这种记忆涉及对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有关过去的信息,如关于集体起源的神话以及与现在有绝对距离的历史事件,它们构成了该社会或时代的集体记忆,相关的人通过不同的文化形式来重温这些记忆[3]370。阿斯曼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在时间层面上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在社会层面上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中剥离出来的[4]。基于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对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的认知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能将单个个体与“我们”这个共同体连接到一起。这种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它的产生和维护是“文化记忆”的职责所在。而对于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大众来说,拥有更多清晰定义的轮廓和更多确定的共同文化特征,更容易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
对于如何传承本地域优秀文化传统,构建基于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全球化时代形成一种聚合力,从阿斯曼的理论中可以得到启发,即通过对共同体的历史与文化的不断回忆来论证“集体”现状的合理性。地方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及其信息资源,并且不断提醒人们去重温和回忆,从而成为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的媒介。一个地方博物馆因此成为地方集体文化记忆的汇聚地,一件件藏品成为地方特征的“标志”,组成地方文化的象征和隐喻系统。观众的每一次参观行为,通过对藏品所体现的地方历史的社会体制、行为与活动的解读,意识到共同的属性和他们所属集体的独特性,从而成为“回忆地方”的集体行为,借此确认并强化自我的身份。因此,地方博物馆作为一个地区不断延续的文脉,成为人们认识与了解自我,维持地方记忆,维护地方文化传统,建构地方认同的重要资源。
(二)地方文化活动中心
伊藤寿郎在20世纪90 年代初提出三代博物馆理论,与前两代博物馆不同,第三代博物馆不是以文物保存为首要任务,而是基于地方社会的需求发掘必要的展品,并以民众的参与体验为主轴。随着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步伐加快,推动着博物馆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从传统意义上的收藏、保存、展示的研究机构,逐步向融地方历史文化、建筑、藏品和人文精神为一体的文化景观转变,通过不断拓展文化与社会服务领域,成为与社会公众持续互动演进的特色空间,扮演地方文化活动中心的角色[5]。
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提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的主题,倡导博物馆提高跨界和“超级连接”的新能力,从而融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当前,我国地方博物馆的功能与角色还在不断拓展,流动展览、博物馆出版、文化创意等业务迅速发展,且在文化、教育等功能之外兼具休闲、娱乐功能。通过设计以展览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元化活动体系,开展俱乐部、讨论组、音乐会、示范表演等活动,地方博物馆不断拓展多元化的传播地方文化的手段,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走进博物馆、体验博物馆的选择,这也将使博物馆成为地方文化活动中心或社交中心,对建构地方认同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二 长沙博物馆的展陈叙事与地方认同
博物馆是记忆的载体与媒介,其路线规划、展品选择、展陈设计、历史叙述等元素构成了符合某种历史话语的叙事系统,集体记忆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生成并塑造参观者的文化认同。长沙是历史上唯一经历三千年历史城址不变的城市,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楚汉文化以及湖湘文化底蕴,又称“楚汉名城”。长沙博物馆共有四层展厅,一、二层四个展厅为基本陈列——“湘江北去·中流击水——长沙历史文化陈列”,以长沙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城市发展变迁为主线,以长沙出土和征集的精美文物为主要载体,综合运用精品文物、辅助展品、图文版面、雕塑、复原场景、视频、互动游戏、多媒体展示装置、触摸展品等多种方式,讲述长沙故事,彰显长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华文明、湖湘文化发展的贡献,激发人们对地方认同的想象。
(一)路线规划兼具整体性和开放性,实现知识引导,提供自由诠释空间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陈列展览同样在利用历史材料构建一个表达当代价值思想的话语系统[6]。博物馆中的展示策划是一个重构现实的过程,它是策展人依据自身的立场来重构一段“文明的痕迹”,因此需要将包罗万象的物品用一种叙事逻辑进行排序,以此达成对特定群体有意义的知识引导和身份建构,这成为博物馆营造记忆的重要途径。
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以时间为序表现长沙从原始的村落慢慢形成城的概念,然后形成国,再回归到城市的发展历程。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按时间先后表现近代百年长沙人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古代长沙部分重在以物说史和证史,表现长沙地方文化的悠久深厚;近代长沙部分则重在以人带史,凸显长沙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两者以1840年为界划分成两个篇章,“在时间上一线贯之,在内容上紧密联系,但在空间上又相对独立,各自成篇”[7]。整个线路设计采用传统线性叙事结构,清晰而缜密。策展人对大量的知识和材料进行筛选、辨别,构建出一个完善的整体,使参观者在游览时对长沙历史文化有一个总体印象和全面认识,从而建构一种地方认同。
这也是国内博物馆通常的做法,即将参观路线的规划纳入自身的意义结构中,采取闭合的流线引导参观者完成参观,这样的路线规划自然意味着参观者要接受博物馆叙事的暗示、启发、隐喻和教育的过程,体现出一种对参观者的知识引导。然而,博物馆叙事所提供的地方认同资源,所激发的地方认同想象最终必须依赖参观者的接收与接受,一旦参观者的叙事加入博物馆叙事之中,就会改变参观路线的单向性和唯一性。长沙历史文化陈列分成四个展厅,没有严格的参观路线限制,既没有对于空间上跨越边界的禁止,也没有规定的参观路线和次序,每个厅的出入口均可自由进出,观众可以自由地选择参观路线,也可以随意地决定从哪里开始和在哪里结束,为观众提供多样的读解可能性和自我诠释的自由空间。由此长沙博物馆的路线规划赋予参观者更多选择,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同时数字化设施、移动终端也帮助参观者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如参观者利用APP提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展品来参观或临时更改路线,就可以抛开博物馆展陈所设定的叙事逻辑,以自我体验和个人兴趣为依据,构筑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叙事。
(二)以地方特色鲜明的实物文物为基础,展现地域文化发展水平,建构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认同
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最显著的传播优势在于它的实物性,策展者运用说故事的能力,将移入博物馆中去脉络化的物件,经过串联整体脉络的知识来加以再脉络化,从而建立历史与现实、未来的关系,实现策展人意图。长沙博物馆的最强音是长沙本地传统文化,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分湘江晨曦、青铜之乡、楚南重镇、大汉王国、湖湘首邑、明清府城六个部分,集中体现长沙的本土传统文化,它突出地表现在博物馆的展品选择、展陈设计、历史叙述等一系列展陈话语系统中,形成了长沙城市认同的象征性文化资源。
长沙博物馆从近5万件藏品中遴选出了上千件地方特色鲜明的代表性展品,包括新石器时期南方最精美的彩陶彩绘鸟纹双耳罐,商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乐器象纹大铜铙,最早能成编演奏的商代青铜编铙,楚国称霸争雄时庞大的剑、戈、矛阵列,长沙国文物陈列组合,唐代长沙窑瓷器系列,长沙城市考古恢宏遗迹五代码头、宋代涵渠及坊市遗迹复原等[7]。这体现出策展人有意识地安排和建构的特征:一方面用这些文物的美感和工艺佐证长沙当时高度的文明发展成就,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文物在年代顺序上的关联来追溯其文明发展的线索。
如策展人选择吴氏长沙国渔阳墓出土的乐器、漆器,曹撰墓出土的铜镜、玉璧,刘氏长沙国“张姬”墓出土的金饼、铜灯、漆器等一批珍贵的西汉王室文物再现长沙国的辉煌历史,勾勒出大汉王国的文明史;以唐墓出土的秘色瓷、定窑白瓷等做工精良、纹饰精美的器物,反映晚唐时期长沙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当时社会风尚的发展与变化。展览中采用的墓葬发掘品和日常用具发挥了一种历史证物的作用。通过从原始的石器和陶器向更加精致的金属用具和瓷器的过渡来展示文明发展的进程,也引导观众由此产生这样的理念:长沙地方文化在古代就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
场景搭建和还原作为一种展示形式能通过引入更多的展示手段和多样的媒体、空间效果,为观众提供展览感知的新渠道,从而使得博物馆提供的传播效果更加丰富。长沙城的城址三千年未发生变化,这不仅成就了长沙在世界城建史上的奇迹,也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展览方开展了城市中心考古遗址的搬迁保护、复原展示,通过各时期文化堆积层、晚唐五代时期码头、宋代官署街坊建筑基址、明王府建筑遗址与城墙遗址等大量城市生活遗迹,真实再现长沙城市发展特性。
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强调一种科学性的研究视角,即展示物质证据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历史叙事。展品多数围绕着自身展开表达,并说明以其为代表的同类物品的文化和物质特性,而并非作为一种神话性话语系统去表现策展人的特定思想理念,因此观众不会被强制去接受策展人规定的解读方式,而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感知角度和方式去对展览信息进行自主的解码和阐释[2]117。也就是说,这些展品被巧妙地纳入讲述长沙本地历史文化的修辞之中,通过展示各种历史文物以重构和再现长沙历史文化的完整发展进程,印证长沙的地域文化发展水平和特征,由此向市民提供充足的为自己的城市文化感到骄傲的理由,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认同。易言之,展览方通过传播并宣扬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在市民当中唤醒一系列积极情感,如家乡情结、安全感、满足感和骄傲感等。
(三)借助影像的力量,个人真实物品的见证,表现长沙人在近代史上的作用
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分倡导经世、引领新政、辛亥首应、建党先声、秋收起义、团结御侮、和平解放七个部分,按时间先后表现近代百年长沙人在重要历史时期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和不畏艰险、勇立潮头的湖湘精神,从而引导观众建构起对长沙的地方认同。
照片在历史叙事中具有作为事实的佐证和连接人类记忆与情感的功能,它将曾经存在、发生过的某个场景及人物“定格”成我们凝视的对象,使历史事件的发生显得更真实,它又具有与记忆完全吻合的凝结时间与空间的特质,能唤起记忆与情感,因此成为博物馆展示中必不可少的角色。
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中展陈大量文物实物,而近代历史文化陈列中更多的是图片和文字资料,整个展览中一共使用1 250件(套)历史文物和2 400多张资料图片,可见图片的比例较高,其中很大部分分布在近代历史文化展厅中。走进这个展厅,在视觉上占据优势比例的是各种类型的历史照片、图片和图表的复制品,多数被安放和悬挂在观众视线高度附近,在视觉上受到更优先处理。如抗日演剧队在长沙街头演出,救护队为负伤战士包扎伤口,长沙举办救亡歌咏会等的老照片,其创作更多是抓拍而成,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现场感,传达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现场气氛。也有一些照片如合影,表现力不强,以静态和摆拍为主,承担历史叙事的功能有限。近代展中还采用了一些油画、版画的复制品来表现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但它们不是原始的历史文物,也不是艺术作品的真迹,其表现历史情境真实性的效果有限。另外还运用纪录片、电影等影像资料表现当时的历史,如观众可以在液晶屏上点击欣赏《南京大屠杀》《八百壮士》《风云儿女》等抗日电影及歌曲,增强展览的形象感染力。
近代展中出现了一些表现了个人生活状态,从而更“接地气”的物品,如陈龙骧烈士使用过的笔筒、龚杰烈士使用过的压书板、陈季临烈士使用过的毛毯、贺尔康烈士在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期间的笔记本等实物,这些留下个人名字和生命轨迹的物品见证或佐证了一段真实经历,与那些出自传承目的而被刻意完成的证据或传统不同,由于未加修饰和夸大,反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采用讲述小人物故事的叙事手法,能牵动观众的好奇心与同情心,从而带出历史议题,拉近展览与观众的距离。如对杨展烈士赴延安前写给父亲的信的展示中,策展人试图在对人物生平调查的框架内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和重建这些被展示个体的个人历史和命运。近代展中还展出了长沙的潘桂清女士给前方将士的慰问信:“我为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所以忍痛鼓励我的丈夫参赴前线作战,在5月以前,我已得悉他光荣地牺牲了,我痛惜,但不悲悼,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牺牲是伟大的,是光荣的……我现在只恨家庭的牵累,不能学木兰的壮志,抱恨终身。只有虔诚祝你们奋勇杀敌,为几千万被难同胞报仇,收复我们中华的大好山河。”这里讲述了她的个人命运是如何被战争改变的经历,也表达出普通百姓所抱持的家仇国恨的真实情感。由于这样的个人生活经历本身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因此其信件在博物馆展示中不需要更多的美学或媒介强化,已经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历史证物的价值。
(四)强化多媒体展演,注重互动和体验,唤起观众的主体性参与
注意力成为信息社会的稀缺资源,博物馆必须与各种文化机构和媒介形式展开竞争,争夺公众注意力。多媒体和互动性能有效唤起公众注意力,国内博物馆大量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交互设计等信息技术,通过角色扮演、互动游戏、虚实对比、富媒体呈现等方式展示藏品、传播智识。
在日益强调用户体验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体验”成为博物馆的核心,博物馆具有了非常感性的环境,装满了不只能看,还能听、摸、闻的东西。在“活态历史”的模式下,观众还能与之交谈互动,参与布置任务、游戏等一系列活动[8]175。长沙博物馆制作了石器与青铜器可触摸展品,让观众在触摸中感受历史;在青铜之乡展区设置了“铙乐悠扬”,让观众亲手敲击电子屏幕上的铜铙,动手演奏乐曲;在汉代展厅设计了“汉趣屋”,让观众体验汉代的投壶、射覆等游戏,瞧一瞧穿上汉服是什么模样,体验席地而坐是什么感觉等。这些展陈设置加强了观众与展品之间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让人们在互动、体验中了解长沙故事、感受长沙人文。
VR、AR等新技术的运用使长沙博物馆的陈列语言日益丰富,文物展示形式出现新的面貌和特征,向更有互动性、浸入程度更深的展示模式过渡。如清代长沙城街道模型结合了AR互动,还原老火宫殿、九芝堂、太平街等代表性地点的当年情景,让人感受古今变迁;“文夕大火”、长沙会战等综合多媒体场景以声、光、电结合运用渲染了当年的悲壮历史。可见,策展人除了精心挑选吸引人的主题和展品之外,必须去关注展览的美学和体验的设计,因为其所造成的感官体验和美感印象会在极短时间内影响观众注意力,激发观众兴趣。
数字互动设施不仅能增强展览的生动性和可感性,更能实现多重空间的重组,创造一种新型空间,使观众进入一种全新的展览境界。此时观众利用智能手机等进入由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构成的虚拟空间,此时人的身体又处在博物馆的实体空间中,人的感官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这种贯穿虚实的身体体验,不仅提供了更充分地展示博物馆文化意义的途径,更使得游走于博物馆空间的观众成为博物馆叙事的主体。如长沙博物馆利用AR技术,开发“云观博”手机APP,多样化呈现文物知识。公众用手机扫一扫感兴趣的文物,就可收听语音导览,查看文物信息,开展留言互动,查找相关文创产品。结合此项AR产品,长沙博物馆还举办“AR寻宝”等新颖有趣的活动,吸引观众前来探索。
长沙博物馆的APP、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数字化空间还建构起一个工作人员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进行互动的场域,提供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连接、转化、交互的可能。博物馆可以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发起讨论,组织集体活动等,也为观众的主体性参与提供了更多可能。
三 结语
博物馆是具有保存集体记忆和建构文化身份功能的文化机构,其历史展示最适于直观传达特定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认同。长沙博物馆定位为本土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播者与城市形象的塑造者,对服务于当下的地方形象和地方认同具有形塑和资源供给的功能,它试图通过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与文化资源,增进市民对长沙的了解,激发内心对长沙的认同感,同时作为城市文化的窗口,为外地人塑造其心中的长沙印象。其对展品的选择和阐释、对展品知识的体系化建构,均体现了博物馆叙事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呈现,激发了地方认同的想象。而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创设了沉浸式互动体验情境,唤起和鼓励了参观者的主体性参与,并与参观者的新媒介技术使用结合起来,提升了博物馆的社会融入度,这就使得地方认同并非以权威训谕的方式而是以渗入融汇的方式作用于参观者,开拓出更为包容和协商的认同机制和更为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