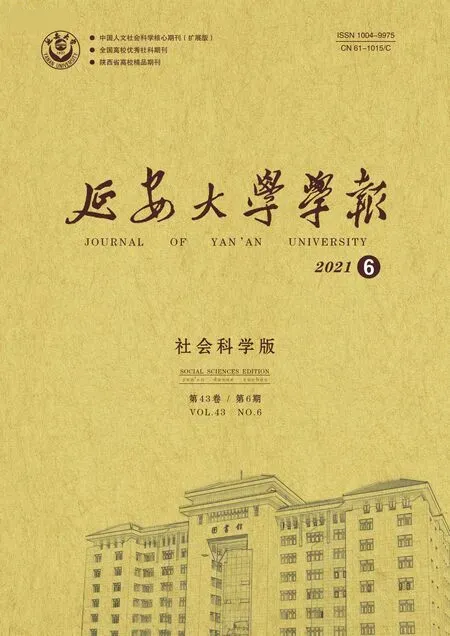论农村社会场域关系的象征性结构
——基于甘肃省两个村庄合并实践的思考
王喜斌,蔡国英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象征性结构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概念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场域既关照宏观意义上作为整体的社会性结构与运作逻辑,又关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心态结构的个体成员的情感、秉性、意愿及行为模式。因此,从根本上说,实践行动所构筑的社会场域(政治场域、生活场域、教育场域、文化场域)具有多面向的象征性内涵与意义,场域存在的客观关系也具有象征性的构型。笔者作为熟悉而又陌生的“他者”,生活在甘肃庄浪县这片土地,旨在透过社会主客位视角阐释当地农村社会场域在社会实践行动中所生发出的诸多象征性结构。一旦将这些象征性结构表达出来,村民日常生活世界所包含的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思维态度、情感秉性、惯习倾向、行动模式将得以显现,这也是一次耐人寻味的社会学考察。
一、田野点及两个行政村合并情况概述
庄浪县隶属于甘肃省平凉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六盘山西麓,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全县共18个乡镇、1个城市社区、293个行政村,总面积1553平方公里,总人口45.16万人。庄浪人文历史悠久,素有“文化之乡”“书画之乡”的美誉,群体文化活动广泛,尤其以正月“迎神”文化活动为代表的各种特色文化展演活动而闻名远近,是“全国文化模范县”。
本研究的田野点位于该县辖区内的陈峡村(以下简称A村)和王家山庄村(以下简称B村),也是笔者的家乡。A村属庄浪县良邑镇一个行政村,全村下设三个社,280余户,共约1300人。一社和二社村民主要属“陈”姓,是A村的主要姓氏,除此之外,还有“苏”“王”“周”“苗”“杨”等十余个姓氏团体;三社属“李”姓,集中居住于“李家岔”。B村原亦属庄浪县良邑镇一个行政村,距离A村约2公里,包括三个社,180余户,约800余人。一社和二社均属“王”姓,同属一个祖先,经过不断地发展演变,至今形成了20余个未过“五服(1)五服:本指以亲疏为差等的五种丧服,后演变谓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身五代。”的亲属团体,分布于“塬上”“巷子”“上街道”“上大场”“新院”“下街道”“下大场”“东坝”“场嘴”几个主要地方。三社属“文”姓,集中分布居住于“文家沟”。2009年之前,A、B两村作为独立的两个行政村而各自存在着。这一时期,除教育之外,两村之间在政治、生活、文化等领域少有交集。2009年,两个行政村“合二为一”,原本作为独立“行政单元”的B村合并成为了A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其所属的一社、二社和三社成了A行政村的四社、五社和六社。至此,原本“不相往来”的村民们也开始在政治、生计、文化等领域有了既具“务实”性,又有“象征性”的实践行动,两个原本独立的社会场域之间也因此产生了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的象征性结构模式。
二、实践行动中农村社会场域关系的多面向象征性结构
布迪厄认为,任何社会成员所面对的场域,往往采取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和表达方式:第一,由现实的社会生活所构成的实际存在的场域,这种类型的场域中,各个组成因素和相互关系都是实际的物和无形精神因素;第二,行动者和社会学家所看到、所观察到的实际场域与第一种实际存在的场域相比,这种场域形式虽具真实的客观存在性,但更多是夹杂着行动者和社会学家的主观感受;第三,行动者和社会学家用语言和概念所表述的场域,是以人们所独有的语言和概念等象征性形式所表达的场域结构,相较于前两种场域形式,这种场域更具有象征性结构特征。笔者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视角,尝试通过透视不同形态的社会实践模式,构建并阐述农村社会场域关系的多面向象征性结构。
(一)政治生活实然一体:实践行动的“社会制约场”
布迪厄认为:“人们固然可以选择自己所考察的特定场域对象,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空间中,这些作为对象的特定场域,它的存在并不是有明确的边界和界限。”[1]161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各场域之间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上的明确界限,也即是说,社会场域本也不具有作为实体性存在的现实可能与意义,只有在赋予其一定的象征性内涵与元素时,才能架构起作为实际存在场域的内涵意义与运行逻辑。
“社会制约场”的概念源出于布迪厄所认为构成社会象征性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的“社会制约性条件”。作为社会场域双重意义结构之一的“社会结构”,其最大的功效就是为个体行动者的心态结构及其运行提供一种规范性制约,即提供“社会制约性条件”。因此,作为“社会制约场”的社会场域对行动于其中的个体成员的行为模式产生着强烈的影响,也为他们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政治性社会动员”。“人们甚至可以说,当社会行动者们决定自身的时候,只有在这个限度内,社会行动者们才是被决定的。”[2]这表明了“社会制约场”存在的客观性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依实际状况来看,村庄场域在扮演“社会制约场”这一象征性“角色”时,具有现实意义上的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具有行政功能的作为独立“行政场域”的行政村,另一种是行政功能依附于其所属行政村而作为“子场域”的“自然村”。不管是哪种存在形式,其场域内涵、性质、独立的运行逻辑以及彼此交错的运行关系都表现出了“社会制约性条件”的意义与功能。
未合并之前,地缘关系构成了两个村庄客观存在的关系网络,各自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场域”而存在,村民们行事各守一方“政治秩序”,在属于自己的“辖区内”参与政治生活。前文已述,B村属单姓宗族村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乡土文化特色依旧浓郁,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熟人社会”。以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来看,“熟人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无讼”,B村村民一直坚守的就是这种内生型的“无讼”政治秩序。在这一秩序框架下,“礼治”替代着“法治”、面子机制(熟人机制)掩盖着行政机制。因此,面对婆媳矛盾、邻里争吵,乃至打架斗殴等事件,村里一般都是请有威望、大家共同信服的年长者进行“家长制”调节,而不是选择“行政干预”的手段加以解决。这一时期,对于B村来讲,“外来的‘行政嵌入性秩序’与乡村在地化的‘内生型秩序’之间在围绕地方性社会进行一系列互构和重组之时,村落社会的公共场域往往成为两种不同力量进行博弈、整合的主要实践场,其形成的不同的关系形态,产生着不同的社会秩序建构效果”。[3]与B村不同,A村属多姓组合村庄,是一个典型的“半熟人社会”,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表现出的是一种“夹生”状态。一直以来,村支书记和其他主要村干部都是由人数最多的陈氏村民来担任,因此行政决策难免有“精英主义”之嫌,长此以往,在各方利益的驱动下,不同的姓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时起、纠纷不断。在这种复杂的村庄结构与事务形态中,“无讼”的行政逻辑变得黯然失色,村庄不得不依靠制度的合法性,即行政干预的办法来有效维持社会秩序。
2009年,两个行政村“合二为一”,作为行政村的B村至此结束了作为独立行政单元的历史,成了A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两个“政治场域”间的界限至此被打破,原本分别构筑在“礼治村庄”和“乡政村庄”之上的村庄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也随即发生了变化。A行政村的政治性决策因B村村民的直接参与而很快打破了原有的“精英主义范式”,B村的“礼治秩序”和“长老统治”[4]更是不复存在。村民们的政治生活至此走上了一条归并路,两个村原本不相往来的村民们也因这次“政治联姻”而开始有所交往。正如B村的一位村民所说:“没想到自己竟能成为隔壁村的人,也没想到原本以为不可能说话的人却说上话了。”依戴维·伊斯顿的观点来看:“政治运行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时刻互动,其运行状况受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交互的。”[5]合并之后,两个原本属于不同场域的个体成员因政治生活上的频繁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嵌于合并后的村庄场域,使得政治生活由合并前的“各自为政”到合并后的“实然一体”,互构出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制约场”,并以生发出的共有政治能量管辖影响着两个场域个体成员的行为模式。
(二)教育实践双向互动:共有精神的“归并包容场”
场域概念的最基本因素,是多面向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多面向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场域的基本构成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架构或形式,而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的和可能的(潜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固定下来的和正在发生(进行中的),以及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各种因素的结合”。[1]138布迪厄这一观点清晰阐明了场域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并且这种精神性存在的生成并不是“与时俱来”“与时俱有”的,往往综合着历史的和现实的、掺杂着实际的和可能的因素。“共有精神场”作为农村社会场域关系中重要的象征性结构,指涉人们在历史的、现实的生存实践中以及未来的心态展望中表现出的集体情感、态度、观念上的价值沉淀。任何场域中的这种“价值沉淀”,一方面是在不同场域的区分和被区分中进行自我区分和相互区分,另一方面又是在各个场域的自我区分和相互区分中存在,这样一来,作为“精神场”的各场域就具有了象征性的内涵与意义,彼此间的关系也就具有了象征性结构。
互动理论认为,在共同的社会世界中,人们共同出现,共同关注,使得社会关系处于一种“永恒的互动”之中。[6]在永恒的互动中,“社会结构系统需要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什么条件、提供什么支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7]这表明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强化,相互支持的关系,乡村学校作为“乌托邦”的存在和“村落中的国家”(2)参见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应该是“他者”眼中农村社会世界的精神彼岸、也是乡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内涵的朴素构想与认知的“始发地”。布迪厄说:“教育工作生产着作为值得在物质或符号方面消费的对象的合法产品(即令人崇拜、喜爱、尊敬、欣赏的等等),也生产着在物质或符号方面消费这些对象的愿望。”[8]这里的“崇拜、喜爱、尊敬、欣赏、愿望”可通约为个体成员稳定的精神心态,指向共有的精神底气。因此也可以说,以学校为实体的公共教育场域孕育着,并在发展变化中不断地再生产着人们的“共有精神场”。
两村未合并之前,都有属于各自的学校,孕育着各自的教育实践、寄托着各自的教育期望,是两个村庄各自“精神资本”和“精神气质”的主要符号表征。这一时期,村庄成员在教育上的持续互动受各自村庄社会结构的制约,同时互动本身又不断重塑并强化保持着已有的结构。B村学校是一个只有四个年级的“初小”,早年间,人们教育观念还比较薄弱,加之繁重的农业生产以及丰盈家庭经济收入的需要,大多数孩子在上完四年级后会辍学务农或者外出打工。A村学校是一个规制健全的“完小”,B村未辍学的孩子上完四年级后会转学到A村继续完成小学学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每年的学区统考中,相较于A村同年级的学生,B村学生的成绩总能名列前茅,这也一直是B村村民们为之乐道和骄傲的事情,正如B村的一位老教师感叹说:“咱们村人虽穷,但在念书上,咱们的娃娃一直很攒劲”。由于拥有规制健全的学校,A村村民显示出了精神上天然的优越感,只是这种优越感随着乡村学校的“集体没落”而逐渐被削弱,这一时期,两所学校各自表征着属于自己场域内的精神象征,折射出了一种着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互动交集的双面向社会关系网络。
2009年,两个村合并之后,B村的“初小”也随即归并到了A村的“完小”,组建了一所全新的小学。至此,原本既互相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两个“教育场域”彻底打破了彼此间无形的界限,以“教育”为媒介对本来“异质”的两个村庄场域进行“精神导入”,成为了两个村庄共有的精神场所,成为了人们精神象征的核心价值点。“结构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导致社会期待的内在化”,[9]在一次“小升初”考试中,B村的一个孩子以全学区模拟考第一名、正式考第六名的好成绩为学校赢得了荣誉,这时的荣誉再也不是B村独有的荣誉了,而是两个村庄共有的精神骄傲。以归并包容的教育场为象征的人们“共有精神”,凝聚着人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想象、寄托着对美好教育生活的最初期望、吸纳并包容着两个村庄社会的各方教育主体,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形塑着两个村庄场域精神领域的整合与团结,表现出了一种归并包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生计生活异质独立:生存心态的“客观外化场”
“不断变化的各种场域,不过是象征性地相交叉的无确定边界的实际场域,在行动参与者面前表现出来的象征性结构。每个场域的存在以及各个场域的特殊运作逻辑,只有在各个场域的参与者看来才是稳定和具有特色的。”[10]由此可知,各场域独特的结构模型和运作逻辑是场域内行动者共同思维情态和行动模式的内化“结晶”,同时,具有这一特性的场域也向其他场域“外化”性地展示着自己成员的稳定“生存心态”,构成了象征着个体成员生存心态的“客观外化场”。
作为生存心态的“客观外化场”既内化着不同场域行动者稳定的“生存心态”,也交融着行动者交流互动的实际策略。高宣扬教授认为,“生存心态”综合着行动者的行动风格、心情、情感和行为模式,与实际的交际策略联系起来,“生存心态”可理解为行动者的精神状态、举止心态、品味爱好、语言风格和行动模式的综合。在生存心态的关照下,个体成员的先前经验结构使新的经验结构化,以保证自身心态的稳定,抵御它在新的信息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因此,生存心态是行动者互构具有象征性内涵和结构的“客观外化场”的社会学动力,也是“客观外化场”作为场域存在与运行的基本逻辑。
“村落作为一种‘集体’话语、记忆和体验形式,使得‘村落集体’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重要的生产生活依托和价值归属,无疑会产生强有力的历史性和传统性。”[11]生存心态是历史和传统的产物,当行动者在“生存心态”这样一种由过往历史和传统实践中积累的稳固生活法则内在化而来的力量引导下进行行动时,既不会感受到必须遵循的外在必然性压力,也无须在各种内在主观意识和自我动机的驱使下做出选择。
未合并之前,两个村的村民之间就有生活生计上的交流与交往,只是在这一时期,人们还习惯性地以自己村庄场域内的成员身份自觉保持着稳定且具有特色的思想情态和行为模式。B村属单姓村庄,村民同属一个宗族,因此在关系称谓和婚丧嫁娶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俗特点。在关系称谓上,和自己直系血缘亲属同辈的人们,习惯于保持和自己直系血缘亲属相同的称谓,如和自己父亲同辈的村民,习惯称他们为“爸爸”。在婚姻嫁娶上,即使是已经出了“五服”的家庭,也不得在同村联姻。若遇丧事,得先请“总管”(3)总管:红白喜事等事务中负责总体事务的人,一般由村里较有威望的人担任。全权负责丧葬事物,再按“地缘”划分请部分“劳客”(4)劳客:红白喜事中请去帮忙的人。去“代劳”(5)代劳:意指帮忙。,出葬当天,几乎所有男性村民全部出动前去“送丧”。相比较于B村,A村是一个由诸多姓氏组合而成的“多姓”村庄,因此在社会称谓和婚丧嫁娶方面没有B村的诸多“讲究”和“过程”,更趋同于现代性的城市模式,A村的村民常常笑话B村村民生活过于死板守旧,B村村民也时常“嘲讽”A村村民生活太过潮流前卫,以至于将民俗村约忘却在脑后。这一时期,两个村庄是各自成员在历史性的遗留和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只属于自己内部成员的“客观外化场”,象征着各自村庄场域独有的向外“符号”和成员独特稳定的“生存心态”。
生活的同质性和相对封闭性是乡庄社会生活场域的典型样态。费孝通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2]两村合并之后,村民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也随之增多,过去陌生人之间“礼尚往来”的客套与生分虽逐渐被“自己人”的那种熟悉与温情所取代,但村民们原本异样强烈的生存心态没有因为村庄场域的组合和成员互动交流的加深而有所或“弱化”和“趋同”。在婚丧嫁娶等关乎“村计民生”的诸多领域,两村村民仍旧保持着各自原有的思维情态和行动模式,既没红白喜事等事务中的合作互助,也没有大小节庆中的人情往来,正如A村的一位村民所言:“两个村子合并十多年了,在这方面却一点都没有变化,还是你唱你的戏、我打我的鼓,互不相干。”这也证明了“生存心态”的相对稳定性会导致实践行动在客观情境的变化面前可能会出现一定时间的滞后性,行动者的预期行为只能得到消极回报,而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四)文化活动交融互动:惯习倾向的“交错表演场”
每一个场域中,行动者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属于自己的“惯习倾向系统”。行动者的“惯习倾向”和场域是一种互动关系,具有场域性,因此只有在一定的场域内才能发挥作用。另外,特定的“惯习倾向”借助于一定的惯习策略,构筑出了不同场域之间“交错表演场”的象征性结构关系。
“交错表演场”一方面展现着各个子场域社会结构背景下行动者的思维习惯、情感取向、行动模式和力量关系,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因各个场域的互动交融而展现出来的共有性情、秉性、习惯和惯习策略。
格尔茨认为文化模式为社会的和心理的过程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程序,用来塑造公众行为。[13]吴文藻先生认为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各方面的结果……是一个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由此看来,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结果,既源于生活,又指导生活。[14]因此,文化及其“文化场域”折射出的物质、制度、精神三元结构的丰富性内涵与外延才能作为“确凿证据”有力阐述作为“交错表演场”的农村社会场域特性及其象征性内涵与结构。
未合并之前,两村以各自的村庄作为独立的文化场域,文化活动保持各自鲜明的特色。以正月的“迎神”节庆活动为例,B村“迎神”活动中的“游庄”(6)游庄:“迎神”活动中“神像”游转村庄。仪式主要以“人抬”为主,社火展演以“马社火”(7)马社火:马社火又叫“马故事”,圆实的骡马披上艳丽的被褥,由小孩子装扮成历史故事人物后端坐其上,凭脸谱、服饰及装扮者手中道具辨识故事情节。为主;A村的“游庄”仪式主要以“车载”为主,“彩车”为社火展演的主要形式。一方面,以“迎神”活动所构筑的公共文化场域显露出了两个村庄社会发展的“硬件”条件。B村村庄“硬件”建设相对落后,村庄道路普遍弯曲狭窄,大型车辆无法通过,因此“游庄”只能选择“人抬”的方式,同时,B村还相对保留了以“骡马”为主要生产工具的较“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因此能为“马社火”的展演提供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比较而言,A村“硬件”建设相对发达,村庄道路宽敞顺直,车载“游庄”和彩车展演也得以进行。另一方面,两种截然不同的“迎神”活动方式也反映出了两个文化场域内人们相对稳定的性情系统和惯习策略。B村村民全属王姓,同属一个祖先,人际关系表现出了涂尔干笔下“机械团结”的协作模式,这为“抬神”和“马社火”展演需要大量的人力协作提供了坚实的条件;A村属多姓组合村庄,相较于B村,社会关系和人际格局呈现出了较分散“有机团结”的模式,因此“迎神”活动也多选择不需要太多人力配合的彩车展演。
合并之后,两个村的文化互动表现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状态。除各自进行自己普通的“迎神”活动外,不同的参与对象和行动主体也会因循着惯习的传统并加上自己的认知与理解,进入到文化互动场域,在各自盛大“迎神”日进行交错展演,彼此庆祝。正月初五是A村的“迎神”日,B村以“兄弟”村的身份,派出自己独具特色的“马社火”队去展演庆祝;正月初九是B村的“迎神”日,A村也已“邻居”村的身份派出自己的彩车队参加庆祝。在这一过程中,在政治意义上原属一个“行政场域”的两个自然村既保持着各自独立的“文化场域”,又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交错表演场”性的场域象征性关系,行动者的文化实践活动也既表现出了各自的文化特色与个性,同时也展现出了两个场域个体成员共有的文化秉性和价值趋同。
三、结论与展望:迈向农村社会场域结构的社会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研究从来就具有关怀“自己社会”的学术情怀,带着“固执”的热爱与迷恋,参与到自己熟知的社会,重新理解本来熟悉的“陌生”世界,以此表达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场域运作逻辑,但作为一种阐释农村社会场域结构与实践关系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尝试,个体化的例证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向层面上的不足与局限。第一,实际存在的场域同语言表达出来的场域之间的关系误差。作为客观存在的实际场域,并不是靠语言上表达和描述就可以客观地说明和呈现。高宣扬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和实践操作关系到语言在描述和分析以及概括过程中对于任何语言对象的修正,[1]161强调语言概括及其各种表达方式同事实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各种社会场域包含着复杂的关系因素,同时也与人们的各种实际“无关利益的利益”相关联,作为“在场”的“主位”者,笔者以自己家乡的“实际状况”为例,论述农村社会场域诸多的象征性结构关系与实践,存在着“当局者迷”的认知假象,因此所做的描述与实际的场域状况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二,对场域关系的实际认知与论述方式之间的关系错位。关于这一点,布迪厄特别强调研究者在论述其观察成果和感受时所惯用的文风和修辞法的重要性。以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社会场域的关系性问题,势必存在着理论、方法、范畴、语言风格和实践认知上的错位,对同一场域和不同场域间的结构与实践关系研究有着“技术”上的实际影响。
研究虽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与局限,但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结论性的观点和展望。
第一,农村社会场域关系的象征性结构不过是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及其创造力的一种存在形式和运作表现。因此,象征性结构的运作也是实践行动的基本形式。一定的实践行动构建了一定的象征性结构,同时所构建出的象征性结构又会生发出新的象征性实践,并保持巩固着旧有的实践行动,复次循环。
第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社会场域关系在原有结构与体系基础上完成了改造与创新。具有普适性价值的主流模式与地方性实践之间实现相互兼容状态的互动与构建,已然成为农村社会场域关系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旨归,也势必会为“并村”实践及其治理提供理论与行动上的双重指导与借鉴。
第三,在探索时代性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其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唯其如是,农村社会场域的结构关系与实践模式才能不仅保留其古老而朴素的传统文化意蕴,又能彰显其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