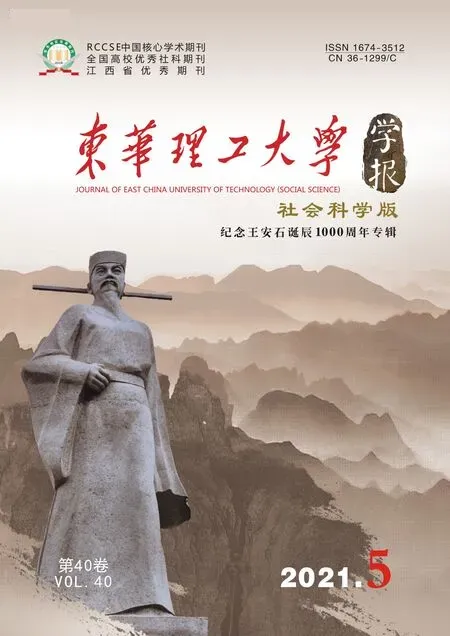论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和他者重构
——以自寓植物诗及历代评价为中心
刘泽华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王安石出生于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抚州),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潜心经学,著书立说,创立“荆公学派”,引致“疑经变古”思潮的兴盛。王安石也推崇“新故相除”的古代朴素哲学思想,并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抨击时弊,反对逸豫,极力主张变法。诗歌创作前期呈现瘦劲刚健,晚年趋近雅丽精严,酷好引经据典,颇有移风易俗之志,在北宋诗坛自出一家,又称“王荆公体”或“半山体”。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是王安石对于自己仕宦生涯进行深刻检视的重要思想结晶,而王安石文士形象的他者重构,则是外界对于王安石的多重认定。可以发现王安石文士形象的书写素材不仅存于王安石以及同代、后代文士的诗歌、词作、文赋、传记、书信等文学创作,还牵涉大量的正史、别史、杂史等史学著作,将这些重要文献记载进行“抽丝剥茧”式的耙梳,可以让我们窥探出王安石文士形象的整体创构以及流变过程。
1 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执拗的君子
王安石是儒家中的变革派,宰相中的读书人。金性尧先生曾在《宋诗三百首》评价王安石为“一个有定见有魄力而又有缺点的杰出政治家”[1]92-93,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客观公允的识解。王安石通过很多的植物意象诗歌,塑造出自我认知的文士形象。这些作品既不是应制、唱和之作,也不是机械的描摹、刻画之作,而是饱含着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情感。
1.1 “孤桐式”的自我肯定
王安石《孤桐》是一首托物明志的五言律诗,南宋李壁补注评曰:“凌霄而不屈,言桐身之条直。公似自况云。”[2]602以冷僻的孤桐形象自喻,表达出作者誓将熙宁变法进行到底的信念与决心,并建构出一个坚定的变革者的形象。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2]602。
梧桐树,天然就长得繁密茂盛,拔地高达二三十米。直冲云霄,不屈服不低头,这是因为深深扎根于大地的缘故。树龄越久树根越壮实,阳光越炽烈枝叶越浓密。即使身处政治清明的盛世,也要有甘愿为解除民瘼而奉献的精神,如果需要就把自己砍伐制成五弦琴吧。“孤桐”是王安石文士形象的真实写照,以“凌霄”表现自己高远宏阔的人生追求,用“五弦琴”表现自己九死不悔的人生信念,背后隐藏着的是王安石昂扬的政治决心与坚毅的政治魄力。譬如,《史记·夏本纪》有一段关于孤桐的记述:“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通于河。”[3]71-72“孤桐”是峄山地区作为贡品进献给大禹的,也是圣洁的象征,表达出诗人“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4]154的自我期许和肯定。面对变法所遭遇的种种打击,王安石矢志不渝地实践着自己强烈的政治担当及历史使命,为了国家的命脉、黎民的生计,即使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王安石笔下繁多的梧桐形象之所以能够岿然屹立、直入凌霄,正是因为“得地本虚心”,让它可以从土壤中汲取养分、能量。如果树根离开大地,那么“孤高几百寻”也会成为枉谈。又如《秋日在梧桐》:
秋日在梧桐,转阴如急毂。冥冥蔽中庭,下视今可暴。高蝉不复嘒,稍得寒鸦宿。百绕有诗(一作衰)翁,行歌待春绿[2]286-287。
秋天梧桐,从树荫蔽日到稀稀落落。之前是因为枝叶繁茂,能够遮掩庭院,而现在树叶飘零,致使稀松处可以透光。“冥冥蔽中庭,下视今可暴”,南宋李壁补注评曰:“日如车行之速也,向苦桐阴之繁,今则疏而可暴矣。”[2]286“高蝉不复嘒,稍得寒鸦宿”,“高蝉”即高处鸣蝉,“寒鸦”即寒天老鸦,因为蝉的不再鸣叫,而使乌鸦获得短暂停歇的机会,实际是借“蝉”“鸦”来暗喻北宋新旧党争。“诗翁”应指王安石自己,说明作者虽年事已高,但内心充溢着创作的热情、灵感,利用诗文创作的契机,表达自己能够重新披甲上阵去完成治国思想与理政实践的愿望。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希望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终极目标。由于部分不合时宜的政策以及执行不当的操作,导致变法步履维艰,直至彻底失败。至此,封建社会越来越趋向凝固与僵化,进行有益变革的空间与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1.2 “古松式”的自我欣赏
王安石《古松》是一首七言律诗,作者借咏松而言己志,间接突显出自己“高大挺拔”“足堪大用”之意。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2]890。
古松的枝干高耸入云,有好几百尺。直冲青天深处,孑然独立于山林之外。夜间山壑,吹拂来松涛阵阵,月冷千山,悬挂秋月与阴云的夜空。这哪里是肥土的栽培力,自是依靠大自然造物化育的仁德神功。假若朝堂宗庙缺乏栋梁之材,就需要取用古松之木,但是如若没有技艺精湛的高明工匠,就请求别去砍伐它。
王安石《酬王浚贤良松泉二诗》其一《松》:
世传寿可三松倒,此语难为常人道。人能百岁自古稀,松得千年未为老。我移两松苦不早,岂望见渠身合抱?但怜众木总漂摇,颜色青青终自保。兔丝茯苓会常有,邂逅食之能寿考。不知篝火定何人,且看森垂覆荒草。君诗爱我亦古意,秀眉昔比南山栲。复谓留侯不及我,人或笑君无白皂。求仙辟谷彼诚悮,未见赤松饥已槁。岂如强饭适志游,封植苍官荫华皓。赤松复自无特操,上下随烟何慅慅。苍官受命与舜同,真可从之忘发缟。诗虽祝我以再黑,积雪已多安可扫?试问苍官值岁寒,戴白孰与苍然好?[2]119-120
王安石“古松”立意高俊,立身高洁,既具思维的感性,又具处世的理性,是其宦海生涯与文士形象的最真实写照。王安石在变法前,默默地积累学问,积攒人脉,积聚声气,渐渐收获到朝堂内外的信赖和褒奖。《宋史·王安石列传》评道:“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5]543无论是仁宗朝,还是英宗朝,王安石多次婉言谢绝朝廷任命。
王安石以“古松”自寓,字里行间足见其自信与自负,又如《前日石上松》:“前日石上松,斸移沙水际。青青折钗股,俯映幽人砌。蟠根今鬯茂,落子还苍翠。三年一楮叶,世事真期费。”[2]288一棵质优的松树,如果没有遇到一位擅长雕刻的“良匠”,那还不如不去采伐它。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个真正懂自己的君王以及一个真正属于自身的时代……
1.3 “梅花式”的自我感知
《梅花》是一首五言绝句,王安石以梅花的坚韧品性与高洁品格来暗喻自己。表明作者即使身处艰难恶劣的环境,依然能够坚持操守、伸张正义,为国家的安定富强而不畏排挤和打击。在王安石顿挫波折的政治生涯中,两度任相又两度辞相。这首《梅花》就是王安石二次罢相后,退居江宁钟山所作: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2]1023。
墙角的几枝腊梅,冒着严寒独自盛开。远远望去,好似一堆白雪。但是作者知道并不是雪,因为有阵阵暗香扑面而来。前两句写梅花不惧霜寒,傲立独放,后两句写梅花纯净洁白,香气远播。以雪喻梅,句意妙绝。通过阵阵暗香,又点出梅胜于雪,更加突显梅花的高洁品性,烘托出作者倔强清幽的内心。冒着严寒盛开的梅花,是不畏风霜雨雪的。只有待到怒放之时,传来的香气才会提醒人们自己存在。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宋诗概说》指出《梅花》可看作“敏锐而狷介”的王安石的自画像。
此外,王安石还写过一些借咏梅而抒己志的诗歌:
春半花才发,多应不奈寒。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2]1024。(《红梅》)
白玉堂前一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唯有春风最相惜,一年一度一归来[6]712。(《梅花》)
江南岁尽多风雪,也有红梅漏泄春。颜色凌寒终惨澹,不应摇落始愁人[2]1087。(《红梅》)
亭亭背暖临沟处,脉脉含芳映雪时。莫恨夜来无伴侣,月明还见影参差[2]1086-1087。(《沟上梅花》)
独山梅花何所似?半开半谢荆棘中。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守蒿蓬。亭亭孤艳带寒日,漠漠远香随野风。移栽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颜色空[2]353。(《独山梅花》)
这些小诗韵味隽永,语言清新,丝毫没有雕琢痕迹。或写梅花高洁孤傲的品性,或写梅花不惧严寒的胆色,与王安石对自我的期许很是契合。这样的王安石,注定是孤独的。王安石的孤独不为人知,也不愿为人知,这与自然界的梅花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1.4 “杏花式”的自我寄寓
通过对上述诗歌的剖析,不难发现王安石喜欢用“孤桐”“古松”“梅花”等类型化的植物来书写自己形貌。除此之外,他还有部分带有自述性质的杏花诗,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塑造的自我文士形象。如《北陂杏花》以杏花的高洁品质自况:
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2]1084。
前两句以形写神,写杏花被春日的池塘水畔环绕,独自在枝头绽放,芬芳飘香,身影妖娆,颇具柔媚、清韵之美;后两句离形写意,写杏花宁可被春风吹拂,化作洁白的飘雪,最后随流水而消逝,也不愿被路边纷乱、喧嚣的车马碾成尘土,沦落尘俗,表现出王安石杏花式的孤芳自赏的隐逸情怀以及刚强耿介的性格特征,与王安石内心的政治抱负相一致。如作于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时期的《杏花》:“石梁度空旷,茅屋临清炯。俯窥娇饶杏,未觉身胜影。嫣如景阳妃,含笑堕宫井。怊怅有微波,残妆坏难整。”[2]22前半段言水面花影尤佳,突出花影之美远胜花本身。后半段言水波起而花影乱,联想到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国破家亡的遭际,前后风情殊别,寄寓着王安石内心憾叹、忧伤、落寞的愁绪,这与王安石政治仕途的蹭蹬、浮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凋零的杏花实际就是王安石政治生涯的一种“植物比德”式的主观映射。
又如《次韵杏花三首》组诗,以杏花表达自己对政治知己的渴求。其一:“只愁风雨劫春回,怕见枝头烂漫开。野鸟不知人意绪,啄教零乱点苍苔。”[2]1227其二:“心怜红蕊与移栽,不惜年年粪壤培。风雨无时谁会得,欲教零乱强催开。”[2]1228其三:“看时高艳先惊眼,折处幽香易满怀。野女强簪看亦丑,少教憔悴逐荆钗。”[2]1228孤独倚墙的杏花,可以看作是王安石的化身。杏花呼唤知音的处境,也是王安石心情的真实写照。很多权臣都反对熙宁变法,王安石身处孤立无援境地,屡屡碰壁,非常渴望得到政治知己,因而常有“野鸟不知人意绪”的寂寞之感,就像倚靠墙头、静待撷取的杏花竭力追寻声气相求者,但是终究知音难觅。如作于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的《杏花》:
垂杨一径紫苔封,人语萧萧院落中。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2]1261。
熙宁变法遭到“旧党”强烈反对,王安石政治仕途也无奈终止。诗中杏花便寄寓着王安石晚年的情志,通过题写杏花,表现自己虽败犹荣以及愿意为变法献身的坚定意志。又如《杏园即事》:“蟠桃移种杏园初,红抹燕脂嫩脸苏。闻道飘零落人世,清香得似旧时无。”[2]1228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5]10550的理念,让王安石在“天人”“古人”“他人”三者关系里重建自我,体现其无怨无悔、执着坚毅、果断勇敢的文士情怀。当王安石深刻感受实施变法的重要性,才会倾吐“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的感慨。当变法遭遇挫折,王安石心中彷徨不定,才会产生“闻道飘零落人世,清香得似旧时无”的愁绪。当自己政治理想彻底无法实现,王安石又发出“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的寄寓,于是辞相归隐江宁钟山“半山园”,希冀过着洗削浮华的“真我”生活。
我们从王安石植物诗歌里“孤桐式”的自我肯定、“古松式”的自我欣赏、“梅花式”的自我感知以及“杏花式”的自我寄寓的书写之中,可以全方位地看出王安石自己建构出的一位“执拗的君子”的文士形象。
2 王安石文士形象的他者重构:孤寂的改革者
王安石个性坚强,情感丰富,然而虚心不足,意气用事。在历史变迁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毁誉参半,有的评价甚高,有的极尽贬损之能事,有的保持中立态度。本文以自宋以来重要文人对王安石的评价为线索,从比较客观公正的视角出发,以综合研究方法进行宏观剖析,力求把最真实的王安石文士形象呈现出来。
2.1 王安石的正面文士形象
对王安石褒扬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以及道德品性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王安石本身拥有杰出的文学成就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其二,评价者和王安石拥有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目标、政治理想;其三,评价者出于一种敬重乡贤的优良传统。
北宋曾巩描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7]248对王安石文章的“古雅”作出肯定;对王安石文学成就进行评价的还有苏、黄等,苏轼对王安石文章赞不绝口:“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8]1077从王安石文章的学识深厚、思辨性强、辞藻多变、风格卓绝等方面作出评价;北宋黄庭坚评道:“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9]696从性情、风度方面对王安石作出肯定评价;南宋陆九渊评价甚高:“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10]232从操守、道术方面对王安石作出评价;清代蔡上翔引南宋无名氏的“高识宏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宋朝百年以来所未有者。”[11]329从推行“熙丰变法”的利民程度方面对王安石作出肯定评价;近代梁启超更是认定“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12]5“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12]5,分别肯定了王安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杰出贡献。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杰出文学成就与高尚道德品质为后世文人所推崇,这也让王安石的正面文士形象出现在很多文史作品中。
2.2 王安石的双面文士形象
一些古代文士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持中立态度,既肯定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与道德品质,又对王安石的执拗性格、执政能力以及变法的不妥之处进行批判。但是这些观点基本停留在品评王安石的个性上,并不妄议王安石的人品。
北宋宰相韩琦认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5]10553指出王安石作为翰林学士是非常称职的,但是作为宰相就有些不妥;北宋谏臣唐介认为:“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5]10329“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5]10329虽然王安石好学,但是论议迂阔,让王安石执政,则天下必乱。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政敌,王安石需要改革的地方,司马光必定反对,但是司马光对其依然给出比较公允的评价:“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13]245
同样认为变法带来不利影响的,还有南宋理学家朱熹:“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5]10553但是针对王安石的文才与品德,朱熹也不否认,认为其“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5]10553。近代吕思勉先生评价较为公允:“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14]405-406
综上所述,对王安石的中性评价多认为王安石文学素养丰厚,但政治谋略不足。
2.3 王安石的负面文士形象
自古以来的变法都会面临着重重阻力和不确定性,而锐意进取的王安石势必会引起多方力量的阻挠,所以对王安石的贬低以及毁谤也就在所难免。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兴利益集团不断动摇既得利益集团根基;二是王安石成为政治党争或思想流派相互攻击的牺牲品;三是王安石变法客观上给社会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四是王安石过于专注的工作习惯以及过于疏放的生活习惯。
北宋朱光庭认为:“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恃宠养交,寖成大弊。”[15]10583更有严有禧者,把王安石与奸臣并列:“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16]6南宋罗大经也认为:“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17]49而明代《警世通言》认为王安石是“异类”,百姓都想“烹而食之”,以解胸中之恨。
北宋苏洵《辨奸论》描述王安石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18]272认为其生活行为怪异,不拘小节。北宋吕诲也认为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5]10553,外貌看似厚道,内心奸诈无比,高度怀疑王安石是乱臣贼子。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认为:“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19]257由于王安石的改革思想过于超前,加之依靠政府力量强制推行,逐渐从不与民夺利演变为与民争利,失去民意的可靠支持,非议自然不能断绝。
3 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与他者重构的异同处
王安石以德性立身,以学识行世,以仁惠为念,只是因为思维超前,忽略现实的客观状态,导致非议不断。但是大部分非议集中在介甫的个性上,并不妄议人品。把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与他者重构进行横向对比,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出王安石的整体文士形象。
3.1 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与他者重构的相同处:“君子之争”
王安石在《孤桐》《古松》《梅花》及《北陂杏花》等带有自述性质的作品里,对自我评价基本都含有褒义成分,或抒发自己孤独苦闷的心绪,或抒发自己坚贞高洁的品格,或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境遇,或抒发自己孑然一身的性情,或抒发自己遗世特出的姿态。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也有很多文人肯定王安石的政治功绩与文学成就,如北宋的曾巩、苏轼、黄庭坚,清代的蔡上翔,近代的梁启超等。尽管王安石变法的实践效果不佳,甚至可以说与变法本意背道而驰,但是不管新党还是旧党,更倾向于“君子之争”而并不是基于“意气之争”的相互倾轧、相互攻讦。“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5]10541严格自律的王安石用实际行动证明,没有赏心悦目的外貌,但是可以拥有厚重的精神积淀;没有左右逢源的性格,但是可以拥有坚毅的品格力量。王安石一生几乎没有私敌,和同僚结怨也是因为对变法持不同意见。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20]141同代人很少能理解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他是孤独的;而现代人对王安石感到十分亲切,他又是欣慰的。
3.2 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与他者重构的相异处:“不相兼容”
从宋代始,就有很多批判王安石的声音,攻击对象包括王安石的个人性格、变法的具体措施等[21]。北宋朱光庭认为王安石“破坏祖宗法度”;明代《警世通言》把王安石视为“异类”,百姓都想要“烹而食之”;清代严有禧认为王安石“扰民致乱”。上述评价完全否定王安石对历史的贡献。可以看出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与他者重构发生一定的分歧,而分歧的产生与王安石自身的性格因素以及变法的不相容性有着密切联系。
王安石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但是操之过急,“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6]795。只认定一个长远目标,而忽略实现目标的过程,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变法的超前性与现实的落后性、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都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近代前,对于王安石评价是以贬损为主,而在近现代对于王安石评价以褒扬为主,这就在客观上解释了为什么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变法超前性与现实落后性的矛盾体。加之自身性格的缺陷,又触及官僚贵族阶级的根本利益,最终让变法措施从保境安民逐渐走向扰民乱民[22]。
4 结语
王安石以文学成就彪炳千古,更以政治改革的标新与思想学说的立异而影响深远。通过大量的自寓诗歌创作,一方面王安石书写出真实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也倾透着准确的自我认知。而历代文士们对王安石褒贬不一的评价,也从众多侧面为我们塑造出一个更加鲜活生动、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从开始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到晚年归隐钟山,无所羁绊,登山临水,勾留古今,发出了“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的慨叹,王安石的一生沉浮宦海,可用一句话暂且概括:一位执拗的君子,一次孤寂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