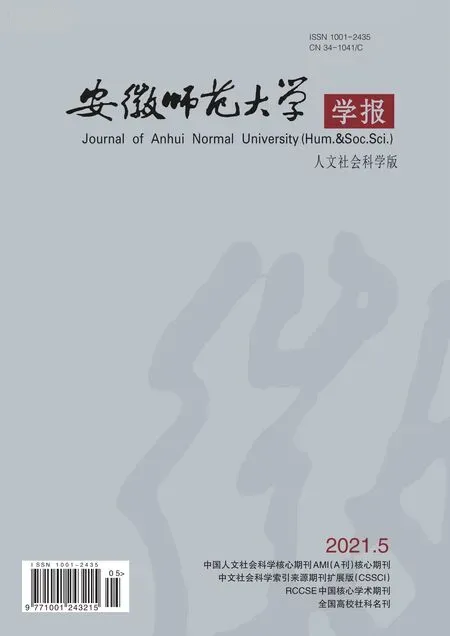1949—1966年香港话剧创作研究*
胡文谦,胡星亮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97;2.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23)
1949年至1966年,是当代香港话剧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香港话剧舞台出现创作落后于现实、剧本落后于演出的严重情形。香港话剧发展需要新的剧本,可是写剧本的人不多,并且创作者还大都是老一辈剧作家。这一时期香港反映现实的创作剧也不多,大都是演出古装剧和翻译(改译)剧。但是尽管如此,身处香港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戏剧家仍然在艰难地推进香港戏剧运动。他们努力创作剧本以延续香港话剧的血脉,他们努力开展学校戏剧运动以培育剧坛新人,从而在那个特殊时空中萌生了“香港话剧”(属于香港的话剧),对香港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目前最需要的是创作”
回顾1949至1966年间的香港话剧舞台,人们感慨最多的,就是戏剧人才和戏剧作品的贫乏。话剧在香港,从1911年“清平乐”“镜非台”剧社成立,演出《庄子试妻》《金债肉偿》等剧算起,其起步并不晚;然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香港话剧长期处于文明戏阶段。直到抗战爆发,随着夏衍、欧阳予倩、胡春冰、阳翰笙、宋之的等戏剧家,和中国旅行剧团、中华艺术剧团、中国救亡剧团等戏剧团体的南下香港,他们把内地的《保卫卢沟桥》(集体创作)、《前夜》(阳翰笙)、《春风秋雨》(阿英)、《夜光杯》(尤兢)、《群魔乱舞》(陈白尘)、《黄花岗》(夏衍、胡春冰等)、《雾重庆》(宋之的),以及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带到香港剧坛,才使香港观众感受到真正的话剧艺术。同时,李援华、卢敦、朱克、鲍汉琳、陈有后等香港原先在内地学习戏剧或受内地戏剧影响的年轻人,也纷纷组织剧团或在学校开展演剧活动,促进了话剧在香港的发展。1941年底香港沦陷,香港话剧舞台也随之消沉。抗战胜利后,内地部分戏剧家赴港组织中原剧艺社、建国剧社,演出夏衍的《芳草天涯》、陈白尘的《升官图》、以及贺敬之等的歌剧《白毛女》,加上本地剧人和战时留下的内地剧人的演出,香港的话剧活动逐渐恢复。但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因内地戏剧家陆续北归以及香港与内地意识形态差异的彰显,香港的话剧活动又沉寂下来。尽管在此前后有姚克、胡春冰、徐訏、柳存仁、贾亦棣、黎觉奔等戏剧家相继南下香港,还有香港本地的李援华、卢敦、朱克、鲍汉琳、陈有后,以及从海外归来的熊式一等戏剧家,然而真正创作剧本的寥寥无几。又因为当时在香港创作话剧剧本不能维持生存,这些人都是业余从事话剧创作,并且他们都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老一辈戏剧家,年轻人创作剧本的几乎没有。
由此带来这一时期香港话剧作品的贫乏,尤其是缺少新创作的剧本。姚克曾经在多个场合谈到这个问题,指出:“经常演出话剧必须有许多优秀的剧本做后盾,才能应付裕如。香港的剧作家寥寥无几,创作剧本少得实在可怜,用过去的老剧本——如《雷雨》《日出》之类——又不一定合适,用翻译的西洋剧本又不易为一般观众所接受。这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据研究者统计,1949至1966年间,香港话剧界“每年的创作剧本不超过七个……每年公演的话剧剧目不超过五十出”;而如果“拿创作剧本的数目跟公演剧目相比,显而易见,香港的剧本创作跟话剧演出二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创作剧本的发展远远追不上话剧演出的需求”。[2]31故1956年就有戏剧家指出:“创作落后于现实”“剧本落后于演出”,已“是当前香港剧运上的严重问题”。[3]这个严重影响香港话剧发展的“剧本荒”问题,长时期都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而另一方面,香港话剧的发展又急切需要新的创作剧本。1954年胡春冰就因此而大力提倡“剧本创作运动”,他说:“在话剧方面说,在戏剧教育方面说,目前最需要的是创作,长长短短的剧本,各式各样的戏剧,都被急切地要求着。剧本荒的现象,它的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严重的程度的确令到戏剧工作者不能再因循坐视。‘剧本创作运动’的提出,是目前大家第一个共同的课题。”[4]胡春冰的提倡得到广泛响应,如陈有后强调“鼓励创作、翻译和改编等工作为当前急务”[5],黎觉奔呼吁“剧本创作的重工业运动”[3],等等,都可见戏剧界对“剧本荒”问题的重视。然而这个被戏剧家普遍看作是“严重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的“剧本荒”,并非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所以至1963年,虽然情形稍有好转,姚克还是尖锐地指出:“近十年来,香港的话剧虽有蓬勃之象,但仍没有作经常演出的把握,其原因之一就在新剧本的难得。为剧运的前途着想,我们需要新的剧本。如果没有新剧本的产生,本港的话剧必然会停滞于现在的阶段,不能有长足的迈进。”[6]
如何破解话剧舞台的“剧本荒”?戏剧家们知难而进、身体力行。1952年,香港话剧作家、学者发起成立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主要成员有马鉴、胡春冰、姚克、谭国始、陈有后、鲍汉琳、容宜燕、黄凝霖、柳存仁、雷浩然、黎觉奔等。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是这一时期香港最具影响力的话剧创作和演出团体,它的成立,“在香港话剧史来说,是起了‘大本营’的作用,它团结了全港剧人,协助全港各戏剧团体和各学校的戏剧工作,担当香港剧运的主要角色”。[1]为了推动戏剧创作,“中文戏剧组”同仁创办《戏剧艺术》杂志(胡春冰主编),发起“剧本创作与翻译运动”,举办“创作及翻译剧本比赛”,鼓励、扶掖话剧剧本创作和翻译。同时,他们努力推动香港政府有关部门举办“校际戏剧比赛”(1950—1959)、“香港艺术节”(1955—1960)等演剧活动。“中文戏剧组”同仁不仅积极创作剧本参加“香港艺术节”演出,还鼓励、指导、帮助青年学生创作剧本参加“校际戏剧比赛”。这些戏剧活动,以及这一时期香港组建的“香港业余话剧社”“香港话剧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剧艺社”“南国实验剧团”等剧社的戏剧活动,在戏剧运动、演剧艺术等方面推动了香港话剧的发展,剧本创作方面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也有所促进。
这一时期香港的话剧剧本创作和演出以古装剧为多。如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参加六届香港艺术节的剧目——胡春冰的《红楼梦》(1955)、《锦扇缘》(1957)、《美人计》(1958)、《李太白》(1959)、姚克的《清宫怨》(1955)、熊式一的《西厢记》(1956)、柳存仁的《红拂》(1960)——全都是古装剧。其次是翻译(改译)剧,就是把外国戏剧“中国化”“本土化”,改译为香港观众能够接受的样态。比较好的,有胡春冰根据意大利哥尔多尼《扇子》改译的《锦扇缘》(1957),李援华改译英国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1958),朱克根据苏联高尔基《底层》改译的《人间地狱》(1965)等。为什么要演出翻译(改译)剧?有论者指出:“在我们并未能产生一两位出色而有创作者前,不妨借他山之石以攻错。”[7]可见上演翻译(改译)剧也是为了推动和提升香港的创作剧。相对来说,这一时期香港的现实剧创作不多。这与当时香港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话剧的发展,虽然没有出现文学界那样左、右对峙的尖锐局面,但是,在整个香港社会政治、文学的左派与右派尖锐对峙的格局中,其生存与发展也是极为艰难的。胡春冰当年曾感慨“今日的香港,一切的戏都不容易上演。……古装的演不起,时装的避忌多”[8],就显示出当时话剧发展的艰难情境。就剧本创作来说,虽然在话剧界“绿背浪潮”没有直接形成张扬反共意识的“美元文化”,但是,间接的影响还是明显的。比如,内地戏剧家的作品不准上演,本地的创作剧要通过港英政府的审查,在学校戏剧比赛中“左倾”剧目受到压抑,等等,都使得话剧的发展、尤其是现实剧的创作受到很大限制。“校际戏剧比赛”举办10届而被停办,就是因为在社会政治左、右势力尖锐对立的香港,意识形态对于戏剧舞台的制约。“时装的避忌多”,“古装的”演剧也就成为人们较多的选择;而“时装的避忌”有时在“古装戏”演剧中也会存在。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那个特殊时空发展话剧,显得尤为艰难。然而戏剧家们在努力着、坚持着。
二、古装剧创作的兴盛
1949至1966年间的香港话剧舞台,古装剧的创作和演出居多,也较多受到观众喜爱。以1955至1960年间举办的六届香港艺术节为例,戏剧类节目中“最为令人注目,也最有代表性”的,是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的话剧演出。[9]623如上所述,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参加香港艺术节的剧目,全都是古装剧。这一时期其他较有影响的话剧演出,如姚克的《西施》(1956)、《秦始皇帝》(1959)和《钗头凤》(1960),柳存仁的《涅槃》(1953),熊式一的《王宝钏》(1956),黎觉奔的《红楼梦》(1962)和《赵氏孤儿》(1964),贾亦棣的《香妃》(1963),鲍汉琳的《三笑缘》(1963),李援华的《昭君出塞》(1964)和《孟丽君》(1965)等等,也是古装剧。①这些剧目,除姚克的《清宫怨》是写于1942年,《王宝钏》和《西厢记》是熊式一分别于1933年、1935年根据传统戏曲改编的话剧剧本外,其他都是新的创作。其中,柳存仁的《涅槃》、李援华的《昭君出塞》是独幕剧,其他都是大型的多幕剧。
这些剧作主要描写了中国古代三类不同的社会人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国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中国古代女性的生存和生命。
姚克的《秦始皇帝》、黎觉奔的《赵氏孤儿》、柳存仁的《涅槃》、贾亦棣的《香妃》等剧,都是讲述中国古代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秦始皇帝》搬演秦始皇在亲政之初,为了除掉政敌、巩固权势而阴险密谋,使宫廷充满屠杀恐怖,使王室骨肉相恨相残,揭示出权势欲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泯灭。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悠久,戏曲舞台上长演不衰。黎觉奔的话剧《赵氏孤儿》,则在春秋时代晋国社会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上,着重描写了程婴、公孙杵臼等忠臣志士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高贵精神和人格。柳存仁的《涅槃》是写文天祥之死,作者接续20世纪40年代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的剧情,突出表现文天祥带领一群爱国将士,历尽艰辛、英勇抗敌的忠肝义胆和浩然正气。香妃的传说在新疆影响深远,历来就有以这位美丽而又大义凛然的女子为对象的创作。贾亦棣的话剧《香妃》,着重是写对民族意识的尊重,写维吾尔族青年男女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和坚贞不渝的生死之爱。
描写中国古代男女青年爱情的,有姚克和吴雯的《钗头凤》、胡春冰的《锦扇缘》和《李太白》、鲍汉琳的《三笑缘》以及胡春冰、黎觉奔各自改编的《红楼梦》等剧。《钗头凤》《李太白》《三笑缘》,分别以陆游与唐婉、李白与杨玉环、唐伯虎与秋香的爱情故事为对象,或写爱情的凄婉以批判封建礼教对于美好爱情的扼杀,或写爱情的真率脱俗以彰显人性的高尚纯洁,或写爱情的喜悦以表达对于自由平等的人格和情感的追求,等等,其爱情叙事各有千秋。两部《红楼梦》剧本,胡春冰是以林黛玉为中心,透过她与贾宝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世界,表达反抗封建专制、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黎觉奔则是聚焦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批判封建宗法制度的丑恶,对原著改编也有不同的视角和理解。胡春冰改译的《锦扇缘》,是一次外国戏剧“中国化”“本土化”的成功实践,其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充溢着中国古典色彩,又体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姚克的《西施》、胡春冰的《美人计》、柳存仁的《红拂》、李援华的《昭君出塞》和《孟丽君》等剧,主要是呈现中国古代女性的生存和生命。孟丽君的叛逆性格,及其反抗传统、勇敢争取自由,终为女性扬眉吐气;孙安坚强泼辣、有胆有识,不依附男人而勇于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在李援华、胡春冰笔下,都闪烁着她们不让须眉的精彩生命。而在《西施》《红拂》《昭君出塞》中,作者对传统历史故事进行新的阐释,更可见这些古代女性的风采。不同于西施在传统文艺作品中只是一个“爱国女子”,姚克笔下的西施有自己的情感世界,着重描绘了作为一个“人”的西施的内心情感,以及她与吴王夫差、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矛盾冲突。传统戏曲《红拂传》是写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着墨于乱世英雄李世民、虬髯客和李靖,柳存仁的话剧则是着重写红拂,写她抛弃宫中安逸生活而追求自由和幸福,写她有勇有谋、刚柔相济的侠骨柔情①此剧是写“红拂慧眼识英雄”,但不是像评论者所说写她“矢志与一群忠义之士合力为国驰驱”(陈丽音《简述香港的话剧剧本创作(1950—1974)》,《香港话剧论文集》,中天制作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5页)。剧中着重是写红拂有勇有谋地激将李靖弃杨(素)投李(世民),化解李靖与虬髯客的冲突,促使虬髯客不再与李世民争霸天下。。王昭君在传统戏剧舞台上,或是被写成命运不济的怨妇,或是被写成肩负和番使命的英雄,李援华的《昭君出塞》刻画了一个“人”和一个“女人”的王昭君形象。她自请和番是不愿在宫中做“活死人”而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悲愤“什么时候,男人才把女人当成人”是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关于这些剧作,有三点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首先是为什么当时香港创作演出了这么多古装剧。当时,不是没有戏剧家提倡创作反映现实的戏剧。1952年,在第三届香港校际戏剧比赛总结会上,胡春冰就呼吁“多创作多翻译有时代精神、和大众生活相接近的剧本”;1954年,胡春冰提倡“剧本创作运动”,再次强调:“写现实,写此时此地有血有肉的现实,而又具有普遍性,这是我们目前对创作内容的要求。”②分别见胡春冰《第三届校际戏剧比赛总结》(《星岛日报》1953年1月9日)、《序〈天明后〉》(《星岛日报》1954年5月21日)。但为什么公演的大都是古装剧?甚至连胡春冰自己从1955年到1959年,他为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参加香港艺术节创作的《红楼梦》《锦扇缘》《美人计》《李太白》四部作品,也全是古装剧?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当时香港社会政治左、右势力尖锐对峙的结果。诚然,左、右社会政治势力对峙确实影响到香港话剧与现实的关系,创作演出古装剧及改译剧能够比较容易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查;不过另一方面,从接受层面来说,可能还有一个观众欣赏的问题。战争年代已经过去,香港正步入都市化和全面经济建设时期,香港市民的审美需求,也在发生从注重社会使命感向注重审美、娱乐的转变。所以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戏剧家李援华,深深感慨当时“有些人委实太捕风捉影”而“给我们惹出颇大的麻烦”[10],而同时他又说,“为何有这么多的古装戏?可能是吸引观众吧……主要是风气和投观众之所好”。[11]58实际上当时就有人指出过这一点,话剧演出“老是拿历史剧来借尸还魂,或以民间故事的情节去讨好观众”。[7]
其次,这些古装剧是不是“消闲作品”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当时香港“是冷战的敏感时期,很多大陆剧作家的作品不能上演,本地的创作,也要通过政府的检查。(1949年开始的校际戏剧比赛办了十届之后停办,很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剧作家不无避忌,退而编写一些小市民意识的消闲作品,历史剧更盛极一时,成为逃过政治嫌疑的避难所”。①方梓勋:《香港话剧选·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方梓勋后来还说过:“那时候的剧作,大多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剧和传奇故事剧,虽然与当时香港的社会关系不大,但还可说是接近市民大众的心态的‘消闲式’文学。”(《欢乐今宵与人民剧场》,《香港戏剧学刊》1998年第1期。)如上所述,社会政治不是这一时期香港创作演出古装剧的唯一原因;而就“市民意识”来说,这些古装剧确实是有“小市民意识”或“接近市民大众的心态”,然而,是否如此便一定就是“消闲作品”呢?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当时香港创作演出的某些古装剧确实是有“消闲”倾向,然而,上述较有影响的剧作不能以此而论。这些剧作,或借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而体现坚持正义、反抗邪恶的精神,或张扬中国古代社会的忠孝节义而遥接民族文化传统,或改编中外古典名著而彰显反封建思想意识,或表现女性的生存和生命而为长期被压抑的女性呐喊,等等,都是有其主题内涵的,决非“消闲作品”或“消闲式文学”。以黎觉奔创作《赵氏孤儿》为例。此剧没有写“大报仇”主题和“大团圆”结局,剧中也没有残忍恐怖的杀戮场面,而是着重刻画了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忠义”。作者说,“在今天的世界里,一切为了正义、一切为了永久和平”,所以不要强调那种“狭隘报复思想”,而应该突出忠臣志士坚持正义、反抗邪恶的“舍生取义”精神。[12]故不能说“这些‘历史剧’又明显地没有多少以古喻今的寄寓”。[13]导言“左派”戏剧家更是尤其注重古装剧的“以古喻今”。比如李援华创作《孟丽君》,其出发点就是对当代不幸妇女的同情和怜悯[14],所以他强调:“戏是演给当代人看的,编剧本不同写历史,就算历史剧,也不过是借古喻今而已。”[15]241
再次,是关于这些古装剧的评价问题。其中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大都否定,一种是大都肯定。例如《三笑缘》,当年认为它“打破婢女与解元和书僮与相国义女间的阶级悬殊,而终于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有意义,但是,它没有透过性格和情节表现出来,“看完这个戏后,似乎觉得这秋香并无什么值得‘追’之处;而这个唐伯虎,也没有什么值得秋香死心塌地地去‘爱’上他的因素”。[16]如今此剧却被誉为“从思想内涵到艺术表现,都做了创造性的改编,使其成为一出既有极强的娱乐性,又蕴含着高雅意趣的优秀喜剧”。[17]76实事求是地说,古装剧中不是没有好的创作,姚克的《西施》、胡春冰的《锦扇缘》、李援华的《昭君出塞》,即便在今天也是优秀作品;但是,当年演出的大量古装剧并非都是好的,否则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剧本荒”。古装剧的艺术表现也是如此,既有《西施》这样“先将西洋戏剧与中国固有的戏剧冶为一炉,然后铸成一种新的戏剧”的探索[18]前言,也有如《三笑缘》等剧,着意敷衍故事,其思想内涵没有比较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些,都需要细致地辨别分析。
三、“写此时此地有血有肉的现实”
这一时期香港话剧舞台也有“写此时此地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作品。
应该说,戏剧反映现实是香港戏剧家的努力追求。因此不只是胡春冰多次强调,姚克、李援华等戏剧家同样撰文呼吁。从抗战时代走过来,“感到当时国家多难,希望通过戏剧,对国家民族作出轻微的贡献”的李援华不用说,战后仍然注重写“反映社会的现实剧”,认为“戏剧应该与社教配合的。演员排剧时,应该受些感染;观众看戏之余,我希望他们与我产生一点共鸣……(希望)我底微弱的声音能唤起一些同情或反省”。②分别见李援华《自序》(《李援华戏剧集独幕剧》,光露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我怎样编写〈风雨山房〉》(《李援华作品选》,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同样地,战时强调“戏剧之与教育联系极为密切”,故戏剧创作“题材须具现实性”的姚克,战后赴港,仍然认为“戏剧是与社会教育有关的艺术”,所以演戏“应该避免那些有问题的戏剧”,而要“提出某一个值得社会注意的问题”。③分别见姚克《戏剧与教育》(《半月戏剧》第3卷第7期,1941年6月),《怎样演出戏剧》(香港剧艺社1957年版,第33页)。只是由于1950年代香港社会对于政治过度敏感,在相当程度上压抑了现实剧的创作。进入1960年代,香港社会政治势力的左、右对峙相对缓和,话剧舞台就开始出现反映现实的戏剧超过古装剧的发展趋势。
这些现实剧按题材可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搬演社会陋习、人性黑暗、现实问题。
熊式一的《梁上佳人》(1959)、鲍汉琳的《无妻之累》(1961)、黎觉奔的《五世其昌》(1965),以及王德民的《人猫之间》(1955)、《离婚》(1957)、《自杀者》(1957)和《忙人》(1968)等剧,着重是嘲讽社会陋习的。三幕风俗喜剧《梁上佳人》据英国巴里的同名剧改译,讲述文质彬彬、十分阔绰却没钱的公子司徒大维,原先已经和自己所不爱的富家女张海伦订婚,后来又与进入家中盗窃的美丽纯朴、天真浪漫的赵文瑛发生恋爱的故事。其中穿插了警察总局的毕帮办,赵文瑛的父亲、“盗窃世家”老板赵鹤亭,司徒大维的叔父、太平绅士司徒寿年,以及司徒大维的母亲、香港慈善公益事业领袖司徒夫人等人士,作者“大大的和香港各种风头人物开玩笑”[19]76,讽刺了这些上流社会的附庸风雅、空虚无聊。鲍汉琳曾翻译多部英国喜剧,三幕剧《无妻之累》也有英国风俗喜剧的意味,写一个男子在妻子去世后,先后受到女佣、女管家、女朋友和姐姐管束的苦恼和麻烦。这两部喜剧都轻松有趣,情节曲折有致,对话幽默生动,只是社会内涵稍嫌单薄。四幕剧《五世其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有权势有地位的大家庭里,家中的年轻一代受到社会上流行的“自由”论调影响,故几代人之间在思想观念上产生冲突,社会陋习冲击到大家庭的人际关系,对于社会现实有较多关注。比较尖锐的是王德民的《人猫之间》《离婚》《自杀者》等独幕剧和三幕剧《忙人》,它们或写某都市少女爱猫甚于人而骄纵任性,或写年轻夫妻为家庭琐事而动辄吵闹离婚,或写某些女性喜怒无常爱玩自杀闹剧,或写某些人为了吃喝玩乐而忙得昏天黑地的生命空虚,等等,以喜剧形式嘲讽了那些无聊庸俗者的言行举止。
批判人性黑暗的,主要有王德民的《大慈善家》(1958)、柳存仁的《我爱夏日长》(1960)、李援华的《海鸥》(1967)、《风雨山房》(1968)和《天涯何处无芳草》(1969)等剧。《大慈善家》和《我爱夏日长》都是三幕喜剧,前者写财主戴善仁表面上既善且仁,热心慈善捐款等公益事业,实际上他对社会贫困者冷酷无情没有同情心,显示出其两面嘴脸和伪善本质;后者写杨教授为了试探女儿阿珠的男友夏逸长对恋爱是否真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毒品转运者”,多番设计以考验之。最终,冲着财产而来的夏逸长逃之夭夭,其“爱人是假,爱钱是真”的人性虚伪原形毕露。李援华也比较注重对于人性的探讨。他说:“我们把戏剧与教育结合,歌颂人性的美德,批评人类的缺点。”①李援华:《从罗师演剧谈到主流、路向的探索》,罗师剧社《面临抉择》演出场刊,1985年。他的这几部剧作更多是以悲剧形式去“批评人类的缺点”。独幕剧《海鸥》讲述商人尤熙住旅店因无聊而糟蹋了店里漂亮的哑巴女工,三幕剧《风雨山房》揭露张功荒淫无耻肆意欺辱女性,还心毒手辣企图谋夺妻子祖上的遗产,三幕剧《天涯何处无芳草》写留学生史鸿飞冒充富家子弟到处谈情说爱玩弄女性,都是揭露和抨击人性的黑暗。
揭示香港现实问题的剧作在1950年代极少,仅有麦秋描写当时香港难民潮的《爱之至高》(1957)等个别作品,至1960年代才逐渐增多,出现姚克的《陋巷》(1962)、尹庆源的《工厂燃犀录》(1963)、朱克等的《七十二家房客》(1964)和《人间地狱》(1965),以及徐訏的《红楼今梦》《看戏》《白手兴学》(均为1976年)和《客从他乡来》(1977)等。1960年朱瑞棠曾响应禁毒戒毒号召创作了大型剧《毒海余生》。1961年,香港戒毒会筹建石鼓洲戒毒医院,邀请姚克写戏作为演剧筹款之用,同时向社会宣传吸毒问题的严重性,姚克经过半年多实地走访,创作了八景剧《陋巷》。此剧讲述一群原先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因为吸毒而堕落,生活在“人间地狱”般的陋巷的故事。作者写了这些吸毒者的堕落沉沦、可恶可恨,他们的艰难人生及其善良人性,揭示了毒贩等社会邪恶势力的横行霸道、奸诈狠毒,以及社会正义力量的抗争和胜利。《七十二家房客》是改编内地的同名滑稽戏,描绘了香港拥挤不堪的住房现状和底层社会民众的艰难生存,以及警察借机贪污受贿、欺压勒索的情形。改编自高尔基《底层》的《人间地狱》,在香港贫民窟的背景中,展现了挣扎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苦难人生。《工厂燃犀录》又名《工字不出头》,是当时香港剧坛少见的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工人在工厂的艰苦劳动,及其在厂里受到资本家的欺骗压榨和在社会上受到黑社会的威逼利诱等,剧中都有所揭露。徐訏的几部独幕剧,《红楼今梦》讽刺学界某些所谓研究的穿凿附会、无中生有和自欺欺人;《看戏》以“舞台小人生”展示底层贫困、少女卖淫、夫妻情变、汉奸发财、贪官落魄等人生百态;《白手兴学》批判那种名为“兴学”而实为投机赚钱的丑陋行径;《客从他乡来》用“灵的世界”的“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对比“人的世界”的“争执、吵闹、斗争、倾轧”,等等,都是聚焦香港现实问题的创作。
关于这一时期香港的现实剧,首先需要探讨的,是与上述古装剧相比较,为什么现实剧创作不多且少有成功之作。学术界普遍地将其归因于这一时期香港社会的政治敏感。1968年香港戏剧界召开“香港中国戏剧现况”研讨会,有人提出“现实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能否搬上舞台”的问题,“可以看得出大多数的与会者在这个问题上仍是左遮右挡、迂回退避,充分地表现了一直延绵到那个时候的二十多年间的政治龟缩和政治过敏症”。①曾游:《批判现实主义的可贵努力》,见冬眠《六分一》,七十年代月刊社1974年版,第2页。可见政治敏感对于现实剧创作的压抑是明显的。李援华就坦陈:“自问我的创作没有脱离现实,但不能扣紧时代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受知识、经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勇气。”[10]所以,除了姚克受邀创作的《陋巷》敢于直面香港尖锐、严峻的现实问题,其他如熊式一、鲍汉琳、徐訏、李援华、朱克、王德民等,他们的剧作或是以娴熟的技巧、风趣的笔墨对于社会陋习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或是正视现实然而没有触及现实中的尖锐问题,因而都不够深刻。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被学术界所忽视,那就是创作者的艺术素养问题。这一时期香港的戏剧创作者,真正可以称为剧作家的寥寥无几。他们写古装剧,至少还有原本就精彩生动、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能够吸引观众,写现实剧则无此优势,故大多数作品都是罗列生活琐事,很少能够从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刻画中去揭示现实内涵的,因此,也就少有成功或比较成功的作品。
然而尽管如此,上述现实剧创作对于香港话剧发展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促使话剧植根于香港社会现实,二是它带来香港话剧艺术的突破。香港话剧舞台在1949年之前,主要是演出内地戏剧家创作的剧本。长期被殖民的香港被称为“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香港话剧也被形容为“借来的情感,述说他人的故事”。可以说,此前“在”香港的话剧大都不“属”香港话剧,是这一时期戏剧家的努力,促使香港话剧逐渐发展出其独特性。当然不是说上述现实剧都做到了这一点。比如《梁上佳人》,作者认为其“最重要的地方便是把全剧的气氛,使得它香港化,所以这出戏前前后后都特别有许多本地风光的点缀”。[20]368作者是有意识地要“香港化”,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到,那个“梁上佳人”故事与香港社会少有关联。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李援华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徐訏的《看戏》、尹庆源的《工厂燃犀录》,尤其是姚克的《陋巷》。姚克为写《陋巷》而深入香港九龙城寨实地观察,剧中搬演的就是香港某些阴暗、污浊角落的现实情形,以及生存于其中的香港底层社会人们的喜怒哀乐。它改变了此前香港话剧作为内地话剧延伸的状况,促使香港话剧成为中国话剧在香港发展的独特状态,并且逐渐建构了自己的戏剧文化和品格。所以,那种认为姚克等“南下”戏剧家,“他们对香港既不熟识,也无归属感,若要他们写出蕴涵本地意识的作品,自然是很困难的事”[21]序的看法,是需要商榷的。应该说,正是姚克、徐訏等“南下”戏剧家和李援华等本土戏剧家的共同努力,在那个特殊时空中萌生了本土的“香港话剧”。
这些现实剧对于香港话剧发展,在艺术审美方面也有一些突破。毋庸讳言,上述现实剧大多数在艺术上还嫌粗糙简陋,但是,其中也有值得肯定的作品。例如,熊式一的《梁上佳人》、鲍汉琳的《无妻之累》,其故事叙述流畅好看,徐訏的《看戏》在“舞台小人生”中穿插“人生大舞台”的剧情巧构,等等,都有较好的艺术创造。姚克的《陋巷》,更是以组合“生活片段”的情节结构、人物群像的性格塑造,和不落幕、不换景而以灯光控制舞台时空变化等创新,突破长期以来香港话剧“两种传统的模式:一种是情节集中型,另一种是规限于时间律的延展型”[7],而轰动香港剧坛。香港话剧此前长期处于文明戏阶段,这些现实剧和上述古装剧一起,逐渐提升了香港话剧的艺术水平。
四、开启“香港话剧”的新时代
综上所述,香港话剧发展在这一时期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还是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对于这一点,相当长时期里文艺界、学术界重视和研究都不够。在1968年香港戏剧界召开的“香港中国戏剧现况”研讨会上,人们对香港话剧就曾严厉指责:“贯穿整个会议、笼罩着整个会场的,还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戏剧运动在香港竟有寸步难行的现象?为什么在创作剧方面差不多交了白卷?’一位讲者乃慨乎言之:‘很不幸,自一九四九年以还,香港的话剧说实在的从未向前跨进过半步,只是停留在拙劣的模拟的阶段。’”①曾游:《批判现实主义的可贵努力》,见冬眠《六分一》,七十年代月刊社1974年版,第2页。这种观点影响了后人对于这一时期香港话剧的评价,甚至20世纪末香港戏剧界编辑当代香港话剧集,有《躁动的青春(香港剧本十年集:七十年代)》《破浪的舞台(香港剧本十年集:八十年代)》《八色风采(香港剧本十年集:九十年代)》,唯独没有对于五六十年代香港话剧的整理和研究。
而实际上,当年就有人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反驳。姚克说:“战后香港的话剧恢复活动,可是发展得比较慢;话剧观众也逐年都有增加,可是距理想的程度还很远。但从大体上说,这些年来话剧界不是没有值得一提的成绩,热心分子不断地进行演出,同时青年学生爱好话剧的兴趣普遍提高,学校演剧日益蓬勃,造成香港话剧活动一片热闹现象,已是难得的事。瞻望香港话剧前途,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1]当年还是学生的学校戏剧爱好者钟景辉后来也指出,以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为代表的老一辈戏剧家的创作、演出和戏剧活动,“它使香港的戏剧工作者有了一个团结的根基,推动演出及协助学校戏剧的发展”。[9]623姚克和钟景辉的评价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演出和戏剧活动,对于香港话剧发展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这些老一辈的戏剧“热心分子不断地进行演出”——包括演出他们自己的创作剧——推动了香港的话剧发展,提升了香港话剧的艺术水平。老一辈戏剧家不仅自己创作和演出,而且言传身教带动了整个剧坛的发展。他们努力以自己的戏剧艺术创造感染和影响学校里及社会上的戏剧爱好者。香港话剧在这一时期大都是戏剧“发烧友”的业余活动,“以‘爱美的’一种艺术活动为前提,只求做好艺术工作,使戏剧成为一件艺术作品”②容宜燕:《〈父母颂〉义演的意义》,世界戏剧社《父母颂》演出场刊,1966年9月。,所以与战时演剧着重社会使命感不同,这一时期演剧注重艺术的提升。比如,作为当年香港剧坛领军人物的姚克,其《陋巷》的探索、创新,及其“要新戏剧,因为新戏剧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22]呼吁,引起剧坛震惊、反思和借鉴;该剧1968年、1971年重演,正值香港大专戏剧节、校协戏剧社蓬勃兴起之时,从剧本到演出都给年轻剧人留下深刻印象。再如胡春冰改译《锦扇缘》,他将中外古典戏剧融会贯通加以运用的中国化、本土化艺术创造,戏剧界就曾精到地加以评论:“改编成了中国的古装剧,用中国优良传统的表演艺术上演,这个大胆的新尝试,将使各国优美的古典文学与戏剧,和中国大众接近,在文化的交流与丰富上,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验。”[23]序它引导了后来香港演出外国戏剧的中国化、本土化的改译风气。此外,他们还举办各种戏剧讲座,如1952年暑期姚克、胡春冰、马鉴、柳存仁等讲“中国戏剧源流”,1953年春胡春冰、马鉴讲“戏剧与中国文化”,1953年暑期姚克等讲“中国现代戏剧”,1955年底李援华讲“今日英国戏剧”,1960年暑期熊式一等讲“剧本之写作”,1962年春李援华讲“剧本的创作与改编”,1963年春熊式一讲“中西戏剧之比较”,等等,使学校和社会的戏剧爱好者能够得到艺术指导,丰富了他们的戏剧知识,开阔了他们的艺术视野。
其次,是在老一辈戏剧家的大力推动下,香港政府有关部门举办“校际戏剧比赛”,促使“青年学生爱好话剧的兴趣普遍提高,学校演剧日益蓬勃”。老一辈戏剧家在此用力甚多,因为他们知道“香港的话剧活动,内在的力量还是在学校”[1],“戏剧的新内容、新形式的创造与试验,商业剧场是负担不起来的。这要靠青年之富于创造性、尝试精神、冒险精神和非功利主义的态度。话剧的成就,全靠摸索与实验得来,而这种进取精神,只有求之于青年的团体”。[24]姚克、胡春冰、马鉴、容宜燕、柳存仁、黎觉奔、鲍汉琳、李援华、陈有后、谭国始等,他们或在各中学组织学生剧社演剧并带队参加校际戏剧比赛,或身兼校际戏剧比赛评委而热情评点参赛剧目的优劣长短,或编辑“学校戏剧丛书”为学生演剧提供艺术资源,从而成为推动香港学校戏剧发展的中坚。后来成为香港话剧界主力的钟景辉、林大庆、袁立勋、殷巧儿、莫纫兰、冯德禄、蔡锡昌等,都曾深情回忆老一辈戏剧家对他们的鼓励和扶掖。如钟景辉所说,“校际戏剧比赛对推动香港剧运起了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参加的学校非常踊跃,培养了一班对戏剧产生浓厚兴趣的积极分子”,促使学校戏剧成为六七十年代“香港戏剧发展的生力军及强而有力的戏剧主流”。[9]619
再次,是老一辈戏剧家的创作和演出,在这一时期香港特殊时空中,促使“香港话剧”的萌生。香港话剧本土意识的初步形成就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常用“华洋杂处、中西汇合”来描述香港文学艺术,其中的“华”和“中”,既指中国文化传统,也包括香港文学艺术逐渐形成的、自成一格的本土性和独特性。正是在这里,上述老一辈戏剧家的创作和演出为“香港话剧”的萌生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古装剧,遥接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使香港话剧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他们的现实剧,植根于香港社会,描绘香港芸芸众生的生存和生命,使香港话剧与香港那片土地和人民发生密切联系。这两类创作都影响深远。前者,直到世纪之交仍有杜国威的《聊斋新志》、潘惠森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等剧出现;后者,《陋巷》等剧“意味着香港本土独特文化的意识产生”,“这个价值相当重要,影响往后香港创作剧本的取材”,[13]211带动70年代《会考一九七四》(香港校协戏剧社)、80年代《我系香港人》(杜国威等)等“本土话剧”的创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话剧发展中,这两种影响相互渗透,促使戏剧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去建构本土性的香港话剧,出现曾柱昭和袁立勋的《逝海》、陈尹莹的《花近高楼》、杜国威的《南海十三郎》等优秀作品。这些,都得益于在这一时期特殊时空中,香港话剧主体意识的萌生,戏剧家把“在”香港的中国话剧逐渐转化为“属于”香港的话剧,努力追求并逐渐创造出了“香港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