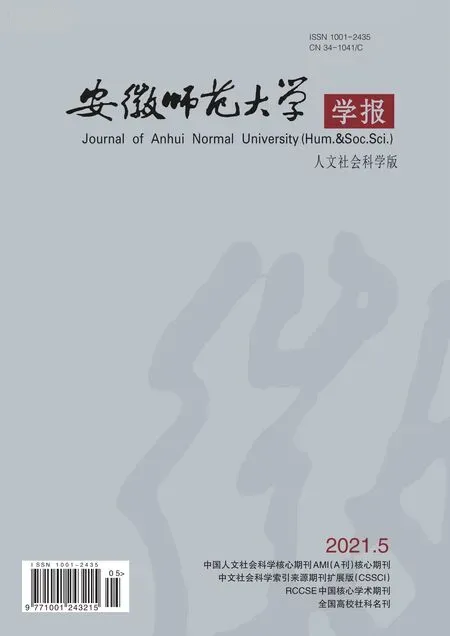李商隐《哭刘蕡》“湓浦书来”补笺*
刘学锴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关于李商隐开成末至会昌初曾有长达数月的江乡之游这一考证,自冯浩、张采田发明以来,岑仲勉先生首先提出有力质疑。在岑说启发下,我自1980年至2002年,曾写过三篇考证文章,对冯、张之说从不同角度加以驳正。首先通过对义山《赠刘司户蕡》诗的细读和关键词语“后归”所提供的内证,以及冯、张持为南游江乡确证的罗衮《请褒赠刘蕡疏》中“身死异土,六十余年”的误引误解,还原罗疏原文并作出正确解释,指出原文“沉沦绝世,六十余年”是从被贬之日算起至罗疏上奏之时已六十余年。又通过对武、宣两朝有关的政局变化的分析和义山大中初年行踪的考述和哭蕡诸诗提及黄陵春雪晤别的回忆,推断二人此次相遇当在大中二年春初,而据哭蕡五律“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及七律“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二联,断定蕡当卒于大中三年秋,从而证明刘蕡并未死于柳州贬所,而是已放还北归至湘阴黄陵一带。后又得见刘蕡次子刘珵墓志,其中明确提到其父刘蕡“贬官累迁至澧州员外司户”,从而证实了刘蕡确已从柳州贬所“后归”的考证结论。以文本内证、罗疏原文正确解读、出土文物所载刘蕡内迁事实否定了冯、张谓刘蕡在贬柳途中与正作江乡之游的义山晤别的考证结论。继又考证排比义山自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的所有行踪及开成五年十月随王茂元出镇陈许行前、途中、到后所拟全部表状启牒等公私文翰,逐一注释系时,从而完全证实了在这四五个月期间,义山绝无可能分身作江乡之游,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否定了冯、张的江乡之游说,并提出了新的考证结论。三篇文章都对义山、刘蕡黄陵晤别后蕡的去向作过或然的推测。初曾疑其可能赴江州谒见投靠时任江州刺史的昔日座主杨嗣复,后又疑其投靠的人是据史载大中年间曾任江州刺史的同贬岭南者裴夷直,但都缺乏确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从湓浦(即江州)将刘蕡死讯告知时在长安的义山者,应是与刘蕡、义山都熟识的友人。虽然这只是主要考证结论之余的一个小尾巴,但其悬而未决不仅使人感到有缺憾,也影响对《哭刘蕡》这首杰作的阐释。这篇短文,就是试图清除这一缺憾的。
先说杨嗣复。杨于会昌六年八月量移江州刺史,至大中二年春初刘、李黄陵晤别时,仍在江州任上。但二月即奉诏入京任吏部尚书,路经岳州时染疾一日而卒。刘即使曾至江州谒杨,于杨离任赴京道卒后,也不太可能继续待在江州直至三年秋逝世。故此推想虽有人事关系上的合理成分,却与大的背景不合,故基本上可以排除。
再说裴夷直。这是一位与刘、李两位都熟识的人物。与刘更是同患难的至交。大和八年裴、刘同在宣州王质幕,皆一代名流。开成二年冬,义山赴兴元令狐楚幕,即与时在兴元幕的刘蕡结识,令狐楚待蕡如师友。开成五年文宗逝世,武宗即位。宰相杨嗣复因曾阿附杨贤妃欲立安王溶为皇嗣,被宦官仇士良(立武宗为帝之主谋)及武宗所嫉恨,八月先贬为湖南观察使,翌年(会昌元年)三月,又叠贬为潮州司马。裴夷直因不肯在武宗即位的册牒上署名,仕途上又曾得到杨的提拔,被视为杨党,于开成五年十一月,由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寻又远贬为驩州(今越南最南端的荣市)司户参军。刘蕡为杨之门生。大和二年应举对策痛斥宦官专权,早为宦官深嫉,于是远贬杨、裴的同时,也被诬以罪(当是党附杨嗣复,不支持新君之罪),远贬为柳州司户参军。裴在驩州贬所,有《献刘蕡书情》诗寄刘,更可证二人系同罪同时被远贬。总之,以裴、刘、李这样的关系,如大中三年秋裴在江州刺史任上,则将刘之死讯驰书告知远在长安的义山,自是情理中事。《新唐书·裴夷直传》载:“累进中书舍人。武宗立,夷直视册牒,不肯署,乃出为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户参军。宣宗初内徙,复拜江、华等州刺史。”这似乎是裴曾任江州刺史的权威依据。但据《庐山记》,“大中三年兴复东林寺,江州刺史崔黯为捐私钱以倡施者。”目前又无任何文献依据可以证明大中三年秋前崔已离江州刺史任。故《新唐书·裴夷直传》谓裴宣宗立,复拜江州刺史的记载有误。但千唐志斋新藏的两方墓志却为“湓浦书来秋雨翻”提供了裴夷直宦历及时间的确切新证。兹将有关文字迻录如下:
《唐故朝散大夫左散骑常侍赠工部尚书裴公(夷直)墓铭并序》
文宗皇帝重文学端鲠之士,公特受宸睠,迁谏议大夫,旋兼知制诰,遽拜中书舍人。补袞之职,倚用山甫。公感激弥切,屡启忠荩,为邪臣所恶。无何,文宗升遐,奸人得志,遂以矫妄陷公。开成五年,出为杭州刺史。寻窜逐南裔,无所不及。十年之间,恬然处顺……臮大中皇帝即位,荡雪冤抑,征于崇山,且以潮、循、韶、江四授郡佐。换硖州刺史,转历阳、姑苏……大中十一年,征拜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
其妻李弘墓志文亦云:
裴公当文宗朝,宠遇特异,旦夕将大用。时相(按,其中应有杨嗣复)每欲敷奏政事,必倚以为援。持权者由是多忌之。及武宗即位……裴公自中书舍人牧余杭。未几,中以非罪流播九真……十年海壖,方遂归北。
两墓志都同样提到自武宗于开成五年正月即位后裴夷直出为杭州刺史直至贬驩,量移潮、循、韶、江,“四授郡佐”,方遂归北的时间为“十年”,自开成五年出为杭刺至大中三年量移江州郡佐,正好十年。墓志明明说的是“郡佐”,即州郡司马,《新唐书·裴夷直传》却变成了“江州刺史”,显然是错误的。潮、循、韶、江司马,都是自驩州贬所离开后所授的量移官。这种量移官,一般都是新朝成立后对前朝贬臣一种临时性政治安排,不占编制,也无政事需处理,在郡的时间就是等待下一次量移或牵复,因而时间一般较短。裴之自驩量移潮州司马,应在会昌六年八月牛党诸旧相量移内地稍后,约该年冬或大中元年初,而最迟在大中三年秋已量移江州司马。不到三年时间已“四授郡佐”(自循州司马量移韶州司马时曾作《将发循州社日于所居馆宴送》,系秋社时作),平均每州不过半年。至换硖州刺史,已属牵复,为一州之临民长官,有权有事有责,一般任期较长(多为三年或二年),故自硖州刺史改和州、苏州刺史用了七年左右时间,其中,任苏州刺史的时间很短,大中十年六月以兵部郎中任,下年即刺华州。这也证明大中三年裴已量移江州司马的推断是正确的。既是司马,就和大中三年崔黯任江州刺史没有任何矛盾,反过来说明了《新唐书·裴夷直传》谓宣宗立,复拜江州刺史纪事的错误。
由裴量移过程的“四授郡佐”的经历和刘珵墓志谓刘蕡“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的记载,刘蕡自柳州至澧州之间,应有另一次量移,否则“累迁”就不好理解。但书阙无征,目前只能作这样的合理推断。这也意味着大中二年春初商隐与刘蕡在湘水入口处黄陵晤别,商隐是由北而南返桂林向幕主郑亚复命,而刘蕡则是由另一量移之地顺湘水北上,越洞庭至澧州这一新的量移地报到。量移官虽无政务及权力,但报到手续必须履行,便于地方官长监护,不可能先至其他地方拜访座主或滞留其地(我先前曾疑其至江州谒杨嗣复)。实际上,刘蕡是否于大中二年春至江州谒杨,或大中三年至江州访裴并卒于江州,与商隐诗“湓浦书来”并无必然联系。澧州在洞庭西北澧水将入湖处,离长江很近,顺流而至江州,路程也不长,故能较早得知刘蕡卒于澧州贬所的消息,遂将噩耗驰书告知远在长安的李商隐。此时正值秋雨翻飞之日,故有“湓浦书来秋雨翻”的著名诗句,仿佛那翻飞的秋雨都化作了两位才人的凄其悲愤情思和泪雨。
纪昀是对李商隐持严苛态度的评家,每多讥评乃至否定,即使像《无题》、《马嵬》七律、《隋宫》七律等杰作亦在所难免。但对赠、哭刘蕡五首诗,却持完全肯定态度,艺术上更给予高度评价,谓“哭蕡诗四首俱佳”,《赠刘司户蕡》“起二句赋而比也,不待次联承明,已觉冤气抑塞,此神到之笔。七句合到本位,只‘凤巢西隔九重门’一句竟住,不消更说,绝好收法”。对这首《哭刘蕡》七律,更以“悲壮淋漓”作概括精当之极赞。管世铭亦云:“不知其人视其友,观义山《哭刘蕡》诗,知非仅工词赋者。”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这对那种“类以才人浪子目义山”(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的传统看法是有力的纠正。
“湓浦书来秋雨翻”所涉及的仅仅是个刘蕡死讯何时从江州传至远在长安的义山处的小问题,却因《新唐书·裴夷直传》的误载而长期悬而未决。此次因夷直及其妻两方墓志的详实记载而知其量移过程“四授郡佐”之事而纠史之误,又因裴斥外远贬长达“十年”方牵复任硖州刺史而补史之阙,亦因此消解笔者过去文章中对“黄陵别后”刘蕡去向的疑团,对“湓浦书来”的原因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包括墓志在内的出土文物对史实考证及文学作品笺释的作用,这是又一显例。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的解决不大可能一次性完成,往往需要新材料和时间。
2004年再版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吸收了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中研治整理义山诗文的考证研究新成果,全书面貌较之1988年初版,已大不相同。前年中华书局让我对2004年以来累积的新注释、新材料再作一次总增订补正,今年即将出第三版。效前贤冯浩三改义山诗笺注的经验,作书不惮改之努力,草此短文,也算对《李商隐诗歌集解》三版出书的一点纪念,表达对出版社的一份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