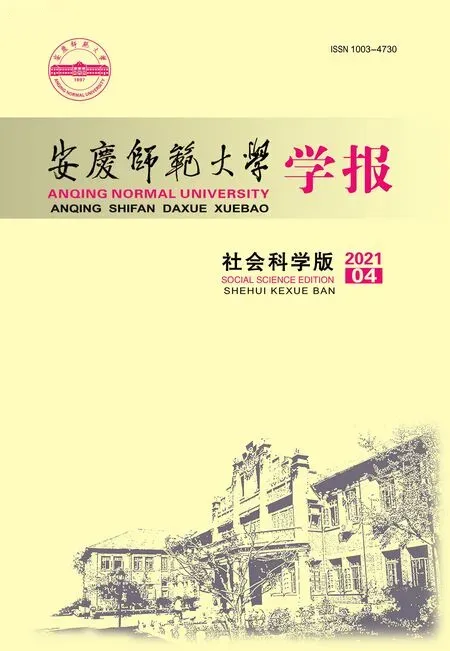宿松县志修纂及版本存佚考论
王永环
(安庆师范大学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安庆246011)
宿松县地处安徽西南部长江北岸,为皖、鄂、赣三省交界之地。郡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一方历史沿革、山川地理、政治风云、经济文化,常以志记之,以求观兴废,知得失,通古今,察未来。县志乃是一县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关于宿松县志的修纂情况,刘尚恒的《安徽方志考略》就现存宿松县志略有述评,但此文稿没有正式出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了宿松现存县志卷数、纂者、刻本,无详细修纂历史,版本存佚情况也不甚准确。本文在此基础之上,试作考论。
一、明代初修
中国地方志书成型于南宋,元代有所发展。明代以前宿松县志的修纂,不见文献记载,难觅其踪。从东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编修“耆旧传”“风俗记”“水道记”,再至唐宋时期的方志“图经”或“图志”无宿松县修志记载。《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著录《怀宁图经》,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五载《望江县图经》,而无宿松图经。怀宁、望江等县修纂“图经”一类的志书,同样作为同安郡和舒州下辖的宿松县也理应修纂此类志书,可能各种因素的影响,传世文献没有记载流传下来其修纂的志书。元代也无宿松修志的活动记载。总之,明代之前宿松无可考的县志修纂历史。
明代地方志修纂开始兴起。有文献可考的宿松县志修纂历史是从明代开始的。方谟《序》:“宿松旧志岁久滋讹,未有厘正之者。弘治甲寅,邑令吴兴陈侯克谨莅任三载,政务稍暇,乃命举人吴怀辈重加纂集,分上下二卷。”[1]由此可见,弘治甲寅之前宿松已有修志,陈恪为重新集纂。邬正阶《序》:“弘治间邑侯陈、施二公始作志,而书皆不存。兵备道凤翥张先生,邑之瑰奇、忠信、才德之兼备焉者也。生当明季,于艰难藂脞之秋,奋慷慨孤忠之节,流离播迁,不忘翰墨,犹手录一编,欲以表扬前哲,昭示来兹。”[2]邬正阶所言弘治间邑侯陈、施二公始作志,疑为误记,因陈、施二公之前志书皆已失传,无从考索。宿松有确切记载的修志始于明弘治七年(1494)知县陈恪,道光《宿松县志》著录明弘治甲寅年翰林院检讨方谟《序》,《原修姓氏》著录“明弘治七年,主修宿松县知县陈恪,纂修举人吴怀”[2],以此确证弘治七年始有修志。
明弘治壬戌(1502)知县施溥续修宿松县志,道光《宿松县志》收录刑科前庶吉士杨禠《序》曰:“宿松旧有志,为前令陈侯克谨所刊。未几,克谨擢侍御去。丙辰,施侯惟中莅。公廉博雅,修学校,毁尼寺,重农恤孤,凡百张弛皆称是。尤留心掌故,乃于暇日命吴生泰旁搜博采,增删旧志,辑为一书。侯亲执铅椠,公于去取,列图于前,述文于后。阅数月,缮镌成编,无脱略,无冗复,详简适中。披其图则自源徂委,由流溯源。”[2]但明代宿松修志具体情形尚不清楚,因为明代之志皆不存。
从以上材料可知,明代宿松县志,至少修纂了两次以上,其中弘治七年陈恪修纂的《宿松县志》、弘治十五年施溥纂修的《宿松县志》有确切的时间记载。明代宿松县志全部失传。
二、清代重修
清代是地方志修纂的鼎盛时期,从地方志修纂理论到修纂的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并且由于清代印刷技术的成熟,清代多种印刷技术并存,印刷工艺趋于完善,为大规模的重复印书提供了方便,也使得多数清代纂修方志得以保存下来。宿松县志的修纂次数在清代最多,体例也逐渐成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清修宿松县志共五部,分别是康熙十四年(1675)《宿松县志》三十六卷,朱维高修、胡永昌纂;康熙二十二年(1683)《宿松县志》三十六卷,朱维高原本,朱卷、石颂功续修;康熙四十二年(1703)《宿松县志》三十六卷,增刻本;道光八年(1828)《宿松县志》二十八卷,邬正阶、石葆元等修纂;同治九年(1870)《宿松县志》二十六卷,黄传焘修、赵世暹等纂,抄本。
道光《宿松县志·原修姓氏》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知县孙继文主修宿松县志。朱维高《序》曰:“得前令孙继文编志十卷。披阅旧序,始知明弘治间曾续邑乘。兵燹以往,旧家失守,遗书罕藏,仅存张绅凤翥笔录半稿,作粉本而辑之,存文献于既堙,竢述作于有待旁搜远绍。微孙令不及此第,引类多舛,闻见颇遗,抑且持论失中,发挥甚略。”[1]孙继文以张凤翥抄录的旧志半稿为底本,手加增辑而修成新志。朱维高对孙继文所修县志颇为不满,认为其分类多混乱错讹,资料的搜集遗漏较多,认为孙志太简略。李士桢《序》曰:“孙君亦以其邑志进予,冁然曰松之为志更有难于诸邑者。微孙君不几于六官之阙其一乎,厥功诚伟哉。”[1]又曰:“孙君能网罗轶事,采辑旧闻,折衷百代,勒成一书,功讵不伟哉?客有疑其近略者,不佞曰画工涂鬼魅易工,涂人物难肖。”[1]李士桢在为孙志作的序中对其修志做了高度肯定,认为孙君续修宿松县志不易,厥功至伟。孙志现已失传,不能睹其全貌。
康熙年间,曾多次重修宿松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邑侯朱维高、知县胡永昌复重订而继辑之,于康熙十四年(1658)刻成。此志以孙继文志和明弘治志为蓝本,稽考研订,资料颇为详备。该志小序甚精,以朱维高序为多。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保存较为完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此书卷三十二、卷三十三两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知县朱卷奉檄增修,该志多处有“朱卷曰”小序,增补资料翔实,如增记开垦田亩数量、朱卷捐资修建城池、革除弊政事迹等,并制定有《增修邑志凡例》,此志于康熙二十四年刊竣。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此书,实际查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无此书,应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有误。到目前为止,未见此次增修传本。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有《宿松县志》增刻本,无修纂人记录,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藏本记为唐宗圣修,此志载唐宗圣为现任知县,据此推测为唐宗圣修。此志卷十四职官增现任知县唐宗圣一人,卷十八选举例监增康熙二十五年选贡朱书以下等十二人,卷二十八列女有续补,并有“康熙癸未¨月杨金续载”字样,艺文志略有增补,其余均未有增加。该志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残本,存卷五至卷三十六;安徽图书馆藏本也为残本,存卷一至卷四,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六;天津图书馆藏本为藏书家任凤苞收藏本,1952年捐赠予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即现天津图书馆。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实为康熙四十二年增刻本,卷二十八和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藏本一样,有“康熙癸未¨月杨金续载”字样,康熙癸未即康熙四十二年,因此成文出版社影印本记为康熙二十四年刻本有误。康熙四十二年增刻本现有传本四种,这四种本子略有差异,如成文出版社影印本与安徽省图书馆藏本卷三十二七言律诗多王式昭《谒金忠宣公祠》、石圣历《前题》《登小孤山》三首诗,七言绝句多石圣历的《小孤山》《游石莲洞》两首诗等。康熙三志时间间隔较短,皆是后志在前志门类基础上加以增订而成,体例散乱,有目无纲。
道光五年(1825)邬正阶开始纂修宿松县志,未完而调任,继任者郑敦亮接着续修,于道光八年(1828)完成并刊刻。该志共二十八卷首一卷。
同治九年(1870),黄传涛、赵世暹等续修宿松县志,也未曾刊刻,只有少数几部抄本流传下来。同治志抄本最后记载“时维咸丰辛亥年清和月上浣日公同建修”,据此表明咸丰元(辛亥)年曾续修宿松县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没有记载此志,现今已失传,也无其他文献记载此次修志。同治志是在咸丰志的基础上增补修纂而成,由于同治志的修志时间没有修改,记载还是咸丰辛亥年,因此为我们了解咸丰志提供了文献信息。
同治志与道光志在体例上有很大不同,比之道光志缺少图、《水利志》、《杂志》;《地舆志》无沿革、星野、疆域、形势、山川、风俗、市镇、冢墓、古迹、十景等十目;《食货志》无盐法、恩赉、物产三目;《学校志》少试棚一目;把驿传置于《艺文志》之后;《人物志》只有烈女一目,把兵事、书目置于《人物志》之后,体例较为混乱。
至此可知,清代修纂宿松县志共七次,现有四部存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五部有误。其中康熙三志的体例一脉相承,只是内容有所增加,道光志为全新的体例,同治志的体例在道光志的基础上略有变化。
现存清代宿松县志保存最完整、体例最完善、成就最高者当属邬正阶、郑敦亮纂修的《宿松县志》,主要表现四个方面:一是纲目清晰,分类详备。其《凡例》云“旧志有目无纲,未免散无统纪”,为此,邬正阶、郑敦亮对前志篇目重新整理,又云“今遵《江南通志》列为十门,提纲挈目,以类相从,庶有条不紊”[2],职官有表,年代为纲,简洁清晰。人物志分理学、忠节、孝友、仕迹、文学、武功、义行、隐逸、寿民、流寓、仙释十一类,归类详尽,尽显本县人文盛况。烈女收录占三卷之多,类目分为前志节孝、节烈、慈孝,新编旌表节孝、贞节、贞烈、节烈,额奖节孝、贞节、贞烈,旌节孝、贞节、贞烈、节烈,待旌节孝、贞节等,分目详细,彰显旧社会女性养老抚幼、坚韧勤劳和慈孝敬老的传统美德,堪称志书中之佳作。二是考证严谨、详注出处。全书征引历代正史及各类文献典籍,内容全面,考证严谨,文字精炼流畅,文风朴实。郡国沿革与廿二史互证,《凡例》曰:“郡国沿革具详廿二史……参互考证,不敢以烦琐为嫌。”[2]并对前志之讹误以小字列于各条之下。每条资料出处都有小字注明,每条信息都有据可查。三是主次分明,一目了然。山川一目较为详备,凡例曰:“舆地最重山川,分条特书,山必详其脉络,水必析其源委。”志山按方位排列,具体位置、名称由来、山形特征一一详介,如《山川》“严恭山”条:“唐武德四年,改宿松县为严州,以此得名。山在县北三十里,环亘十余里,出苍术。山高五里,脉出蕲州,界至安坪。”[3]志水先梳理松水干流、支流总况,再以位置方向分条记述。四是资料丰富,价值较高。坛庙详列规制、祀典。《学校志》规制、礼乐具列,以显尊师劝学。学宫配有文庙及崇圣祠陈设图七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文志》收录本县学人诗文以及撰写本县风土人物的诗文佳作,厘为两卷。其收录本县学人之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如萧穆云:“然元人贾良有《余忠宣公死节记》,明人金星耀有谏崇祯皇帝《止杀疏》,石思琳《答郑大司寇三俊问兵贼大略书》,郑三俊所撰《明故巡抚延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赠兵部右侍郎金公墓志铭》等篇,皆煌煌大文,有关经世史事实用,外间大概未之见,幸赖此志详载之。其他传记等类,亦多有关于本邑文献,而各家专集已多散佚,亦赖此志存其崖略。虽称为县志之佳制,可也。”[4]由此可见,该志是宿松县志的集大成之作。虽然其编排亦有欠妥之处,如《学校志》之下又有碑记、序文等,不符体例,略显混乱,虽是相关之文,但后有《艺文志》,应归于艺文。
现存道光《宿松县志》有初印本和后刊印本,该志在第一次完成刊刻之后又有改动,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初印本,宿松县图书馆藏本为后刊印本,两个版本有七处略有不同,如卷十九《选举志·吏仕》龚之韩、李旵,初印本列明朝,后印本列清朝。安庆民间收藏家孙志方先生收藏之道光志又有道光九年刊印的《宿松县志乐输题名》一册,国图藏本以及宿松县图书馆藏本皆无《乐输题名》。
三、民国新体例
民国时期是中国地方志由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过渡的重要时期。宿松修志与时俱进,修志体例与内容反映了时代变化的新特点。民国年间,时局动荡,唯有俞庆澜等续修宿松县志,该志五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十年(1921)活字本。民国《宿松县志》纂于民国九年(1920),是以道光《宿松县志》和同治《宿松县志》为蓝本,改易卷帙,增删补订而成。
民国《宿松县志》于旧志的体例变化较大,如《舆地》《建置》并为《地理》;新增《民族志》,户口、风俗、典礼归于《民族志》,于《民族志》下新增子目“宗教”和“地方自治”;分旧志《食货》为《赋税》和《实业》,《实业》分类详尽,有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森林、畜牧、渔业、艺术、物产九类,在安庆其他民国县志中,只有民国《桐城志略》中有农业、工业、商业三类,民国《太湖县志》、民国《潜山县志》、民国《怀宁县志》均无此类目;新增司法、交通和政略;又仿章学诚《和州志》中的“前志列传”作“先志列传”。该志资料来源,凡道光八年以前的据道光志,同治九年以前的据同治志,同治九年以后的据光绪《续修安徽通志》、地方载籍及家传谱牒。其中引用地方载籍(如《仙田集略小传》)、家传谱牒(如家状、家乘)等独具特色,这在其他方志中鲜有见到。民国《宿松县志·凡例》:“新增宋元教职官二人皆录自家乘,依时次另列学官表第一类之后。至选举表中道光前科第仕宦有新入者,亦多以家乘为据,各将来历注明。”新增南宋教授一人吴文通,据吴氏家谱;补元代教谕一人王正一,据王氏家谱,以上新增二人均为旧志漏载。选举表中前志缺载,增补多参家谱。其对旧志的谬误以按语悉加订正。每条资料均注明出处。民国《宿松县志》卷首有总目提纲,述其建纲立目之依据、理论,篇中类下又设小序,提挈全篇,其凡例述其编纂原委尤详。该志资料丰富,《杂志》中的《内国公债》一目,记载了清末民初向国内发行公债情况(包括公债种类、总额、面额、利率、兑期及办法)和宿松摊派情况十分详细,如“民国元年,中央政府因各国大借款谈判中止,垫款亦停止不交。曾制定‘元年六厘公债条例’,定额为二万元,备充拨交中国银行资本,整理短期借款及各省纸币之用,年息六厘,债票分千元、百元、五十元、十元四种,九二发行,每百元实收九十二元,以全国契税、印花税为担保,期限三十五年,前五年付息,后三十年抽籖还本。以待议院通过,致未实行。”民国《太湖县志》、民国《潜山县志》、民国《怀宁县志》、民国《桐城志略》皆无此类记载。
由上述可见,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民国《宿松县志》就实际情况对县志的修纂类目做出了较大调整,保存了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资料,实是一份难得的近代经济史料。
四、小 结
宿松县志的纂修历经明代、清代和民国三代,县志的修纂无论在背景,还是体例与内容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从背景上看,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编修方志的鼎盛期,清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为大规模广泛修志提供了条件。康、乾、嘉三代为纂修一统志下发的诏令及省发修志檄文,促进了各地普遍修志。各府及直隶州志要经各省最高长官督抚监修及审查,各州县志由各省学政负责。政府官员、州府县学教授、教谕、训导、乡进士、乡贡进士、举人、太学生、贡士等无不参与其中。康熙朝宿松县志的修纂明显受到清廷修纂一统志的影响,宿松县志的纂修是为一统志提供资料,清代一统志的修纂对地方县志的修纂有巨大影响,宿松县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下修纂的县志,一是体例上几乎一样,无太大差别;二是注重志书的政治作用,辑录的内容要“有裨于政治”。从体例上看,康熙《宿松县志》有目无纲,散无统纪,但到道光时,体例则发生很大变动。究其原因,与清代中期以后方志修纂理论的成熟密切相关。梁启超说:“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5]因此,乾隆中叶以后“在修志方法上,学者中存在不同的主张,形成为三派,即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以毕沅、戴震、孙星衍为代表的地理派(王重民先生称该派为考据学派)和地方封建集团派。”[6]其中章学诚为主的历史派影响最大,他主张“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7]从内容上看,康熙时期宿松县志的修纂是在前志的基础上重修,对于变动不大的细目则继承前志,到道光《宿松县志》体例发生较大变化。由此可见,宿松县志的修纂不仅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也受到方志修纂理论发展的影响,因而在体例、内容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动。方志修纂的发展告诉我们,地方志的修纂具有时代性,受到时代发展与方志理论发展的双重影响。
综上所述,自明至民国,宿松县志可考的修纂次数共十次,明代两次,清代七次,民国一次。明代宿松县志已全部失传,清代的宿松县志今存四种;民国一种今存。考查宿松县志的修纂次数和存佚情况,对于准确把握宿松县方志修纂历史,更好地发掘和利用蕴藏其间的地域文化资源,皆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