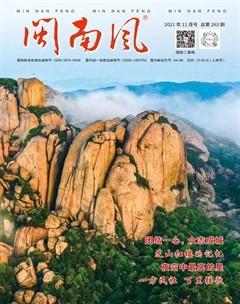老屋的情愫
林进结
坐落于旧村内的老屋是我远在南洋的亲人的故居,也是我们一家的故居。只是老屋已不是百年前的老屋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母省吃俭用养猪挣钱,我们三兄弟用从外祖父家借来的铁推车,到山上石场把乱石碎片一趟趟地推回家,远在新加坡的伯母也寄钱来,几番努力,老屋终于修葺一新。
故居终随岁月而老化。现在村落扩大,一家人早已搬到旧村外的新居,只有父亲一人固守着老屋。旧村中的许多人家也搬到村外居住,老村中很宁静,守在那也很孤单,时时只能与屋外的风雨为伴。儿孙们总是劝告他搬到新居,但父亲也总拒绝说:“我住这里很好,很好。”父亲对老屋倍加珍惜,像呵护自己的亲人似的。他整天捣鼓着,时时拿着瓦刀,和了水泥,东补西抹的,时而墙,时而沟,时而屋顶。所以老屋虽然陈旧,但大厅上的红砖依然泛着红颜色,祖宗灵牌的台桌清洁如新——父亲时常巡看、拂尘、擦洗。老屋在父亲的看护下,依然安然无恙,不像村里有的旧房子成了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荒凉样。
我知道父亲眷念着什么。许多风雨交加的日子,父亲会细听窗外凄厉的风声,凝视屋檐如麻的雨脚。那风雨会勾起父亲对他的亲人们背井离乡的撕痛。
我的家族里有许多亲人在早年间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现在远方的亲人中,长辈已经不多。伯父、伯母仙逝后,二姑姑也仅存惟一。听长辈们说,那时这位姑姑很想回家看看,但终究没有如愿。或许是她太苍老了,或许是故乡太遥远了,或许远方的生活不尽是在天堂里,没有“荣归故里”应有的自豪而徘徊。故乡只能留在她的记忆中,出现在她的梦里。现在,一抔黄土在另一个世界掩埋了曾经有过的希冀,也许姑姑不明白,这不仅是她永生的内疚,也是故乡永远的遗憾了。
老屋牵挂着远方,远方也时时记挂着老屋。1975年夏天,七十多岁的伯母回到故乡,住在老屋。她精神很好,慈祥的样子就像是奶奶。她给我们带来许多吃的、用的,像布料、旧衣裤、饼干、自行车等。她还亲自教我煮咖啡,告诉我一家人在南洋开荒、养猪等情形。现在,许多东西已淡出了我的生活,但有许多并没有淡出我的记忆。每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想起伯母,就想像她描述的一家在南洋的生活情景。
同辈中,只有堂姐阿娇曾带两位女儿回家,那时正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两个外甥女肥胖黝黑,年纪比我大。她们叫我小舅舅,让我很有亲近感,我想她们虽然来自异国他鄉,但骨子里还是血脉相连。她们此行的目的是游北京,去前先回老屋看看。可惜那时北京不太宁静,去不成了。后来在南方转了一圈回去了。临行前堂姐说有机会还会回来,还想去北京。至今,我也没有再见到这位大姐,也不知她们游北京的愿望实现与否。
后辈中虽有许多人回过乡,到过老屋,但蜻蜓点水似的。对于他们,我比较陌生。我想他们生在南洋,长在南洋,祖居是什么样,老屋是什么样应当不会存有印记。对他们而言,老屋只是从前辈嘴里得到的传说,或许晚辈们只知道遥远的故乡还有一座祖坟,一份祖业而已,而老屋的情感寄托,已是淡淡地烟化了。有时,前往所谓的故乡只是代老一辈人完成了他们的心愿。老一辈人在终老的时节已经不能再看故乡一眼,也难于叶落归根了,委托家人后辈来到他们陌生的,遥远的地方,捎来一点歉意,一种感伤,一份哀怨,一声问候。
其实,我的这种看法也很快被颠覆了。后辈中堂侄财春时常往返于南洋和“唐山”,与同住新加坡的乡亲林振钦一道积极参与爱国爱乡活动,捐款集资给桑梓助公益事业,拳拳之心可鉴。回到老屋总不忘给祖先焚香。那年堂侄回乡祭祖,其间虔诚地听着父亲絮絮叨叨地讲述家族的历史,了解老屋与南洋亲人的关系。在回到旅居的县城后又匆匆赶回新居。父亲问明缘由,原来是伯母去世前曾嘱托一定要从故乡带回一抔土,洒在她和伯父的坟上。父亲明白家乡的一抔黄土、一杯清水对于远游人的意义。他挖出了一堆沙土,用红布包了一大包,并到井里打了桶水,装了一小瓶。父亲把土和水递给侄儿说:“告诉爷爷、奶奶,这是咱自家的土和水。”父亲一路送堂侄走出村外,他说:“财春啊!我老了,你要记住,这里还有你的兄弟……”堂侄真诚地说,叔公,您放心吧!我是大房子孙,我还会再来的。
在很多时候,例如夜深人静,例如美好佳节,我经常反省。我确信他们回到故乡,探访老屋,不仅仅是因为老辈的嘱咐,同祖同根的本能是在血液里流淌和激荡着的。族性的召唤,信念的寄托,情感的凝聚都使得天涯咫尺,我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它连结,悠远,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