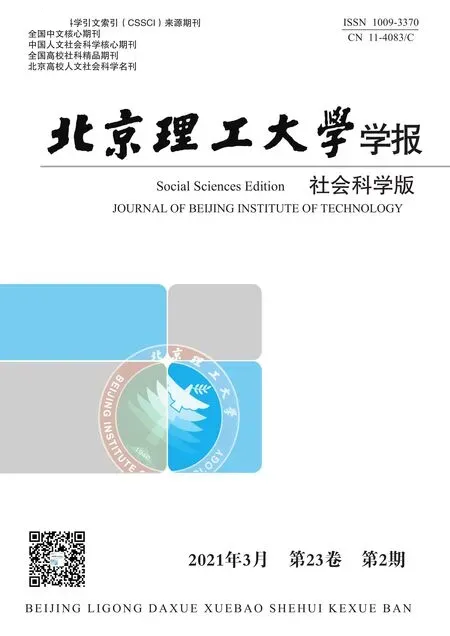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李敬峰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系,陕西 西安 710119)
阳明心学以“新天下耳目”[1]28的姿态打破一世皆安于朱子学的现状时,旋即在全国传播开来。阳明心学在是时全国不同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是齐头并进还是参差不齐,这关乎到阳明心学的地域性和多样性,关系到地域儒学与阳明心学的争鸣互动与交融相益等富有意义的学术问题。
一、辨难与阐扬: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初传
(代表人物:吕柟、马理、韩邦奇、杨爵、南大吉和南逢吉等)
阳明心学传入关中地区的确切时间是一个颇有价值但又难以考证的问题,然这并非无状可寻,据晚清学人柏景伟(1830—1891)载:
关中沦于金、元,许鲁斋衍朱子之绪,一时奉天、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明则段容思起于皋兰,吕泾野振于高陵,先后王平川、韩苑洛,其学又微别,而阳明崛起东南,渭南南元善传其说以归,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2]69
柏景伟认为关中有王学之音,当源于阳明亲炙弟子南大吉(1487—1541)于嘉靖五年(1526年)罢职回乡之后,在渭南地区积极传播阳明心学。实际上,早在南大吉之前,就已经有诸多关中士人与阳明有所往来:三原籍李伸(1471—?)在正德年间(1506—1521)巡按江西之时,曾与阳明“与为讲友,自谓深得其学。”[3]259“关学集大成者”吕柟(1479—1542)在正德七年(1512年)就与阳明“得数过从说《论语》,心甚善之。”[4]233同州人尚班爵亦师从阳明问学,成为阳明在关中的另一及门弟子。另外,曾于1521—1526年任职陕西提学副使的唐龙(1477—1546)亦与阳明交情深厚,推重其学,交辩有年,将阳明心学带入关中亦甚为可信[5]218。如此事例,不胜枚举。如果抛开传播的范围和效果不论,阳明心学传入关中地区应在正德年间,而非嘉靖年间。柏景伟所说的关中地区有王学始于南大吉,则主要是指传播的自觉程度和师承渊源而论。实际上,南大吉传播王学也主要限于其家乡关中东部的渭南一隅,而广大的关中地区对阳明心学基本上持抵制和批判的态度,与江南炽热风靡之势迥然有别。基于关中这种复杂的情形,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初传便形成了辩难与阐扬并存的景象。
众所周知,关中地区自南宋后,关学、程朱理学就主导着这一区域的学术,一方面可从《明史》的“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蠖秩然”[6]7222看出明代学术的大背景,更可从柏景伟的“关中沦于金、元,许鲁斋衍朱子之绪,一时奉天、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一见关中学术。而当阳明心学传入程朱理学主导已久的关中地区时,学者“骤闻阳明之学而骇之,有此辩难”[7]1041,这就精确地揭示出关中大部分学者面对学界新声之心态,是时关中地区以吕柟、杨爵、马理等为代表的关中大儒皆以辩难、批判阳明心学为务,他们“宗程朱以为阶梯”[3]258,围绕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良知”“知行”“格物”等展开辩难。就良知来说,吕柟在肯定阳明“良知”学说所具的警醒世道人心、一扫旧学阴霾之功后,着重指出阳明“良知”之教的弊病在于:
何廷仁言“阳明子以良知教人,于学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浑沦的说话,若圣人教人,则不如是。人之资质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学问有浅深,不可概以此语之。”[8]99
在吕柟看来,阳明的“良知”之教不分受教者资质、工夫、学问等方面的差异,将所有人等同视之,皆以良知教之,有悖于圣人因材施教的方法和原则,故而不足取,亦不足信。很明显,吕柟主要是从教法上来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这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阳明的本意,因为阳明所讲的“良知”主要是从本体立论。“良知”作为本体,圣凡相一,无有不同。吕柟挚友马理(1479—1556)也对阳明的“良知”思想予以批驳:
夫良知者,即孩提之童,良心所发,不虑而知者也,与夫隐微之独知异矣,与夫格致之后至知,则又异矣。其师(王阳明)曰:“此知即彼知也。”又以中途有悟,如梦斯觉为言,此真曹溪(禅宗)余裔,其师如此,徒可知矣。乃又以其所见非程、朱之学。[9]322
较之吕柟,马理宗本程朱理学之意更为明显,他认为阳明所讲“良知”与程朱旨意不符,反倒与禅宗如出一辙。可以看出,吕柟、马理等主要发挥的是关学、朱子学“践履笃实、下学上达”的学派精神,对纯粹的形上之学并不钟情。虽然他们不认同阳明的“良知”之教,但并非完全排斥,从另一件事中可见端倪:
时阳明先生讲学东南,当路某深嫉之,主试者以道学发策,有焚书禁学之议,先生(吕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1]43
上述之事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年)会试之时,主试者嫉妒阳明心学,欲以焚阳明之书,禁阳明之学命题,吕柟极力辩护,终于阻止此议的实施。以此可见吕柟等人并不因不认同阳明之学而落井下石,显示出其兼容并包的关学底蕴。在他们的影响下,关中士人如吕潜、郭郛、张节、李挺等,多以排斥阳明心学为务,如郭郛以朱子学“主敬”自律,不为心学所动:“学道全凭敬作箴,须臾离敬道难寻。”[1]43这些关中士人对阳明心学的辩难,相当程度上延缓了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速度,成为明代中期关中地区回应阳明心学的基调。必须指出的是,主流声音之外仍有阳明及门弟子南大吉、南逢吉兄弟在渭南一地不遗余力地传播阳明心学,为阳明心学在关中的传播奠定良好基础。南大吉与吕柟、马理等生卒年大致相当,他在嘉靖二年任职浙江绍兴府时,恰逢阳明讲学绍兴,南大吉遂与其弟南逢吉一起拜师阳明,精研心学,并在次年修缮稽山书院,礼请阳明讲学,一时好学之士皆慕名前来,文教鼎盛一时,尤其是南大吉在绍兴刊刻《传习录》,极大地促进阳明心学的传播。然好景不长,在嘉靖五年(1526年),南大吉因开罪同僚,被罢职回乡,阳明在表达同情之余,也对其寄予厚望:
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归,谓天为无意乎?谓天为无意乎?[10]210-211
在这段话中,阳明盛赞关中地区自古豪杰之士辈出的卓异士风,此风在张载之后,学绝道丧,萎靡不继,阳明则希望南大吉能够通过在关中地区传播其学,来提振这一风气,以此足见阳明的自信和对南大吉北归的期许。南大吉不负师命,以道自担,可从其北归所作之诗“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1]52来见其传道之志。传道情形,冯从吾载:“先生既归,益以道自任,寻温旧学不辍。以书抵其侣马西玄诸君,阐明致良知之学。构湭西书院,以教四方来学之士。”[1]51冯氏所述不差,南大吉以传播师说自任,在渭南宣讲阳明心学达15年之久,直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因病去世,可见其用力之笃。同时,其弟南逢吉亦在致仕归乡后,继续在渭南传播阳明心学,教化一方。南氏兄弟虽有传播、光大之功,但影响区域有限,尚未扩散至广大的关中地区。这种状况的改观有待于晚明冯从吾、张舜典等人来推动和完成。要之,这一阶段就争辩的思想而言,主要是围绕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展开,是朱子学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是旧学对新学的排挤,是官方学术对异己思想的拒斥。
二、晚明关中地区阳明心学的鼎盛与会通
(代表人物:冯从吾、张舜典、张国祥等)
顾宪成(1550—1612)在描述中晚明学界现状时说:“弘正以前,天下之尊朱也甚于尊孔子……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11]144,顾氏此言不虚。嘉靖末、隆庆初,得益于阁臣徐阶(1503—1583)、李春芳(1511—1184)的推动,阳明心学在全国的传播趋于高峰。
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 两执政尊王氏学……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12]415
可以看出,仰赖于徐、李二人的政治影响和名人效应,阳明心学已然渗透到科场程式之中。
徐文贞(徐阶) 素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竞依坛坫,旁畅其说。[13]180
阳明心学在是时全国的热火朝天,并未带动在关中的传播势头。究其因,主要是此时关中地区传道者严重断层:“关中成、弘间人才济济称盛。自嘉靖来渐衰,至于今日,则寥落而孤弱极矣”[14]104,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地区发生有历史记载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地震:
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15]549
这次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关学翘楚韩邦奇、马理、王维桢等皆未能幸免,这对关中学术的延续造成毁灭性打击,极大地影响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这种低迷之状迟至晚明才略有改观。心学一系的许孚远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至万历十六年(1588年)督学关中,任陕西提学副使,“开正学书院,拔志趋向上士讲明正学”[2]71,一时关中学风为之一振,“凡寓内后进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绪论者,不翅如泰山北斗”[1]279,在他的直接影响下,门下弟子出现了服膺心学的冯从吾(1557—1627)、张舜典(1557—1629)等辈,他们再度复振关学:“(张舜典)与长安冯少墟先生同时倡道,同为远迩学者所宗,横渠、泾野而后,关学为之一振”[16]222,许孙荃(1640—1688)称:“有明关学,继文简公(吕柟)而起者,长安则有冯少墟先生,岐阳则有张鸡山先生,二公生同时,东西相望,与往复辩论,倡明斯道,学者景从,一时称极盛焉!”[17]109就冯从吾而言,他服膺阳明心学,但并不以此自限,而是对阳明心学保持一种较为中肯之态度,当赞则赞,当批则批。首先,他对阳明的“良知”之教高度赞道:“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圣学真脉,有功于吾道不小”[1]301,又言:“阳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于圣学,不可轻议”[1]144,由此可见冯从吾对阳明提揭“良知”,直指本心,抉发根本的赞赏。无独有偶,张舜典亦盛赞阳明的“良知“学说:
辞章口耳,圣道支离。公排群议,独揭良知。致之一字,工夫靡遗。虞渊取日,人心仲尼。[17]137
可见,张舜典与冯从吾一样,皆高赞阳明提揭“良知”的晰迷破惑之功。平实而论,阳明在朱子学流弊尽显之时,标揭“致良知”,即知即行,即行即知,绝非只是为标新立异,而是要凸显道德的统领性作用,以期矫正朱子学的“支离繁琐”之病。阳明的这种思维模式深刻影响到冯从吾,他反复指出:
圣人之学,心学也。[1]32
圣贤学问总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终日孳孳,终属枝叶。[1]197
吾儒学问要在心性。[1]310
很明显,冯从吾完全是从心学的角度来理解和定位圣人之学的,这就与关中一贯的尊奉程朱理学的学术传统相异。冯从吾对学问根本的强调,更可彰显心学的影响:
学问之道,全要在本源处透彻,未发处得力,本原处一透,未发出得力,则发皆中节,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诸凡事为,自是停当。[1]225-226
冯从吾将学问之道的根本落脚在体悟本体上,主张在本源出用力,在未发处着手,唯有在本源透彻,则已发自然符合中道。显然,冯从吾的主张与程朱理学所主导的“下学而上达”的为学之道明显不同,而与心学的直从本体入手,“先立乎其大”旨趣相近。这并非是说冯从吾不重视工夫,恰恰相反,冯从吾、张舜典皆对晚明阳明后学好高骛远、轻视工夫所造成的“玄虚而荡”“情识而肆”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皆主张用程朱理学的“主敬”工夫来补救王学之失:
学问工夫又总之归于一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间,敬者,众善之根;肆者,众恶之门。敬者,众福之根;肆者,众祸之门。敬则父子,人人敬则天下治;人人肆则天下乱。[1]213
“主敬”为程朱一系的工夫纲领,但受到阳明心学的否定[12]34,而冯从吾却看重程朱一系的主敬工夫,将其作为工夫纲领、众善根本、圣门之要、善治根本,这就赋予“敬”无以复加的地位,意在通过实实在在的工夫来涵养本源,以期纠治阳明后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1]158之弊病,显豁出明显的援朱救王特质。张舜典亦持类似看法,多次表达对程朱“主敬”思想的推崇:
谁哉我之师,人心有仲尼。考亭严主敬,姚江致良知。[17]39
出处隐显,阙惟一敬;可质三王,可俟后圣。[17]139
张舜典不仅拔擢“敬”的地位,更把“主敬”与“致良知”分别作为朱熹、阳明的标志性思想,相提并论,以期各取所长,相资为用。总之,从晚明关中地区代表性人物对阳明心学的接受可以看出,他们所思考的思想主题就是如何在本体与工夫层面实现朱王会通,这种会通已经有效地推动关学心学化,实现心学与关学的交融互构,推动阳明心学在关中的传播达至鼎盛,并使张载关学思想旨趣在晚明发生根本性转向,从推崇外在的格物致知和礼仪之学转变为以崇尚心性之学为主。在这种转变中,关学并未完全随着阳明心学滑转,而是仍然保持着其躬行践履、倡导实行的学术特色,并依此来修正阳明后学的空虚邋等之弊。
三、清初关中地区阳明心学的延续和修正
(代表人物:李二曲、王心敬、王吉相等)
明清易代,阳明心学被作为亡国学术遭到清算,并在清初形成尊朱黜王的学术思潮。在这种大背景的裹挟下,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形势保持着修正与批判交错并存的理论图景。相对而言,羽翼、修正王学的成就和影响更为突出,缘由在于清初关中地区出现了以李二曲、王心敬等为代表的尊奉阳明心学的二曲学派。他们的影响可从李元春的“二曲之学盛吾乡,几如阳明之学盛天下”[18]383评价中得以详见。李二曲(1 627-1 705),陕西周至人,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全祖望指出:“关学自横渠而后,三原、泾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复盛”[19]233,梁启超称其为“王学后劲”[20]233。二曲生逢尊朱辟王日趋高涨之时,虽宗本阳明心学,但却因应时变,推动阳明心学的自我补正和更新:
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16]59
姚江当学术支离蔽锢之余,倡“致良知”,直指人心一念独知之微,以为是王霸、义利、人鬼关也。当几觌体直下,令人洞悟本性,简易痛快,大有功于世教。[16]130
明末清初,关中学者对阳明的“良知”之教已经不再像明代中期的学者那样排斥,而是极力肯定和赞赏。二曲肯定“良知”,亦主要是认为阳明标揭“良知”,简易直接,洞彻本体,为人点出入学之方,使人皆有成贤入圣之道。不唯如此,二曲着重凸显阳明所讲“良知”可以导向王道事功的一面,以矫正世人对阳明心学有内圣无外王的偏见。正是对“致良知”的这种深契,二曲在修正王学时,着意以此为基,开辟出兼取朱王的路径:
以致良知为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废。上学下达,一以贯之。故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16]130
二曲针对朱子学、阳明心学的各自所长,提出以阳明心学为本体,以程朱理学为工夫的方法,来纠补各自所偏,如此方能实现相互补救。这并不意味着二曲是中间派,在两者之间,他更为偏好的是阳明心学:
问:学须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中正无弊,单“致良知”,恐有渗漏?曰:识得“良知”,则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调理脉息,保养元气,其与治病于标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否则,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存甚?养甚?谁省?谁察?[16]136
二曲认为朱子学所讲的“主敬穷理”必须由阳明所讲的“良知”作为头脑,否则“主敬穷理”就会落空,就会茫然无下手处。这就将宗本阳明、兼取程朱之意显豁出来。要之,二曲在清初尊朱崇王的大势下,不随波逐流,逆风而上,依然坚守、修正阳明心学,以期为阳明心学争夺生存空间。
二曲之后,从庙堂到民间,尊朱辟王之风愈演愈烈,二曲高弟王心敬[21]4261(1 658-1 738),陕西户县人,历康雍乾三世,以学术造诣闻名于朝野,阁臣朱轼、额伦特、年羹尧、鄂尔泰等迭次举荐,其学被时人以“原是陆王者”[22]894“似得之王阳明”[2]96相称,以此足见其学宗阳明之特质。他在著述中反复强调心学宗旨之“心外无理”“心外无道”作为自己立论的根基,更祖述师说,以调停朱王为务。他首先对那种诋毁阳明心学的行为进行反驳:
陆王之立本良知,非陆王之私创,乃孟子之本旨。陆王可排,孟子亦可排耶?孟子之立本良知不为禅,陆王之立本良知遂禅耶?[22]882
王心敬的辩护逻辑是这样的:陆王心学源自孟子,而孟子思想纯正无疑,自然陆王心学亦不容质疑,因此那种诋毁阳明心学为禅学的是站不住脚的。但这并不是说王心敬只是盲目地恪守门户。相反,他对阳明心学之弊病亦有清醒的认识:
陆王立论,意在张皇本体之本善,未免于尽性复性实工夫容有脱疏,殊与六经四子本旨有异。苟不善学,虚见不实之弊所不能免。[22]885
王心敬认为陆王之学为矫正朱子学的支离闻见之病,偏于强调内在,过于凸显本体,这就难免在下学工夫上有所脱略,流入蹈空不实。王心敬这一指陈显然是切中阳明后学弊病的。就朱子学来说,王心敬亦明白指出:
学朱子自平正稳确,但朱子生平之学,日进日邃,亦屡变益精。其初鉴程门末流之弊也,故其言道问学处居多,其后鉴学者多牵于文句训诂也,故又时时为之指示本体。[22]885
在王心敬看来,朱子学平实稳健,步步着实,只是为纠正程门后学,尤其是明道一系偏于体悟之病,所以在格物穷理、道问学等方面强调的多了,而后学则在此方向上愈走愈远。换而言之,朱子学本身并无多大问题,主要是后学偏离其说,导致种种流弊。面对愈演愈烈的门户之争,基于心学、理学的各自所长,王心敬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大抵论其立心,皆守先待后之大儒。论其得力,则紫阳学之功勤而密姚江之功锐而精。合之皆可入圣,分之皆可成家。无紫阳,此道空疏,师心之病无以救;无姚江,此道闻见支离之弊无以救也。[22]882
王心敬认为朱子学笃实,可以防空疏不实之病,阳明心学挺立道德主体,可以抵制支离之弊,两者不可偏废,必须兼取并用:
专尊陆王而轻排程朱,是不知工夫外原无本体,不惟不知程朱,并不知陆王;若专尊程朱而轻排陆王,是不知本体外无有工夫,不惟不知陆王,并不知程朱。[23]360
程朱,陆王不能尊其一,废其一,否则是两相不知。王心敬面对清初的门户之争,采取的是以心学为基,会通朱王,修正王学的方式。总括来看,清初关中地区尊奉王学的学者,在愈演愈烈的门户之争下,在朱子学重新定为一尊的情势下,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继续羽翼和修正阳明心学,延续晚明冯从吾、张舜典等以心学为本、会通朱王的思路,主张以程朱理学的“主敬”工夫来补救阳明心学的空虚不实之弊,舍弃阳明心学好高骛远、偏于心性体悟的学术倾向,推动阳明心学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使得阳明心学在清初展现出新的学术取向。
四、清末关中地区传统阳明心学的维系和终结
(代表人物:刘古愚、李寅、柏景伟等)
阳明心学在清初的关中地区有李二曲、王心敬辈在极力回护,回护的结果可从张秉直(1695—1761)的“尝恨二曲、丰川(王心敬)以陆王之余派煽惑陕右,致令吾乡学者不知程朱的传”[24]4评述中略见一斑。张氏之论难免有过分夸大之嫌。实际上,在二曲、心敬弘道关中之际,宗本朱子的部分关中学者如李因笃、王弘撰、王建常、刘鸣珂、史调等人极力批判阳明思想,措辞激烈,态度严苛。李因笃(1632—1692)就说:“先朝天下之乱,由于学术之不正,其首祸乃王阳明也”[25]500,这就将亡国之罪归于阳明。史调(1697—1747)称阳明为“圣门罪人”[26]37,类似言论不一而足,反映出当时关中地区与是时全国的主流趋势是大体相近的。也就是说,随着关中地区朱子学群体的崛起和壮大,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走向势弱,以致尊奉阳明心学者几无其人,而程朱理学在二曲、心敬之后重新主导关中地区,这一风气在后来的李元春(1769—1854)、贺瑞麟(1824—1893)得到进一步强化。贺瑞麟:“窃谓千古学术,孔孟程朱已立定铁案,吾辈只随他脚下盘旋,方不错走了路”[27]224,李元春:“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顾横诋之亦大可感矣”[19]11,二氏将独尊程朱、排斥阳明之意明白无疑地表露出来。随着全国形势的转变,阳明心学在沉寂了百余年后,到晚清又迎来转机[28]145,渐趋开始复苏。首先可从清廷统治者得到映射,一是康熙极力推崇朱子学,但终康熙一朝及整个清季,始终未取缔阳明从祀孔庙的政治礼遇,二是乾隆于1751年南巡期间,专谒阳明祠,1784年再度南巡期间,诏令修葺阳明祠,并御赐“名世真才”匾额。上层态度的松动,为阳明心学留下一线生机。早在乾隆初年,李绂(1675—1750)刊刻《陆子学谱》,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刘原道刊刻《阳明先生年谱》,嘉庆、道光年间,王学著作得以大量刊行,如嘉庆三年(1798年)刘永宦刊行《王文成公集要》,道光五年(1825年)张恢等人补刻《广理学备考》,专门收录心学一系的《王阳明集》《王心斋集》《王龙溪集》等,此后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皆有大量阳明学著作得以刊行。心学著作在清代中期的解禁,为阳明心学在晚清的复兴奠定底子。但阳明心学的复苏主要局限在有心学传统的江南地区,而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则要晚至清末才出现。以刘古愚(1843—1903)、李寅(1838—1877)、柏景伟(1831—1891)等为代表的关中学者,在晚清世道多变之际,依然艰难维系、改造和传播心学思想,尤以刘古愚的成就最为杰出。刘古愚,名光蕡,号古愚,陕西咸阳人,与康有为(1858—1927)并成为“南康北刘”。康有为称其学“以良知不昧为基”[29]7,李岳瑞(1862—1927)称:“先生之学,渊源姚江,会综洛、闽,而其用归于阜民富国”[29]281,张骥亦说:“先生学术推重姚江。”[3]537从这些赞语中可见刘古愚归宗阳明心学的学术旨趣。
以程朱为孔门正派正途,陆王为异,所谓异同者,谁定之耶?其非孔子预定,为孰正、孰异?则为各私其门户之说也,明矣。……今之辨程朱、陆王者,何异于是?学术之不同也,自古至今,所谓正统、嫡传,亦未有全体胥同,而无丝毫之不异。正如孪生之子,虽极相似,亦必不尽同。……则何必学圣人者而仅朱子之一途为正业?[29]122
在刘古愚看来,学界将程朱理学视为名门正派,而将陆王心学打入异类杂学,实乃是门户之见。因为程朱、陆王皆是圣贤之学,并无正统、异类之分,两者正如同孪生子,皆为正统,不必苛求两者一切皆同。学习圣贤无须只将朱子学视为正途。刘古愚表面上在程朱、陆王异同问题上力破门户之见,但实际上字里行间他都是在为抬升阳明心学而努力。可从其对阳明“致良知”的评价中一见其志:
阳明会和二家之说,括以“致良知”三字,单传直指,一针见血,使学人闻言立悟,有所执持,以徇徇于学文之途。故自阳明之说出,海内学人蠭起,名儒辈出。自周程创兴儒教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29]124
刘古愚认为阳明的“致良知”折中、融汇陈献章、湛若水两家思想,直指根本,为人开示简易直接的为学门径,使人人有入圣之门,一时硕儒辈出,前世不及,后世不逮,开一代风气之先。刘古愚肯定阳明“致良知”在教化大众上的普及之功。更进一步,他不惜笔墨对诋毁阳明“良知”思想的学说进行严厉批驳:
凡诋阳明者,谓入于禅,遁于虚,皆胸中有物,未尝平心以究其旨。一见“致良知”三字,怒气即生,遂不惮刻论深文,以罗致其罪也。[29]124
明末国初,诸儒鉴王学末流空疏之失,欲矫而救之,遂痛诋阳明。夫矫末流之空疏,可也,以空疏诋阳明,不可也。诋阳明而以“致良知”一语为遁于虚,尤不可也。[29]124
刘古愚着重分析学界将阳明“致良知”等同于“禅”的缘由:一方面是学者私意作祟,不能公心领会阳明“良知”精髓;另一方面是学界将王学末流空虚之病迁怨至阳明本人。刘古愚并非只是一味墨守心学,他因应时变,对阳明“良知”学说进行世俗化和经世化的推阐:
夫“良知”者何?即世俗所谓“良心”也,“致良知”者何?“作事不昧良心”也,此则蠢愚可晓,妇孺能喻矣。[29]124
很显然,刘古愚以“良心”解释“良知”,以“不昧良心”解释“致良知”,无疑是在为阳明思想祛魅,将其简单化、通俗化,使其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和认可。刘古愚有感于王门末学将“致良知”虚无化,故着意将“良知”思想向经世化一面转进,以纠治心学之偏。名士陈三立(1853—1937)就敏锐地点出刘古愚“尤取阳明本诸良知者归于经世”[29]2,陈氏所言不虚,刘古愚以“良知”为基,积极开拓“良知”的经世致用维度:“日本仿行西法,不遗余力,而其学校必先伦理……其道何由?阳明以“格物”为“诚意”之功夫者,此也”[29]20-21,又说:“中国‘格物’之学,必须以伦理为本,能兼西人而无流弊也”[29]21,刘古愚的意思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实学、实业必须在诚意、良知、伦理等的范导下开展才有积极的意义,否则必将祸害无穷。刘古愚身体力行,践行其说,学习西学,创办近代教育,开设工厂,投身实业,并在陕西积极开展维新运动等,无不处处强调“良知”的规范和引导。但刘古愚对阳明心学的这种通俗化、经世化的解读,实际上是减杀了心学的理论强度。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传播阳明心学时,深化阳明心学。相反,他终结了心学形态之关学[30]103。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当然与刘古愚本身对阳明思想的改造有关,另一方面是清代关中地区的心学气息原本就十分薄弱,纵观《关学宗传》所录清代关中学人,尊奉阳明者几无其人,再者亦与清末民初整个理学衰败,传统心学理论转换,出现“今人一见人讲道学,即以假道学诋之”[31]100密切相关。要之,这一阶段主要是如何对阳明思想进行提揭、改造和复振,以期在时代激变之际存续和阐扬阳明心学。
五、结语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区域学术形态的特质:(1)影响相对有限,基本上没有撼动关中地区张载及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阳明心学在明末清初的关中地区达至鼎盛,相对于明清四百余年的传播历程,更像是昙花一现。(2)呈现出抛物线、马鞍状的传播趋势,但起伏程度并不明显。阳明心学在关中的传播经历初传低迷,至明末清初达至鼎盛,随后即进入低迷、衰退状态,至晚清有刘古愚等坚守,但难挽颓势。(3)以会通朱王为基调。以冯从吾、李二曲、王心敬、刘古愚等为代表的关中主流学者,学宗阳明,但并不以阳明心学自限,而是主张以张载、朱子学之笃实稳健工夫来补正阳明心学的空虚邋等之病,以阳明心学之简易明捷来矫正朱子学的支离繁琐之弊。换言之,会通朱王一直是关中地区阳明心学的主题。阳明心学与关学是双向的争鸣与互动关系,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亦不断更新和生成着关学,推动关学的心学化转向,开启关学的多元化面向,使其融汇到全国性的学术思潮当中,成为地域学派全国化的典范。反过来,关学以张载、朱子学之崇尚礼教、笃实践履来补正和发明阳明心学,推进阳明心学的自我重构和完善,可从刘宗周“异时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以重躬行,而学者误之,反遗行而言知。得先生(吕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一发千钧”[7]11得到印证。关学的这种推阐将阳明心学在尽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丰富和呈现阳明心学多维的学术样态,尤在明清之际成为坚守和捍卫阳明心学的重镇,成为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鲜活的典型。总之,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表明阳明心学在全国的接受与传播绝非是同步等质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显豁出关中地区特有的保守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