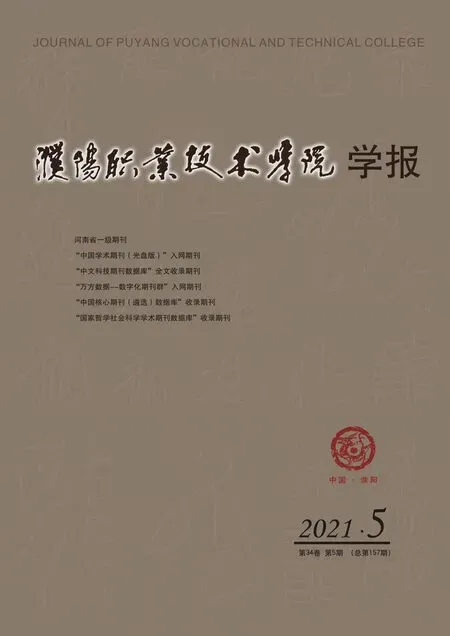从“知人论世”说看《水浒传》的价值取向
王莹雪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404120)
《水浒传》创作于元末明初,文本时间为北宋末年。元末明初与北宋末年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时期,是统治者走向灭亡的时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是阶级压迫残酷的时代,是政治最为黑暗的时代。作者施耐庵,主人公宋江,生逢此时,有着相同的政治抱负,有着同样的悲剧命运。小说《水浒传》与创作时代中的人们、作者施耐庵皆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今之读者,若欲读懂文本孕育的精髓,需要了解作者施耐庵的思想渊源以及人生经历,需要读懂创作时代的社会环境,如此方能领悟寄托于宋江身上的个人怀抱,才能洞悉作品的价值取向。
达到以上的审美目的,需要采用孟子的“知人论世”的文学鉴赏方法,从作者施耐庵与社会时代特征这两个方面来剖析作品产生的思想渊源与价值取向。以下我们就从“知人论世”说、“知人论世”在小说中的解析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孟子的“知人论世”说
阅读古代作品,犹如与古人交心。读懂古人的作品,就要成为古人的知音。了解古人,知晓古人身世,是连接古人——作品——今人的最佳纽带。亚圣孟子将此种文学鉴赏之法称之为“知人论世”,他在《孟子·万章下》提出了“知人论世”的主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234)焦循在《孟子正义》注释“尚”即“上”,友好之意,“尚友”即“上友古人”[2](126)。知人论世就是要与古人交朋友,了解、读懂朋友。孟子的“知人论世”原本是以人和社会两个支撑点来解读文本,从而达到正确解读人与社会的目的。后之论者将其推而广之,引入到文学评论的领域,成为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方法和原则。随之,“知人论世”成为文学批评的范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大理论。
知人论世的具体做法是,在阅读文本时,要解读文本的作者即古人及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换言之,“知人论世”这一文学评论法,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解读作者,包括家世、成长环境、思想、人生经历等因素;二是解读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把握其对作者的影响。这一方法,可以引导读者对作品的价值取向做出尽可能正确的结论。根据“知人论世”说,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小说《水浒传》的价值取向,文本中的一些困惑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作者施耐庵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特征入手。
二、“人”与“世”:施耐庵与元明之际的中国社会
(一)施耐庵生平事迹
通常认为,施耐庵为泰州白驹场人,生于1296年,卒于1370年,享年75岁。施耐庵生于元朝,死于明朝初年,生逢改朝易代、由乱入治的元末明初历史的关键点。作为雄才大略、身怀治国大志的施耐庵,在这一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漫长的追求人生理想的坎坷曲折之路。在元末明初壮观雄阔的历史舞台上,施耐庵扮演了两大角色:怀才不遇的士人、皓首穷经的书会才人兼小说家。
1.末世文人,仕途蹭蹬。施耐庵心怀天下,抱有治国济民的理想。施耐庵忙忙碌碌,奔波半生,却因怀才不遇,而半世一事无成。施耐庵40岁以前致力于考取功名,但一生不得志。施耐庵少以才学闻名乡里,19岁参加延祐科举,中秀才。29岁参加乡试,中举人;后赴京城(大都)参加会试,不第,途中经过梁山泊,施耐庵进行实地考察,为小说创作打前站。36岁时,施耐庵被地方政府推荐为“乡贡进士”,施氏家谱把施耐庵称为“元朝辛未科进士”,原因就在于事实上大家都把乡贡进士称为进士。经好友刘本善推荐,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在此次任上,施耐庵大量搜集民间水浒英雄故事,为写作《水浒传》积累了大量的素材。38岁时,施耐庵再次赴京城会试,应试不第。40余岁时,施耐庵任钱塘县尹,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欲施展抱负,大干一场。不料,大权落在蒙古官员手中,施耐庵手脚被缚,无能为力。绝望的施耐庵“官钱塘二载”之后,返回家乡苏州,收集水浒资料,成为书会才人。52岁时,施耐庵在苏州设馆收徒。据说当时18岁的罗贯中,就是施耐庵的第一批得意门生,师徒二人合作完成小说《水浒传》的创作。其间,施耐庵曾幻想参加张士诚的起义军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依旧是无果而终。
施耐庵考场失意,落第举人的士人身份,决定了在《水浒传》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书生形象”如王伦、吴用。“白衣秀士”王伦,是落第秀才;智多星吴用,是乡间的教书先生。在他们身上,无不闪烁着作者施耐庵的身影,无不寄托着他的个人怀抱。仕途潦倒,报国无门的文人形象,在小说人物宋江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2.书会才人,小说作家。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大才子,他所生活的时代——元末,正是元杂剧兴盛之时,施耐庵家乡恰是杂剧创作的中心。江南苏州,杂剧素材丰富多彩,才华横溢的施耐庵,充满激情、孜孜不倦地投入到了杂剧的整理、材料收集的工作之中。早期,施耐庵进京赶考途中,曾考察过梁山泊,那时壮志满怀的施耐庵尚未有创作《水浒传》的意图。这一时段的积累,却给后来事业惨败、立志著书的施耐庵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张士诚兵败身亡,保持晚节的施耐庵誓不投降朱明王朝,隐居创作长篇小说《水浒传》,成为名副其实的书会才人。晚年的施耐庵,将余生光阴投入到了小说《水浒传》的创作,成为古典名著之一的作家而流芳后世。
(二)元明之际社会历史
施耐庵人生的活动主要发生于元明交替之时,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文学创作、晚年遭际无不与时代背景关系密切。元朝末年,政治黑暗,苛政猛如虎,民族压迫日益加深,汉族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激化。因此,元朝统治的90多年内,反抗不断,元朝末年,农民起义更是风起云涌,元朝统治摇摇欲坠。在这新旧王朝交替、风云际会之时,曾经两次科举未中、仕途不得志、几度沦为下僚而无法施展才华抱负的失意文人施耐庵,乘时而动,重振雄风,认为大展宏图的时机已经降临了。怀着“治国平天下”之志,施耐庵毅然参加了同乡盐商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军。
张士诚的起义军转战江南所向披靡,占领苏州,割据江南,成立大周王朝,自号“吴王”。张士诚建立“宾贤馆”,礼遇读书人。施耐庵在内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张士诚是位“明君”,自己是千里马。被一些文人奉为“礼贤下士”“明君”的张士诚,实质上,是第二个袁绍,表面上尊重文人,其实是残暴愚昧,不纳忠言,“忠不必用,贤不必以”。不仅如此,张士诚生活极其奢侈,耽于酒色,不思进取。最重要的是其政治目光短浅,一旦遇到当世人中蛟龙的朱元璋,张士诚屡战屡败。张周政权,江河日下,人才纷纷离去。施耐庵的政治理想,随着张士诚的失败而再度宣告破产。
曾一度认为得逢明君的施耐庵,再次铩羽而归。尽管张士诚不是纳谏如流的刘备,也不是善于纳言的曹操,而是外宽内忌、善谋少决的袁绍。面对色厉内荏、好谋无断的主人,施耐庵不离不弃地跟随张士诚。拣尽寒枝不肯栖,施耐庵坚守“忠臣不事二主”之志,多次拒绝朱元璋盛情邀请。从这一点来讲,施耐庵的忠心近乎愚,类似于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朱元璋斥责《水浒传》为造反之书,将施耐庵关入大牢。经同年刘伯温的多方周旋,施耐庵得以重见天日。晚年的施耐庵,过着稳定而隐居的著书生活,小说《水浒传》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施耐庵的这段兵戎生涯,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素养,这为梁山泊抗击政府围剿所组织的败高球、赢童贯、三山聚义打青州等军事战争的描写,提供了较为详尽的、专业的军事知识储备。浦玉生认为,《水浒传》“45回以后施耐庵转入军事行动,以张士诚起义为原型的军事活动隐晦曲折地写入书中”[3](23)。
综上所述,元朝末年民族矛盾尖锐、政治黑暗的社会背景,与小说《水浒传》文本描写的两宋之交的社会政治生态是非常相似的,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与小说文本描写的社会状况相映成趣,相互印证。
三、从“知人论世说”看《水浒传》的价值取向
(一)反贪官——官逼民反
施耐庵生逢政治黑暗的元朝末年,贪官遍地皆是,堵塞了忠贞之士报国之门。因此,施耐庵“官钱塘二载”弃官而去。元朝末年,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元杂剧《窦娥冤》集中反映了这一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在前期,也就是天下大乱之前,施耐庵并未对元朝朝廷彻底失望,仍然抱有幻想,希望统治者英明,渴望廉洁、清正的官员出现,这一思想倾向在小说《水浒传》中得以尽情展现。一贪官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耿直官吏的登场。贪官与清正之官并蒂描写,充分体现了施耐庵对黑暗政治仍抱有一丝的幻想,表达了对清明政治的向往之情。
“乱自上作”“官逼民反”是小说《水浒传》所揭示的梁山泊造反的政治原因。梁山军只反抗贪官,却不反对朝廷。宋江之所以与朝廷军队开战,是为掌握与朝廷求和的主动权。小说《水浒传》塑造了自上而下各个层次的贪官,大贪官如高俅、童贯、杨戬、蔡京等四人,小苍蝇者如郓城县的知县、青州知府等人。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贪官的极度仇视,认为对搜刮而来的钱财应该人人可得。因此,作者设计了“智取生辰纲”的情节。劫取生辰纲的第一发起人是赤发鬼刘唐,十足的江湖人士,有此强人的想法可以理解。刘唐劫取生辰纲的理由是:“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4](178)第二个劝说晁盖参与的人,却是饱读孔孟圣贤之书的教书先生智多星吴用。吴用不认为拦路抢劫是可耻的事情,却说:“此一事却好。”[4](182)第三个主动参与者是后来极力想同梁山划清界限的一清先生公孙胜,出家人却对尘世之事念念不忘,实在出人意料。公孙胜说:“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古人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4](195)而后又坚决斩断尘缘,前后判若两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细加研究便会发现,公孙胜同晁盖、吴用、刘唐等人在“反对贪官,劫其不义之财”这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从而促成了行动上的一致;在与朝廷为敌、聚义造反方面,公孙胜却不赞成,拒绝参加。公孙胜矛盾的心理,前后相反的举动,反映了施耐庵前期痛恨元朝贪官,却执着于功名的复杂心态。这也是“反贪官而不反朝廷”的政治思想在公孙胜身上的体现。
刘唐、晁盖、吴用等人皆认为“不义之财”,当取就取。“不义之财”指的是贪官搜刮的民脂民膏,劫取生辰纲在江湖中已有先例,也就是反贪官、取不义财,成为江湖人士的共同心愿。小说大写特写的“七义劫取生辰纲”,从行动上打响了反对贪官的第一枪。后来,三山聚义打青州,攻打大名府,梁山泊将城池中的粮草、钱粮据为己有,在他们看来,这些是不义之财,是民脂民膏。只取粮草,不占城池,梁山泊“替天(宋朝皇帝)行道”,清除贪官污吏、人民蛀虫,体现了“反贪官,不反朝廷”的思想基调。
(二)正统、平民化——忠君思想
有学者考证,施耐庵原籍苏州阊门外施家巷,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5](9)。故施耐庵服膺儒学,而伦理纲常理应是形成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素。施耐庵有着强烈的忠君思想,一是58岁以前,忠于元朝统治者,即使不满黑暗政治,抱怨怀才不遇,但那却未萌生不臣之心;二是忠于“张士诚”。虽然张士诚不是真心实意地对待他,虽然张士诚因个人原因,称不上明君,也难以成大事;尽管朱元璋比张士诚优秀数倍,是未来天下之主,是当世神武英明之君,深得士人之心,有志之士趋之若鹜。但是,施耐庵对此却置若罔闻、矢志不渝地跟随张士诚左右,忠心耿耿,永无二志。施耐庵前期忠于元朝统治,是典型的忠臣,虽然近乎愚;忠于张士诚,则是忠君的延伸之义,其内涵是忠于主人。在小说《水浒传》中施耐庵极力表达自己的忠君思想,当然在文本中的“忠君”内涵的思想支持因素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与施耐庵相同,小说《水浒传》的“忠君”思想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统的忠君思想。正统的忠君思想,指的是臣子对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君主的忠心。小说中的宋江,受过儒学的影响,忠于朝廷,忠于君主,坚决不做“犯上作乱”不忠之事。即使被奸人、贪官所逼,被迫落草为寇,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反朝廷的大事,但最终目标是为了得到朝廷的招安,走上一条忠君报国之路。二是以忠义为道德核心的忠君思想。孔子《论语》强调了忠的道德含义:“为人谋,而不忠乎?”[6](4)指出了“忠”的对象,没有严格地限定为正统皇室的“君主”。展现乱世纷争、风云际会的历史画面的小说作品,往往着力表现文人武将对乱世明主(割据势力或起义军领袖)的忠诚。乱世文人、武将对枭雄明主的忠诚,基于“忠义、诚信”的伦理道德。例如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中歌颂了忠于各方诸侯的忠诚之士,如张飞、赵云、关羽、诸葛亮之于刘备,太史慈、甘宁之于孙权,许褚、典韦之于曹操,田丰、沮授之于袁绍等。小说《水浒传》宣扬了基于兄弟、江湖之义的“忠君”思想,这里的“君”,已经平民化了,不再是“君主”之君,而是值得追随的江湖带头“大哥”,即宋江。宋江坚决主张走招安路线,虽然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极力反对,但是等到宋江率众归附朝廷,他们依旧追随。招安后宋江屡立战功,却忠而被谤,为奸臣所害,李逵、吴用、花荣等人誓死追随其于地下,这真是可歌可泣的忠诚之举。
(三)造反有理——反招安
在“造反事业”如火如荼之际,梁山泊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政治走向,无非有两种:一是走农民起义军推翻北宋朝廷之路,将造反事业进行到底;二是以胜求和,逼迫朝廷接受招安。继续造反的政治路线将会使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成为封建士大夫眼中的逆贼,同时历史证明,农民起义军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李自成起义等。饱读诗书、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的宋江,绝不愿意成为黄巢第二。招安的政治路线,渠道上能够畅通,但招安之后,在奸臣当道的朝堂之上,前景如何,令人堪忧。因此,在造反与招安的问题上,梁山泊存在两种态度。李逵首先发难,反对招安,其次是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李逵是出于鲁莽、坦率,以造反为乐趣,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心思缜密、头脑冷静,是在充分认识黑暗政治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招安的,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洞悉了官场阴暗不见天日,预计到了招安后的悲惨结局。如此,这场争论使得梁山泊英雄顿时陷入了既不愿一生为寇,又担忧招安后前途未卜的两难处境。因此,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宴会,不欢而散。
招安前后,梁山泊诸位英雄的人生境遇截然相反。招安前,梁山泊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梁山好汉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一家人。招安后,梁山好汉流血牺牲,得不到朝廷信任,遭到奸臣陷害,景象凄凉,命运惨不忍睹。鲜明对比之下,作者施耐庵显然是支持梁山泊反对贪官与奸臣的,是反对招安的。
施耐庵支持水浒英雄造反,是因为他痛恨贪官和奸臣。在小说中施耐庵描写了蔡京利用生日大肆搜取钱财,梁中书为讨好岳父,榨取民脂民膏,名为“生辰纲”。为了表达对贪官的痛恨,施耐庵特设置了“劫取生辰纲”的情节,以雪对贪官的痛恨之情。施耐庵同样痛恨奸臣,小说开始讲述不学无术的高俅如何发迹,成为殿军太尉。朝廷任用了游手好闲、不孝之徒为官,预示着北宋末年政治的黑暗。高俅睚眦必报、妒贤嫉能,伙同童贯等人蒙蔽圣听,陷害梁山英雄。
施耐庵反对招安、支持造反,除了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皇帝懦弱的政治背景之外,还有其个人原因。施耐庵早年励精图治,想大干一番事业,被当道的蒙古官员掣肘,无法实现政治才干。这与宋江等忠义之士被当道的奸臣陷害,报国无门,何其相似。中晚年的施耐庵处于元朝末年,元朝统治更加残酷,政治异常黑暗,各地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对元朝统治者彻底绝望的施耐庵选择了造反,参加到了农民起义的洪流中。施耐庵认为只有通过造反才能够换来清明政治、国泰民安,因此极力支持造反。支持水浒英雄造反,是施耐庵人生政治智慧的结晶。
施耐庵追随张士诚起义,尽心尽力辅佐之。后来张士诚败局已定,树倒猢狲散,追随者做鸟兽散,施耐庵却依然不离不弃。及张士诚自焚而亡,施耐庵不事二主。尽管朱元璋多次表达诚意,善意邀请,施耐庵屡次拒绝,态度坚决。施耐庵不降朱明王朝,那么自然不会主张宋江等人投降朝廷。他以宋江投降朝廷,遭遇被害身亡的悲惨命运,从侧面证明其反对招安、誓死不降决心的合理性。
(四)抗击外敌———保家卫国
整个北宋王朝统治期间,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长期与大宋王朝对峙。到了北宋末年,朝政日非,奸臣当道,军事力量极度衰弱。北宋王朝,屡次遭到辽、金的侵略,给中原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抗击外邦侵略,是当时社会政治主题。宋江率领梁山泊降军,与辽军作战,抵抗辽军侵略,是在保家卫国,乃正义之举,符合当时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前期对社会造成一定破坏的梁山“好汉”,后期成为了类似岳飞的抗辽英雄,为人们所赞赏不已。从这个角度讲,梁山好汉是忠义之士。
施耐庵对梁山抗击辽军的壮举,也是赞叹不已。同时,施耐庵将梁山草莽英雄转化为以保家卫国为思想灵魂的忠义英雄。施耐庵对梁山义军在抗击辽军中付出的惨重代价持以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支持宋江等人的保家卫国事业,另一方面又为梁山好汉一个个在战斗中惨死的悲剧命运感到万般的悲痛,抒发了无限的伤感。这般微妙的情愫,以及设计梁山英雄抗辽的情节,并设置他们在战斗中一个个死去的悲惨命运,其创作动机皆来源于施耐庵经历的社会历史画面与他的人生体验。元朝的统治阶级是我国少数民族蒙古族,对汉族采取了歧视的民族政策。元朝末年,苛政猛如虎,汉族人民不堪重负,被迫起来反抗。
对于农民起义军,封建统治者、文人士大夫往往对其嗤之以鼻,甚至骂其为贼,如《三国演义》罗贯中视“黄巾军”为贼,《水浒传》称“方腊”为贼。但是,反抗蒙古族残酷统治的元末农民起义军,施耐庵不仅思想上是认同的,行动上更是大力支持,加入了这场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之中。同是造反派,同是义军,施耐庵视方腊起义军为贼,视梁山义军为忠义英雄。其原因就在于梁山义军后来归附汉族政权北宋朝廷,最重要的是抗击了辽军的侵略,顺应了人心民意。元朝末年,抗击暴元统治,成为当世英雄的共识,甚至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创作时代与故事文本时代是何其相似,两个遥遥相望的历史画面,施耐庵的《水浒传》一书架起了两个相似的社会历史时代。
施耐庵把自己的个人情怀与人生价值,寄托于宋江义军身上。明写梁山泊,实则写元末起义军;明写宋江,实写张士诚。浦玉生认为,“水浒的原型是以宋江起义为名,行张士诚起义之实”[7](2)。
知人论世,是今之学者常用的文学评论方法,其实质是以史证文,以达到合理解读文学作品的目的。文学作品终究是艺术作品,尤其是小说具有虚构性;历史是真实的,不容半点虚假成分在其中。从文学与历史的实质来讲,“知人论世”文学评点法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尽管如此,就小说《水浒传》而言,所叙宋江造反等事与《宋史》以及其他故事内容有诸多不符之处,唯有与施耐庵生平以及元末社会现状极其相似。
只有采用“知人论世”评论准绳,才能合理理解小说《水浒传》中很多令人费解的情节,解答人物形象所做出的不可思议,甚至前后矛盾的言行,比如武松之于造反与招安前后不一的态度。因此,“知人论世”法,是解读施耐庵小说《水浒传》的不二法门,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