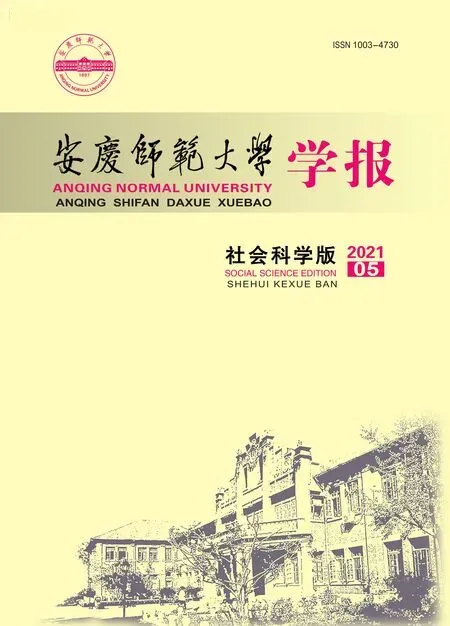“警世钟”疑案拾遗
贾高邦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1904年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展开了对《警世钟》一书的调查,查禁时中、启文、镜今、东大陆四家书社,抓捕王振楷、茅伯树、潘锡泉、程吉甫①各材料中所载四人的名字略有不同,王振楷即王正楷、茅伯树即茅伯如、潘锡泉即潘锡全、程吉甫即程吉孚。四名书店执事,制造了“警世钟案”。学界对于“警世钟”一案的关注甚少,仅有张运君的《论清政府对〈警世钟〉的查禁》[1]一文,其结论“‘警世钟案’是清政府制造的暴行”②过去学界多认为“警世钟案”是清政府制造或由其主导的,除张运君在《论清政府对〈警世钟〉的查禁》一文中持此观点外,其他学者如王鉴清也曾提出类似看法。参见王鉴清:《陈天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值得商榷。
“警世钟案”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其前后历时数月。其间,《字林西报》《申报》《时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等多家报纸对该案持续报道。这些报纸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报道内容各有侧重,为我们研究“警世钟”一案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除当时的报纸外,尚有上海市档案馆编纂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以及上海市档案馆藏的《工部局逮捕出售“警世钟”一书的书商的申诉》等档案资料。本文运用这些资料,以期还原“警世钟”一案的审理原貌。
一、“警世钟案”案情梳理
陈天华的《警世钟》一文大约写成于1903 年,全文通俗易懂,抒发了深切的爱国热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警世钟》一文写成之后,勘定成册,首布于日本,之后传入国内,引起强烈反响[2],而“警世钟案”的起因正在于这本小册子。
(一)工部局针对《警世钟》的调查
以往学者研究“警世钟案”,皆以工部局逮捕茅伯树等四人为起点,而忽略了案发之前工部局的调查阶段。实际上,早在工部局逮捕各书社执事之前,其针对《警世钟》一书的明察暗访便已开始。关于“警世钟案”的案前调查,租界内的华文报纸虽无报道,但《字林西报》却有较为详细记载,这些记载散见于12月9日的初审记录中:
西捕马克涛(McDowell)在会审公廨上说:“11月30 日,督察长将这本书交给他,并要求他对该书在上海的传播进行调查,这本书的名字叫《警世钟》。”当天,工部局派了一名本地人(native)前往调查。“他获得了12册,其中6册来自茅伯树在河南路的商店,另6册则从王振楷在山东路的商店买得。”
第二天(12 月1 日),本案的一名证人(witness)③《字林西报》的报道将其称为witness,笔者认为将其译为证人似有不妥,这位witness不仅参与了案件调查而且还提出了申请搜查令,似乎受到工部局的指令,应该是类似于线人一类的角色,而非单纯意义上的证人。为了行文准确,后文中的所有引注均直接以“witness”称呼。前往山东路调查。“他去了山东路的王氏书店,询问这些书是怎么来的。然后,经理出示了一个手写的账簿,上面显示有二十三本书(《警世钟》)进入了他们的商店。经理说,这些书是从一个名叫潘锡泉的中间人那里购买到的。潘锡泉随后被他唤来,潘说他是从茅伯树河南路的商店里拿到这23 本书的。潘陪着witness到了位于河南路的书店,那里的经理人茅伯树承认是他提供了23本书给潘。他(茅)也提供了他的账本,上面显示他一次性就得到了550本《警世钟》。当被问及从何处购买时,他(茅)说从爱而考克路1.731号,一个中国人开的印刷厂里。witness 申请了搜查令。爱而考克路1.731 号,在那里,他找到了程吉甫(显然是程吉甫在负责这些书)。witness 在处所内搜寻,但没有发现所提及的那本书(《警世钟》),而发现了几本针对中国政府的煽动性书籍。河南路书店的茅伯树确定程吉甫就是为他提供了550册《警世钟》,并收到付款的人。程吉甫说,这些书的原件是从日本获得的,并在爱而考克路的印刷厂复印。目前负责出版的人不在,跑到江西去了。witness 说,也许被捕者会辩称他们不是商店的主人,但无论如何他们显然是负责人。在任何情况下,被捕者都说他们的主人目前不在上海。中间人潘锡泉承认他从河南路书店购买了23本书,然后将其卖给了山东路书店。”[3]
通过马克涛和witness 的法庭发言,可以勾勒出该案案发之前的调查环节。11月30日,督察长命令西捕马克涛调查《警世钟》一书。当天(11 月30 日),工部局派出了一名当地人前往茅伯树、王振楷的书店调查,发现了两书店出售《警世钟》的事实。第二天(12 月1 日),一名witness 前往王振楷的书店继续调查,顺藤摸瓜找出了中间商潘锡泉。而通过查询账簿,witness 最终锁定了这些书来自于程吉甫的印刷厂。
(二)“警世钟”一案的案发
关于“警世钟”一案的案发,《申报》与《字林西部》皆有记载,其内容基本一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案发时间的记录。
12月9日《申报》所载案发时的情况:
英美等国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查知今日界內各书坊出售警世钟一书,专事谤讟洋人。因派人至山东路启文社购得。询悉由时中书局托售。及询之,時中书局称是镜今书局托售。诘之,镜今书局又称是东大陆书局托售。互相推诿,莫得主名①按《字林西报》所载,这些内容实际上应该是11月30日和12月1日(即案前调查阶段)发生的事。。因请公廨谳員黃耀宿司馬,饬提各局主讯究,司马准之。立即签发差协同五十四号西探及某华探将启文文社执事人茅伯树……程吉孚拘入四马路老巡捕房押候解送公堂讯究[4]。
12月9日《字林西报》所载案发时的情况:
会审公廨,1904 年 12 月8 日②此处,《字林西报》记载的案发(工部局捕人)时间是12月8日。而《申报》在12月9日报道该案时,并没有报道案发时间。之后的《上海地方志》《上海审判志》皆载“十一月初三(12月9日)清廷会同工部局查禁出售《警世钟》,并逮捕时中、启文、镜今、东大陆等书局执事。”按《字林西报》为工部局官方报纸,其所记载的时期当无误。而《上海地方志》《上海审判志》皆载案发时间在12月9日,这种说法有可能是两书在转录《申报》的记载时产生的疏漏,而将《申报》的刊载时间误以为案发时间。,谳员孙,观审巴切特(Barchet):四名书商被指控在1904 年的不同日期在租界范围内,散播反外国文学作品。此案被押候,将在第二天早晨由英国观审审理[5]。
可以看出,相较于复杂的案前调查,抓捕过程相对简单。工部局提请会审公廨捕人,经公廨谳员同意后,工部局便差人将四人拘入巡捕房。
(三)“警世钟”一案的初审
对于案件的初审,12月10日《申报》所载的内容较少:
启文社、时中书局、镜今书局、大陆书局等因出售警世钟一书谤毁洋人,经工部局董查获各局伙黄珍嘉③租界内的报纸多引《字林西报》的消息,《字林西报》为英文报纸,其报道几位中国人的姓名为:Mow Pah-zue(茅伯树)、Zun Keh-foh(程吉甫)、Wong Chung-sha(王振楷)、Per Sze-zeh(潘锡泉)。《申报》等报纸在转引《字林西报》的消息时,多有错误,如将Wong Chung-sha(王振楷)译为“黄珍嘉”。(王振楷)等,昨日解案,请究启文等书局。公延律师爱礼司到案伸办。先由五十四号西探禀称启文等书局售卖犯禁之书有违定竟,请为究办。爱律师称此书系由东洋寄来请各家代售,为数不多、已将告罄。司马著将黄(王)等交人保出再行核夺[6]。
而《字林西报》对于案件的初审记载非常详细:
初审日期在12月9日,由会审公廨对四人进行初审,观审为副领事德为门(Twyman),清方谳员黄煊。茅伯树、王振楷、潘锡泉的辩护律师为爱礼司(Ellis)。西捕马克涛(McDowell)以及一名证人(witness)出庭。马克涛以及证人首先在法庭上展示证据,接下来双方进行了交叉询问:
爱礼司询问(交叉询问)了一下。
证人(witness)说,被派去买书的那个人不是警察内部的人。
爱礼司先生问他是谁,西捕马克涛拒绝说:没必要说这个人是谁。
爱礼司先生向法庭申诉说:证人是否应回答这个问题。
法院说,他们确实不能强迫证人回答问题,仅这种情况除外——证人向法院作记录是允许的(这些记录的内容是关于一些当地人买书,证人从一些不知名人士那里得到了12本书)
马克涛说,如果他提到该男子是谁,该男子将有被杀的危险。
爱礼司先生反对这种说法。他说,如果该男子来到法院,并说他从某些商店购买了那么多书籍,那么这将是直接证据。
马克涛说,他可能会让这个人来,但是那个人很害怕[3]。
从现有材料来看,初审时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马克涛以及证人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问题,而于案件事实则并不关切。被告律师对于马克涛以及证人的案前调查持怀疑态度,并坚持要让那位买书人出庭作证,但西捕坚决不同意。交叉询问完毕,爱礼司向法院申请暂时将这几名被捕者交保释放。
(四)“警世钟案”的覆审及判决
对于覆审的过程,《申报》及其他报纸略有提及,英文版《字林西报》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整个案件的覆审过程。覆审日期为12月29日,代理观审海轧士(Higgs),清方谳员黄煊。除了茅伯树等三人的律师爱礼司以外,程吉甫也聘请了律师李楠芳(A.L.Ahlo)。双方继续在庭上交锋,《字林西报》有详细报道:
爱礼司先生继续对西捕马克涛进行询问(交叉询问)。
witness 说,据他所见,(到他来书店时为止)在山东路王振楷的书店中没有煽动性的书籍。王振楷负责这家书店,据说真正的老板不在这里。证人要求(王振楷)提供商店的账簿,并抄写其中一部分,以供他检查。他没有问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因为他从书本中得到了所有想要的证据。将书《警世钟》卖给店主的中间商是在witness 在商店的时候过来的,他告诉witness他是从河南路的一家商店买到这些书的。witness 在检查湖南路商店的书时发现,有五百本《警世钟》从他们那经手。它们是从新闸路的一家印刷厂买来的。
李楠芳先生说:witness 去了位于新闸路的印刷厂,并在那里找到了程吉甫。他(程)负责这些书,并承认他已将500本《警世钟》卖给了湖南路的商店,并收到了钱。witness不知道程吉甫是否是印刷厂的东家。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以东家的身份被追究起诉。这四名被告只是被控散发这种煽动性文学,witness认为这一点是证据确凿的。
一名华捕在被告被捕时陪同西捕马克涛,为西捕的陈述提供了佐证。
爱礼司先生说,他不打算请任何证人为他的被告(佐证)。
李楠芳先生叫来了被告程吉甫。程说他在一段时间内,曾是新闸路印刷厂的一名收货人,他还受雇于其他企业,他并不是印刷机构的东家。
另一位(由李楠芳先生请来的)当地证人,他说他也是印刷厂的收款人,他说他记得现有的东家和以前的东家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份合作协议以及加金的支付就是在这位当地证人的确认、见证下签署确认的。)相反,程吉甫的名字却没有以现任东家的身份出现在这些文件中。
爱礼司先生说,他代表被告在法院讲话时几乎没有话要说。关于被告王振楷,他要求法院查看警方的指控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证据的支持。指控上说:“在1904 年的多个日期,在租界范围内,涉嫌聚集非法传播的排外文学。”在法院判定王振楷有罪之前,必须对王振楷在该书店中所起的作用予以证明。西捕马克涛则说,当东家不在时,由王振楷负责。然而,法院没有证据表明东家何时离开,或者王振楷是否出售了任何书籍。在上次的初审中,马克涛提供了证据,证明有一个本地人(native)去商店买了六本书。当律师问到那个买书的人是谁时,马克涛拒绝说出,说如果他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后者将有被暗杀的危险。律师认为,这种陈述只是夸大案件,而不是真正地把聚焦点集中在(对囚徒的)指控上。法院说,他们(法院)不能强迫证人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证人不回答,他们(法院)将不得不从记录中剔除所有有关购买书本的当地人的陈述,并简单地只记录“证人从一些陌生人手中收到了12本书”。
在爱礼司先生讲话的时候,中方谳员命令王振楷站在长凳前。
在爱礼司先生继续的时候,马克涛主张质询王振楷的权利。
爱礼司先生强烈反对,说王振楷在这场辩护中不能作为证人被询问(言下之意,王振楷本人是被告)
马克涛说,有必要质询王振楷,主要是因为现任观审海轧士先生上次初审时没有出席。
观审海轧士指出,尽管他没有出席上次听证会,但是他面前有完整的证据记录。
庭审继续进行。爱礼司先生说,他的另外两个被告从事书商的业务。马克涛本人则说,从询问和收到的信息来看,这些囚犯从事的是合法且受人尊敬的售书业务。囚犯很可能在不知道书内容的情况下卖书,这是很自然的事。一个强有力的证明事实是“他们不知道书的内容,而且他们全力地配合了巡捕调取信息”。因此,律师将要求法院从宽处理这个问题。证据表明,囚犯并没有出售此类文学作品的习惯。在法院认定这是一个严重的案件之前,它必须满足这一特征——“这些人知道文学作品的性质”。尽管巡捕将这些小册子描述为危险和煽动性的作品,但法院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并说明“这些特定表述是否应被认为是危险的,或者仅仅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小册子的发行非常有限,因为这本书包含大量的垃圾信息。这些句子(巡捕还仔细、优雅地翻译了出来),根本不会导致恐惧。律师争辩说,尽管可能存在无知,但他的被告都是直率而又受人尊敬的人,他要求撤销对他们的指控。
李楠芳先生代表程吉甫说,检察官没有展示出被告有责任或者拥有新闸路印刷厂的所有权。“印刷厂的老板自己会做苦力工作”这样的认定合理吗?被告的地位仅仅是一个收款人而已。由前任和现任所有者(东家)签署的合作协议和销售票据均已制作和核实,没有证据与之相抵触,很明显,被告与印刷业务无关。根据销售单,之前的所有者(东家)是独立的授予人,并被购买者确认。因此,很明显,被告与这个行业(印刷)没有任何关系。几家受人尊敬的商家表示,他们知道被告是印刷厂雇用的收款人,并且他还充当了他们自己店里的收款人。仆人对主人的行为(无法直接或间接控制)不承担责任。被告与《警世钟》一书的联系不会比“(s..ship?)公司的船将其书籍带到上海、或将书籍从蒸锅运到印刷厂的苦力”之间的联系更多。律师辩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被告有罪,他要求驳回指控。
马克涛说,程吉甫承认他将这本书的500 册拷贝带到了河南路并收到了付款。
李楠芳先生指出,携带这些书只是对雇主所做的苦力工作,收到付款也是代表雇主收的,程吉甫本人只是他雇主的收款人而已[5]。
可以看出,与初审时律师针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诘问有所不同,覆审时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证据的实质内容。
爱礼司的论据主要是两点,一点是所谓的“不知者无罪”:“他们(茅等三人)不知道书的内容,而且他们全力地配合了巡捕调取信息。在法院认定这是一个严重的案件之前,它必须满足这一特征——‘这些人知道文学作品的性质’。”另一点则是对该书的内容是否具有危险性和煽动性表示质疑:“法院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并说明‘这些特定表述是否应被认为是危险的,或者仅仅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小册子的发行非常有限,因为这本书包含大量的垃圾信息。这些句子(巡捕还仔细、优雅地翻译了出来),根本不会导致恐惧。”
而李楠芳则对程吉甫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表示质疑,其认为程吉甫并非刷厂真正的东家,不应该代人受过:“(程)携带这些书只是对雇主所做的苦力工作,收到付款也是代表雇主收的,程吉甫本人只是他雇主的收款人而已。”当日的覆审被保留裁决。
1905年1月2日,案件最终判决。尽管在覆审期间,律师据理力争,但法庭(会审公廨)坚持认为所有的被告都有罪(all the defendants were guilty)。程吉甫被认定在印刷《警世钟》一书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判押西狱2年。茅伯树、潘锡泉各押西狱八个月,王振楷三个月①关于判决结果,上海各报纸都有记载。详见:《严惩谤书》,《申报》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廿八日(1905年1月3日);《警世钟定案》,《大陆报》1904年第11期(53-54页);The Anti-Foreign Crusade,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03,1905(005)。。
(五)“警世钟案”后续
“警世钟案”宣判之后,舆论一片哗然,首先是在沪各大报刊的报道。以仇俄排外著称的《警钟日报》撰文称“《警世钟》一书其词旨究有如何违碍之处?职等并未见过”[7],根本不以《警世钟》所言为禁忌。而保皇党所办之《时报》也撰文抨击该判决:“‘警世钟’一案,株连及售书之人,监禁二者。此本为无礼之尤者。试问办理此案,以中律定乎?以西律定乎?以中律定,则中国虽甚文字之狱,未有罪及售书人者……以西律定……今既无明文,又益之以失入。彼将视我民为何如人乎?”[8]甚至连一向反对革命、立论最为保守的《申报》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在前,既无禁止明文,彼书贾但知贩售为利,安能尽知书中之议论若何?且时中、启文、镜今三书局皆能指出寄售之人,其情亦似可谅。乃茅、潘、各人遽受判押西牢之罪,平心论之,未免过当。”[9]
相较于媒体,知识界不仅关注该案的审判结果,更关注其背后的主权问题与民族危机。“警世钟案”宣判后,夏曾佑曾两次撰文评议:“自古专制国之有权者,莫过于朝廷,而今则更有大于朝廷者;专制国之臣民,莫不以得罪朝廷为大戒,而今则更有甚于得罪朝廷者;专制国之官吏,莫不趋奉朝廷,而今则官吏所趋奉,更有过于朝廷者。以此思惧,惧可知矣。”[10]除了表示对清廷无能的不满,还表达了对列强悍然干涉中国司法主权的愤怒。在其《续论〈警世钟〉案》一文中,夏将这种愤怒上升为一种民族主义情感:“外人讥诮我、指斥我之报章书籍,几于汗牛充栋,我又将何以待之?夫权力虽有强弱,而民间之谤议初非国家所能禁止,尤非外人所能干与。今如许其干与,则是外人将强我之官长,以钳制我之人民;而我之官长亦将明告我之人民,不得有开罪外人之语。”[11]
审判结果公布之后,“同业公愤,迫不能平”,书业同行对于四名书商的判决也表示不满。商务印书馆总理夏瑞芳邀同各书局执事一起向上海道台袁树勋公禀以示抗议[12]。书商们抗议的理由有几点:一是书商“素称清苦”,其缺少文化,“不解书中命意”,只得“向有书之处辗转访配,以报买者之命”而已。二是官府无明文禁止,“警世钟一书即官府尚未有明禁”。三是惩罚过重,书商援引《大清律例》“凡私家收藏应禁之书者,杖一百,并于犯人名下追银十两,给付告人充赏”,并以乾隆朝屈氏私藏禁书案作对比,其做法不过是“止须销毁、毋庸查办”而已。四是不依中国法律,“或谓其书有诋毁外人之词,得罪友邦、恐伤睦谊,不得不略加惩儆。然治中国之愍,只能用中国之律。公廨委员,不能置祖训王章于不顾。而惟陪审西员意见是从也。”[13]
更值得玩味的是清廷的态度。上海道台袁树勋收到书业公禀后,竟也认为此案判决不当。“其潘锡泉、茅伯如、王正楷贩卖未经悬禁之书,寔系无辜受累,应即复讯、交保省释。惟程吉甫,系前在苏报馆案内从轻释放之人,此书又由伊出卖,是否即伊所著,虽无确证,要其为人,素不安分,应改押半年(保)释,以示薄惩。”[14]袁树勋即令黄煊照会英总领事,黄煊随即“转呈递公禀为之乞恩”。袁树勋在札文中表示,希望将程吉甫改为收禁六月,其余茅、潘、王等三人著司马提案讯释作罢[12]。
在收到袁树勋的照会后,上海租界当局并未将案件改判。“黄司马遵即照会英副领事德君,请重行提讯。去后兹得德君函覆略谓此案早经断定,难以更改,本副領事无覆讯之权如必欲更正,只好令其上控,本副领事于此案早作了结,不便再问云云。”[14]之后,袁树勋第二次照会英领事,再请重行提讯。“以警世钟案公堂会讯所判罪名深不平允,难以折服该业众商,是以昨日复又照会租界领袖德总领事,克纳贝君,请为重行提讯、改判,以昭平允云。”[15]但这次照会没有得到回应,《时报》在1905 年 5 月 31 日最后一次报道“警世钟案”,谓:“覆讯警世钟一案迭经关道袁观察照催领袖德总领事,转咨英总领事定期覆讯。在案茲悉德领事迄未照覆,直至昨日始由德领事照覆到道,略谓已于前日据情咨照英领事察办矣!”[16]此时距离案发已过去七个月之久,案件拖延至此尚未覆讯,袁树勋的努力已无济于事。
二、“警世钟案”是清政府制造的暴行吗
通过梳理案情,不难看出,“警世钟案”绝非清政府制造或主导,理由有六:其一,从案发原因看,《警世钟》一书“语涉排外”才是案发的根由。其二,该案自案前调查至案发阶段,未见清方派人参与;其三,该案在审判过程中,清方谳员的作用微乎其微;其四,该案的审判依据并非“中国常例”;其五,从清廷的态度看,其根本无意于惩罚书商,上海道对于案件的审理结果不满,其多次照会英领事请求覆审无果;其六,清廷事后虽有查禁《警世钟》的举动,但明显滞后于工部局,此时的查禁也并非在租界内,实已与案情无关。
(一)《警世钟》“语涉排外”才是该案爆发的主因
这一点,从《字林西报》对该案报道的标题上即可看出。每期《字林西报》都会开辟“Mixed Court”专栏,对会审公廨审理的案件进行报道,每个报道的抬头处都会起一简洁的标题①由于《字林西报》乃是工部局的官方报纸,因此它所取的标题相当于工部局对案件的官方定性。。比如1905 年 1 月 3 日与“警世钟案”同时刊登在“Mixed Court”栏下的就有一个“Bribery and Corruption”案,只看标题便知案件性质。“警世钟案”被《字林西报》报道过四次,四次报道的标题无一例外都是“Anti-foreign Crusade”(“排外活动”)。可见租界当局自始至终都是以“排外活动”给“警世钟案”定性的。
副领事德为门在给濮兰德的回复中给出了他对于“警世钟案”的看法,他认为下面四种类型的作品,其作者、出版商、经销商都应该受到处罚。这四种作品包括排外的作品、反宗教的作品、有伤风化的作品以及煽动叛乱的作品。“《警世钟》显然属于第一类作品”[17]。
《中外日报》就更为明确指出:“即各报纪载此事,亦有毁谤外人之语,则知此案诸人之获咎,殆不由得罪朝廷而起。”[18]既然此案“不由得罪朝廷而起”,清廷自然没有制造、主导“警世钟案”的理由,充其量不过工部局的帮凶而已。
(二)案发前的调查至案发时的捕人阶段,未见清方派人参与
《大陆报》载:“警世钟一书,语涉排外事,为工部局所觉,遂逮治印刷人及代售人,盖著书人以远飏也”[19],即只言工部局拿人,而未言华官参与。《中外日报》记载:“抑更有进者,闻此案初不由于华官之访拿”[18],直言“此案初不由华官之访拿”。《字林西报》12 月9 日的初审记录与此相吻合,西捕马克涛说:“11月30日,督察长(Captain-Superintendent)将这本书交给他,并要求他对该书在上海的传播进行调查,这本书的名字叫《警世钟》。”[3]督察长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领导,不管西捕还是华捕均要受工部局警务处领导[20],可知查禁《警世钟》一开始便是由工部局策划、实施的。
(三)该案在审判过程中,清方谳员的作用微乎其微
本案由会审公廨审理,审判人员由一名中方谳员和一名外国观审组成。但了解会审公廨历史的人都明白,此机构乃是列强攫取中国司法主权的一个楔子。尤其是到了20 世纪初,此机构名曰会审,实际上“惟近来洋官于互控之案大率把持袒护,虽有会审之名,殊失秉公之道。又往往干预华民案件,几归独断”,会审公廨近乎完全由工部局操控[21]。
“警世钟案”分为初审和覆审,两次审理时,清方的谳员黄煊都在场。但是从《字林西报》所载两日的庭审记录来看,整个过程,黄谳员几乎没有存在感。“在爱礼司先生讲话的时候,黄谳员命令王振楷站在长凳前,在爱礼司先生继续的时候,马克涛主张质询王振楷的权利”[5],这是中方谳员唯一一次发言。清方谳员虽然参与了案件的审理,但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其“惟陪审西员意见是从也”[13],在此案中发挥的作用甚微。
(四)该案的判决未依“中国常例”
根据《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凡有华民控告华民及洋商控告华民,无论钱债与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讯定断,并照中国常例审讯。”[22]可见,如果被告是中国人,应按照“中国常例审讯”,是应当适用《大清律例》的。
从定罪来看,《大清律例》有规定收藏禁书的犯罪行为。“凡私家收藏天象器物、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画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23]但是“夫应禁、不应禁之权,只能操之官府,不能令商人自为臆定”。《警世钟》一书此前并未被列为禁书,更何况此案中的售书之人根本不知书中的内容。即使在文字狱最盛之乾隆朝,也没有“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的先例①详见《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从量刑来看,《大清律例》中没有监禁收押的刑罚②《大清律例卷四·名例律·五刑》只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主刑,而徒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监禁刑。,而且相较于《大清律例》规定的“杖一百”,程吉甫等四人的量刑(监禁2年至3个月不等)显然过重了。
据此可以肯定,此案的判决绝非依据中国法律。试想,如果此案系清廷主导,岂有不以“中国常例”审判的道理?
(五)清廷根本无意于惩罚书商
收到上海书业联合送来的公禀后,袁树勋非常不满,曾前后两次照会英领事。第一次,他引用前番“苏报案”的例子作比较,认为(《警世钟》)“较之邹、章之倡言革命,情同叛逆者,罪之轻重,正自不同。邹、章不过监禁二年,售书者并未波及”,“两案相衡,尚应议从末减,况出售书贾牵连被逮者耶”[14]。按照袁树勋的意思,此案根本不应该牵连售书之人,最多是将程吉甫判押西狱半年以示薄惩(之所以惩罚程吉甫是因此他一开始没有老实交代书的来路),其余三人交保释放作罢[14]。
在第一次照会无果之后,他再次照会英领事,认为此案“深不平允,难以折服该业众商”[15],但此事还是不了了之。虽然最终的结果是清廷屈就于工部局,但双方就该案存在很大的分歧是没有疑问的。
(六)清廷查禁《警世钟》的举动滞后
清廷事后虽有查禁《警世钟》的举动,但明显滞后于工部局,而且此时的查禁已不在租界内,与本案几名当事人无关。清廷最早关于查禁《警世钟》一书的记录来自张之洞的《札北臬司通饬各属查禁逆书》,这份札饬写于1904 年12 月9 日,在案发之后1 天,也即工部局派人调查之后的第9 天,而查禁范围是两湖地区。札饬中写道:“兹经本部堂访获《警世钟》一书,系自上海传来”[24]446,此即明言清廷查禁《警世钟》是受上海方面影响。
札饬中处处透露着清廷畏惧列强的心理,如称此书“扰乱和局”“倡言排外,将以继穷凶极恶之拳匪而激成瓜分”等[24]446。清廷极力查禁《警世钟》固然是出于本意(《警世钟》一书本有仇满言论),但畏惧洋人才是根本。张之洞在札饬中写得很清楚:“勿启衅端”“召侮速亡”[24]446。在清廷眼中,得罪洋人会招来灾祸。而且张之洞在部署查禁《警世钟》之时,“警世钟案”已经在初审了。二者之间虽有联系,也只能是清廷的查禁受了工部局拿人的影响,而不可能是工部局听命于清廷。
三、“警世钟案”的深层背景
“警世钟案”并非清政府制造,其究竟缘何而起?又为何是此种走向?蔡斐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一文中提出了“司法是一种变量之和”的观点,他延续了美国法社会学家布莱克与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的研究路径,提倡“由个案发散至社会”的思路①详见蔡斐:《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司法》2012第6期第69页。。“警世钟案”与“苏报案”一样,也非纯粹的司法案件。该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整个案件有工部局的运作(背后有列强的授意),有上海道的参与(代表了清政府的态度)。案件的当事人既包括当时的革命者,又包括租界治下的普通书商。案件从案发到判决到社会反响,与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就大的背景来看,鸦片战争以来,在华人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排外情绪。就列强而言,在经历了“拳乱”之后,其对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十分警惕。就清廷而言,其虽与列强达成了和解,但终究存在矛盾。就双方的力量对比看,清廷在租界内的影响远不如工部局(背后的列强)。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本案最重要的当事人、《警世钟》一书的作者陈天华恰巧没有到案。
(一)华人社会中的排外情绪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种排外的情绪便始终笼罩在中国人身上。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全国各地华洋矛盾尖锐、教案频发,最终酿成了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的惨祸。庚子国变是中国人排外情绪最激烈的宣泄②据统计,自1842年至1911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1 998起,仅庚子年(1900年)一年教案就多达411起。参见赵树好、徐传武主编:《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与列强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解[25],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并没有消失。相反,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不断蚕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警惕西方势力的渗透。相较于之前的教案与义和团运动,彼时的排外运动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民族国家观念和以主权意识为基调的近代民族主义,而以非理性的排外主义(类似于教案、义和团式的)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民族思想渐趋式微,并归于沉寂[26]。
庚子之后,激进的排外运动明显减少,华人转而为一种“文明排外”。1900年,《清议报》发表《排外平议》,其认为“排外之道有二:野蛮人之排外也,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也,排以心力”[27],首次提出“文明排外”的主张,并认为这两种排外策略“排外之心虽同,而排外之术迥异”[27],对庚子事变造成的“覆败”后果进行反思。陈天华在《警世钟》里也明确表示要“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28],其传递的“文明排外”观念,正是这一时段华人社会排外情绪的一个缩影。
(二)列强的警惕心理
义和团运动使列强深刻感受到蔓延在华人社会中的排外情绪的威胁,给列强“脆弱”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在反思和改变对华政策①1903年2月至3月,《字林西报》对李佳白(Gilbert Reid)《中国排外动乱的根源》一文连续转载。李佳白认为,中国排外动乱的根源可以分为六个方面,即中国政府、外国力量、中国百姓、外国商人及其代表、天主教教会、新教教会。而激起“拳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国的侵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FEB.18、FEB.24、FEB.26 and MAR.4,1903.)。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但列强也见识到了中国人强大的民气,瓦德西在其《拳乱笔记》,中坦言:“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列强遂放弃明目张胆的瓜分政策,转而扶持清政府,采取所谓的“保全主义”策略。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6页。的同时,列强也在紧密关注中国人的“排外动态”,对华人的排外情绪严防死守。面对排外的讯息,稍有风吹草动,列强就会格外警惕。
1903年5月1日,《字林西报》报道了一则来自云南昭通府的新闻,并冠以“More Anti-foreign”(“更加排外”)的标题,但新闻的内容不过是有人在法国领事的大门上贴出了“外国鬼”的字样,而报社方面却认为这是出于“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得了的行为[29]。1904 年2 月,《字林西报》撰文,报道广东出现排外公告,并认为“这天一定会发生大屠杀”,并且派遣了军舰。但实际情况却是“连任何公开示威都没有,(这一天)就过去了”。事后证明,这些公告“很有可能只是一些流氓借以引发骚乱的手段”[30]。1904 年4 月13 日《新闻报》转引伦敦路透社的报道:“廿六日,伦敦露透(即路透社——引者)电云,英国晨报之烟台通讯员电称,中国排外政策业已加增,遍于北京全地。”[31]1904年8月31日,《字林西报》报道“Tsai Yuan②类似于哥老会的民间组织,详见The Tsai Yuan Sect,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10,1904(005)。及其排外计划”,并将“Tsai Yuan”称之为“新义和团”[32],“这些新组织起来的社党打算将他们的国家从不道德的铁路、电话、外国学校、外国宗教及不断增长的税收中解救出来。”[33]1904年11月15日,《字林西报》转引北京的报道说“反外活动再次复苏”[34]。1904年12 月5 日,《字林西报》报道:“最近《北华捷报》的很多通讯员报道了有关排外的谣传。不长时间之前,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听到一群中国人在讨论怎样消灭外国人。在颍州府,天地会形成了很大规模,排外的文学作品也在那里流传。”[35]从这些外文报纸中可以看出,列强的心态是非常敏感的。尽管有些排外活动确实很严重,足以引起列强的注意,但大多数报道其实是小题大做,甚至还有一些完全是列强的捕风捉影。
租界作为列强的核心利益所在,界内华洋杂居,其矛盾冲突较华界更为复杂。上海租界当局对于华人社会的排外情绪尤为关注。1904 年11月30日,工部局董事会就几名“怀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一案进行讨论,总董“建议发布一份布告,明确表示工部局无意保护煽动性和革命性的社团,而将重点放在检查被这些学生租用的房屋内有无排外刊物”[36]。可见,工部局对于案件涉及的其他政治问题,并不感兴趣,其关注的焦点只在于其“是否排外”。
(三)清廷与列强之间的矛盾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与列强表面达成和解。但实际上,其互相并不信任,各方之间矛盾重重。上至清廷与欧美各国政府、公使团,下至上海道、县与各国驻沪领事、工部局,具体到会审公廨中的谳员与观审,处处都在明争暗斗。
且不论清廷与列强在其他利益上的交涉,仅就租界内司法主权问题,双方就争得不可开交。“警世钟案”之前的“苏报案”与之后的“大闹会审公堂案”,皆是司法主权争端具体化的例证③苏报案所反映的问题更为复杂,其不仅涉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更涉及政治、外交,而且列强内部在如何处理“苏报案”的问题上态度也不一致。按照蔡斐的观点,“苏报案”是一裹挟着政治与司法等诸多问题的关键个案。参见蔡斐:《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司法》2012第6期第138页。。彼时,清廷对于列强干涉司法极为不满,双方分歧很大。以工部局的跨界捕人为例,1904 年12 月10日,上海道台袁树勋照会领袖领事美国总领事古纳,指出“工部局未经会审公廨签票在租界外任意抓人,是违章越权,今有界外捕人,一律凭会审公廨签票”[20]53。而工部局对此却不以为然:“会议经讨论后,决定说明采取这种办法是惯常之事,在过去几年中曾进行了相似的捕人之事,同时要求领事团批准工部局在这一案件上的处理意见”[36]694。对于工部局的这种态度,清方自然也不甘示弱,“从这些信件来看,目前(清方)谳员似乎打算拒绝签发搜查证,或审理租界外面发生的案件。总董认为当地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从中作梗的办法。”[37]除此之外,双方在对未决女犯暂押场所上也存在重大分歧,工部局方面坚持认为女犯应该暂押工部局巡捕房,而清廷方面则认为未决女犯应暂押会审公廨押所,这个分歧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大闹会审公堂案”[38]。
(四)清政府与工部局的力量对比
在租界内,无论是拿人、引渡抑或是审判,清政府都要受制于工部局。前者“苏报案”中,清政府与列强之间就司法主权问题有过一轮交锋。清政府虽然在收回领事裁判权方面有过努力,但却以失败告终。可以说,租界就是“国中之国”。清政府想从租界拿人,抑或是引渡,需要“外人允我查拿”,要绕过工部局这一关是不可能的[39]。至于审判,1902 年的《上海租界权限章程》规定:“两造皆为华人,与外人无涉之刑事案件,及关于界内华人之政治犯案件,必须由犯罪地界内之会审公堂受理。”,这就将审判的权限限定在会审公廨这一华洋混合的机构之中。会审公廨(堂)虽然由清方谳员和外国观审两方组成,但20世纪初,其实际运作已经由工部局把持[21],清廷想借由会审公廨掌握审判的主动权,几乎是妄想。
(五)案发之前,陈天华的去向
《警世钟》一书虽然在租界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案发时,其作者陈天华既不在租界,也不在华界。1904 年秋,陈天华与黄兴等人预谋在湖南起事,不幸事泄。陈天华经江西走上海,与黄兴等四人在租界预谋再次举事。此时恰好发生了革命党人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一案,陈天华因此案受牵连被捕,但会审公廨并未重判陈天华,而仅将其交保释放[40]。此事之后,租界内的革命党人一时人心惶惶,陈天华不得已再次出走日本[41]。陈天华的出走对本案的走向影响甚大。
四、如何认定“警世钟案”
通过前番对案情的梳理,已经可以认定此案绝非清廷主导。结合案发之前的社会背景,可以得出结论:“警世钟案”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背后是列强)策划实施的,是继“苏报案”之后列强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又一次践踏。此案还是一桩冤案,其实质则是列强针对华人社会排外情绪的惩戒。而清政府在该案中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清廷确有查禁《警世钟》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清廷与列强存在固有矛盾;更为重要的一点,该书作者陈天华并未到案,这使得清廷与列强在最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当事人”问题上难以达成契合。
(一)“警世钟案”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践踏
根据属地管辖原则,在租界内设立会审公廨,已然干涉了中国司法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这套“华洋混合”的机构存在,由其审理租界内所有的涉外案件,均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
但“警世钟案”又不同于其他案件,该案不止是“由会审公廨审理”这么简单。从程序来看,该案自调查至抓捕、审判的整个诉讼程序均系工部局(背后是列强)主导,列强的触手已超出了会审公廨仅有的审判职权。从实体依据来看,四名“案犯”即使是中国人也没有按照“中国常例”审判,这已经超出了《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因此该案对中国司法主权的损害是全方位的。
(二)“警世钟案”是一桩冤案
表面来看,会审公廨在审理此案时,遵循了近代司法程序,初审、交保、覆审一应俱全,在庭审时四名被告均聘请了律师,在法庭上还有证据展示、交叉询问等环节。但这些形式上的“文明”却无法带来实质的正义。该案之所以是冤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审判时“于法无据”。尽管古代中国没有现代刑法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刑罚也常被西方诟病为“野蛮”,但至少在朴素的观念中,百姓是相信律条的。
正如《时报》发出的质疑:“试问办理此案,以中律定乎?以西律定乎?”[8]如果按照《大清律例》,“则中国虽甚文字之狱,未有罪及售书人者”。如果按照西律,“则西律之于出版,原分而为三,凡著作人、印刷人、发行人均有责任,又其书之有妨害安宁秩序与破坏风俗者,皆有处分。然所谓处分者,亦不过未发卖时,则没收之;既卖出时,则著作者与发行者或处以十一日以上、一年以下之轻禁锢;或处以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未闻有监禁至二年者。”[8]而且,即使按照西律,租界当局也应该“颁发出版法律,俾书贾周知,然后可治之以罪”[8]。但彼时租界内既没有关于出版审查的法律,也没有列出禁书的名单。可见,无论是根据中律还是西律,该案的审判都没有法律依据。
德为门对工部局的恣意妄为甚至得意洋洋:“列一份书单出来,并将所有性质恶劣的书都规定进去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不告诉他们禁书的范围而让书商在售书的时候时刻提心吊胆(时时处于危险之中)反而是一件好事情。”[17]他这样的说辞与“刑不可知,威不可测”[42]实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恫吓与列强所标榜的司法文明显然自相违背,这不仅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更是对西方自身法治理念的侮辱。
(三)“警世钟案”的实质是列强针对华人社会排外情绪的惩戒
“警世钟案”的发生,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一股排外主义的情绪。在庚子国变之前,这种排外情绪是古老中国自发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是盲目的、激进的、野蛮的,其最终酿成了“合诸国之力以为报复”[27]的悲剧。而庚子国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主权意识开始在中国社会勃兴,“野蛮排外”逐渐演变为“文明排外”。《警世钟》此书恰是20世纪初“文明排外”意识的一个缩影。
尽管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强调“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28]72“我生平最恨义和团的”[28]75,但在列强眼中其“文明排外”的主张与“拳乱”别无二致,终究是要损害列强在华利益的。列强的这种看法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教案与“拳乱”的前车之鉴使得列强对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极为敏感,稍有“排外”字眼,便要防微杜渐,根本不在乎文明与否。二是该书所传递的主权意识对列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尽管《警世钟》字里行间都在与义和团划清界限,声称“平日待各国的人,外面极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尽要保护”[28]91-92。但若真的唤醒中国人的主权意识,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必然损害列强在华利益,这是列强根本不能接受的。
中国社会中的排外主义的大环境,以及《警世钟》一书所传递的“文明排外”的小气候,是列强不惜下重手查禁《警世钟》并严惩书商的主要原因。列强的举动,除了“禁逆书以杜乱萌”的惩戒目的,防止排外情绪的蔓延,同时也是在敲打清政府,迫其更加恭顺。
(四)清政府在该案中的心态是极其矛盾的
对于洋人,清政府是畏惧的;对于革命者,清政府是憎恨的。《警世钟》一书既排外又有仇满。这就决定了清政府在查禁《警世钟》一书的立场上与列强不谋而合。
但对于洋人,清政府除了畏惧也有不满;而对于书商,清政府却是同情居多,正如袁树勋所言,即使《苏报》所载言论“倡言革命,情同叛逆”,清政府也没有惩罚售书者。而此案相较“苏报案”,“罪之轻重,正自不同”,书商“寔系无辜受累”。
此种矛盾的心态决定了清政府在对待“警世钟”一案的态度上与列强明显不同。工部局从查禁《警世钟》到审判四名书商再到答复袁树勋的照会,其态度是明确的,是一以贯之的强硬。但清政府只在查禁《警世钟》一书的问题上顺着列强的路子;而对于书商,清政府甚至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五)列强与清政府难以找到第二个契合点
列强与清政府对待该案的态度不同,有一重要原因,就是本案最主要的当事人、《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没有被捕。陈天华的“缺席”,使得双方只在查禁《警世钟》的问题上有共识,而在如何处理当事人(书商)的问题上难以找到契合点。
试想,如果“警世钟案”案发时,陈天华也在国内,那该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走向了。至少,此时四名书商会变得无足轻重,那工部局是否还会严惩他们?上海书报业是否还会有联合公禀?袁树勋是否还要照会英领事?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五、结 语
仅从“警世钟案”的结果来看,当然是工部局大获全胜。清政府在本案中态度暧昧、反抗无力,很大程度上迁就了列强。
但从之后的历史演进来看,列强镇压中国人排外情绪的做法是徒劳的,这样做反而会激怒中国人,因为彼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主权意识已然觉醒。“警世钟案”不久,1905年租界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这被认为是一场文明理性的反抗列强的斗争[26]。1905 年下半年,会审公廨再起波澜,发生了著名的“大闹会审公堂案”。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两件事都是“警世钟案”的延续。抵制美货运动代表了民间的呼声,整个运动所体现出来的文明理性与《警世钟》一书所倡导的“文明排外”的内核是一致的。而“大闹会审公堂”一案则是清政府对于列强干涉中国司法主权行为的反击,当谳员关炯之大呼“既然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38]时,多年以来清廷在会审公廨积压的怨气终于爆发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