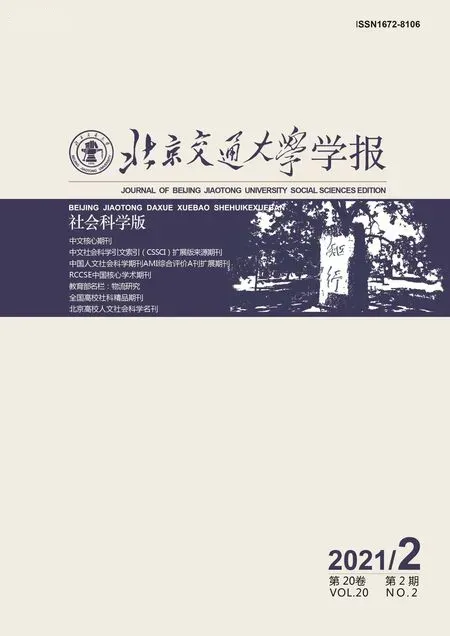论防疫常态化中的免疫辩证法
程 广 云
(1.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5;2.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48)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生命政治理论得到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以为,除了福柯(Michel Foucault)、阿甘本(Ciorgio Agamben)和奈格里(Toni Negri)等生命政治理论之外,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所提出的免疫辩证法是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的。本文首先梳理生命政治理论谱系,阐明免疫辩证法在这一谱系中属于第三条路线;然后解释免疫辩证法的含义,及其作为生命政治理论的两条路线的结合与我们通常所谓辩证法的区别;最后探讨免疫辩证法应用于防疫常态化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一、免疫辩证法在生命政治理论谱系中的位置
要厘清埃斯波西托免疫辩证法在生命政治理论中的位置,首先要梳理生命政治理论的谱系。在谈到生命政治理论谱系的时候,大家通常都从福柯开始。吴冠军[1](P46)(2016)曾描述过这样一个谱系:“从福柯到阿甘本,生命政治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向:从生命政治的治理论(‘正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转到生命政治的主权论(‘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政治);批判的焦点从作为‘常态化的权力’的生命权力,重新回归在例外状态下决断生死的至高权力。”这个说法比较了福柯和阿甘本:一个是常态,一个是非常态,就是一个“例外状态”。吴冠军认为:“掌握在主权者手里的至高权力(古典时代)与蔓延在各个社会机构中的生命权力(现时代),在权力施行与操作上正相背反:前者让你活(let live)并使你死(take life),后者则使你活(make live)、让你死(let die);前者是一种特殊状况(例外状态)下使用的权力,而后者则是一个‘常态化的权力’(power of regularization)。”[1](P18)疫情期间关于生命政治研究,绝大多数就是在这两种生命政治理论中进行比较:治理状态或生命政治的“正常状态”、主权状态或生命政治的“例外状态”。
其一,治理状态或生命政治的“正常状态”。“生命政治,即人的自然生命越来越被纳入到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中。”[2](P163)但是,“被纳入到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中”的不直接是“人的自然生命”(vivant),而是通过人口(population)间接表现出来。蓝江认为,福柯所倡导的“治理术”主要就是人口统计学,它推动了生命的数据化和档案化,直到今天形成数字时代的新治理模式——“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构建数字时代的新秩序结构——“算法秩序(order of algorithms)”(1)参见蓝江:“生命档案化、算法治理和流众——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引自《非常状态的反思:生命政治·城市·风险治理》,2020年第63,65-66,68页。沈湘平、石峰主编,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内部刊物)。。
其二,主权状态或生命政治的“例外状态”。关于“例外状态”究竟在“法内”还是在“法外”,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两方:“一方是试图将例外状态包含于法秩序范围之内的学者,另一方则认为它是某种外在的事物,亦即基本上是政治的、或至少是超法律的现象。……一种是客观的必要状态理论(objektive Notstandstheorie),其主张在必要状态中所有施行于法律之外或与法律抵触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也因此是法律上可追诉的;另一种则是主观的必要状态理论(subjektive Notstandstheorie),其主张例外权力乃立基于国家‘宪法的或前宪法的(自然的)权利’,就此而言善意便足以确保其免责。”[3](P31-32)而阿甘本则将“例外状态”等同于“悬法状态”,他从“悬法的系谱学考察”中得出结论:“(1)例外状态不是独裁(无论是宪政的或非宪政的、委任的或主权的),而是一个缺乏法的空间、一个无法地带,在其中所有法律性的决定——首先便是公与私的区分本身——都停止行动。……必要状态不是一个‘法的状态’,而是一个没有法的空间(即便如此,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将自身呈现为源自于法之悬置的一种无法状态[anomia])。”“(2)这个缺乏法的空间,似乎基于某种理由,对法秩序来说具有非常根本的重要性,以至于它必须以各种方式试图确保自己与它具有某种关系。”“(3)与法的悬置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是有关在悬法期间所为之行动的问题,而此行动的本质似乎逃离了一切法律性的定义。因为它们既非违法、亦非执法或立法,其便仿佛被置于一个对法而言绝对的非场所(non-luogo)之中。”“(4)法×·力(原文如此)的构想是对于这个无可定义和非场所的回应。”[3](P78-79)在这“例外状态”的四个规定中,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悬法”既非“法内”,亦非“法外”,而是“无法”;二是这种“无法状态”“对法秩序具有非常根本的重要性”。这里就蕴含了类似免疫逻辑的逻辑了!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虽不等于霍布斯的“丛林状态”,但也适用于那句话:“‘对人们而言人就是狼’(homo hominis lupus)。”[2](P148)阿甘本由此提出了“神圣人”即强盗即狼人(loupgarou)的概念。蓝江进而提出了今天的新神圣人——“流众(precarit)”(2)参见蓝江:“生命档案化、算法治理和流众——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引自《非常状态的反思:生命政治·城市·风险治理》,2020年第74页。沈湘平、石峰主编,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内部刊物)。。
其三,关于“例外状态”与“正常状态”的关系,阿甘本有一个概要比较:“赤裸生命(小写的人民)与政治存在(大写的人民)、排除与纳入、‘zoē’(生命)与‘bios’(生活)。”[2](P238)
此外,埃斯波西托提到了自己和奈格里、阿甘本观点的区别。他们都是从福柯出发的。但从福柯的问题出发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就是“把生命理解为一个本质上积极的、充满创新和生产性的过程”,这条路线指的就是奈格里,是从斯宾诺莎、马克思到德勒兹的发展脉络,按照埃斯波西托的表述就是“强调生命政治动态中的生产性和扩张性元素”——“它的生命力元素”,比如《帝国》;第二条路线就是“把它看成某种消极的东西——一种面对生命的致命退缩”,这条路线指的就是阿甘本,是对海德格尔、施密特和本雅明等人思想的发展,按照埃斯波西托的表述就是“以强烈的去历史化方式强调生命政治现象的否定性乃至悲剧性基调”。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做了这个比较以后试图确立自己的生命政治理论的路线,按照埃斯波西托自己的表述就是“既没有……放弃历史维度,也没有……急于把哲学视角溶化到历史学的视角之中”,这就是他创立的免疫逻辑的生命政治理论,这是一种阐释学路径,或者按照他的说法是“一种别样的范式”,是“所谓的免疫学”[4](P235)。
那么,埃斯波西托所谓“免疫学”是什么意思呢?仅从生命政治理论谱系来考量,我们可以发现其意图在于超越福柯以来以奈格里和阿甘本为代表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积极的、充满创新的、生产性的和扩张性的”,另一条则是“消极的、致命退缩的、否定性的和悲剧性的”。免疫逻辑就是将“消极的”生命过程转化为“积极的”生命过程。不仅如此,埃斯波西托所谓“免疫范式”同样意图超越福柯“生命政治的治理论”和阿甘本“生命政治的主权论”的对立以及“例外状态”与“正常状态”的对立。免疫逻辑也是将“例外状态”转化为“正常状态”。当然,这种转化本身需要经受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考量。疫情期间阿甘本对意大利政府实行“例外状态”的谴责之所以无法为绝大多数人们所理解和同情,正因为为遏制疫情蔓延,保护人民生命而实行“例外状态”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这场争论也说明了固守“例外状态”与“正常状态”的划分是无谓的,这一界限必须被突破,并且正在被突破。
总起来说,埃斯波西托的免疫辩证法或免疫逻辑或免疫范式等等在整个生命政治理论谱系中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就是从福柯出发的第三条生命政治理论路线。
二、免疫辩证法和通常所谓辩证法
“免疫”,首先具有生物医学和政治—司法的双重语义。“从生物医学的范畴来看,免疫性指面对某一疾病,生命机体自身自然的或诱发出现的抗感染条件,从政治—司法语言层面来看,鉴于具体职责或责任在正常情况下的对主体的相互钳制,免疫性指主体自身的一种暂时性或决定性的责任豁免。”[5](P185)有一些词源学、语源学的探究:“免疫,或者用它的拉丁语拼写‘Immunitas’,是作为共同体(Communitas)的对立面或者说反面(revescio)出现的。这两个单词最初都起源于词根‘munus’,它在拉丁语中表示‘礼品’、‘帮助’或‘职责’。但是,‘共同体’具有积极内涵而‘免疫’则是消极性的。”[4](P236)免疫、免疫过程或免疫化指“某种特定的情境”或“环境”,“可以保护(mette in salvo)某个人远离整个共同体都冒着的某种风险。”[4](P236)“使人免受他或她(以及整个共同体)所面对的危险。”[6](P210)简单地说,“免疫”在生物医学层面上是指免除疾病感染,在政治—司法层面上是指法律责任豁免。免疫的本质是生物或社会机体对异物的防御,通过对异物的识别以及处理,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的稳态。就此,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从生物医学免疫来讲,这次新冠疫情当中关于中医药的争论很大,这已经是持续已久的争论了,不过这次争论可能有些地方离开了科学,有些地方受到了意识形态影响。有一种说法是,中医药主要是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病,中医药的主要功能是增强人体免疫力。“是药三分毒,无毒不入药”,“以毒攻毒”,用较少的伤害去避免更大的伤害。对健康的人有“毒”的或许对患病的人是“药”,例如,砒霜经提炼及配以适当剂量可用于治疗白血病。恐怕不仅中医药这样,西医药也是如此。“古希腊的药(pharmakon)一词从一开始就有‘治疗’和‘毒药’双重意思——毒药就是治疗,通过毒药来治愈。”(3)[意]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免疫的两面性”(中),蓝江译,载“欧陆思想联萌”公众号,2021年1月4日。因此,药都有副作用,需要“对症下药”。只是中医药注重系统性。大家知道传染病的历史:一号病鼠疫、二号病霍乱、三号病天花,还有别的病——艾滋病、埃博拉等等。严格地说,据说只有天花是被人类通过接种天花疫苗真正战胜了的。现在婴儿一出生就接种疫苗,使之获得免疫能力,这是人工免疫,和自然免疫不一样。其他传染病并未被人类真正战胜,只是由于改良公共卫生条件等等得以消解。
从政治—司法免疫来讲,这也是埃斯波西托曾说过的,法律本身是共同体的一种免疫,就是把个体的暴力转化为共同体的暴力,也是把非法的暴力转化为合法的暴力,这就具有一种免疫特征。如同我们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比如,未成年人的一些豁免权、外交豁免权、大赦和特赦等等,也就是说法律明文规定在共同体中某些特殊的个体他/她享有免除法律惩罚和法律制裁的某些特权。
总起来说,生物机体也好,社会机体也罢,它们作为广义上的系统,正常运行的必要前提是秩序,这是被物理学中的熵理论所证实了的。每个系统都有一定的容错率,即允许一定的混乱存在,但过度的混乱也势必导致秩序的崩溃,即系统的解体。医药和法律都是维护系统稳态的工具。医药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消除生物机体内部的混乱而维持生物机体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存在的终极意义也是消除社会机体内部的混乱而维持社会机体秩序的正常运行,二者所运用的手段都具有强制性。生物医学免疫、政治—司法免疫,埃斯波西托的免疫辩证法有这么两个含义,这是免疫辩证法第一层面的意思。
第二层面,免疫体现了两条生命政治理论路线的结合,这也是非常明确的。前文已经提到“贯穿生命政治范式的两种主要阐释的分野”:“一种是肯定意义的和生产性的,一种是否定意义的或致死性的。”换句话说,“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保护性的和毁灭性的。”埃斯波西托说:免疫“使两者形成因果关系(一种否定的关系)的内在表达、一种语义的结合”、“一种内在的二律背反的模式,即生命通过权力保护自身。”整个生命政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生命和权力之间的一种张力,但是免疫是生命政治的一种特有形式,“是生命保护的一种否定形式。”[5](P186)所谓免疫(Immunitas)和一般的生命政治形式一样,但是一种否定形式,“体现的是共同体(Communitas)的否定和缺失(privativa)形式。”[5](P189)在某种意义上,免疫——作为两种生命政治理论路线的合题——就可以理解为“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又可以理解为填充“悬法状态”,变“无法”为“有法”。
第三层面,我们再进一步追究,免疫辩证法和我们通常所谓辩证法又有什么关系呢?埃斯波西托在论述免疫辩证法的时候也提到了几个代表人物,比如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等等,他们之间关系是可以考究的。福柯曾比较过辩证逻辑和策略逻辑(logique de stratégie)的区别,辩证逻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辩证法,“它在同质(homogène)的要素中使矛盾项运转。……策略逻辑不会在一个同质要素中突出矛盾项,这个同质要素允诺矛盾项在统一性中得到解决。策略逻辑的作用是:在仍处于不相称状态的互不相称的项之间建立起可能的衔接。策略逻辑,是衔接异质的逻辑,它不是将矛盾同质化的逻辑。”[7](P56)也就是说,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像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区别,从这里可以找到一个脉络。我们通常所谓辩证法,像黑格尔的正反合,反题被正题兼容或化解成合题了,或恩格斯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都有这个意思,这是通常所谓辩证法。当然,这种辩证法后来发展,与包括像列宁、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哈特和奈格理在谈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说:“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是全部启蒙和现代性,而是现代主权传统。”[8](P144)主权我们已说过了,“例外状态”下主权的表现就是“将多样性和差异性削减为二元对立”,通常所谓辩证法也是把多样性和差异性削减为二元对立,我们对于现代性通常是这么理解的。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中,启蒙辩证法会走向一种理性极权,而否定辩证法则强调否定不可能走向肯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式挑战,这种挑战针对哈特和奈格里所谓“现代支配、排斥和控制的核心逻辑”,就是它“将多样性和差异性削减为二元对立,接下来再把差异融入统一秩序之中”[8](P144)。由此可见,我们多元的社会和文化,在这样一个“例外状态”、非常状态中,一个最危险的倾向是什么?——就是两极化!多元化被削减为两极化,整个社会就会走向一个极端。
在预防社会和文化的极化上,我们可以将生命政治跟身份政治比较,将免疫辩证法跟承认辩证法比较。身份政治不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承认基础上。按照泰勒的观点,“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转向“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是从现代性政治到后现代政治的转向。“认同的政治”是“平等尊严的政治”,“承认的政治”是“差异的政治”。前者是同质性的,以表现为单一性的现代性社会和文化为背景;后者是异质性的,以表现为多样性的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为背景。从“认同的政治”到“承认的政治”,从“平等尊严的政治”到“差异的政治”,是全球化时代之政治的基本转向。这也就是多元社会—文化背景下西方“政治正确”的前提和基础。今天,西方“政治正确”亦即以承认逻辑为核心的身份政治也有一种极化倾向,譬如疫情期间出现的反科学倾向。以免疫逻辑为核心的生命政治或许可以救偏补弊。免疫辩证法不是使矛盾同质化,而是使异质性事物在共同体中共在的方法,它超越了认同和承认的逻辑,既不是“党同伐异”,也不仅仅是“求同存异”,而是更进一步——“相反相成”。免疫范式使相异者和相反者在共同体中共在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证明。
移植辩证法是免疫辩证法的延展。机体处理异物具有各种机能:对于植物而言,嫁接就是将彼物移植于此物。对于动物而言,消化是机体同化异物的机能,而怀孕则是机体容纳异物的机能。器官移植也要克服一种排异性,就是获得一种免疫性。埃斯波西托在讨论免疫问题时,他就提到了移植问题,免疫辩证法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移植辩证法,也就是说人类可能往这个方向走,这也是在技术上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我们现在讲“后人类”等等,移植发展到最后是这么一个局面:人类身体器官全都可以移植,现在心脏可以移植,将来大脑可以移植的话,人类就不是我们原生态意义上的人类,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后人类”,也就是赛博格(Cyborg)。至于文化和文明的移植,在历史上同样屡见不鲜。
三、免疫辩证法应用于防疫常态化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大家知道,新冠疫情也可以说是一个好莱坞导演都设想不出来的一幕大戏,剧情不断发生逆转。因为我们面对的新冠病毒是“流氓病毒”,它不同于一般病毒,所以整个疫情的发展超出人们的认知,这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疫情防控就只能被这个病毒牵着走。先看国内,概括起来,迄今为止,整个疫情防控大概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像武汉保卫战和湖北保卫战,这个阶段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当然,这两个阶段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衔接的。第二个阶段是“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后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防疫常态化),但进入也不是截然的,好像哪一天就进入了。防疫常态化说明这场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持久战的状态。再看国外,哈特和奈格理曾引用过这一句话:“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8](P138)各国的抗疫模式不一样,议论比较多的像新加坡的“佛系抗疫”和英国的“群体免疫”。有人总结,西方是“群体免疫”,东亚是“全体免疫”,这是两种文化和文明模式的选择。
从我们国家防疫模式来讨论,我们国家防疫模式就是按照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起初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主要就是一个字——“封”,从武汉“封城”(1月23日),一直到武汉解封(4月8日),而且解封以后其实还有些措施在延续。不仅“封城”(武汉),而且“封省”(湖北),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封”国。这次“封”是非常彻底的,不仅“封城”,而且城市里每一个居民区也封,农村“封村”。疫情高发期间全国几乎每一个人宅家,也就是两个字“隔离”。这个隔离状态一开始就受到西方一些自由主义者们的批评,同时受到中国一些自由主义者们的呼应,说是违反人权,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尤其迁徙自由——禁足)。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人讽刺:“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中西抗疫成效差距,有人说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有人说是民族性格的问题,也许二者都是主要因素,或者还有其他次要因素。当然,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非常惨重的,造成了一段时间的停摆,直到现在这样一种停摆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成为世界最大“安全岛”,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种种次生灾害大家都耳闻目睹了。这里最主要的是对我们现代市民社会和传统乡土社会的影响。有人曾经对比了唐朝和宋朝城市,把长安和开封做了一个对比:在唐以前城市是分区的,就跟我们疫情期间一样,区与区间是相互隔离的,所以没有多少市民生活。到了宋朝以后街巷才四通八达,才有一些市民生活,比如说书唱戏等等,所以宋元时期才有戏剧、小说等等。这是开放式街区制和封闭式街坊制的区分。这次疫情最主要的就是摧毁了我们的市民生活。整个社会被区格化,即使对于乡土社会,这种状态也都属于例外。进入防疫常态化以后,整个局面是否结束?并没有结束!整个局面是原有局面一半的延续,它可以理解为从全隔离到半隔离。譬如我们现在有一点还需要注意,就是社交距离(一米间距)问题,防疫常态化要求人与人之间无接触、少聚集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生命(安全、健康)、权利(自由、隐私)、责任(义务)等等这些问题讨论都提升上来。这里不拟评述各种价值立场,只是强调:我们既不能从既定理论规范,也不能从现成生活方式考虑这些问题,既要考虑实际境况,更要考虑可能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替代型的生活模式,这种替代型的生活模式在这次防疫中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1980)中早已提出了“电子小屋”的概念,当时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测,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成为现实,每个人宅在家可以远程上课、远程开会等等,还有一些虚拟社区。当然虚拟社区也有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许多人以匿名状态出现,匿名状态加上共振效应容易引发群体极化,甚至导致人们毫无底线,在现实区格化基础上进而产生思想区格化,加深社会撕裂,这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种替代型的生活模式正在出现,并赋予我们原有的一些概念以崭新的经验内涵。譬如,前面提到“致命退缩”,有许多人认为,我们现在都不叫“生活”了,最严重的时候退缩到了生存需要,各人满足自己生存需要。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从生态的理由、人类的理由,或者从种族的理由、国家的理由,我们看看我们各人原有生活方式里还有多少是必要的,所有这些非必要的状态还有没有必要延续?像天天宅在家,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聚会,像那些聚餐,真的就是自由吗?其实不是自由!宅家生活缩小了隐私范围还是扩大了隐私范围?这里说的这一切不是说我们仍然保留甚至扩大了自由和隐私(显然有些防疫措施比如监控、追踪等等缩小甚至取消了隐私和自由),而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一种替代型的生活模式,譬如在相当场合下,线上工作与消费替代线下工作与消费。约定俗成,习成自然,历史上,人类随着技术进步,已经无数次替代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必然加速人类生活方式的替代与更新。
历史证明,人类在“例外状态”下所取得的进步比在“正常状态”下所取得的进步更大、更快。譬如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国家在不到一年内实现了从粗放式防控到精准式防控,每次疫情的输入和反弹都得到了愈益迅速和有力的控制,风险区管控和密接者追踪的定位愈益精准,这除了得益于基层治理等制度优势之外,当然也得益于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有些学者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至高权力—赤裸生命’之间的二元对立变成‘数字权力—透明生命’”(4)参见王庆丰:“重思‘例外状态’”,引自《非常状态的反思:生命政治·城市·风险治理》2020年第86页。沈湘平、石峰主编,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内部刊物)。。但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保护隐私数据即不得将防疫所获得的个人数据应用于防疫之外的目的,这样一种法治意识—实践也在愈益增强。
免疫有着多种多样形式,我们讲的隔离就是一种形式,我们讲的半隔离状态——不接触、少聚集这种半隔离状态也是一种免疫形式,但这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一种替代型的生活方式才是一种内在形式。总之,防疫常态化不在于强化外在免疫措施,而在于强化内在免疫措施,亦即寻找到一种更为安全、健康同时更为自由、隐私的生活替代方式。
免疫除了生物医学上和政治—司法上两个意义以外,还可以从其他意义来考虑,比如精神免疫、心理免疫。我们现在仍然以一种隔离方式来对待一切,包括在一些争论中,也是以隔离方式来对待,争论双方好像把对方看做是病毒,我们把他/她都隔离起来,这是不能长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在精神免疫和心理免疫的意义上也要实现从外在免疫到内在免疫。隔离、排除、消灭异己,就是一种外在免疫形式;理解、宽容、包容异己,就是一种内在免疫形式。
综上所述,免疫辩证法就是“例外状态”的常态化,此种理论定位与防疫常态化的实践定位是一致的。免疫辩证法应用于防疫常态化的一般原则即在于寻找一种替代型生活方式,其一般方法是从外在免疫转化为内在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