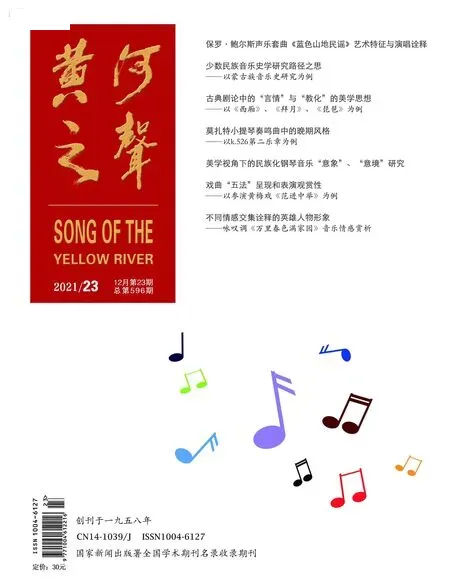西周“乐政”下礼乐功能的多个指向性研究
李 琪
“乐政”一词是西周时期“乐与政通”、“乐礼治政”的高度概括,然而以政治属性为导向的乐舞价值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舞蹈的原始形态是一种以满足自我生理需求为目的的本能运动,这种原始形态的舞蹈是巫觋文化中巫觋为沟通神灵、降神祈福的手段,人类谋取生存与持续发展拼搏的过程中,用乐舞的方式满足精神诉求,表达对超自然现象的敬畏。当上古时期的“舞蹈生命活动”与政治的发生发展相关联,周公的“礼乐治政”将政治制度的建设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力结合,使得舞蹈的功用性质也从表达生命情调的直接表达转化为巩固政权的手段。周代,从“娱神”到“颂人”再到“治人”,乐舞不断被赋予新的功能,“一方面‘礼’与‘巫’杂糅在一起,而另一方面礼的种种特质和特点又表现出不同于‘巫’的文化内涵。并清晰地展示出一种特有的文化发展方向”[1]可见乐舞的祭祀特性被延续,此外教化和娱乐的“治人”的功能被挖掘,乐舞在继承中发展,保留其自身祭祀的特性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特征,成为具有祭祀功能和政治导向为目的的艺术活动。周代的“乐制”是在夏、商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制定的一整套的、较为明确的宫廷礼仪和祭祀的乐舞制度,即礼乐制度,它沿袭了夏、商的宗教崇拜的祭祀的仪式,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产物。
一、召祭天下,舞以象功德的礼仪性
以“制礼作乐”为标志,从“娱神”到“娱人”再到“治人”,乐舞沦为政治工具,其功用性也为之转变。周代“乐政”依旧延续了乐舞祭祀的特性,并在其原有的“祭神”特性基础上,经历“祀神”“颂人”“颂己”的变化。
(一)以“昭”其功
“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也”[2]。上古时期巫术和舞蹈为一体,巫觋将手舞足蹈的方式当作娱神祭祀的手段。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氏族时期用杀牛祭庆丰产的乐舞;以求雨祭鬼祀神为目的的朱襄氏之乐;以“宣导之”为目的祈求水土相服的阴康氏之乐,都是如此巫师之所以足之蹈之的案例。五帝时期,农业发展步入正轨,乐舞的作用也成为帝王“颂人”的工具。例如:通过祭奠天神以满足“敬宗收族”的黄帝的《咸池》乐舞;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后,制乐祭祖、祈求先王庇佑,对黄帝乐舞增修而制的《承云》;帝喾时期,为明道祭祖而制的《九招》、《六列》、《六英》;击石、舞百兽以此祀先帝乐舞,即尧时期的《大章》;舜时期修缮帝喾时代的乐舞,并将其取名为《九韶》,以此来祭祀祖先,以明帝德。可见,此时的乐舞的内容虽然发生了从“娱神”到“颂人”的变化,但是乐舞的本质都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具有功利性的巫仪宗教祭祀活动。
祭祀内容从“人神合一”的神灵祭祀,到为了表示忠孝节义而制定的、以明先帝之功德的乐舞仪式,虽然以此丰富了舞蹈本身的意义,顺应了新形式下的变革与进步,但是其本质并未发生变化。乐舞从“颂人”到“颂己”的转变是在夏禹以后。夏禹因治水有功所以制乐制礼,并将其以昭其功的乐舞命名为《夏龠》。尔后,史料中清晰可见的“以康帝徳”被“以昭其功”而代替。例如:商汤制乐舞《大濩》(又名《桑林》),“濩”的仪式虽然有自然崇拜的痕迹,但其主要内容还是为了强调、颂扬当时的帝王商汤灭夏的功绩。到了周代自然也有当朝创作的《大武》,以享先祖。《大武》有六个篇章,舞者手持舞具——干戚而舞,乐舞主题是展示周武王伐纣的场景,舞蹈宏大的规模正是对周王建国之时的威仪场面的有力体现。
《淮南子·奇俗训》所云:“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舞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3]而这正是反映了,在社会变革下,乐舞的功用产生了质的转变。“舞蹈生产活动”在不同时期应运而生,其性质与功能的转化正是舞蹈自身存在与价值的反映。
(二)以“别”尊卑
“乐政”体系中的保留了乐舞“祭祀”的特性,不仅肩负对统治者功德的颂扬,还是以“别”尊卑的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拿肩负祭祀功能的“六代舞”来看,“六代舞”是周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之一,是歌颂上古至周初六代帝王的代表性乐舞。在周代乐舞文化中,其主要是服务天子级别的祭祀乐舞,且对祭祀对象、舞容及乐歌、仪制规模、演出场地、服饰舞具、等都做了明确的规范与区别。《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祖先……”[4]。可见周代乐舞制度有着程式性与规范性,祭祀对象不同选用的乐的等级也不同。乐舞祭祀的功能的政治属性显著,礼乐制度下乐舞功用性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等级制度的产物,以彰显天子独尊,尊卑有别的等级特征。拿祭天来说,古人认为“王者父天地母”,乐舞《云门》冠以祭祀天神之名。原是黄帝祭祀云图腾,颛顼时期增修注入了各地音乐即“八风”,加入了新的形式,以祭祀祖先(黄帝)。周代统治者以《云门》为首部,规格宏大,最重要的祭祀天神只有天子,以彰显天人合一、君权授之天命。除了祭祀的乐部、规模、场地、程序等无不体现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
由此可见,祭祀舞蹈转变为周代统治者礼乐治政的工具,无论是统治者希望通过乐舞祭祀的内容以彰显帝王功德,亦或是为了区别尊卑,总的来说周代乐舞祭祀的“礼”与“乐”都是周公“功成作乐”的体现。五帝时代的乐舞是以“以象上帝”、“以祭上帝”、“以明帝德”为目的,夏禹以后的乐舞多是“以见其善”、“以昭其功”、“以嘉其德”,制乐以歌颂当世之帝代替祭祀先朝之帝。禹王之乐开启了“娱神”到“娱人”的指向性变化,乐舞的发生与发展超越了祭祀先祖的特性,转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手段,由“颂人”变为“颂己”。周代统治者更是把舞蹈当成“象功”、“象德”的政治功绩,并希望通过宗教、礼学治国。
二、寓教于贵,“理”以束其行的教化性
周代礼乐治政是以“礼”来规范德行、区别贵贱,以“乐”调和君民关系,使“礼”“乐”相辅相成,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地位。以政治属性为导向的西周乐舞有着说教性凌驾于娱乐性的特点,这也是被称之为‘伦理的舞’的主要原因。这种寓教于礼乐的意识形态观念也是乐舞高度政治化的一大特征,这种是从国子到民众的自上而下的臣民教化活动。
雅乐正身,寓教于乐舞的国子之教。礼乐的教化功能早在舜帝时期就被发掘,《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5]可见舜帝认为乐舞可以化育人心,培养正直温和、宽容谨慎、刚强却不暴虐、简达而不傲慢的优秀品格与高尚的德行。舜帝时是由其臣子负责主持乐舞教育青少年,到了西周形成了专门的乐舞教育体系。乐工舞人各司其职,由大司乐教贵族子弟学习六代舞,舞师教学六小舞,并按照其乐舞功能将文舞、武舞分门别类,这说的“大舞”“小舞”则是西周王室贵族子弟专门修习的乐舞。这里主要讲的六小舞也是周代的道具舞,是根据表演是舞者手持舞具而区分、命名的,因为其修订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化国子,六小舞有“文”“武”之别,文舞规训臣民礼仪德行,武舞强健体格,达到文武兼备。
以舞载道,“德教”“明理”“束行”的民众教化。先秦的舞蹈被称为“论理性乐舞”,一方面是为了让民众信服统治者君权神授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让民众在乐舞的熏陶下削减对等级社会中压迫剥削的不满与排斥,以维护社会秩序。“理”性的思想教化,也体现在礼乐祭祀仪式中。歌颂祖先和昭示帝王的丰功伟绩的宫廷乐舞节奏缓慢,韵律平缓,低婉严肃的氛围使诸侯百姓心生肃穆,诸侯百姓可以在乐舞中对先帝产生肃敬,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百姓的精神世界,束缚个性,达到行为上的约束,并服从周王的管理。西周的乐教目的也是为了培养顺民。所谓同姓同德、同心同德,通过祭祀共同先祖,消除各地不同风俗带来的混乱和不安,到达“人和”的目的。“修六礼”、“明七教”、“齐八政”、“一道德”也是周代统治者对民众产生行为约束、个性影响、思想引导的措施,从“理”与“德”束缚中,达到风俗雅化的目的。如此可见,乐舞为礼服务,通过潜移默化的乐教,感化“顽民”、教化民众、团结人心,具有广泛的伦理道德的意义。
等级森严。周代乐舞超越了祭祀功能,赋予其“理”性与教化功能,无论是教育国子还是感化民众,其根本目的是用乐舞“治人”,实现统治者的政治巩固。为此,祭神、娱神、祀鬼不再是乐舞的第一要义,而是更直接的为周王的统治而服务,社会性功能的融合使乐舞文化良性发展,乐舞教化使得等级分明,各有所敬,秩序井然,内心安宁,相亲相爱,以乐治人达到人格教化。
三、宣情怡志,“娱”以尽其兴的娱乐性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娱乐宣情最直接的表达,然而西周时期的宴乐舞是在“礼”的规范与约束下以调节人际关系的的乐舞。这种宴会作乐作舞的现象早在夏代就已显现,和夏王沉迷乐舞享乐用来自我娱乐消遣不同的是,西周的乐舞同样是具有政治与教化功能。无论是宗庙典礼仪式结束后以表敬意的飨礼仪式,还是政余之时宴请各路诸侯、四方宾客举办燕礼活动,宴乐舞都要遵循“礼”的规定,集政治性、规范性,同时发挥自身的娱乐性、观赏性。以娱乐为主的“燕乐”礼仪活动,会在作乐时表演舞蹈供人欣赏,或是贵族宾客在觥筹交错后起舞尽兴。《诗经》“雅”部分收录有关诸侯宴舞、亲友宴饮的燕乐舞蹈的描写,无论是君臣、臣臣其乐融融、载歌载舞,还是亲朋好友饮酒共舞,互诉衷肠,都是自娱自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情以外现的方式正是傅毅在《舞赋》中对“足之蹈之”可抒发语言、诗歌不足以表达的情感,例如《小雅·宾之初筵》表现了君臣筵席上,君臣、臣臣其乐融融,和谐欢乐,趁兴起舞的宴饮舞蹈,伴随着鼓、笙、籥声,宾主“屡舞仙仙”步态踉跄,以歌咏言,以舞尽兴,边歌边舞,欢聚一堂。[6]
虽然宴飨乐舞是娱乐性质的舞蹈,但是在西周的礼乐体系下承载着政治教化功能,恪守礼乐原则。乐舞的社会性功能的融合是统治者保持社会秩序的体现。
结 语
宫廷雅乐在周代乐舞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乐政”一词概括了周代雅乐制度高度政治化。以政治属性为导向的“制礼作乐”归根到底表达的是乐舞与政治的关系,即政治、礼节、乐舞、教化的同一。礼与乐、乐与政、政与教之间的相辅相成,使乐舞肩负了祭祀祖先、歌功颂德、臣民教化、娱乐欣赏的功用。从“娱神”“娱人”到“治人”,西周乐舞完成了功能性的不断转变,其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舞以“康”功德、舞以“别”尊卑、以“理”束其行、以舞“和”民心、以舞“尽”其兴。西周以礼乐并举来促使社会外在规范和人民内在心灵的愉悦和满足,实现天人共舞,和谐万民的统治。
常说舞蹈源于生活,舞蹈的存在、发生与发展中反映着社会文化形态的缩影,正是古代思想家们喜欢乐舞的风气体现朝代兴盛衰败的直接表现。当乐舞遇上政治,经历了原始社会时期生命情调的直接表达与精神寄托到封建阶级统治时乐政体系的逐步形成,成为政治统治的有效手段,舞蹈性质与功用性的转变,再到礼乐文化的瓦解与破坏,如今,新时期的舞蹈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的融合与发展。可见乐舞的功用性是多元的,乐舞文化的不断渗透,是历史的需要,是整个教育活动的需要,也是乐舞教育学本身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