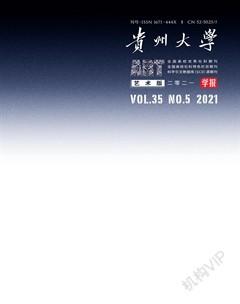论电影空间中的本土性与现代性之关系
陆心宇
摘 要:本土性是电影空间之中超越性的现实源泉:一种对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的真实反思,不能是抽象的,而须是本土场域里发生的。作为创作材质的南方性构成了贝赫·泽特林的电影神话学的意义源泉。泽特林的后南方电影对南方本土性的抽象化塑造了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多重的美学反思,即在浪漫化的视野中呈现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生命力。电影的超越性把现实的他者性时间化以抵抗异化的未来性。在电影空间中从本土性到超越性的转变之意涵正在于塑造作为历史抽象物的美学能指。
关键词:电影空间; 电影哲学; 本土性; 现代性; 他者性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5-0033-10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5.005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贝赫·泽特林(Benh Zeitlin)的《南方的野獸》(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2012,以下简称《野兽》)来探讨电影空间中的本土元素如何超出地理的界域而成为一种刻画人类状况的一般的美学能指,从而在现代性问题的视域中刻画构筑电影神话学的美学机理。
一、泽特林的电影神话学实践
作为美国新生代导演,泽特林在电影创作中的初心是追寻一种基于本土经验的超现实主义。他曾深受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与捷克导演杨·史云梅耶(Jan vankmajer)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影响。在欧洲同史云梅耶合作期间,泽特林曾构想一部关于海底村落的超现实主义电影,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幻象叙事的空间性似乎应该安顿于他所熟悉的本土,而非虚构的或异域风情的场所。[1]这一构想最初的产物是短片《海上荣耀》(Glory at Seay,2008,以下简称《荣耀》),它是一部关于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的创痛与幸存的哀歌。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现代史上第四大飓风,主要受灾地区路易斯安那州,造成了约1200人失踪和1250亿美元的损失。作为灾后的叙事,《荣耀》建构了“灾后幸存者在海底寻找失踪的亲人的后卡特里娜想象。”[2]自这部短片起,泽特林的电影空间的本土性就确立为美国南方。
泽特林凭借《野兽》斩获众多荣誉,其中包括戛纳金摄影机奖(2012)、第85届奥斯卡四项提名(2013)、丹麦波迪奖最佳美国电影(2014),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新生代导演之一。《野兽》可以被看作一种基于现实的历史性而创制现代神话的美学实践。在此我们首先回顾其叙事线索中的历史性与想象因素之间的关系。《野兽》的叙事有两条线索。其一是关于一个8岁女孩玉米球面对失去双亲的现实而寻求自立的教化小说(Buildungsroman)。这条私人叙事线索改编自露西·阿力巴(Lucy Alibar)的戏剧《美味佳肴》(Juicy and Delicious,2010),它首先是关于一个女孩如何面对父亲濒死经验的半自传叙事。在《野兽》中,女主角的名字“玉米球”(Hushpuppy)正是致敬改编作品的标题,它取自美国南方食谱黄金玉米球,最初起源于印第安部落,并且在内战期间流行于南方地区。这个专名也暗示《野兽》之地理空间设定为美国南方。其次是关于一个虚构的多元文化社群“浴缸村”(Bathtub)如何从全球气候变暖引致的灾变后果里谋求生存的生态小说(Climate Fiction,或Cli-Fi)。[3]其中“浴缸村”(Bathtub)的名字呼应了《荣耀》寻亲漂流中的载具:一个由浴缸改造而成的航船。两条叙事线索在私人与公共记忆的层面都与现实性保持关联。玉米球的私人叙事指向编剧阿力巴本身的自传经验,而“浴缸村”的幸存体验又与后卡特里娜的南方记忆相通。这是电影在想象的南方与现实的南方之间建立的基础关联。叙事中的神话元素同样体现在两个层面:浴缸村的酒神精神以及玉米球的克里斯马。浴缸村的生活形式是一种后工业的波西米亚风格:在四面环水由布满铁锈的废弃机械所建立的社区景观里,当地居民享受着丰盛的自然物产,并且借助节日的狂欢与宴饮而缔造共同体的内在团结。在影片的想象中,玉米球的克里斯马在于一种倾听万物的超自然力量。在经历了一场类似卡特里娜飓风的灾变之后,浴缸村的居民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而玉米球所具有的同自然沟通的禀赋最终完成了拯救整个社区的奇迹。
对于泽特林而言,用电影创制神话是一种保存集体记忆与情感的方式。《野兽》旨在为卡特里娜幸存者的创痛记忆与情感塑造一份电影的纪念碑。于是,在电影空间的构筑中,泽特林运用南方景观作为想象与现实、超越与本土、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中介物。他试图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新奥尔良的自然风貌里寻求一种寓于表象的超越性。“在那场飓风之后,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一个超自然的空间,就像是末世景观。这或许并非每一个个体的体验,但于我而言,这是把叙事提升到神话或传说层面的重要契机,正如在《荣耀》里我曾尝试的那样。”[1]26在泽特林看来,构筑公共记忆是向受难者表达尊重的方式,也是为未来世代留下某种反思的契机。创制一份电影神话为面向过去的回忆赋予了某种抵抗时间与遗忘的超越性。另一方面,电影神话的创制避免了把卡特里娜飓风安顿于一种严格的因果解释的框架里,从而避免了气候议题中的争议性部分。电影神话的创制能够专注于共同体的情感本身。
为此,《野兽》试图在电影空间的构筑中把后卡特里娜视阈中的南方地理风貌转变为一种承载集体记忆的历史能指。在泽特林看来,新奥尔良的水文景观正是融合本土性与超越性的关键契机,“在新奥尔良,水就像是希腊神话里的神祇,掌控着此地的一切,而当地人的生活始终在各水域之间平衡地铺展。水就是吸引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它尤其展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某种原生态的东西。……(我的电影)倘若安顿在坚实的大地上,就会变得不可理喻了。”[1]24-25 在《电影神话学:电影中的哲学》中,欧文·辛格(Irving Singer)认为,电影作为梦的创制过程蕴含着某种集体无意识,并且由此在现代生活中替代了传统的神话叙事,揭示出某种关于人对世界之前反思的感知与介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辛格强调,电影之神话性元素往往依赖于现实的具体语境,它从现实的事物与事件中抽象出某种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超现实元素,而这种现实的抽象物在另一个语境里则往往并不具有超越性。“神话创制既有着哲学性,又有着明显的人造性、虚构性,它依赖于我们的想象力对叙事与事件的依赖性,从而我们知道它在其他语境中是非现实的。”[4]10泽特林的电影叙事恰恰对应于现代神话创制的美学过程,即:从寓于南方地理景观的本土性之中抽绎出视觉的超越性。
本土性与超越性是泽特林的电影空间所追求的两极。从表面上看,追求本土性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放弃普遍意识,而这也就意味着无法完成一般叙事向神话叙事的转变。安德鲁·冯·汉迪(Andrew Von Hendy)在《神话的现代建构》中指出:“那最终被认定为‘神话的特定的子类文体恰是‘文学的范本,这类叙事所传达的洞见可谓意蕴深邃而不可穷尽,乃至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本土的场域与历史的情境。”[5]25从这点看,从一般的叙事到神话的变形取决于文本空间对本土空间的超越性。在这点上,电影与文学是相似的。对于作为现代神话的电影,威廉·法洛(William K.Ferrell)指出,神话蕴含着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而在现代世界中文学与电影则扮演着传统社会中神话叙事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如同古希腊人的故事对他们的孩子所产生的影响,电影与小说如今则继续提供着一种生存的模式。……神话,就其小说与电影的形式而言,塑造着一种针对当代社会之机械化与世俗化的自然的反题。”[6]19对于法洛而言,电影作为现代神话,并不仅仅提供一种完成了的世界观或价值,而是在公共空间里充当“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公开讨论的源泉”,从而呈现并塑造着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当电影的空间性超越于本土的界域,它就跃迁入普遍的人类意识的领域,从而转变为一种现代神话。既然神话叙事追求通达人类的普遍意识,为何还需要强调某种本土性的表征呢?对此,汉迪指出,神话的本质是在时间之中对永恒意识的本土化表达:“它们是本土的,在时间中实现了对永恒意识的澄明。”[5]3-4他甚至明确点明了神话的双重标准:“‘神话在其内容上所采取的双重标准可能展现出某种悖论的特征:它可以说是‘在其飞跃中是不受限制的,然而又是可本土化的(localizable)。”[5]63换言之,对神话而言,超越性恰恰是根植于本土性而发生的:唯有根植于本土的特殊性,才可能激发出通达人类之普遍意识的超越性。
在切入对泽特林电影从本土性到超越性的审美路径的分析之前,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叙事可以实现神话化(Mythologization)。谢林在《神话哲学》中指出,神话并非被发明的,而是经过意识演变的产物。“神话的观念既不是被发明的,也不是刻意被采纳的——作为一个独立于思想与意志的过程的产物,它们对于那属于这个过程的意识而言是清晰而切近的现实。民族或个体都只是这个过程的工具,他们无法考察这一过程,而只能无理解地服务于它。因为他们无法避开这些表象,乃至决定接纳或不接纳它们。它们并非外在地影响他们,而是在他们之中,却令他们不明所以。它们源于意识本身的某个内在部分,向意识呈现为某种必然性,却不允许丝毫怀疑其真理性。”[7]135换言之,作为能指的神话本身是一种基于观察视角的范畴,而这种观察的前提是悬置其所指的真实性。因而,谢林指出:“神话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的现象。”[7]43对于谢林而言,希腊神话是诸神的历史或神谱,蕴含着某种关于意识本身的前反思知识,从而与哲学有着共通的主题,但它唯独不是苏格拉底从德尔斐神庙里得到启示的来源,或安提戈涅藉以对抗克瑞翁的诸神的召唤。也就是说,在谢林所揭显的现代神话概念里,神话不再是生活世界本身的根基,从而其神圣性变形为思辨性。这是现代人对待神话的理論姿态。正如汉迪所言:“神话学并非一组故事,而是关于寓言式解读的学院派的科学,‘构筑神话并非发明或重演一个‘mythos,而是介入这种诠释的实践。”[5]2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一份现代叙事试图转变为神话时,它所呈现的超越性恰恰不是现实的超越,而是一种过早介入叙事的意识过程,它在为现实赋予魔幻性的同时施展现代的祛魅,从而在叙事之中构筑反思的视角。就电影神话学的审美兴趣而言,在电影空间中建构超越性与魔幻性不是为了在观众之中创造相信,而是引导反思。从这个角度看,当我们说本土性是电影空间之中超越性的现实源泉时,我们更确切地是指:一种对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真实反思,不能是抽象的,而须是在本土场域里发生的。接下来我们将借助对泽特林电影的空间性之分析来具体地探索这条从本土性到超越性或反思性的美学路径。
二、南方,抑或后南方?
南方性(Southerness)是美国艺术传统中的一种经典的空间性元素。南方叙事通常通过浪漫化南方经验里的质朴粗粝来呈现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活景观,从而构筑对现代性的批判视域。后南方的叙事则从南方的生活形式里抽象出一些关乎人文地理的元素,即所谓南方性。南方性的特征是粗糙性(Roughness),因而也被称作“粗糙南方”(Rough South),甚至“肮脏南方”(Dirty South)。在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中,粗粝南方或肮脏南方是在美国本土经验里建构的针对资本主义都市性的美学反题。作为一种反讽的能指,它暗示着一种更切近自然并且蕴含超越性的新的生活形式。因而,后南方叙事则是南方传统的一种当代变体,旨在用南方生活形式里的审美元素来构筑一种抽象能指,呈现更一般的人类生活经验,并且从中展望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后南方的本质在于从经过浪漫化与抽象化的南方的本土性里开拓出后现代的视域。因而,从后南方审美框架来看,《野兽》似乎以虚化的南方场景来呈现一种针对后现代的人类经验与对资本主义生活形式的美学反思。从后南方引申出后现代的美学路径同样出现在泽特林的《温蒂》(Wendy,2020)之中,它呈现了高度发达与阶层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罗列塔利亚的个体的异化经验,并且试图在追寻自然、他处、童年、往昔的乡愁中探索一种超越异化的审美经验。
不过,《野兽》之为后南方并不能仅仅从浴缸村的虚构空间性与魔幻现实主义的灵韵来确定。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同样是虚构的空间,但它无疑属于南方。格洛里亚·内勒(Gloria Naylor)的《戴妈妈》(Mama Day)运用魔幻元素来叙述一个非裔南方女子探寻身份本真性的历程,而其中作为故土的岛屿维罗泉(Willow Spring)是一个位于乔治亚海岸的虚构场所。即便如此,这部作品仍然属于南方而非后南方的范畴。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泽特林的《野兽》的空间性从南方转向后南方,乃至从本土性的经验中开拓出对一般人类经验的文化能指呢?简言之,借助对南方之为他者的美学建构来塑造一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题,从而以反讽的方式从破碎的、粗糙的、肮脏的美学表征里开拓出内在的超越性。
根据上文的分析,《野兽》的电影空间中的物质元素立足于南方的本土性。不过,这种南方性并不止于自然风貌,而更在于调用一系列社会文化的视觉元素。在此,笔者试图探讨《野兽》如何具体地构筑具有本土文化与历史意蕴的电影空间。在总体上,南方性是一种作为资本主义都市景观的反题,后者在全球化进程中在人文地理的形态上趋于高度同质化。而作为视觉元素的南方性则旨在呈现这种同质化过程的例外。扎卡里·弗农(Zackary Vernon)指出,粗糙南方相当于美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里的一块飞地,它在自然风貌、社会景观、阶级构成上都蕴含着某种回归本真性的理想,而这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构成了一种想象的他处。[8]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里,美国南方似乎低效、迟缓、质朴,保持着某种前资本主义的乡村风貌。南方的这种局外人的位置意味着它是现代性的他者,反映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格格不入的状态。这种在整体之中的例外状态把南方本身对乡土与田园的依恋悖谬地转变为了一种游牧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钱德勒·宾汉(Chandler Bingham)把南方的地方性归结为波西米亚风格,并提出了所谓“波西米亚风格的南方”(Bohemian South)的概念。[9]
除了对南方之局外人身份的调用,另一个建构南方性的美学元素是对浴缸村本身的描写,它是一个经历了类似于卡特里娜飓风之灾变的南方社区。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后卡特里娜特征。根据丹尼尔·斯普茨(Daniel Spoth)的分析,《野兽》属于布拉德·里查德(Brad Richard)所提出的灾难诗学(Poetics of Disaster)的范畴。在美国南方文学中,灾难诗学是一个经典的类型。左拉·尼尔·赫斯顿的非裔女性文学《他们眼望上苍》(1937)关乎1928年的奥基乔比飓风,而威廉·福克纳的《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1939)中第二部分“老人”关乎1927年的密西西比洪水。按照斯普茨的分析,这类叙事的显著特征在于:通过为南方人与灾后的土地之间的关系赋予浪漫化的美学表征,来呈现对本土生活方式的依恋。在这种对土地的依恋中蕴含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现代的工业化都市)之间的价值分歧,由此引申出一种关于现代本身的悲剧性。[10]在这个审美范型里,《野兽》中浴缸村的居民不仅承受着自然的暴力,而且作为粗糙南方的居民也承受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因为在后者看来,他们的生活是粗糙的、肮脏的、底层的。
浴缸村的另一重南方性在于它的多种族的社区文化反映了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地方文化,即: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根据尼古拉斯·斯皮茨尔的分析(Nicholas R.Spitzer),“克里奥尔”(Creole)这个词源自葡萄牙语中的“Crioulo”,最初指对某地的本土关系,后来特指法国与西班牙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与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文化。在南北战争期间,它进而演变为指代在路易斯安那州作为自由民的有色人口(gens libres de couleur)。在当代用法里,它则是指由非裔、西班牙裔、法裔、印第安裔构成的多种族社区。[11]在《野兽》中的浴缸村的地理位置处在新奥尔良,可谓美国南方之南方。浴缸村的社区形态正是基于克里奥尔化的超现实主义虚构。
此外,食物也是展现地方性的视觉符号。玛西·法尔利斯(Marcie Cohen Ferris)曾指出,南方食物与烹饪是在电影空间中呈现南方性的视觉元素,这一点曾体现于众多经典电影中,包括《诺玛·蕾》《钢木兰》《为黛西小姐开车》《密西西比风情画》《冷山》等。在《野兽》的浴缸村中,丰沛的食物与共享的饮食方式的铺展体现了“一种无法安慰的丧失与变故之后的古朴的南方之爱与幸存体验。”[12]
至此我们看到,《野兽》的创作运用了一系列叙事与视觉元素来呈现文化与历史层面的南方性。现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如何从这种本土性过渡到超越性:从南方性到后南方性的变形中,呈现出一种关怀人类的现代性反思。“后南方”(Post-Southerness)的概念意味着构筑一种抽象的历史能指。这是一种吊诡的审美机制:在调用隶属于南方的地理文化元素之后,如何可能抹去对这种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呢?这是通过在历史之中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完成的。在美国的语境中,虽然南方是地理的概念,但南方性卻是历史与文化的概念。就后者而言,它并不局限于地理上的美国南方。事实上,南方研究在美国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文化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艺术,还包括音乐、电影、建筑、食物等各类文化载体。就此而论,南方的抽象性蕴含于南方本身的概念之中。自1980年代以来,路易斯·辛普森(Lewis P.Simpson)在美国南方文化研究领域开启了所谓“后南方时代”,而其他代表人物包括迈克尔·克莱林(Michael Kreyling)、斯科特·罗米尼(Scott Romine)、马丁·波恩(Martyn Bone)、杰·华生(Jay Watson)等。传统的南方研究探寻着粗糙南方性中的乡土的身份意识,而后南方研究则从否定性的视角来重塑身份之本真性。华生指出:“后南方的南方看上去并非依赖于某种体现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特殊性的‘现实的或稳固的根基,而仅仅维系在一系列关乎‘南方性的表象和交流符号,而它们又是不断更新的。”[13]从这段评论可以看出,虽然“后南方”是一种否定的、抽象的空间性表征,但是它们仍然属于南方性。这里蕴含着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美学路径:当南方的文化元素转变为一种文化的共相时,它摆脱了对南方本身的依赖性,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能指,但与此同时它仍然属于南方性。也就是说,从一种地方文化中抽象出某些元素来构筑文化能指时,这种符号就跃迁入了更一般的文化经验之中,但它以否定与抽象的方式仍然保存着原生的本土性精神。抽象作为一种否定的过程,最终带来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合题,即基于本土性的现代美学符号。从这个框架来看,《野兽》完全属于后南方的领域。在电影空间性的文化符号完成了从南方到后南方的转换后,泽特林的《野兽》成为了一种基于本土性而呈现一般的现代性问题的能指。
在这一部分的结尾,有必要指出评论家对这种抽象化的美学路径所提出的问题。其一,当《野兽》浪漫化波西米亚风格的生活形态时,它弱化了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弗农认为,“对较低阶层的电影美学化”会误导观众相信贫穷“是被选择的和自我施加的状态”,从而压抑了反思与共情的能力。[14]其二,《野兽》在抽象化的美学表达中弱化甚至褫夺了历史性维度。克里斯托弗·洛伊德(Christopher Lloyd)指出,當《野兽》调用南方性的元素来构筑一个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他处时,它呈现了南方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边缘位置,而一场飓风揭示出了南方的这种脆弱性。但是,洛伊德认为,泽特林的电影空间完全缺乏历史性维度。譬如,在《野兽》中的非裔的社会处境“没有得到充分的历史化: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制塑造了该地区的这种被抛弃的生活,但这种现实的遗迹却在电影中完全缺场。”[15]换言之,在追寻一种想象的与神话的超越性时,《野兽》似乎牺牲了社会与历史反思的可能性。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抽象化的美学表征仍然有着其历史的维度。《野兽》的后南方特征塑造了反映现代性问题的美学表征,而它的抽象性的代价固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美国南方语境中的具体的历史纽带。但是,在创制一种现代电影神话时,他仍然保留甚至凸显了作为粗糙南方概念之本质的边缘感,并由此呈现了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他者意识。在现代性问题的场域里,他者的问题本身又可以充当反思包括种族问题在内的身份政治的框架,因而历史性的反思并没有消失或被压抑,而是以现代性的问题在普遍的层面重新提出。
三、从后南方到后现代
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粗糙南方的概念在美国文化中衍生出丰沛的艺术实践,它们的美学特征通常被界定为“沙砾文学”或“格利特利特”(Grit Lit),一种当代的南方美学类型。这种类型蕴含着一种反讽,即借助一些看似疯癫、愤怒、绝望的边缘角色的形象,来呈现针对现代性原则本身的反思并且展现出一种未曾异化的希望。汤姆·富兰克林(Tom Franklin)指出:“什么是沙砾文学?它是肮脏的南方,完全褪去了浪漫化的表象或追忆往昔的虚妄乡愁,一切都随风而散。……它是关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救赎希望的人试图竭力拯救生活,尽管这种努力可能只是从卡车轰鸣而过的乡间公路旁的酒吧里买一箱啤酒,颤巍巍地搬运到森林里,借酒浇愁。这种无畏的意识能够在纸面呈现一个人,让你感受他所站的地方。仿佛一个倒下的人重新站了起来对你说:‘再坚持一下,我还没有死。这就是沙砾文学。”[16]1-9泽特林的电影几乎都属于这一范畴。在《野兽》中,尽管电影空间性被认为缺乏历史维度,但是它所展现的精神却与沙砾文学所把握的南方性之精神完全一致。在玉米球的关于浴缸村之描述的旁白里,有这样一段话:“他们建造了一堵墙来隔绝我们,以为我们会在这里沉沦消失。但我们却一直都在。”在破败的后工业景观里,浴缸村的社区在酒神精神的滋养下保持着一种充沛的生命力与不曾熄灭的希望。也就是说,在本土性元素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中,乡土的精神并有消失。
这种留存的乡土精神构成了对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的现代性的批判。借助沙砾文学里典型的“肮脏南方”,泽特林所虚构的浴缸村的生活形式蕴含着一种针对现代性的美学批判。借助尼采所揭显的酒神精神,它为肮脏南方之肮脏完成了一场美学的颠倒,使之从失败的个体转变为超越的共同体之理想形态,从而为其恢复了失落的尊严。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异化视域下,任何一种接近自然的生活形态都被置于边缘与破碎的境地,而颠倒则越出了这种异化视域。具体而言,酒的元素在《野兽》中是一种呈现肮脏南方之反讽的视觉符号。玉米球的父亲温科(Wink)与他在浴缸村的朋友们都嗜酒,这点体现了沙砾文学中的否定性的意象。但是,在浴缸村里的酒文化同时又是一种生命力的表征,正如温科在飓风中的愤怒彰显着一种求生的意志与力量。在尼采的视域里,宴饮体现着一种狄奥尼索斯的精神,统一自身与他者。借助于非理性的精神,这种统一性不仅构成了共同体之中的团结,也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原初的关系。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写道:“自然在这些时候以最高力量而表达自身,当沉浸在狄奥尼索斯的迷醉里,在喧哗之中,在麻醉的刺激物的影响下,它狂野地穿透灵魂的一切尺度,或者在春日里使一切萌动得到释放。自然把个体的生命重新维系在一起,并且使他们感受到与彼此同在,从而个体性的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就此被揭露为某种意志软弱的持续状态。”[17]122-123浴缸村的共同体形态是现代的个体主义之颠倒。在《野兽》的电影表象中,宴饮的形态是它的隐喻。不同于典型的西方餐桌,一大盆海鲜肆意倾倒在一张餐桌上,各取所需,不分彼此。现代生活里的计算理性、界限、个体意识在这里似乎是缺场的。除了宴饮,在温科家里的日常生活里,就餐被称作“喂食时刻”。而温科总是提醒女儿玉米球要把食物同宠物狗一同分享。自身与他者的统一从共同体的团结延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共存。浴缸村的酒文化还经常伴随着音乐、吟唱、漫游、烟花,如同节日的狂欢。正如玉米球所说,浴缸村似乎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节日。但在《野兽》的电影空间里,这些节日似乎是无名的,从而它们更接近于为生命本身而庆祝,或者说生命本身被活成了一场庆祝。可以说,泽特林的后南方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人性肖像:不是计算的、不是经济的、不是个体主义的。要之,它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的现代人,但它却是《野兽》的电影空间里的理想人。
在《野兽》中,这种现代性批判具体地呈现为生态的反思。借用帕特里卡·雅戈(Patricia Yaeger)的话来说,浴缸村的居民实践着一种“肮脏的生态学”(Dirty Ecology),即从其他的阶层所遗弃的废物中重新塑造出生活工具。[18]在《野兽》与此前的《荣耀》中,船都是由各种废弃机械设备拼凑而成,而这种回收物构成了泽特林最具标志性的风格元素。这种废物回收的生活形态看似是肮脏的,但实质是环保的。正如酒的精神构成对原子个体主义的批判,肮脏在此构成了生态批判。在浴缸村里,房屋与机械表面的污渍与铁锈营造出一种后工业的景观,以及通常被归咎于工业活动的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生态剧变,似乎都指向工业化的人类世的危机。泽特林的《野兽》是一种多元的能指。在生态的视域里,它指向全球生态危机里的慢暴力。“慢暴力”(Slow Violence)是由罗布·尼克森(Rob Nixon)提出的概念,它是指“一种缓慢发生乃至于不可见的暴力,这种暴力带来在时空上离散状的延迟的破坏,并且这种损耗性的暴力通常并不被认作是暴力。”[19]尼克森用这一概念来建构环保主义的伦理反思。现代的人类生活风格看似洁净与文雅,但在本质上却把自然当作他者而施加暴力。生态的暴力同样是针对他者的压迫,因而在结构上与身份政治(包括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同构的。
现在,我们来看《野兽》在对慢暴力的刻画中所呈现的和解的希望。在《野兽》中,远古的欧洲野牛(Aurchs)从融化冰川里的复苏是一个生态的隐喻,它作为源于自然又强于人类的他者回应着工业化人类世对地球的慢暴力。阿力·布洛科斯(Ali Brox)认为《野兽》的隐喻含义在于“让慢暴力变得可见”。在布洛科斯的解读中,远古野牛群的重现抹平了时间与空间的差异,从而创制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效果,回应了如何表现慢暴力的美学课题。[3]野牛群的出现是自然对人类所施加的慢暴力的回应。在影片的结尾,玉米球与野牛群直接对峙,并且借助超自然的力量而实现了一种沟通:“你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朋友,但我还必须保护我的朋友。”她的话语使得野牛群屈膝,并且成功地保护了浴缸村的居民。这似乎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解的瞬间。野牛屈膝的瞬间出现了一组关于玉米球的脸部特写,浮现了一种微妙的胜利者的微笑。这种微笑背后的心态是什么?玉米球重新成为了自然的征服者么?
在此,笔者试图探讨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为:玉米球学会了他父亲温科所教给她的兽化的生存技艺——捕猎、杀戮、滋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而生存于自然。这一个解释似乎在人与非人之间的连续性,从而电影标题中的“野兽”不仅指向野牛群,而且喻指浴缸村的居民及其后南方性。然而,尽管玉米球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了其父亲的战斗意志中的勇气,但她在与野牛的沟通之中却并没有任何作为捕猎者的姿态。她的倾听能力是一种与暴力完全相反的技能。在《野兽》中,玉米球总是在倾听,她倾听人的心跳,也倾听螃蟹与树叶。也就是说,玉米球与野牛群所象征的自然本身之间达成的和解,并非基于暴力与征服,而是一种倾听的姿态。这就引向了第二种解释,即她学会了浴缸村的教师巴特斯布娃小姐(Miss Bathsheba)的面向自然的平等主义。在倾听之中蕴含着一种平等的姿态。然而,玉米球的倾听却并非磨平人与非人之界限的绝对的平等。当玉米球把野牛称作“我的朋友”(my friends)时,她同样强调它们与浴缸村的居民是不同的,后者是她必须保护的另一些“我自己的朋友”(mine)。也就是说,《野兽》中的和解并非以牺牲人与非人的自然之间的质的差异性为代价。这样,玉米球的倾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面向自然的姿态呢?《野兽》并没有给出答案。也就是说,玉米球与野牛群的和解是突兀的,它并没有给出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深层的合题。这种缺场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判。阿莱斯·诺克斯-罗素(Allyse Knox-Russell)认为,《野兽》没有呈现一种乌托邦式的和解,从而止步于“缺乏乐观主义的未来性”,而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正如玉米球并没有真正习得生存的技能却最终失去了父亲而必须独自面对世界,人类同样也没有真正从人类世的创痛里找到自然与现代生活之间真正的和解,而只是被抛入了一个陌生的未来。[20]然而,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的基调更接近于某种喜剧性。在电影海报及浴缸村的狂欢形态的铺展里,酒神精神并没有在终局里消失。从电影神话学的角度看,一个具体的生态答案的缺场恰恰体现了电影神话学的特征。对于现代性问题所牵涉到的各类具体的症候而言,电影无法也不必给出一个乌托邦式的解答。作为现代神话,《野兽》的价值在于呈现出在现代性框架里的他者所蕴含的力量,使其从不可见的边缘重新呈现在视野的中心。对他者重新获得的感知本身——正如玉米球的沟通能力一样——是希望所在。
最后,笔者试图以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为参照,阐述泽特林的电影神话学中蕴含的符号学原则。在这一点上,笔者受益于编辑与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特此鸣谢。 在《今日神话》(Le mythe,aujourd'hui,1956)一文中,罗兰·巴特把神话归结为一种话语类型。这种话语类型既可以采取语言形式,也可以是任何表意的符号载体,比如摄影、绘画、海报、仪式、物体等。[21]113当然,这也就包含了电影在内。在符号学的视域中,巴特强调,神话并非概念或理念,而是一种表意或意指的形态,其本质在于符号的形式。巴特指出:“神话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它所传达的信息之对象,而在于它传达这种信息的方式:对神话而言,它有形式的界限,但却没有‘实质的界限。这是否意味着,一切事物都可能转变为神话呢?没错,我确信如此,因为世界在意义的指示上有着无限的丰富性。”[21]107从巴特的角度看,泽特林以后卡特里娜飓风的创痛记忆为题材而创制电影神话是合乎神话的符号学本质的。神话之生成在于构筑一种特定的符号学结构,而这种结构是独立于叙事内容的纯粹形式。根据巴特的分析,在一般的话语类型中,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比如,在作为情感符号的玫瑰中,“玫瑰”(能指)指向“我的情感”(所指)。而神话则是一种二阶的话语类型,它的能指本身就调用了语言之中的符号,而神话之所指则超越于这些符号既有的意义。根据巴特的观点,那些被神话创制者所调用的符号本身有着其固定的意义,“它们的意义已经是完整的,并且蕴含着知识、历史、记忆、一套关于事实、观念、选择的相对秩序。”[21]116与此相对,神话创制的过程则将悬置这些符号之中既有的意义,从而为新的意义预留空间。他写道:“当它变成形式,意义就把它的偶然性抛在身后;它放空自身,它变得贫瘠,历史蒸发了,只有符号留存。”[21]116在此意义上,巴特把神话创制在二阶层面上对语言所作的符号学操作归结为变形:“在神话的概念与其意义之间建立统一性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变形的关系。”[21]121泽特林在其电影神话学的美学实验中把南方的符号学元素(语言、食物、生活观念、地理景观、社群文化等)转变为后南方的抽象质素,而这一过程恰恰暗合巴特所揭显的神话对既有符号的变形。后南方正是这种变形的结果:它通过对南方性之地理界域的抽象,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意义空间。在泽特林的电影神话中,后南方為后现代的反思提供了符号学的空间。巴特用一个空间化的隐喻来描述神话创制对既有的符号所作的变形:它是一种不在场证明(alibi)。巴特指出,不在场证明的空间性取决于在场与缺场之间的交叠,它在自我的同一性之中揭显出否定的双重性:“我不在你认为我在的地方,但我在你认为我不在的地方。”[21]121神话与不在场证明的相似性在于:它否定既有的符号学意义,从而指向他处。由此,神话构筑了一种全新的形式,或者说一个在他处的意义空间。从巴特的结构主义神话理论来看,泽特林的电影神话学之美学动力在于一个关键的变形,即从南方到后南方的转变。
不过,笔者试图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结构主义的解释做一点补充。在巴特的结构主义理论中,神话的本质在于构筑一种符号学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完全独立于材质。然而,从上述对泽特林电影中的审美质素的分析来看,南方、后南方、后现代之间的意义关联并非外在的、非时间的、纯形式的,而是内在的、历史的、寓于材质之中的。甚至可以说,作为创作材质的南方性构成了其电影神话学的意义源泉。泽特林的确引入了一种经典的结构变换,即颠倒(inversion)。比如,在《野兽》中,贫穷的社群变成丰饶的部落、肮脏的后工业景观变成生态的乌托邦、弱小的儿童变成拯救的英雄。颠倒的美学意义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反转”(peripeteia,reversal),它是构筑戏剧性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然而,在泽特林的电影空间中,颠倒的形式并非外在而任意地施加于南方性的美学质素。相反,从南方到后南方的转换源于对南方的乡土形态同工业化现代都市之关系的历史反思。也就是说,泽特林的电影神话学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符号学重构。这种重构的目的在于:从本土经验之中开拓出一种与在他处的观者建立共情的可能性,乃至在具体的本土性与一般的现代性之间建立意义的关联。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阐述了泽特林的电影神话学如何把作为本土性元素的南方转变为一种抽象的能指,即后南方,从而用以构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审美批判。在南方与后南方之间,《野兽》被塑造为一种多元的能指,在本土性的层面它为卡特里娜飓风的经历者与幸存者塑造了一份公共的记忆,而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它指向现代性问题。就后者而论,它不仅透视着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布尔乔亞生活方式之异化,而且揭显着工业化的人类世对自然的慢暴力。至此,电影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所体现的超越性是越出界限,即打破现代主体主义的视域,从而面向他者,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超越性是历史的超越性。它在《野兽》中体现为对肮脏南方之反讽的重释。在这种反讽里,出现了一系列中心与边缘的对峙。位于中心的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处在边缘的则是抵抗异化的波西米亚生活风格与承受着慢暴力的自然本身。反讽构筑了一种颠倒,它使得位于边缘的他者转变为了一种逃离过去的未来性。泽特林借助围绕南方性的本土元素构筑了一部电影神话,并由此为卡特里娜飓风的创痛记忆铸就了公共记忆。在电影神话学的浪漫化的抽象里,南方性又超出了本土的限域转变为一种新的共相,从而指向现代性场域中的他者问题。综上所述,在电影空间中从本土性到超越性的转变之意涵正在于塑造作为历史抽象物的美学能指。这项研究起草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电影哲学》期间,得到了笔者博士后合作导师韩水法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尚新建教授、周程教授、仰海峰教授也予以了慷慨的支持。其中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讨论,深受博士导师孙向晨教授的启发。此外,在写作期间,笔者有幸得以在位于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大学访问并加深对南方电影与文学的研究。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Foundas Scott.Louisiana Story[J].Film Comment,2012(03):24-27.
[2] Taubin A.In Search of Wild Things[J].Film Comment,2012(02):60-62.
[3] Brox A.The Monster of Representation:Climate Change and Magical Realism in “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J].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2016,49(01):139-155.
[4] Singer I.Cinematic Mythmaking:Philosophy in Film[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0.
[5] Von Hendy A.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Myth[M].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6] Ferrell WK.Literature and Film as Modern Mythology[M].Westport:Praeger,2000.
[7] Schelling FWJ.Historical-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ythology[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7.
[8] Vernon Z.Southern Cinematic Slumming The Rough South Turn in Post-South Film[M]//The Bohemian South.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7:148-164.
[9] Bingham SC.Bohemian Groves in Southern Soil[M]//Shawn Chandler Bingham and Lindsey A.Freeman.The Bohemian South.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7:1-19.
[10] Spoth D.Slow Violence and the (Post)Southern Disaster Narrative in Hurston,Faulkner,and 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J].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2015,68 (1-2):145-166.
[11] Spitzer NR.The Creole State:An Introduction to Louisiana Traditional Culture[EB/OL].http://www.louisianafolklife.org/LT/Articles_Essays/creole_art_creole_state.html.1985.
[12] Ferris MC.The “Stuff” of Southern Food:Food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American South[M]//The Larder:Food Studies Methods from the American South.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3:276-311.
[13] Watson J.Mapping out a Postsouthern Cinema[M]//American Cinema and the Southern Imaginary.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1:219-252.
[14] Vernon Z.Romanticizing the Rough South Contemporary Cultural Nakedness and the Rise of Grit Lit[J].Southern Cultures.2016,22(03):77-94.
[15] Lloyd C.Creaturely,Throwaway Life after Katrina:Salvage the Bones and 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J].South:A Scholarly Journal.2016,48(02):246-264.
[16] Franklin T.Whats Grit Lit?[M]//Grit Lit:A Rough South Reader.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2012:1-9.
[17] Nietzsche F.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Other Writing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8] Yaeger P.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 and Dirty Ecology[EB/OL].Southern Spaces.https://southernspaces.org/2013/beasts-southern-wild-and-dirty-ecology/.2013.
[19] Nixon R.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0] Knox-Russell A.Futurity without Optimism:Detaching from Anthropocentrism and Grieving Our Fathers in 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M]//Affective Ecocriticism:Emotion,Embodiment,Environment.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8:213-232.
[21] Barthes R.Myth Today[M]//Mythologies.New York,NY:The Noonday Press,1972:109-64.
(責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