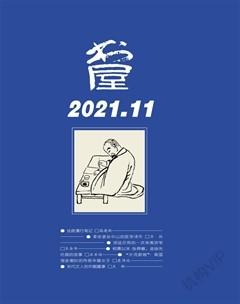会心不远
续小强
《白石老人自述》是一本极薄的小书。虽薄虽小,我却以为,这是走近齐白石最重要的一本书。罗家伦讲得好:“这是一篇很好的自传,很好的理由是朴实无华,而且充满了作者的乡土气味。”“最动人的文学是最真诚的文学。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哪能不使人感动?”
据三联版《白石老人自述》的《写在前面》:“1962年,齐白石的口述记录稿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名为《白石老人自述》;1967年台湾版面世。”南渡的罗家伦是否据此所称的版本而写的这篇感想呢?幸好孔夫子旧书网有一份《传记文学》1963年第三卷的合订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记文学》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分“上、中、下”三辑选载了《白石老人自述》的内容;在第三卷的第五期则刊载了罗家伦的这篇《看完〈白石老人自述〉的感想》。据此,大约可以确定地说,罗家伦正是读完《传记文学》的连续三期的选载后,兴之所至,才一挥而就如此“感想”的。罗家伦文章的末尾,记叙其与陈师曾等几位朋友访过白石老人;为白石老人张贴了画的润格他生出了不少反感;读了这篇自述,他见识了老人为生活艰苦奋斗的情形,才将这反感“消释于无形了”。
一部字数不多的自述,让暮年的罗家伦时隔三十多年才觉出了白石翁的“好”。不过,他认为的“好”,是自述中读到的白石老人的艰苦奋斗,是其反复说的自述文字的真诚与白石老人为人的厚道。于白石老人的艺術之美,罗家伦却持有保留赞美的态度:“至于他说他的画‘学八大山人冷逸一路也不能说是到家。八大的画笔奇简而意弥深;白石殊有未逮。白石画常以粗线条见长,龙蛇飞舞,笔力遒劲,至于画的韵味,则断难与八大相提并论。但在当今,已不容易了!”
其实,一个“不容易”,是无法概括白石老人艺术成就的。也许,这一番话,是传统士大夫情怀的罗家伦,对时已贵为“人民画家”的白石老人的复杂情绪的一种表达吧。也许,这仅仅是历史学家罗家伦对艺术家齐白石跨界的见仁见智的独特理解。不过,说实在的,如果真是要道出白石老人绘画艺术的“好”,却真真正正还是“不容易”的。
这个“不容易”,我以为只考验着如我一般喜读书而不懂作画的艺术爱好者。殊不知,这个类似的问题也一直纠缠着如韩羽先生这般的艺术家。新冠疫情初定,从韩羽先生处“讨”来一册他的新作《我读齐白石》,卷首小引便是:“‘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是我读白石老人画作时必兴之叹。”如此看来,韩羽先生也长期地苦苦琢磨着白石老人绘画的“好”与“好处”。他继而又说:“叹之,复好奇之,横看竖看,边想边写,有冀觅其端倪;断断续续,记之如下,以莛撞钟,能耶否耶?”于文学创作、水墨艺术均有非凡实践和杰出建树的韩羽先生,如此彬彬自谦,如此孜孜以求,让我这个白石老人艺术的爱好者,对他的这本小书,也有了欣欣然的特别的期待。
要说“好”,确乎是应有一个“尺度”和“标准”的。在《我读齐白石》的跋语中,韩羽先生对白石老人的“定位”是从他对中国绘画艺术史的理解开始的。他以自己“杂七杂八的印象”,把中国绘画史分为三期:远古时期“类似现下的装饰图案”的“纹样绘画期”;秦汉至宋元时期,“存形莫善于画”,“明劝诫,著升沉”,描摹客观物象,记录现实生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到了明清时期是第三个阶段,绘画的教化功能转向欣赏功能,画家自我意识升阶入室,由我描画别人改换为我描画我自己,“聊写胸中逸气”。韩羽先生认为,“西方,也大率类此,只是说法不同,对第三个阶段,他们命曰‘现代派,我们名曰‘文人画”。如果说,小引中反映了韩羽先生数十年求索探秘白石老人伟大艺术的谦谦状态,那么,跋语中这几段一改韩公蕴藉文风的斩钉截铁,则可看作韩羽先生数十年求索之后对于白石老人发自真心的悟知与认定。
《我读齐白石》的正文,共五十篇文字。其中五篇,曾经收在201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画人画语》中。除却这五篇,其余主体,都是近三年韩羽先生的新作。文字篇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伸缩自如,灵活洒脱;除两篇专谈日记与诗的文章外,均采取正面进攻的“打法”,即“看画说话”,用韩羽“小引”里的话是“横看竖看,边想边写”,用文学研究的专业说法,大概即是文本细读法。
正文之外,韩羽先生与编辑一道工作,尽可能配了他所谈论的白石老人的画作。这些画作,由中国知网检索可以看到,自五十年代起,即广泛地见诸各类报刊,且为艺术同道与研究论者反复提及或论述。以《王朝闻文艺论集》所收其不同时期写作的齐白石的专题文章看,韩羽谈论的齐白石画作的大部与王朝闻文章提及(举例)的白石老人的作品大体也是一致的。只是王朝闻所谈极为简约,而韩羽先生则是一路穷追猛打,刨根问底。面对业已经典化的白石老人的作品,韩羽先生的细读虽显得“笨拙”,然经其回春妙手抽丝剥茧之后,白石老人画作的新鲜美好才恍然第一次如出水芙蓉般展现在了我等一般的艺术爱好者的面前了。
同为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的两栖实践者,我认为韩羽与王朝闻的心气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王朝闻其旨在宏观立论,无暇细分缕析,而韩羽重在“看画说话”,招招皆为文本精读。在《壮气溢于毫端》一文中,韩羽专门谈论了王朝闻所提及的齐白石的残荷、秋荷,他引了《秋声赋》,一通描摹之后,他总结道:“这是笔势墨痕构成的形式感,使视觉、听觉打通而形成的错觉,是由不同感官相互暗示而获得的心醉神迷的审美感受。”至于王朝闻提及的白石老人的“柴耙”,韩羽先生以《说柴筢》一文对白石老人这幅经典作品作了极为全面也极为深刻的解说,并进一步引申,由此延展到了“画什么”“为什么画”“如何画好”以及“书”与“画”之关系等等重要问题。对于王朝闻多次提及的“钩丝刚一着水群鱼就来”的画面以及老舍先生《蛙声十里出山泉》的“命题作画”,韩羽先生都是缓缓道来,作了独到的艺术解读。由以上的举例,似乎可以这样说,王朝闻所作齐白石的文章,如同“艺术概论课”,讲的是“一般与抽象”,而韩羽先生所作的“看齐白石画说自己话”的文章,则如同“作品赏析”,讲的是个别(特殊)与具体。王朝闻、韩羽两位先生如此的对话,超越了时空,确有一种别样的“相谈甚欢”的美好。
要说,韩羽着眼的,只是个别与具体的作品,只是一味地想“看画说话”,觅寻白石老人作品的真正的“好”和“好处”,就这本书直接的阅读效果,是这样的。但透过这些文字,去体察韩羽的内心动因,我以为,他仍然是有他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抱负的。白石老人的画作,向他提出了挑战,提出了问题,在追问与探索的过程中,也滋养了他自己的艺术,或者说,在潜意识中,他既是白石老人画作的一般欣赏者,也是白石老人“画论”的探求者。多年积累下来,由这一本小书,他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画艺术问题的总结提炼与自我艺术生命的强烈激发。在此意义上讲,韩羽的《我读齐白石》,其实也是一次独具韩羽艺术个性的理论创新。
比如,对齐白石多次提及的“似与不似”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王朝闻对齐白石“似与不似”的解读,重点在于客观物象的似与不似,以及继承传统绘画艺术传统的“似与不似”;韩羽基于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文学阅读感悟以及艺术创作实践,对“似与不似”则有他自己的发明。《我读齐白石》的书中约有五篇文章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似与不似絮语》中,他所提出的,是其有关“似与不似”的总体性的论点,即:“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就字面看,似是绘画之法,远非如此,实是已关联到作品与欣赏、作者与读者相互互动的更深层面,由‘技而‘道了。”他进而分析得出他的观点,“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间,也就是读者想象力驰骋的活动空间”。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是”与“似”两个同音字的不同意味,由张潮之“情必近于痴而始真”的“似痴”,到《艺概》之“似花还似非花”“不离不即”的悟解,结语以绝对的语气说道:“齐白石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就是‘似,而不是‘是,这话虽不是他首创,但自古迄今明此理的画家多矣,而能以天才的多样的绘画典范验证之发扬之者,首推齐白石。”
另有一文《“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有关“似与不似”的见解亦极为独特。此一篇如果从与上述文章“互动”的层面来生发,堪称姊妹篇。他说,齐白石的“似与不似”论,“人人云云我亦云,数十年,仍无异于终身面墙”。“恰好有他一幅画稿,试窥蛛丝马迹”。他引了这幅画稿的跋语,“画存其草,真有天然之趣。”正是这个“草”,引发了韩羽“似与不似”的思考,正是这个“天然之趣”,使得韩羽揣摩到了,“‘天然之趣是何趣,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他所熟悉所喜爱的‘趣”。接下来的话语,虽是对白石老人的领悟,我看则实为韩羽艺术创作的自况:“或谓,画画儿,看画儿,何得如此啰唆,答曰:人之与人与物与事,总有好、恶之分,亲、疏之别,人的眼睛也就成为本能,总希望从对象中看到自己之所喜好所熟悉所向往的东西,或者说,就是‘发现自己。观人观物如是,艺术欣赏活动尤其如是,艺术欣赏者最惬意于从欣赏对象中发现自己所熟悉所喜爱所向往的东西,不如此不足以愉悦。而艺术创造者也竭尽所能将自己所熟悉所喜爱所向往的东西融入艺术作品之中,唯如此方得尽情尽兴。这是出之人的本能,饥则必食,渴则必饮,不得不然也。”如是,韩羽探测到,“似与不似”实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普遍规律,以及这一规律如何发生作用的隐秘。最后他说:“如谓这‘似与不似的鸟儿是白石老人就砖地上‘画存其草,不如说这只鸟的影儿早就储存于他胸中了。偶尔相遇,撞出火花,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初见林黛玉,‘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你看,韩羽的博学与幽默悄然而出了。
《境内映花灯边生影》所发明的,则是“似与不似之间”的“画理”。这篇文章由白石老人无题无跋、就笔墨论不能算作上品的“母鸡驮小鸡”画而引发。“先说‘母鸡驮小鸡未必有其事。”“再说‘母鸡驮小鸡当必有其理。”再问:“这小鸡雏是怎地到了母鸡背上的?我思摸八成是白石老人助了一臂之力,是画笔起的作用。”“比懂鸟语的公冶长更善解鸟意的老头儿的一颗心,正是这颗心,使整个画面暖烘烘起来。”再下来,就是韩羽公独有的妙悟了:“这幅画把生活中的‘本来如彼的‘彼,画成了‘应该如此的‘此,说是‘无中生有固然不可,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似也卯榫不合。不妨以他自己说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对对号。母鸡驮小鸡,未必有其事,不亦‘不似;母鸡驮小鸡,当必有其理,当然是‘似了。正是这‘似与不似的间隙里,才得以作出了这妙文章。”
《再说“蛙声”》篇谈的是白石老人的经典名作《蛙声十里出山泉》。于此,韩羽发明的独特处至少有三。一是他认为的美和美的由来,“美,总是躲躲闪闪,‘藏猫儿。若想和它照面,还需‘缘分,要看有缘无缘了。”蛙声何以言美?不知关联着眼睛和耳朵,也关联着心态。二是绘画的“合理的虚构”,蛙声的由听入画可视可看,异体而同化,“蝌蚪起的就是‘药引子作用……既不能把它画得太像,也不能画得太不像,约略像个蝌蚪样儿,方恰到好处,这不妨叫作点到为止”。由此,他对“似与不似”的艺术实操概括为:“画中物象,不等同于生活中的真实事物。生活中的事物,一旦进入画中就具有了‘假定性,换个说法,也就是合理的虚构。”三是绘畫的“推敲”功夫,韩羽由其创作的体会思考得就更深了,“点到为止”之“止”,也是有条件而存在的:画题“蛙声”的暗示,以及画面山间溪水的急流,调动起欣赏者的不同感官,互相打通而“视形类声”;“知止”“止于至善”,如要“点”到“至善”之恰到好处之“处”,“并非率尔挥毫就能信手拈来”,而真是要下如贾岛般的“推敲”功夫。
“似与不似”,是一个大问题,却也并非是韩羽关注的唯一的问题。在这本小书中,基于白石老人的画作与诗作(日记),韩羽公对其他传统绘画的老问题也都有极个性而深刻的思考。比如,笔墨的问题,雅俗之辨的问题,诗与画的关系问题,画跋的问题,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的问题,写意与写生的问题,诸如此类普遍的常识性问题,由白石翁的画作,他都“读”出了不凡的见解;于白石翁绘画的理解,于绘画艺术的实践,均有不凡的启发意义。
同时,从韩羽这本小书的多篇文章中,我们真可清晰可见他对白石老人人性幽微之处探察的探察,对白石老人伟大人格魅力的崇仰。以及,那种莫名的相惜之情。谈到齐白石跋《谷穗螳螂》“墙角种粟,当作画看”时,韩羽言:“耐人寻味之‘味,不离文字,不在文字。文人雅士,有爱梅者,有爱莲者,有爱菊者,有爱兰者,似未闻有以谷‘当作花看者,即种谷之农民虽爱谷亦未闻有以‘当作花看者。”“‘当作花看,就是审美之极致。”“审美之极致,就是古人说的‘神与物游‘物我两忘。”《谁能忍住不笑》谈白石老人画的“也该歇歇”的秃顶老头儿,傻得有趣,真得动人,韩羽一再提及“情必始于痴而始真”的道理,白石画之人情、世情,实出于白石老人之人情与世情。《看图识画》提及的“牧牛图”,韩羽认为实是“亲情图”,如此的定评,与《白石老人自述》中对其少年经历的叙写,是极为吻合的。《“跋语”的跋语》中韩羽谈他对“草间偷活”四字跋的体悟,我相信韩羽“似是诙谐,逗人欲笑。咂摸咀嚼,竟眼中生雾,心中酸楚”的阅读体验,绝不是文字的虚与委蛇,而是内心的真实疼痛了。更有韩羽多次提及且屡作发挥的谈白石翁《小鱼都来》的文字:“白石老人画‘钓鱼图,大笔一抹,将那‘钓钩抹去,换上小鱼喜爱的食物。只这一抹,何止抹去一‘钓钩,直是‘一扫群雄,使所有的‘钓鱼图都为之相形见绌了。为何这么大力量,善心佛心也,‘民胞物与也。”“这幅‘钓鱼图,虽没有人,但有一巨大身影从那没有‘钓钩的钓竿显现出来,那就是画家的‘自我,就是钓竿之‘形与画家之‘神的兼备”。
韩羽的这本小书,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读了约四遍。又由他的这一部小书,读了关于齐白石的其他一些书,还通过知网,浏览了自王朝闻第一篇文章以来的许多许多篇的文章或论文。我深深地感到,韩羽先生的这本小书的独特价值,真是太过于贵而重了。他的文字,是一如既往的深入浅出;他的角度,是如诗歌少年般的机敏;他的思考,仍然是如其水墨画一般的活泼可爱。他时而静,时而动,时而哀,时而笑,时而歌,时而叹,时而深沉,时而婉约,真是为我们活泼泼呈现了一个可感多姿、丰富而深情的齐白石的艺术世界。
私下里,韩羽先生经常谈及白石翁《他日相呼》的画,和画中的两只小鸡。每每抚及此书,我总在想,这是多么地相像,隔了时空许多年的两位同是童心与稚气满满的老先生。那条被衔来拽去的蚯蚓,也许正是传统绘画艺术何为好的“好”字。白石老人曾为工笔草虫册题“可惜无声”。因了韩羽先生的这部书,白石老人在天之灵是可以得到许多许多的慰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