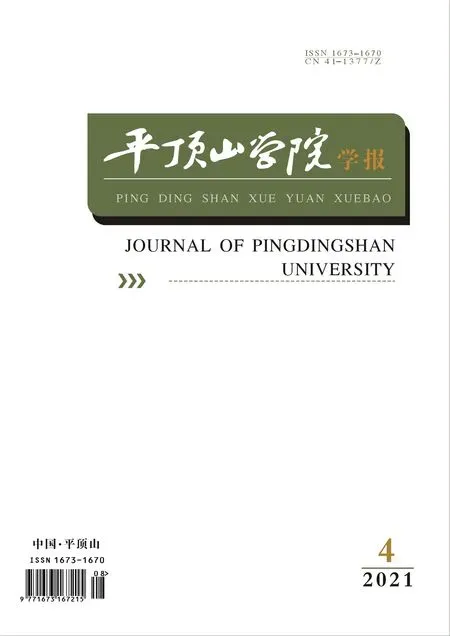魏晋诸葛亮评价的演变
陈德鹏
(平顶山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魏晋时期,国家由分裂而统一,又由统一而再分裂,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普通文人,他们对时人时事、前人前事的看法,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对诸葛亮的评价就是如此:三国时观点对立,有赞扬有批评,甚至有政治谩骂;西晋实现统一,基本确立了诸葛亮忠臣良相的历史地位;东晋史家的论述则失之于琐碎,以致出现自相矛盾的评价,但仍然维护诸葛亮忠臣良相的地位。
一
三国时,蜀、吴、魏立场各异,对诸葛亮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刘备说自己与诸葛亮的关系“犹鱼之有水”,给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定下了基调;刘备之后,诸葛亮又成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掌舵人。所以,蜀汉是肯定诸葛亮的,即便有某些批评或反对的声音,也很难形成文字流传下来。如,辅汉将军张裔经常称赞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1]933被刘璋治罪而后投降刘备的彭羕认为诸葛亮是“当世伊(尹)、吕(望)也”[1]919。刘备死后,雍闿降吴,被吴国任命署理永昌太守。雍闿想拉拢永昌官吏吕凯,后者不愿叛蜀,在檄文中称“诸葛丞相英才挺出”[1]966。邓芝出使吴国,为了结成蜀吴联盟,对孙权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1]989这里,邓芝不仅认为诸葛亮是当时的人杰,而且是蜀国的实际统治者,把他与孙权并列。
作为亦敌亦友的吴国,其国人对诸葛亮的评价有颂扬也有批评。一方面,吴国人对诸葛亮颇有好感,充分肯定其才能和重要作用。如,东吴重臣张昭曾向孙权推荐诸葛亮,说明他很欣赏诸葛亮。大鸿胪张俨认为诸葛亮之才高于司马懿,说“仲达之才,减于孔明”;而诸葛亮作为丞相,“虽古之管(仲)、晏(婴),何以加之乎”[1]856。辅义中郎将张温认为,“诸葛亮达见计数”[1]1229。在吴蜀盟约中,双方充分肯定了诸葛亮的重要地位:“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1]1045另一方面,吴国也有人批评诸葛亮连年征战,劳而无功。如张俨在《述佐篇》中提到一种看法:“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2]729此说虽然也是在赞扬诸葛亮,即承认诸葛亮真有“匡佐之才”,但主旨却是批评诸葛亮自不量力,连年劳师征伐,一无所获。而张俨则对此进行了反驳[2]729。
作为敌国,曹魏对诸葛亮的评价更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从政治角度极力贬低诸葛亮。魏明帝曹叡就是如此,他认为:1.诸葛亮辅佐刘备是“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2]103-104。2.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是“外务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2]104。3.诸葛亮进攻魏国是“虐用其民”“行兵于井底”,其“怀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驱略吏民,盗利祁山”,而“巴蜀将吏士民诸为亮所劫迫,公卿以下皆听束手”[2]104。4.诸葛亮治蜀是“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屦,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2]104。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曹魏大臣孙资等,其认为“孙权、诸葛亮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1]416。
第二种是从旁观或敌对的角度肯定诸葛亮的才能。就像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一样,曹魏阵营中赞赏刘备、诸葛亮的也不乏其人。如,刘备进攻益州时,曹操的手下丞相掾赵戬认为打不下来,傅干却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再加上关羽、张飞,一定能成功[3]521。后来的事实证明傅干是对的。受父亲的影响,傅玄也认为:“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4]再如,刘晔在劝曹操打下汉中后继续进攻巴蜀时说“刘备,人杰也”,而“诸葛亮明于治”,因而应该趁其立足未久赶快进攻。但曹操未采纳[1]404。
第三种是司马懿作为诸葛亮的军事对手,客观地指出了诸葛亮的弱点。1.食少事繁不能持久。在得知诸葛亮每日食米“三四升”、政事“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后,司马懿发出“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的感叹[5]9。2.“虑多决少”贻误战机。魏太和五年(231),蜀军攻魏,诸葛亮亲自率军抢割上邽的麦子,魏军恐惧。司马懿却说:“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5]7后来的事实证明,司马懿的判断是对的。
二
西晋统一之后,三国时的敌对观念消失,对诸葛亮的评价也随之变化,开始从明显的歧异转变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和偏向维护诸葛亮的忠臣良相形象,以巩固统一。
晋武帝司马炎认为,“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因而任命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为官[1]861。后来,司马炎又问给事中樊建诸葛亮治国的情况,樊建说:“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大为赞赏:“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1]82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晋初年,司马炎已经定下了评价诸葛亮的基调:需要诸葛亮这样的忠臣良相来稳固晋朝的统治。但是,作为文人或史家,陈寿、袁准和王隐等人则不可能完全肯定诸葛亮,进而导致作为曹魏继承者的晋朝失去合法根基,否则不仅不客观,还有可能招致最高统治者对其忠心的怀疑。于是,他们评价诸葛亮时,既要与司马氏一致,肯定诸葛亮是忠臣良相,又要批评其不足。
陈寿如是评价诸葛亮: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1]862-863
陈寿对于诸葛亮为相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与管仲、萧何相近,但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予以否定。对于后者,《晋书·陈寿传》提到,有人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因失街亭被诸葛亮治罪,而陈寿本人又被诸葛瞻轻视,所以陈寿在评价诸葛亮父子时才“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导致“议者以此少之”[5]2137-2138。意思是陈寿因为私人恩怨,有意挑诸葛亮父子的毛病,致使陈本人遭人轻视、贬低。此说值得商榷。作为史家,在写敏感的前朝史时,必须保持“政治正确”,否则,一旦惹得皇帝“很生气”,那后果真的“很严重”。所以,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写道:“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1]858在这里,陈寿首先批评诸葛亮辅佐只有弹丸之地的蜀国,拒不来朝曹魏(隐含其继承者晋朝);然后颂扬了晋朝统治者的宽宏大量,说保存了诸葛亮的著作是晋朝前无古人的“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这么一转换,陈寿为诸葛亮立传、搜集诸葛亮的著作,就不是为诸葛亮青史留名,而是为晋朝歌功颂德了。即便如此,陈寿还是主动向皇帝认罪:“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1]860此外,陈寿还对诸葛亮的文风、蜀国不设史官以及年号等作了评价。
与陈寿同时代的袁准,用问答的方式为诸葛亮辩护。1.刘备得到诸葛亮为相后“群臣悦服”。2.刘备死后,诸葛亮“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3.诸葛亮“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4.诸葛亮用兵,“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5.诸葛亮伐魏无功,是因为“大会者不求近功”。6.诸葛亮是“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等等。袁准如此,同样不仅仅是为了评价诸葛亮,也是为晋朝巩固统一总结经验教训。他说:“国家前有寿春之役,后有灭蜀之劳,百姓贫而仓廪虚。故小国(指蜀)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大国(指晋)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3]582-583显然含有提醒最高统治者注意休养生息、巩固统治的意思。
至于王隐在《蜀记》中所记西晋初年关中官员“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而郭冲列举五件事为诸葛亮辩护[1]846-847,则与袁准的辩护一样,表明朝代更替之际官方对诸葛亮的评价有一个演化过程,即从曹魏的批评乃至诋毁逐步向晋朝肯定为忠臣良相转变。
三
东晋偏安,对诸葛亮的评价似乎与破碎的山河一样,陷入零星问题的纠缠,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缺乏整体的宏观把握,甚至自相矛盾,而维护诸葛亮忠臣良相的地位依旧。
东晋中期的史家孙盛对诸葛亮的评论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对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批评,认为“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备之命亮,乱孰甚焉!”[1]848“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情,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1]848其二是对诸葛亮宽纵法正犯法的批评,认为“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国之道,刑纵于宠,毁政乱理之源”,结论是“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1]886-887。孙盛的这两点批评看似有理,却与历史事实相悖。就托孤而言,历朝历代之所以有托孤,就是因为君主年幼,执政能力不足,老君主才任命有才干的人为顾命大臣。不可否认,顾命大臣欺主乃至篡位的事例不在少数,但没有顾命大臣能行吗?所以,不论刘禅与诸葛亮日后能否相容,刘备都得托孤;而刘备敢于托孤,正是基于他对诸葛亮的了解和信任。至于诸葛亮不裁抑法正,仅仅是个例,蜀国并没有因此“失政刑”。所以,孙盛的上述批评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失之于琐碎,缺乏整体观,因而他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是错误的。
处于东晋与前秦矛盾旋涡中的习凿齿,对诸葛亮的评价则不仅琐碎,而且自相矛盾。例如,习氏在谈到诸葛亮因街亭之败杀马谡时感慨:“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原因是“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1]908。这是说,因为蜀国人才少,为了战胜曹魏、完成扶持汉室大业,诸葛亮对犯法的有才之士应该网开一面。但在谈到诸葛亮治蜀时,习氏又赞叹:“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因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诸葛亮就是这样的执法者[1]923。而习氏所依据的,不过是区区两个事例:一个是被诸葛亮治罪的廖立听说诸葛亮去世后哭道:“吾终为左衽矣!”另一个是被诸葛亮治罪的李平听说诸葛亮去世竟然悲痛而死。如此,诸葛亮的公平执法,在杀马谡时是错的,在惩治廖立、李平时又是对的——习氏如此自相矛盾,其“水至平而邪者取法”之语又从何谈起?而他所列的诸葛亮“不能兼上国”的理由,自然也站不住脚。
比习凿齿稍晚的裴松之,其《三国志注》是对《三国志》的补充和辨正,本身就带有零碎的特点,对诸葛亮的评价也逃不出此限,兹不赘述。
当然,不管孙盛、习凿齿、裴松之对诸葛亮是批评还是颂扬,以及观点如何零碎,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在宏观上都认为诸葛亮是忠臣良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肯定已经形成一种固定信仰,以致有时达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如,对于诸葛亮不愿留在东吴的原因,袁准引用诸葛亮的原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裴松之大不以为然,说“袁孝尼著文立论,甚重诸葛之为人,至如此言则失之殊远”,并拿曹操厚待关羽而后者仍不背主做对比,发出袁准是不是认为“孔明之不若云长”的疑问[1]845-846,显然有点儿过分挑剔。一则袁准引用的是诸葛亮自己的话,是历史事实;二则诸葛亮与关羽相比,谁对刘备更忠心很难判断;三则即使说关羽比诸葛亮对刘备更忠心,也无损诸葛亮的形象。但裴松之的吹毛求疵,恰恰说明他对诸葛亮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企图,而这也是诸葛亮被视为忠臣良相已成定论的一个佐证。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有一个从分歧、对立到统一的转变过程,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也从曹魏君臣眼里的“贼”演变为两晋人心目中的忠臣良相。从此,后世史家不论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具体行为,都无法否认诸葛亮是忠臣良相这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