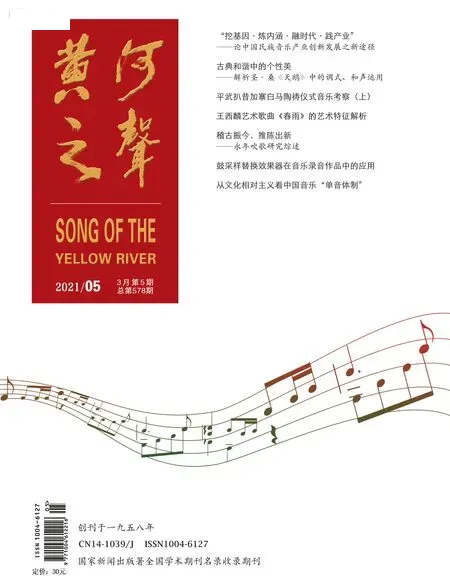浅谈中西方音乐史的异同点及其思考
齐钰/姜春花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音乐随处可见,是我们抒发情感、人际交流的主要路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强,各国文化相互交融,人们渐渐接受了世界不同的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音乐在全球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只有对全球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音乐的异同点进行研究分析,才能够深入了解其不同音乐元素的内涵,真正认识民族音乐,并想方设法促进其发展。对于中西方音乐而言,其历史内容、记载形式、社会影响方面有所区别,也在情感表达、美学鉴赏等方面差异较大。对此,研究分析中西方音乐历史异同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西方音乐历史与历史记写异同点
纵观我国悠久历史,说唱艺术起源时间较早。公元前荀子精心创作的《成相篇》,这是说唱文学的雏形。另外,说书俑文物被发掘,这是说唱艺术出现时间的最佳佐证。汉魏时期十分流行的“相和歌”、南北朝推崇的长篇叙事歌、唐代兴起的“说话”等艺术表现形式均为说唱艺术的最初表现形式。到了宋元时,说唱艺术得以迅速发展。那个时期城市迅速发展,商业日益繁荣,人们的娱乐生活十分丰富,说唱音乐中包含了长篇故事,且情节十分复杂,这样的音乐备受人们喜爱。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固定表演的场所,被称之为“勾栏瓦肆”。“陶真”、“涯词”、“小唱”、“货郎儿”等小型区域十分流行。鼓子词,则是由大量腔铺汇聚而成的大型区域,叫做“诸宫调”、“唱赚”。明清时期,说唱艺术十分繁荣,分化出多种情形。例如,古老曲种(如道情、宣卷、莲花落等),紧跟时代,积极创新,流传于现代。有的曲种无法适应时代所需,故步自封,久而久之便消亡了;还有的曲种,虽然不再以独立体裁存在,但是灿烂的艺术精髓往往被其他音乐体裁所消化,独特的技艺在别的艺术品种中得以延续与发扬。例如,在明朝时已经无法寻觅到货郎儿,然而在昆曲中却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宋元时唱赚和诸宫调在明朝已经消失,但是在元明传奇剧、杂剧中能够感受到它们的魅力。那些得以生存与发扬的说唱曲种,在发展历程中同各地区特色语言与民族音乐融为一体,有的竟然大胆改变了主奏乐器,演变出更有趣、更丰富的新曲种。例如,元明朝代鼓词,到了清代中期在北方便演变成了各种大鼓,但是在南方,则成为了三弦、琵琶进行伴奏,出现了风格独特的弹词。对于西方音乐史而言,作曲家出生、人生阅历、社会背景等则是重难点依据,其中作品自身是重点。但是针对西方作曲家的历史记录而言,同我国古代相关文献所出现的问题较为相似。一般情形下,因某一位作曲家作品在那个年代及后世的影响较为深刻,对此其人格及相关方面极有可能被撰写者夸大提高,可以地遮盖瑕疵。对于西方音乐而言,更注重音乐的社会效应,并不是进行单纯的审美,具有较强的功利心。十八世纪末期,由于美国人被英国所奴役,他们将自己的反抗与斗争等情感表现在《自由之歌》、《波士顿茶税》等歌曲中,鼓舞了人心,推动了独立战争的爆发。战后,人们又创作了《扬基嘟得儿》、《亚当斯和自由》等著名歌曲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同时,1814 年,以上歌曲再一次被创作与填词,延伸出《星条旗》等歌曲。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对西方音乐史进行研究,其不只是分析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还应高度重视其为根源的文化母体。近年来,通过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来发现出我国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重大概念,积极创新,获取最大化的传播效果。对此,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我国十分注重,同时积极寻求自立,加强原创,尽力地复兴我国音乐繁荣。全方位剖析西方音乐历史,加强理解,并渐渐构建成富含我国特色的西方音乐史学理论体系,促使其不仅具有西方音乐史学独特属性,而且还拥有深邃、多元、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
二、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与史料的异同
纵观中西方音乐,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是关键性影响因素。同时,在时间、空间、史料等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首先,从历史跨度角度分析,我国历史久远,文化渊源较为深厚。我国音乐史可追寻到九千多年前,如果把重新奉节挖掘出的石哨视为古代人类乐器,那么我国音乐史便可追寻到十四万年前。同我国音乐发展历程而言,西方音乐跨度只能够比喻为沧海一粟;其次,从空间层面进行剖析。我国音乐发展进程中,本土化特性十分明显。然而,西方音乐史的覆盖范围及视角十分广阔。最后,基于语言文字层面进行剖析,史料语言不只是从前人类记载事情的各种符号,更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关键。对于中国音乐史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古汉语能力是关键,尤其是一些先秦历史,古老文字是主要记载语言,对此应进行有效把握。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面,要求懂得异国语言,并具有分析与解读所研究的音乐作品的能力。中国音乐史研究人员能够获取大规模的音乐历史资料,所以其必须皓首穷经,对历史及音乐进行深层次了解,细细品读古书籍、音乐。同时,研究人员必须拥有较强的古文能力与文学鉴赏能力,否则便会错误理解各种史料,难以真正了解音乐真实的历史。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分析,针对音乐史的研究,我们应广泛查阅资料,互相论证。
然而,不同于中国音乐史研究者,西方音乐研究者只要求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不仅能够流利阅读与准确理解外文原著,而且还能够有效预防可能出现的“学术时差”等一系列问题。另外,翻译过程中,对作品的解读极易掺杂翻译者主观情感,也有可能由于翻译者语言习惯会对读者进行误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然而,不得不承认,获取国外第一手历史资料尤为艰辛。
三、中西方音乐历史著作及分期依据
目前,大量中西音乐史著作被出版发行,不只是一些著名的专著、译著等,而且还包括根据教育教学精心设计的教材。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现阶段我国音乐史显学特征日益明显,而潜心阅读、理解与研究历史的人较少,大多数热衷于著史,字数往往不低于几十万言,然而认真阅读却能够明显感觉到是从他人之“史”中“粘贴”、“复制”的。我国音乐史研究学者黄翔鹏具有严谨的治史观念,要求我们深入、广阔地阅读历史。虽然一生中他都没有创作任何专著,但是从各种文字中能够切身体会到他独特的见解。而西方音乐史著作中,“粘贴”、“复制”者也不胜枚举。甚至有的投机者在外文原著翻译时,巧妙地把其论述或观点占为己有,看起来毫无痕迹,但是往往难逃法眼。反观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其《史记》被代代相传,追究其原因在于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汤因比治史被誉为《历史哲学》,追究其原因在于其提出的观理性思辨。相比较之下,我们从史学史教学对中西音乐史研究及所出版的历史著作进行回顾性分析,时代“烙印”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我们在治史方面的能力较差,所提出的史观较为肤浅。
在叙述主线与分期时,中西方音乐史之间的差别较为明显。通过对我国音乐史著作分析得知,历史划分标准主要是音乐观、朝代、事物发展理念、音乐形态等,其中,大多数作品以朝代为标准,然而,西方音乐史却不是如此。纵观各西方音乐史著作得知,历史发展延续是音乐家作品创造的关键性思路,如奥地利音乐家基塞韦特曾言:“伟大音乐家是音乐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所以大音乐家则代表了每一个时代。这些音乐家所创作的作品则代表了那个时期的音乐风格,这便是音乐历史划分的关键。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西方音乐史实质上体现了其音乐风格的演变,也被叫做音乐风格史。钱穆先生提到:“文化异,斯学术亦异”。值得注意的是,在音乐研究时,研究人员对音乐所蕴含的文化研究较为注重,往往以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分析音乐,挖掘出音乐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引导人们从文学、社会层面对音乐史进行分析,并真切认识到音乐史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繁荣的进程中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西方音乐史而言,其文化土壤有所差异,造成学术研究、专业教育等方面差异较大。蔡良玉教授在音乐史研究中,以中西方音乐为研究对象,重点剖析两者的差异及发展历程。因此,在不断融合的形势下,以不同文化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中西方音乐史,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有利于音乐的发展。
四、中西方音乐的融合之势
中西音乐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互相尊重、借鉴与促进,是中西文化共性与个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我国音乐与全球音乐而言,融合过程中时代性、前瞻性等特色十分显著。首先,从思想内容角度分析。中西文化均推崇健康向上、和谐融合的思想,并借助音乐这一独特的表现形式,倡导真善美,广泛宣传法制、自由、和平,创设优良的环境。从表演形式角度分析,特别是把我国民族独唱与对唱为主的音乐表现形式同国际上推崇的声乐演唱方式相融合,顺利达到相互映衬以及中西合一的良好效果。立足于音乐配器进行探究,通过和声以及复调等对民族声乐表演涉及到的艺术性进行加强。对于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大型歌舞剧而言,服装特点、人物扮相等与我国民族戏剧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歌剧《图兰朵》能够带给人大气、雄浑的感受,将我国民族小调“茉莉花”融入其中,可达到一柔一刚的效果,进而加强音乐作品的世界性以及观赏性,让观众形成特殊感受,不存在距离感与种族感,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梁祝》是我国古老、凄美的爱情故事,向人们呈现出了男女对忠贞爱情的追求以及与命运斗争的精神。作者未运用我国传统乐器进行演奏,而是使用小提琴协奏曲演奏风格,向人们讲述歌曲背后包含的爱情故事。其中,小提琴凄凄诉说,大提琴声声相和,两者之间情景交融,让人沉醉。无论是《图兰朵》,亦或是《梁祝》,均属于民族音乐融合的一种尝试,被称为世界音乐融合的经典作品,中国音乐要想实现健康的发展,需要与世界多元化音乐进行融合,进而成为人民需要的、民族的与完美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西方音乐文化在实际融合的过程中,涉及许多问题,例如未深入理解与发扬经典传统音乐,也没有牢固掌握国外先进的音乐理念及技巧。对此,中西方音乐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应积极向全球传播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只是单纯地收集与整理传统音乐,还需深入了解世界各国文化、音乐、历史等。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文化层次上中西方差异较大,如此音乐文化成型也有所不同。对比两者文化得知,在内容、形式与风格等方面各有特色。通过对两者历史的研究,能够对其音乐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认知。同时,中西方音乐具有加强的比较可行性及必要性,研究中西方音乐史不只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更是在多元化文化时代背景下,我国不得盲目地照搬西方音乐,也不得只是研究中国音乐,应各取所长,积极借鉴优秀的元素与思想,如此才有助于深入地研究音乐,有力地促进音乐繁荣发展。■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