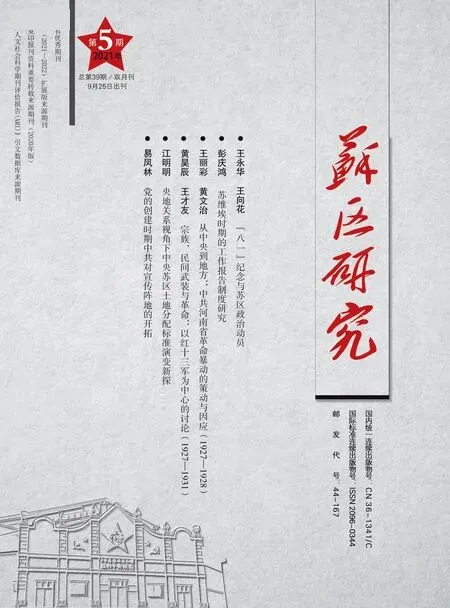央地关系视角下中央苏区土地分配标准演变新探
江明明
提要:土地革命中应以人口还是以劳动力作为土地分配标准,作为中央的中共中央和作为地方的中央苏区观点不一。在反富农不断激进的过程中,双方的分歧逐渐加大,并对分配标准有了新的审视。此后中共中央提出了人口和劳动力混合的分配标准,并试图通过苏区中央局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地方起初试图影响中央局的观点,但最终因《土地法》的颁布而采用了中央的标准。以央地关系的视角纵观土地分配标准演变过程,可知中央与地方在此问题上虽有争论,但其理念、逻辑相同,绝非“路线之争”所能概括。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见土地革命在此时期内所占地位之重要。而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标准问题,是土地革命能否获得群众支持和站稳阶级立场的关键。目前学界对这一关键问题的研究,多从路线斗争着眼,缺乏其他视角。(1)相关研究有金德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配土地的标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论证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正确性,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不仅有利于争取群众,也有利于发展生产,并且不会侵犯中农的利益;无忌:《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土地分配标准是几个?》(《理论探索》1985年第2期)则认为实际上只存在两种分配标准,按劳动力分配和按劳动力与人口共同分配并无多大差别;王明前:《平等与效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与查田运动》(《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论证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贯穿着中共在社会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权衡与取舍;董岩:《试析1929—1933年中共中央与地方苏维埃政府农民土地政策的差异》(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则在对土地革命中中共中央与地方苏维埃政府土地政策的差异进行比较时涉及分配标准问题;宋维志:《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土地分配制度略考》(《东南法学》2016年第2期)其中一节从富农路线之争的角度论述了苏区土地分配标准。上述论文中,王明前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效率与公平的追求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宋维志从土地分配的法学角度进行研究,较有新意,其余文章则多未摆脱正确与错误路线之争的分析框架。苏区时期几乎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合,中央苏区作为苏区的核心,其土地革命可谓重中之重,土地分配标准演变问题也因此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故此,本文拟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以中央苏区的土地分配标准演变为研究对象,对此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首先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谓的中央,指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而地方,则是指各地苏区。并因本文研究重点是土地分配标准,故具体而言,地方则为各地苏区领导土地分配的相关组织和个人(如毛泽东等);苏区中央局则介乎中央与地方之间。本文拟通过梳理中央和地方在土地分配标准问题上的思考与互动,力求在路线之争的分析框架之外,进一步拓展土地革命研究的维度。(2)关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的分歧是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可参见郭德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一、中央与地方对土地分配标准的各自探索
革命之初,中共中央与各地苏区都处于对土地分配标准进行探索的阶段。早在1927年11月底,为做好中共六大讨论土地问题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在《布尔塞维克》发布《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以征求党内意见。此时中共中央受“马克思列宁所言‘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的影响,认为“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为此,中国应该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第一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之辅助,而进于新式技术的生产方法,工业农业大大发展,造成新的习俗,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程度”。(3)《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1927年1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187、196页。可见中共中央此时颇注重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署名“星月”的文章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认为“苏维埃政府应按照土地的数量性质重新的公平分配给各个农民,男女分得土地的多寡,应以两性平均的生产能力来决定,未成年的儿童和老人不能生产,自有公共基金来养育,不必分予土地”(4)星月:《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节录)》(1928年2月27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16页。。很明显,作者认为应该按生产能力即劳动力标准来分配土地,以求发展生产。
随后,中共中央颁布通告,规定:“土地的分配以土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寡为标准。以年满十六岁能自耕种的人为一劳动单位,每一劳动单位平均使用土地(酌量各地情形决定亩数),其余的土地按照各劳动单位所属的四岁以上的人口之多寡平均分给于劳动单位使用。”(5)《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节录)——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5月5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21页。可以看出,此时中共中央主张以劳动力标准为主体,以人口标准为辅助来进行土地分配。与此一脉相承,《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也是大谈中国土地制度与“亚洲式生产”的关系,最后认为要“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6)《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9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41页。,但没有明确规定土地分配标准,而是由苏维埃处理。这说明此时中共中央对土地分配标准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认识。
中共中央远在上海,对土地分配标准还可以继续探讨。但各地的土地革命却迫在眉睫,土地分配是其中必须要明确决定的关键问题。对此,地方上的领导人也不断进行尝试。
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的土地分配过程中,最初采用的是“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的办法,亦即按人口标准进行分配。后来因为收到中央所发的以劳动力标准为主、人口标准为辅的通告,“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7)《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毛泽东实际上并不认同以劳动力作为分配标准,认为“不妥”。然而当时其他的领导人中,则有不少主张按劳动力分配者。(8)《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69页。因此,在随后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9)《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67页。
土地法将两种分配标准并列,但同时又规定以人口分配标准为主体。由此可见,当时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也不统一,而毛泽东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或许是为了增强以人口为标准的说服力,该土地法还特意列举了采用该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以分配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10)《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67页。
以人口为标准,一是简单方便,更易操作;二来可以照顾老幼及其家庭。但在之后的实际分田中,根据地采用的是混合标准:“按人口单位、劳动单位普遍‘均分’,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1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节录)》(1929年2月25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75页。可见地方上此时采取的也是折衷的态度。
正如毛泽东所言,分田后来就多改为只用人口为分配标准了。(12)《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69页。如在闽西,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就规定:“(1)为使农民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照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在有特别情形地方,得以劳动力单位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一倍(十四岁至六十岁能耕种者为一劳动单位),但须农民代表会议请求得县政府批准。”(13)《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01—302页。尽管该决议案允许以劳动力为标准的分配形式存在,但通过增加手续减少了其实施的可能性,且这一分配形式必须要农民代表会议请求,亦即要获得农民群众赞成。但在实践中,农民是不愿意的,如“东乡照劳动力分配引起群众反感”,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凡乡中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分子男女老幼一律分田地,他们自然满意”。(14)《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特委通告第十五号》(1929年11月5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27页。其实,在闽西的土地革命中,关于分田的标准,“闽西起初拟采用第一种(即以劳动力为标准——笔者注),结果在各地群众大会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不接受,最后还是采用第二种——平均分配的办法”。地方领导人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时,认为首先“自然是因为土地革命意义的宣传做得不充分,其次,就因为穷怕了农民,一旦看得有田分便只知拼命要求分田”(15)定龙:《闽西的土地革命》(1930年2月22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49页。。其实,主要原因是后者,即农民对分得田地的强烈要求。中共当时的第一要务是“争取群众”,自然要顺应农民的要求。
对于人口标准和劳动力标准各自的优缺点,地方领导人做过权衡:“以劳动力为标准:一,可以奖励劳动;二,可以改良生产,增加生产量”,坏处则是“一时不能取得更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以人口为标准:一,失掉鼓励劳动,奖励生产的意义;二,劳动者少,分得的田多,无力耕种,影响收获,减少生产量;三,劳动者少,自己耕种不了所分的田,有私相授受给有力者代耕,造成变相收租倾向的可能;四,给于农民共产主义的观念,使对社会主义的土地革命意义模糊”,优点则是“但能得到更广大群众的拥护”。最后,这位署名“定龙”的作者得出结论:“这样比较起来,平均分配(指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笔者注),自然是有些要不得的,他既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要求,所以还是这样做了。”由此看来,有些地方领导人对以人口为标准也不是完全赞成的,只是在群众的要求下不得已而为之。正如毛泽东所言:“很明显,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16)《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可见,地方领导人在探索过程中发现,相比于按劳动力分配土地,人口标准更简单易行,更得群众拥护,因此多采用了这一标准。换言之,地方认为人口标准在当时是合适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
综上,中共中央最初对土地分配标准并未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地方上虽然从争取群众的角度出发选择了人口标准,但并不认为这一标准一定正确。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于土地分配均尚未运用“反富农”话语。中共中央虽强调要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但并未明言如何对待富农。地方上最初在分配土地时,甚至还有向富农“让步”的问题。当时富农对于按人口和按劳动力分配两种标准均不满意,提出要以生产力为标准分配土地,亦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很明显,这种分配标准对富农更为有利。对于富农的这种要求,我们以后见之明,当然会认为要站在阶级立场上严加批判,土地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有利于富农。但当时毛泽东等人似乎完全无此阶级立场,反而认为这一问题“仍当讨论”。(17)《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1页。由此可见,此时全党上下,所谓“反富农”的阶级意识,其实是很淡薄的。而这一切,很快就因共产国际反富农指示的传达而发生改变。
二、反富农背景下中央与地方对土地分配标准的再考量
1929年6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与富农斗争而争取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18)《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87页。。中共中央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19)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接受了共产国际反富农的指示,但中共中央内部对反富农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具体内容可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35页。并通过决议,认为“应坚决的反对富农”。反对富农就必须在农村斗争中“与富农争夺领导权”,因此“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而这一群众基础,“应当从雇农起至中农止”(20)《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9月1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11—313页。。既然要动员广大群众,落实到土地分配问题上,就是要遵从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要求,同时要反对富农。因此,中共中央对土地分配的标准提出了新要求,这在其对《土地暂行法》的修订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暂行法》,其中规定土地“分配的标准,也有两种:(1)按人口分配;(2)按劳动力分配。各乡苏维埃,可以按照本乡的实际情形来决定适当的办法”(21)《土地暂行法——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5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93页。,把土地分配标准的决定权交给地方政府,两种标准均可采用。但到了9月,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中央立即对《土地暂行法》进行修订,规定:“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以人数平均分配为原则,因为各地的土地关系与土地分配状况都极为复杂。所以具体详细办法,只能根据各乡的实际情形由当地农民群众自己协议规定,苏维埃各级政府的任务,只是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坚决拥护贫农的利益,打破富农一切欺骗群众的企图。”(22)《土地暂行法——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会议修订》(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1页。可见,此时中共中央认识到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对于土地分配不再强调明确标准,但明确了大体方针,那就是拥护贫农利益,反对富农在土地分配中的欺瞒多占行为。
此时,地方领导人也提出反对富农,认为“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并认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于富农有利。因为“中国的富农既是以自己劳力为主体的占绝大多数,那末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这于富农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不但有劳力,还伴随着充足的牛力、农具与资本,不比贫农虽有劳力,但伴随的牛力、农具、资本很不充足甚至没有,所以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即在贫农中说,那些劳力多的贫农家庭(如一家八人中四人有劳力),因为多得了田,便比较劳力少的家庭(如一家八人中两人有劳力)具备迅速发展为富农的条件”(23)《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97—398、403页。。按劳动力标准有利于富农,这就为以人口为标准平分土地加上了“反对富农”的意义,且可以预防有些贫农发展为富农,这是地方领导人之前讨论分配标准时未曾提到的。
由于以劳动力为标准有利于富农,之前以劳动力为标准比以人口为标准更有利于发展生产这一观点也被否定了。不仅“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即就发展生产来说也是按人口平均分较按劳力差别分为有利,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土地未分配时多收百分之二十,以前闽西有些同志所忧虑的‘田地分割太小了’‘原先未耕田的人分了田不会耕,田会荒废’种种可以招致生产减少的危险,现在事实证明不足忧虑,并且适得其反,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了。什么原故呢?因为贫农及失业群众得了田,就把一切人力用在田内,从前农村中一切不生产的寄生虫如地主及游民现在不耕田就没饭吃,都迫得耕起田来了;从前贫农中之因土地不足而闲置起来的劳力,亦因得了田而使用出来,因此生产就增加了”。(24)《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03—404页。换言之,经过实践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样能发展生产。但值得注意的是,从逻辑上讲,上述材料其实证明不了地方领导人所谓“即就发展生产来说也是按人口平均分较按劳力差别分为有利”。因为材料中是把闽西按人口分田后的生产效果和未分田时进行对比,而不是比较按人口平分和按劳动力差别分的生产效果,因此只能证明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不会有害生产,也会增加生产,但并不能证明人口标准比劳动力标准更能增加生产。
总之,此时地方上的领导人倾向于认为“事实是所谓发展生产与劳动力为分配标准,在今日恰恰是富农的要求”(25)《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议》(1930年10月19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58页。。劳动力标准既然已被视作“富农的要求”,当然不宜再采用。1930年8月,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苏维埃土地法》,规定:“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依乡村总合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采以劳动力为标准的分配方法。”(26)《苏维埃土地法——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1930年),《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80页。
中央指示苏维埃各级政府要“打破富农一切欺骗群众的企图”。地方领导人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发现,在没收土地时,富农“有发现瞒田瞒谷的,或有以多报少的,以瘦田报作肥田,以肥田报作瘦田,等等弊病”,使得分田时出现“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的现象,引起了普通农民的不满,影响了按人口标准分田的群众意义。(27)《通告秘字第四号——彻底平均分配土地》(1930年11月12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77页。因此,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地方领导人认为,土地分配中的反富农斗争,主要就体现在这里头。“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28)《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1、174页。在此基础上,地方领导人提出和完善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为求迅速破坏封建势力并打击富农起见,分田须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29)《苏维埃土地法——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1930年),《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80页。由此可以发现,在地方看来,将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没收,并按人口平均分配,这已具有打倒地主、反对富农的意义;再加上分配过程中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打破富农企图瞒田和把持肥田的意图,真正实现土地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平均分配,这就已经充分贯彻了中央加紧反对富农,与富农争夺群众领导权的指示。
但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又传来指示:“在决定分配的时候,对于各个农民家庭,可以采取劳动为原则,或按人口来分配。对于这个问题,乡村苏维埃自己可按照当地情形与农民群众的意志来决定。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富农方面常常是大家庭居多,也有几代一家,所以采用劳动率为原则来分配土地,大都是比较适当的。”(30)《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草案》(1930年11月12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72页。也就是说,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富农家庭人口多,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对其有利,应以劳动力为标准。这正好和上文地方领导人的观点相反。那么,孰对孰错呢?其实,双方都只看到了富农的一面,富农不仅家庭大、人口多,而且人口以劳动力为主体,劳动力也多。“因此,无论单纯以哪一种标准来分配土地,对于贫雇农来说都是不利的。”(31)曾耀荣、李丹利:《争取贫雇农: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与解决乡村民生问题探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9页。
瞿秋白在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回信时,刻意将东方部的“劳动为原则,或按人口来分配”,并倾向于“采用劳动率为原则”做了自己的理解:“在分配土地原则方面,我们同意东方部草案中提出的原则,我们认为,根据劳力和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的混合原则是比较合适的。”并且他对单纯的按人口标准或按劳动力标准的土地分配进行了批评:“目前在许多苏区是按人口数量分配土地,富农最占便宜,因为他们都是大家庭。”不仅如此,苏区甚至出现了“富农偷偷把地主的孩子抱到自己家或为自己的儿子招童养媳,目的在于扩大自己的家庭,按人口数量分得更多的土地”。这和东方部的认识是一致的。紧接着,他又批评:“只按劳力分配土地的原则,从江西省的经验看也有缺点。老人、残疾人、孤儿和寡妇就分不到土地。有很多人口的中农家庭也是一样,从中占不到便宜。在机械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一些地方,有人提出:应该把红军家属的土地收回来,因为这些家庭没有劳力耕种土地。”(32)《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这是在通过实践效果提醒东方部,单按劳动力标准也行不通。由此,中共中央确立了劳动力和人口混合的分配标准。与此同时,王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提出了在混合标准基础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不包括地主——笔者注),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不仅将富农所有的多于按照一般平分原则所应得的那部分土地分配出去,并且将富农有的质量上较好的土地设法转移给贫民、雇农和中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33)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见唐正芒:《“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考析》,《上饶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徐保琪:《对王明写〈两条路线底斗争〉与“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关系的一点看法》,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7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8页。
至此,地方上坚持以人口为标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来平均分配土地;中央则确立了以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分配办法。中央与地方的标准不一,中央必定会要求地方贯彻自己的指示,而地方又将如何因应?
三、中央局的两难和土地分配标准的最终入“法”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下文简称“中央局”——笔者注)在宁都小布成立。其成立目的是“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34)《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1931年1月1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0页。。而土地革命则是中共中央想通过中央局进行指导的重要工作内容,中央局的第九号通告就是关于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其开篇就提到:“目前中国的革命依然是在工农民权革命阶段,所以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内容。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之下,对于这一问题曾有极多的精详讨论和正确的决议。”接着,通告就批评各地的土地革命不符合中央的指示:“但各苏维埃区域中党部在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中,发生许多不正确理论上的认识和策略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无疑要妨害土地革命之发展和深入,影响到整个中国革命的推进。”“因此中央局认为,对这些错误加以详细的说明和迅速的纠正,是非常重要的迫切的要求。”
很明显,中央不满意各地方的土地政策,指示中央局用中央的“正确”方针来对地方上“错误”的土地政策进行纠正。而这所谓的“许多不正确理论上的认识和策略上的错误”,肯定包括“以人口作标准来分配土地”。因为后文马上就批评这一分配标准“固然是手续简单,尤其在红军游击队影响下开始土地革命的地方,易于发动群众。但是,这一办法是非阶级的立场。因为不分贫富老幼一样的平分土地,完全使阶级意识模糊,妨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且毫无疑义的在一家人与一家人比较,富农较贫农中农人口多,依照人口分配的结果,还是富农多得土地,所以这一办法是不妥当的”。最后中央提出自己的“正确”标准:“以劳动力为标准(男女自十四岁至五十岁为一个劳动单位),以人口为辅助。应得辅助之非劳动者,所得土地只占一个劳动力所得的三分之一”,即以劳动力和人口混合为标准。为什么说“这一原则是以劳动力为标准,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是在保护贫农中农的利益上向富农进攻”呢?原来这一原则对富农是不适用的,“富农生产工具多,劳动力强,而且有多余资本,虽然他们非劳动力多,但他所得的土地已足以维持生活,因此不给以辅助,这样得辅助的自然是贫农和中农”。也就是说,富农只能按劳动力标准分配土地,贫农、中农则按劳动力和人口混合标准分配土地,这不仅是混合标准,还是双重标准。(35)有的学者认为以劳动力为标准时,也会给非劳动力分田,因此劳动力标准和劳动力人口混合标准大同小异,可以算作一种标准,可参见无忌:《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土地分配标准是几个?》,《理论探索》1985年第2期。由此可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混合标准更主要的是针对富农,其中普通农民采用混合标准,而富农则以劳动力为标准,非劳动力不分田,跟之前的以劳动力为标准明显不同。并且中央要求:“如果过去以人口作标准分配土地的而贫农中农所得的利益少,富农占便宜的,党必须发动群众,依照新的办法重新分配。”(36)《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1931年2月8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1、495—496页。
其实,地方领导人也并非真想照顾地主富农,有意模糊阶级界限。而是正如瞿秋白在信中所反映的那样,地方领导人认为“要么是彻底消灭地主家庭,要么是应给他们分土地,使他们不致饿死”(37)《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11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484页。。既然不能肉体上消灭,就应该分给土地,不然会出问题,这是地方上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点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38)《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既然如此,面对这一通告,地方领导人会如何应对呢?蹊跷的是,才过了两个月,1931年4月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土地分配标准的认识却发生了大转变。之前认为地方上有许多错误,现在却认为“前委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关于土地革命的一切机会主义,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是十分正确的。不仅如此,在分配土地的标准问题上,中央局否定了自己之前的通告,又承认了人口标准的正确。“中央局决定以劳动力为主、以人口为辅的分配方法,而预先没有经过详细审查与研究,没有采用过去斗争的经验,这是不审慎的。”“中央局没有了解中国土地革命是带了残酷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以人口平分,才能迅速的争取群众。”“关于土地问题,确定以人口平分。在没有平均分配好的地方要立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已经分配好了的地方,就要肯定土地私有,不得动摇再分。”这又回到了之前地方领导人采用的人口标准,且之前的“党必须发动群众,依照新的办法重新分配”变成了“不得动摇再分”。不过,最初的地方以人口为标准不论男女老少平均分配,地主及其家属也包括在内。这次则规定“地主家属和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如道士、和尚、地理家等人中间的剥削分子,没有分得土地的权利”,算是对中央的让步。(39)《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1年4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66—372页。
为什么中央局会否定自己先前的通告呢?原因就在地方领导人身上。据欧阳钦报告:
中央局项英同志去后,把分配的标准改为以劳动力为主,人口为辅,并决定十五岁至四十五岁为一劳动单位,通告下去,有些地方执行发生许多问题,有些地方未执行,到中央局扩大会议时,对这一分配标准经过了严重的争论。反对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的理由:一、土地少的地方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许多人家不够吃;二、以人口平均分配简单快,以劳动力人口为准复杂难算,富农可以从中作弊,以延缓土地分配,且以人口平均分配是群众的要求;三、现在农村破产的贫农家庭不一定是人口少,富农家庭也有劳动力多的;四、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贫农、中农的地方按人口平均分配是贫农、中农得到利益,所以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仍是决定以人口为准平均分配。在中央局扩大会议继续时,承认过去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是正确的,唯对于地主家属及和尚道士尼姑等在原则上不分配土地,但允许租借土地给他们。(40)《欧阳钦关于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节录)》(1931年9月3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570页。
原来是各地不执行中央局的通告,或执行时发生问题,从而在扩大会议上进行争论,最终影响了中央局,改回了原来的分配标准。而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反对混合标准,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其复杂难算,给富农以作弊之机。
中共中央原本为贯彻自己的指示而成立中央局,结果中央局却接受了地方的主张,这是中共中央无法容忍的。很快中共中央就写信严厉批评中央局:“在你们决议案中,我们还发现有很多非阶级路线的观点和办法,必须立即加以纠正,才能使土地革命的果实真正落在贫农、雇农和中农的手中,而不为富农攫去。”言下之意,中央局的决议案是有利于富农的非阶级路线。这封信几乎对中央局决议案的观点进行逐一批评,其中涉及分配标准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人口标准有利于富农,会被富农利用来谋利。“你们又肯定说在人口多的地方,只有以人口为平分土地的标准是正确的办法,而且能迅速分配土地,假使在富农家属人口多而贫农、雇农多是‘光杆儿’即有家小而自己又因穷困所迫出外谋生一时不能回乡的地方,富农正好利用你们肯定的原则,很迅速依照人口标准平分土地,则结果必致贫农、雇农与中农受到损害,而富农蒙其实惠。”
第二,“关于平分土地的标准,决议案中肯定以人口为标准是正确的,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中央以为这是错误的。国际决议案及中央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不愿肯定只有一种办法是适当的,而只说大致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因为我们肯定的是平分土地的原则,应该没收富农土地给他坏田自种,分好田给贫农、雇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至于分地的标准,应依各地环境在上述的原则之下,看如何能使贫农、雇农、中农更有利,便如何办”。后面中共中央又分析了农村土地人口的各种情况,认为“所以在我们看来,以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为标准一般是对贫农、雇农有利的。只有在特殊条件下,以人口为标准,才对他们有利。但你们的观点正相反!”
第三,对这两种相反的观点定性。“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实质,很明显的。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路线的办法,后者是非阶级路线的办法。因此你们决议案虽在原则上接受了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声明抛弃了过去非阶级的路线,但这些对立的实质和办法,将完全取消了你们所接受的原则。”最后,“中央要求你们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改正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办法,重新成立决议,使目前苏(区)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能毫无修改和曲解的在群众中彻底执行”。(41)《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局信》(1931年11月10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596—604页。
这里所谓的“苏(区)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下文简称《土地法》)。1931年11月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文简称“一苏大”,当时的文件中多称为“全苏大”)的召开,给中共中央在各苏区确立自己的土地分配标准提供了契机。“一苏大”通过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土地法》,以最高法的形式确定了人口和劳动力混合的分配标准:“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方法;或按照每家有劳动力之多寡同时又按人口之多寡——即混合原则来进行分配;或以中农、贫农、雇农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以劳动力(即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富农每个有劳动力者,所得分田数量,等于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一人所得分田数量)为单位,人口为补助单位去分配”,且“被没收土地的以前的所有者,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富农只能“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4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17—618页。这样一来,从法理上,各地就失去了再和中央、中央局争论的可能性,必须依法执行。
《土地法》颁布后,几乎所有地方都改以人口和劳动力混合标准进行土地分配。1931年12月底颁布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规定:“富农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分坏田”,“雇农、贫农、中农、失业工人、失业独立劳动者,应按照人口将田地好坏均匀,多少均匀的去分配”。(43)《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1931年12月31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30、631页。赣东北也规定“分配土地应以劳动(力)、人口的混合标准来平均分配为原则”(44)《赣东北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土地分配法——省苏第二次执委会修改通过》(1931年12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35页。。中央局也编了《土地问题》的小册子,宣传“分田的方法,要按照各地实际情形来决定,大致雇农、贫农、中农以人口为标准,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劳动力为混合标准”(45)《土地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编》(1932年初),《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50页。。这可以看作是中央局对中共中央批评的回应。地方上开始全面纠正之前的分配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如福建,“最近一年来,在土地法令草案领导之下,纠正过去的错误,彻底没收了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依照人口与劳动力混合的原则,重新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分坏田并没收他们多余的耕牛、农具”(46)《福建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1932年3月17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69页。。江西则“自全苏大会颁布了土地法令之后,坚决执行豪绅地主家属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这一工作,大多数地方确实发动(了)进一步的斗争,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47)《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年6月3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91页。。由此可见,中共中央通过“一苏大”颁布《土地法》,最终确立了人口与劳动力混合的土地分配标准,正如当时的论者所言:“土地问题,到了全苏大会之后,算是已得到了正确的解决。”(48)唯俊:《关于土地问题的几句重复话》(1932年4月13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679页。至于这一标准是否真的能“正确解决”土地问题,则非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四、跳出路线之争的土地革命再审视
行文至此,对中央苏区土地分配标准演变过程的梳理告一段落。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不难发现,中共中央和作为地方的中央苏区在土地分配上并无根本矛盾,双方一开始都在探索,都想通过土地革命来达到争取群众、发展生产、执行阶级路线的效果,并非学术界认为的有路线上的分歧。只不过地方处于土地分配的最前沿,直接面对苏区民众,考虑得更多的是民众的意愿和苏区的现实情况,而中央则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列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希望能以土地分配实践自己的主义。正如巡视员刘作抚向中央报告时所说:按人口平均分配“容易使群众走到均产主义的道路及不正确的倾向,而且消灭了农村的阶级基础,对于将来革命转变有很大的阻碍”。“至群众大数的要求是可以的,但必须指出这一错误,使群众明了这一错误是不正当的,不然即成为农民意识的尾巴主义,因为我们不能领导群众提出正当的要求,群众自己才提出不正当的要求,我们又去满足他的要求。”(49)《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页。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地方的中央苏区倾向于满足群众的要求,而中共中央则倾向于领导群众的要求。
起初,中央与地方都认为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决定土地分配标准,因此双方对人口标准和劳动力标准都不坚持,各地可以任选其一。等到共产国际提出反富农问题后,双方也均认为要反富农。刚开始反富农比较温和,中央认为要打破富农在土地革命中的欺骗企图;地方则认为要反对富农通过种种手段多占土地,因此认为按人口分配可夺取群众,也有利于发展生产,且“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可以防止富农多占田和把持肥田,实现真正的平均分配,而劳动力标准则因有利于富农被否定。随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阶级政策尤其是富农政策的激进,地主富农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而由于富农问题的复杂性,单纯的按照人口标准或劳动力标准分配土地,都难以达到削弱富农的目的,中央提出人口与劳动力混合的分配标准,一般农民按人口分配,富农则按劳动力分配,且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样一来,中央算是实现了土地分配中的争取群众、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目的。中央认为自己的这个标准真正明确了阶级路线,当然视地方标准为模糊了阶级路线。而地方在抗拒中央标准时,其最重要的理由也是阶级路线,认为中央标准复杂难算,有利于富农从中捣鬼。由此可见,双方都认为自己坚守着阶级路线,对方的标准反而实际上有利于阶级敌人。
学术界一直认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土地政策上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但我们揆诸史实,却惊人地发现,此时毛泽东等地方领导人不同意中央的指示,并不是认为中央的做法太过火,不应该打击富农;恰恰相反,地方反对中央的理由是中央的做法会有利于富农,自己的做法才能真正实现阶级路线。换言之,如果我们按学术界之前公认的看法,认为中共中央的标准“左”倾,那么毛泽东等人当时其实是认为中央的标准“形左实右”,自己的标准才更能实现中央的目标。照此推论,我们反而会得出毛泽东等人自认为比中共中央更“左”倾的结论!这种结论很明显是荒谬的,也由此反映出仅以路线斗争难以概括当时土地革命的复杂历史。
反之,我们抛开路线之争,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中共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都从革命理念出发,希望进行土地革命来达到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明确阶级路线的目的,但双方因立场不同,各有偏重。地方领导人从地方的实际出发,更注重群众动员与发展生产,认为阶级路线当然要坚持(比如劳动力标准有利于富农而被否定,通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防止富农偷取革命果实),但要因地制宜;而中央从革命的理论出发,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更注重贯彻阶级路线,且认为贯彻阶级路线本身就可以更好地动员群众和发展生产,因此双方对分配标准产生争论。再者,中央与地方之间还有一个权力统属关系,在中央对地方控制不力的时候,地方自行其是,会对中央的权威形成冲击,这是中央和地方产生冲突的根源。正因如此,双发才会通过中央局进行角力。而最后《土地法》的颁布,则最终显示了中央的权威,地方开始接受中央的控制。
综上,中央与地方在土地政策上没有路线分歧,反而存在很大的一致性。正如相关研究所表明,苏区时期中共的反富农政策有其逻辑自洽之处。(50)孙启正:《苏区时期中共“反富农”问题的逻辑分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中央以反富农的名义提出混合的分配标准,而地方也以反富农的名义反对混合标准,尽管双方对混合标准的态度相反,但他们使用的竟然是同一套话语逻辑!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党内的论争,使用的是同一套话语体系(苏联传入的马列主义),中央与地方都在用这一话语体系论证自己的正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尚处于萌芽之中。中共如何在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并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对主义进行发展和创造,则是革命史研究中亟需进一步探索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