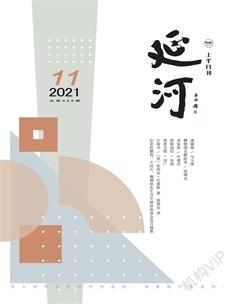一些积雪的证明
王悦
谁的长河落日圆
谁在旷野中呼喊先灵的讯息
谁在颀长的风中找寻悉存之安慰
谁又在雕花门槛外洒下桑椹籽一串
染红了遥远天边的长河落日圆
你在葡萄架的阴凉里安心休憩
你在大丽花的嫣嫣笑靥里
你在南疆金色的光线之外
塑造一轮孤独的长河落日圆
我在工业风小镇中看到电影的质感
我在空旷的烈阳里抚摸泥土的柔软
我在漫天飞舞的棉花絮雨中感受
在疾驰的公路里找寻到
这一片心中的长河落日圆
南疆即景
太阳落下山去,也就是个把分钟的事情
高速公路上,沥青路上裂缝的胶条
如一条条金色的蛇
融进远处蜿蜒的焦点
或许,它们本来就是蛇
弯弯曲曲的金色蛇皮
吐着信子
提醒着公路被太阳施暴的行径
太阳很快就不见了圆润
路旁的白杨树,是新疆公路的护卫队
他们的叶子几乎快要落尽
仅留的顶端,是稀落的红色黄色绿色
仿佛天然的交通指示旗
指引着我们前行
至胡杨林粗犷的更深处
太阳马上要落下去了
也许,山的轮廓要比山本身神秘
胡杨林要比胡杨树本身美丽
金色是南疆的行程码
走到哪里,都需要打开它
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山去
沙雁洲邊的木椅,又将重新凝视湖心
我们也将回归,成为城市中渺小的那一个
慕士塔格峰
我曾一百次幻想 冰山上的来客
携来肃穆几缕,在梦的尽头微笑
骑着马匹的哈萨克族少年,挽着棕马
站在我眼神希冀的最中央
当我们驱车,从喀什的广场
从毛主席扬起的巨袖之下
途径凛冽的帕米尔之风
五个小时后,目睹这传说中的冰山之父
——慕士塔格峰
在卡拉库里湖的水光中
我终接受神秘的山的神父予我的洗礼
这是一种多么心照不宣的聚合
山峰平仄成韵律的舒缓
连呼吸都变成了亵渎
而这一次,我就成了
冰山上的来客
塔克拉克:冬日掠影
云在天空里漂浮了很久
一丝一片盖过日光
因为有雪的凝结
——云便不再像夏日那样绵软
冬日之水仍在河床里奔流
冰柱周遭流动着寒冬掩盖不了的灵动
莽原中布满,化不了的沙棘草
枯芒指向,亿万年前的冰川断崖
每个人的心中都拥有一片大雪
拥有一座温暖透明的屋子
一拉开窗帘就是雪山和马儿
一打开房门就是皑皑的白雪
打馕人
打馕人的火炉
融汇成饥肠辘辘的烈火迷宫
打馕人的窗棂
落满了所有的人间烟火气息
打馕人的笑容
荡动起仅有的冬日暖阳之光
一些关于积雪的证明
来自远山的呐喊
从积雪的托木尔而起
雪水流淌进神秘的峡谷
追逐峡谷最深处的沙石
这些或方或圆的自然物
完成千百年来的沉淀
毫无顾忌地说起一只
在夜间星光下奔走的狼狗
撕扯着北风的凛冽
你可知这名为托木尔的山峰
为你挡下了多少来自西伯利亚的
刺骨之寒
为你流下了多少澄净凝滑的
孤独的泪
那托木尔峰顶端的雪
便是最好的证明
敬畏,再见
我对着雨滴落下的秋夜
看到昏暗灯光中半黄半绿的树叶
像穿着香妃服、画着精致妆容
迎接游客的景区艺人
目光闪烁
我也多么想要
拥有一座土台阶上筑建的坚固小屋
门扉半掩,帘子半垂
从外面只看得见旋转而上的楼梯
门口嵌着我最喜欢的花砖
雪山,离得越来越近
却仍然触摸不到
我自知,还不是那个可以触碰雪山的人
只触得到些许的牛头羊角
就已足够
敬畏,再见
窗外事
这一年
相同的铁轨载着不一样的风景
油菜花早已拂去金黄
剩下混入草原的沉默
云总是庇佑着山峦
和稀稀拉拉的树持有对高原的默认权
也许世间接近幸福的事物有很多
比如在铁桥上看涨潮的黄河水
比如在梦里拍下不可思议的风景
更比如眼前的一片飞奔的绿
比起那些背上涂着红色蓝色的羊群
山丹马场下,那些驰骋的马
和肆意躺在小海子旁边的牦牛
是幸福的
起伏的山峦背后,也许没有云了
高铁飞速,早就没有人看风景了
只有我和他追寻着那一点好看的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