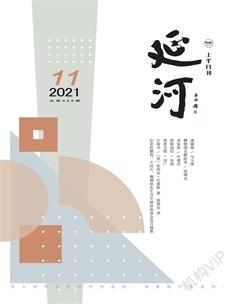勇者无惧
刘广
一
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高足当中,跟随孔子时间最长的是子路,受孔子批评最多的是子路,跟孔子私人感情最深的也是子路,《论语》中记载事迹最多的是子路(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统计是47次),在孔子有生之年卷入政治斗争死于非命的还是子路。很多人会因为孔子的批评和悲剧性结局轻视子路,从而忽略了子路的优点,可以说,子路以一生的努力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并实践着孔子的理想,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血气之勇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已经触碰到了个人先天习气构织的“天花板”,也就是他的命运。甚至,连他所犯的错误,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子路名仲由,子路是他的字,又称为季路,是鲁邑卞人,卞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搏虎勇士卞庄子的故乡,大概此地民风尚勇。子路受乡风民俗熏染,性情粗鄙,推崇勇力,志性高直。如果不是主动招惹孔子,他大约会成为一个“公侯干城”的“赳赳武夫”。戏剧发生的时候孔子三十岁左右,已经立下恢复东周的大志,他设立私学,招收弟子教授“六艺”之学,并且已经小有名气,连执政孟僖子也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过来学习礼制。孔子兴办私学,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对旧有价值惯性系的调整,必然要引起大的反动。
与大部分人一样,子路不能理解认同这一与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同的新鲜事物,而且他比孔子小九岁,正值二十出头,年轻气盛,于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教育”一下孔子。他戴着雄鸡羽毛做的帽子,佩着野猪皮装饰的刀,企图凭借勇力欺凌孔子。
这是一出异常精彩的师徒“相认”大戏,在紧张的冲突中,双方认识了对方。独具慧眼的孔子从这个陵暴自己的青年身上不仅看到了野蛮的勇猛,还看到了这野蛮蒙昧中的高远大志,他决定驯服这个年轻人。子路以士的身位为荣,但孔子为他指出了一个更高的可能——成为君子,一个值得用一生去努力的目标。子路敏锐地发现了此前他所信仰的勇武义气的“无力”,从孔子身上看到了能使自己身上狂暴的力量安静下来的力量。于是子路脱掉武人的衣装,换上儒士之服,献上礼物,通过门人介绍请求做孔子的弟子,成为了孔门实至名归的“大师兄”,忠心耿耿追随孔子一生。从这出好戏,我们既可以看到老师的好,也能发现学生的好。
二
投身孔門之后,子路非常勇猛精进。“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子路听闻了一个做人处事的道理,如果还没有付诸实践,就怕听闻了另一道理了来不及实施这一道理。孔子所说的“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大约指的就是子路、颜渊。这就是求道者的大勇。这种求知若渴、见贤思齐的状态是一个发愿求道者必备的心理状态。《颜渊》篇又说:“子路无宿诺”,子路应允的事情,会马上去做,绝不拖延到第二天。“朝闻道,夕死可矣。”但闻道自然是越早越好。子路的勇猛精进在孔门弟子中罕有人匹敌。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在这则著名的对话中,对于刚勇进取的子路,孔子是抑制的;对于逊顺柔弱的冉有,孔子是鼓励的。上面所说子路的种种才能风格皆源于他的先天禀赋,源于“血气之勇”。血气半是先天半是后天,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发现学生先天的才气禀赋,并将其善的地方引导激发出来,同时消除化解先天秉性中粗陋鄙薄的东西。孔子发现了子路性格中的勇敢正直、旷达忠诚,引导他成为匡正时运的股肱之士。子路之得在其乾阳之锐气,子路之失亦在此,阳极则有“亢龙有悔”之忧。孔子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通过教授上古典章礼乐消减调和子路性情中的粗鄙狂佞之气。孔子遵循每个学生的天性特点诱导他走向自我修持的大道,同时用典章文献开拓视野,增进智慧,用礼仪规范模塑举止言行。在一阴一阳、一收一放之间,达到身心的平衡,从而实现教育的目的。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
古人重祭祀,通过祭祀神灵、祖先连接天人,也获得了自己存在的独特“确证”,祭祀可以看作是古人探索精神不朽的努力。不是自己宗族的神灵、祖先却也去祭祀它,是要祈求非分之福,那就是淫祀,是谄媚。义者,宜也,是一个人在仁智熏染下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能做他应该做的,那他是缺乏勇气。谄非崇拜,更非信仰。行义即大勇。这句话,有可能是孔子针对子路说的,既是表扬子路见善思齐之勇,也是勉励他要化血气之勇为仁智之勇,见义勇为。因义而称勇,后世有义勇军,我们的国歌名称亦源于这个遥远的典故。
三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
子路是著名的“孔门十哲”之一,与冉有并为“政事”课的佼佼者。“由也果,求也艺”,孔子评价二人“可谓具臣矣”,可以称为做具体事务的股肱之臣。子路刚勇果决,见善思齐,有志于匡扶纲纪。因此他的兴趣主要在从政,所以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为政者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为百姓福祉辛苦操劳。”这是孔子的为政观,子路是熟悉的也是认同的,他想了解更深一层的教诲。孔子补充说:“要没有倦怠之意。”为政多是事务性的工作,枯燥乏味,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之情,子路性急鲁莽,更容易犯此毛病。孔子的回答看似简单,其实针对的是子路的病根。需要指出的是,子路、冉有虽然都是优秀的政治家,但他们为政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子路更像往古的为政者,以个人的德行带动感化百姓。而“求也艺”,冉有更像后世的“技术官僚”,善于利用先进的社会治理技能,而对于其中的道德风险是不考虑的。冉有后来利用自己在财务税收方面的技能为季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孔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
子路问怎样可以称为“士”,孔子回答,互相监督勉励,和谐融洽,就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监督勉励,兄弟之间和谐融洽。这也是对子路刚强气质的纠正。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
子路从政之后,问服务君主之道。孔子回答,不要欺骗君主,但是可以冒犯他,在大是大非上据理力争。可见,孔子绝非后代很多人想象的绝对服从君主的愚忠者,反之,他主张从事政治必须坚持原则的。在《先进》篇中,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孔子回答:“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孔子回答,所谓大臣就是要以大道为原则侍奉君主,如果不能施行就停止不做。子路和冉有可以算作具有才干的办事之臣。季子然没有完全理解孔子的话,又追问:“他们可以算绝对服从主上的人了吧?”孔子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涉及杀父弑君这样的大非,他们是断然不会跟从的。”“以道事君”是孔子的一大主张,也是孔门儒士有别于战国毫无底线“朝秦暮楚”之游士的最大特征。
四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子路问如何成为君子。孔子回答要以恭敬严肃的态度进行自我修行、完善自我。前面子路所问为政与事君,都可以看作“士”的职责所在,君子在士之中,在上古的一些时代,还在王之中。但他的身位在士之上。与士侧重事功不同,君子更关注的是自我的修养,是“学而时习之”,是“认识你自己”。恭敬严肃出于对外部世界与个人心志的双重尊重,是自我修养过程中基本的心理状态。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作为一个人,我們所拥有的智力刚好只够我们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我们的智力是何等的不足。”这是修己以敬是一个修行者的“终身大事”,子路却感觉有所不尽,于是进一步追问做到如此了还要如何。孔子回答,完善自我进而安抚周围乡党之人。子路又追问做到如此了还要如何。孔子回答,完善自我进而安抚天下百姓。尧舜于此天下大同,都感到力不从心。修身是平治天下的基础,这是孔子为子路绘制的进阶路线,《大学》将其扩展为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子路仍不满足,问孔子什么是“成人”。“成人”就是完备之人,就是完人。这一提问也显示了子路的勃勃“野心”。人总是一个有局限的存在,如何准确定义理想中的“完人”呢?只能用譬喻。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每次回答都是“能近取譬”,针对问者当时当地的状态给予最准确的回复;这个回答是针对子路的,对于其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四个人都是近世或当代人,有子路景仰效仿的乡贤,甚至还有子路的同门师兄弟,亲切可近。这个回答有赞许,有鼓励,也有期许。但这“成人”太完美也实不易得,于是孔子退而求其次,给出了一个切实可得的“简配”版本:当今的“完人”也未必如此,看见利就能想到以义取,在危急时刻为了维护理想原则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虽就在贫困穷迫之中却不违背自己平生所信仰的理想,也可以称之为“完人”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与“高配”版相比,这个版本少了智慧和礼乐,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忠勇之“质”,虽然礼乐之“文”未备,也算是初步的“成人”了。这可以视作孔子对子路的大赞扬。
五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路有一次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还没有好好侍奉人,哪里能好好侍奉鬼神呢?”侍奉鬼神、祭祀祖先是古代人的一件大事,因为它关涉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就是“我是谁”的问题。人在生活变化之中,往往会通过确认祖先、神祇的方式确认自己生活价值的边界与方位。孔子并不反对祭祀祖先神明,但更赞赏周代以来重人事敬鬼神的风气。谈到鬼神,自然不能不谈到死亡,人们往往通过死来界定生。一个人如果严肃认真思考过死亡,他的人生跟以前相比也许就不一样了。孔子的回答是:“还没有知晓生,哪里能知晓死呢?”他的意思是,不仅要用死来界定生,更要以生来界定死,理解死;以可知探索未知,而非以未知揣测已知,这是孔子的大智慧。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子罕》)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
有一次孔子生重病情势十分危急,子路安排后事,让门人充当送终治丧的近臣。过了一段时间,孔子病情转缓,发现了这件事,严厉斥责子路。面对死亡时的表现是一个人识解修养的集中展现。孔子在生死一线关注的并非丧葬的仪式问题,而是绝对真诚的德行问题。不欺天是对人生的大检点,也是对此生此身的大尊敬,用现代人的言语表达就是我要真诚面对我的人生。面对死亡仍然保持这种审慎与真诚,体现了孔子的大修持。
虽然做得不妥当。但子路对孔子是绝对忠诚的。在孔子病重的时候,子路还进行祈祷,向上天列举孔子的德行功绩祈求上天降福免厄。孔子病情好转后问子路有没有这件事,子路老实回答有的,祈祷的诔词是“向天神地祇为你祈祷”。孔子说:“这样说来,我的祈祷由来已久。”对于古典修行者来说,祈祷与自省是同义词,修行者的自我反省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他寻求的不是福报,是自我的完善;自我修持完善就是对上天的祈祷,他的行为就是对天道的遵从展示,他的言辞就是对上天的誓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无需另外的祈祷。对此子路和很多人并不了解。孔子的这种鬼神和生死观并无半点神秘色彩,更不会将人引向宗教崇拜,他注重的是“下学而上达”,通过个人的努力理解天人之际,因而他不是教主,而是一个修行者。这也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的铸造,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注重现世生活,绝少宗教信仰的民族。
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先进》)
一天,几个高足陪孔子坐着聊天,老先生很高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诚为人生一大乐事,于是老师想来一次“随堂测试”。在轻松的环境下,人往往能够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子路天性争强好胜,又是大师兄,马上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他尚勇,要培养百姓勇敢之气,加强国防建设,摆脱超级大国的侵扰,实现自主自强。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道德教化,提高百姓的整体素质,这是子路与战国策士不同的地方。对于子路的言行,孔子是报以批评的微笑。孔子并不怀疑子路的能力和发心,他批评的是子路行事的态度——在日常举止之间如果不能遵从礼让,为政理国也难以此为凭据,修身乃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另外一次是颜渊和子路侍奉孔子身边,一个是孔子最心仪的学生,一个是孔子最亲近的弟子。孔子说,何不谈谈你们各自的志向呢?子路又率先回答说:“希望跟朋友们共享车马衣饰,即使用坏了也没有遗憾。”颜渊则回答:“希望不自夸其善,不自夸其功。”子路豪爽大气,有政治家的胸襟;颜渊矜持自省,有修行者的气度。一个外向,一个内敛;一个重“仁”,一个重“义”;一个侧重“外王”,一个侧重“内圣”。对话展示了孔门弟子不同的价值取向。从持气取义的角度讲,孟子与子路的确有相似之处,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其“私淑弟子”。
在孔子的调养和自身努力下,子路在为政方面的才能很快就展现出来,后来被尊为“孔门十哲”之一,与冉有同为“孔门四科”之政事科的代表。据说他曾经两次担任鲁国执政季氏的大管家,晚年还在衛国任职。孔子对子路也多有称赞:“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仅仅凭借只言片语就可以判断孰曲孰直,也只有子路具有如此才能吧。片言折狱,一靠的是过人的判断力,二靠的是公正之心。
七
子曰:“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
孔子称赞子路说,能够身穿破旧的衣服与穿着豪奢的达官贵人平等交流而丝毫不感到不自在的,大约只有子路了。子路追求的并非物质享受与官阶名位,所以对此并不在意,且不认为自己比“肉食者”卑鄙粗陋,故能平等视之而无羞赧之色。在中西古典时代,智识阶层存在着一种由来已久的“价值自信”——凭借自身的节操志向与才华,可以与君王并驾齐驱甚至睥睨王侯,“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出自《诗经·邶风·雄雉》,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好呢?对老师的称赞,子路非常受用,终身咏诵这两句诗,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对此,孔子不以为意,说这本就是做人的一个普通道理,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在鼓励之余,孔子还要对子路进行鞭策,“不忮不求”与“贫而无谄”一样,可能源于人的消极的自尊乃至怨望,还属于士和君子节操保守消极的一面,要成为君子,还要化阴为阳,从消极保守走向积极进取。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
“用之则行”就是直,“舍之则藏”就是“衣褐怀宝”,也就是《易经》的“退藏于密”,也就是孔子之“卷”。这时在一旁的大师兄子路听了有些不服气,但也知道心性之修养不及小师弟,就拿自己擅长的说事儿。他本想也让孔子夸奖一下自己,没想到遭到一顿痛批:“徒手搏虎,徒身涉河,死了也不知后悔的人,我不与他同行。定要临事小心,审慎谋划再做决定的人,我才与他共事。”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可谓子路的写照。他勇力好义,是条响当当的汉子,但心性粗野率直,尚勇而轻学,执“直”而不知“卷”。“直”是德行之基,但如果只知道“直”乃至执着于“直”,是远远不够的,人心、人世还有很多不直的地方。了解、理解乃至利用这种“不直”而坚持砥砺自己的“直”,是有志于世者必然的选择。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
子路尚勇,所以问君子是否尚勇,以期获得老师的赞许。勇敢是成为仁者自然也是君子的必要条件,仁爱却非成为勇者的必要条件,因为靠血气、信仰、名利甚至恐惧的推动都可以使一个人勇敢乃至轻死忘身。对于子路的小算盘,孔子是清楚的,他没有肯定,免得子路骄傲,而是给他讲君子之勇与庶众之勇的根本不同。君子之勇以义为依据。义者,宜也,在坚持大道的原则下做最适宜的事情,所以“道”“义”常常连言。君子如果只讲勇敢而不讲道义底线,只能沦为作乱的贼子;普通人往往只讲勇敢不讲道义底线,或者仅仅把果敢看作道义当成美德,则会变成打家劫舍的盗贼或者戕害无辜的帮凶。问题是小人也讲“义”,黑社会也拜关二爷,如何区别小人之“义”与君子之“义”而不为外物所惑是孔子留给子路的一个大大的思考题。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
音乐是心绪和情志的体现,君子之音应温柔中和。礼以节人,乐以发和。音乐是心志乃至生命韵律的体现,子路鼓瑟,据说有“北鄙杀伐之音”,因而老师不满意了,门人因此有些不尊敬大师兄了,孔子只能再出来打个比方纠正:“子路已经登上大道之正堂,但还没有进入深微之内室。”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先进》)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
心性的差异自然反映在气质上。孔门高足子羔憨直,曾参朴钝,子张偏执,子路粗鲁。闵子骞陪侍孔子的时候,说话和悦明辨是非;子路陪侍的时候,刚强不饶;冉有、子贡则是和乐从容。弟子各尽其性,斐然成章,孔子很开心,但也有一丝担忧,子路刚强不折,在乱世恐怕难以尽其天年。子路最后死于卫乱不得寿终正寝,逐本溯源还是因为他强直好义的秉性,但也与其轻视学习有直接关系。
八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子路做季氏的管家,推荐师弟高柴(字子羔)做季氏的封邑费的长官。孔子对这件事却是反对的:“你这是害了人家孩子啊!”當时子羔只有二十岁左右,刚到孔子门下,还没有系统深入地学习为政之道,而且二十岁的青年,人生的经验还不丰富,更不用说为政的经验了。这样的人为政,即害人又害己,所以孔子说:“贼夫人之子。”孔子的意思子路是明白的,但自己一片好心却被老师斥责,心里总有些不爽,狡辩了几句。对此,孔子勃然大怒。“正如你这样,所以我厌恶那些佞人啊!”明知自己不对,却不承认错误还要巧言辩解甚至无理取闹就是“佞”。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则名言,谈论的是认知与智慧及德行的关系。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这种诚实的态度本身就是智慧。子路强直多佞,强不知以为知,所以孔子以此训诫之。这也反映了孔子的认识论——通过确定自己知道的,界定自己不知道的,从而明晰认知的边界;不仅要知道自己的“知”,更要了解自己的“不知”,知其无知才是真正的智慧。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谓“自知其无知”。这是伟大的谦虚,也是伟大的真诚。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对于子路轻视学习的倾向,孔子也是屡次进行教育纠正。孔子用“六蔽”指出了不学习的弊端,语气的强烈是《论语》中少见的。所谓“蔽”就是遮蔽,因为人是有局限的存在,在认识世界的整全时必然如盲人摸象力有不逮,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的关于“洞穴”的隐喻。
九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
孔子致力恢复东周之文明礼制,却到处碰壁,虽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内心偶尔也会溢出悲怆之感,这个悲怆伤感或者牢骚是人之常情,也是对孔子勇猛精进的一个保护,但这里面没有怨恨,“不怨天,不尤人”是孔子的伟大特质。孔子为什么要去海外,因为按照当时的天下观,夏商周三代的核心区域称为“中国”或者“华夏”,文明辐射到的蛮夷民族区域称为“四海”。孔子要到当前国家秩序影响不到的地带开创一片新天地,能够跟随孔子的大约只有勇猛忠诚的子路。这也是对子路的大赞扬。子路听到后自然很开心,但孔子又当头一盆冷水:“子路好勇超过我,但对于言辞行为却缺乏裁决判断。”孔子讲乘桴浮于海,乃是一时负面情绪之释放,并非真要逃世,因为无所逃遁。《庄子·人间世》说得很清楚:“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子之爱亲”是基于先天血缘,是生物性的,是“命”;“臣之君”是基于统治秩序,是政治性的,是“义”,有人的地方就有尊卑贵贱,就有秩序,所以“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孔子当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只是发发牢骚宣泄一下而已,子路却当真了,这是子路的可爱,也是子路的幼稚。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子路的意思,管仲这样的怕死鬼加叛徒怎么算得上杀身成义的志士呢。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说桓公将诸侯联合起来尊王攘夷,而且不是靠了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一旁的子贡对此也有些不理解,孔子解释说,管仲辅佐桓公成为诸侯的领袖,结束了华夏散乱败落的局面,现在我们都在享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沦为无君臣父子之别、披散着头发在左边系扣子的蛮夷之人。正是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不服从周天子权威的势力,提高了周天子的威信,避免了从春秋到战国的迅速滑落;同时击退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的进攻袭扰,防止了西周东迁这样历史悲剧的发生。因而齐桓公和管仲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是有大贡献的。正是遇到了齐桓公,管仲才看到了一个创造历史、造福苍生的机会,所以他放弃匹夫匹妇的小忠小信,成就利国利民的大仁大义。管仲所做的,正是孔子所想做的,所以孔子反复许其仁。
十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不能理解历史,也很难把握当下。鲁定公九年前后,季桓子的大管家公山弗扰掌握了实权,牢牢控制了季氏的封邑费,将主人架空,如同三桓架空鲁君一样。在古人看来,虽然没有公开造反,这已经等同于叛乱。公山弗扰知道孔子的大名,要召孔子为其所用,孔子心动想要去。这时候大弟子子路不高兴了,公开反对。孔子解释自己的动机:“召我的人难道是白白召我去吗?应该是要委以重任。如果能任用我,我就要借此恢复东周之制。”这一年正是孔子五十知天命之时,他兴办私学,在鲁国的名气越来越大,鲁国的权臣阳货等人想要笼络他为己所用。孔子厚积数十载正准备出来纠正时弊,在东方恢复西周文王周公之礼制文化。当然最终他也没有应阳货和公山弗扰之召。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孔子在鲁国主持改革失败后周游列国,担任过季氏大管家的子路也毅然跟随老师共赴艰难。后来晋国执政赵简子攻打大夫范氏,范氏的家臣佛肸在中牟叛乱,也召孔子去。孔子又做出心动想去的姿态。这下子路急了,他用孔子的话来教育孔子。孔子回答:“对的,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是还有这样的话吗,不是说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吗?我难道是葫芦吗,怎么能只是悬挂在那里不被食用呢?”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不会放弃他的节操趋于下流,这是孔子的自信。晋为周之宗亲,巍巍一大国,也许还有变晋为周的可能。据说孔子还真的去了,只不过走到晋国边境的黄河边上,听说赵简子杀了鸣犊、舜华两位贤人,他十分感慨又返回了卫国。从这一事件来看,子路的判断还是十分准确的。他不仅是孔子的首徒,有时候还是孔子的“诤友”。在孔子三千弟子中,只有子路敢公开规劝甚至指责他的言行。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如果说前面只是规劝,那这次子路真有些让孔子难堪了。孔子的名气很大,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也想见一见这位名人,这让孔子也很为难,在推辞了几次,最后还是不得已与其见面了。对这次会见,疾恶如仇的子路极不高兴,不顾及老师颜面当众说了一些狠话,以至于逼得孔子为此发誓。以他跟随孔子二十几年对孔子的了解和判断,他并不怀疑老师与南子之间有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而是批评老师这样做太不爱惜羽毛了,会惹心性不是那么高尚的人做不好的猜测。事实证明,孔子和子路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几千年来,一直有人拿这件事情攻击诋毁孔子。在古代,发誓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用古希腊哲人的话说,誓言是对自己的诅咒。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子路的鲁莽急躁乃至可爱,也可以看出他与孔子关系的亲昵程度,他从公共学习领域进入私人生活领域,从不同角度体会孔子的为学为人之道,甚至在很多时候扮演着孔子言行“纠察者”的角色。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叶公名诸梁,是楚国的股肱之臣,听闻了孔子的大名,就向子路打听,结果子路没有回答他。子路不回答有多层考虑,但不答总归是失礼示弱的表现,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你这么不这样回答他,我老师一贯的为人是读书修行发奋努力以致忘记吃饭,欢悦起来忘记了忧愁,都不知道时间流逝自己即将老去。” 孔子对自己的描述,是一个永远努力、永远精进因而也永远年轻的学习者的形象。人终究可以通过学习修行与现实的政治共同体甚至与时间抗衡。不知后来叶公有没有听说孔子的这一宣言并理解他,估计是没有。因为孔子并没有到楚国去,后人还编排了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自称喜好龙,等真的龙(孔子)现身了,他却不知所措了。
十一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在随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子路也遇到了一些隐逸之士。所谓隐逸之士,并非一般人认为的隐居在深山老林荒无人烟地方的人,而是将自己非凡的才能、识解隐藏起来,不让外人知晓,或者逃遁到现存政治秩序的影响区域之外,从而专心于自我心性趣味的修养。由于人的心性喜好不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也不同,因此隐士永遠存在。
有一次师徒一行要渡河,不知道津渡在什么地方,孔子看到长沮、桀溺在田里并排耕地,就让子路去打听在何处渡河。长沮没有回答子路的问题,而是问车上执舆而立的是谁。因为他已经远远看到这个人气度不凡,可见其眼光之老辣。子路回答,是孔丘。进一步确认,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回答,正是。长沮说,那他正是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的人啊。此段对答,颇似后世禅宗的公案,子路问以具体的津渡在何处,长沮达以抽象的人生的津渡。现实的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困难乃至苦难,如何解决或者摆脱这些艰难苦恨走出一条通往幸福安详的路是哲人和宗教家思考的一大问题。长沮大约是道家人士,在这里将孔子比为这个时代乃至以后若干时代的“知津者”,这是对孔子的大赞扬,与仪封人将孔子誉为“木铎”有相似之处。但长沮的称赞里还隐含着讽刺——知津者不知津渡在哪里,儒者的眼光仍然有局限性。子路有点摸不到头脑,他很老实,又去问一旁的桀溺。桀溺也没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你是谁。子路回答,仲由。桀溺说,你就是那个孔丘的学生吗?可见子路的名气在当时也是比较响的。子路回答,对的。桀溺说,天下无道,如洪水泛滥,谁能改变它呢?你与其跟随逃避恶人政治之士不如跟随逃避整个世代(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政治共同体)之士呢?他一边说一边耘地,也没有告诉子路在哪里能找到渡口。
子路灰溜溜地回去见孔子,把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有些怅然地说:“鸟兽之间是很难沟通的。”道家避世,是方外之人;儒家治世,是方内之人。孔子对道家的隐逸高士是十分尊敬的,也是能理解的,孔子能理解道家的避世,但道家有时候不能理解孔子或者儒家的汲汲于世事,觉得他们太笨了,太辛苦了,太可怜了,在试图做一件注定不能成功的事情。道家的宗主老子与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人性有善有恶的。这与同时代的柏拉图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柏拉图说,人性中有狮子,有九头怪,也有“人性中的人”。道家与儒家不同的一点是,道家对人性的看法稍微偏悲观一些,更多看到的是“狮子”和“九头怪”,认为普通大众蒙昧愚顽,难以教育改变,更倾向于独善其身。孔子更看重“人性中的人”,希望通过教育唤醒它。孔子回答,我不与这些人(指普通百姓)在一起还能与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有道的话,我哪里还会出来奔波辛劳呢。孔子当然理解普通大众的品行次第,也想与道家的隐逸之士一样与朋友弟子在水边高台吹吹风,聊聊天。但谁来教育大众呢?他不满于“自度”还要“度人”,还要返回来帮一下水深火热中的苍生,也就是要“普度众生”。这个返回,显示了孔子和儒家的热道衷肠,显示了孔子和儒家的大慈悲。所以达摩在东渡前说:“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但长沮、桀溺的话并非没有道理,所以孔子有怅然若失之情。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子路有一次跟随孔子出行,落在了后面,遇到一位老人家,感觉这位老人家出言不凡,就很恭敬地拱手站立在一旁。老人家看子路恭敬有礼,就留他住宿,还杀鸡做米饭招待他,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一行并将情况告诉了老师,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啊。他让子路返回再见一见这位老人家,大约是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等子路回去,老人家已经出行不在了。可能是老人家料到孔子会遣子路回来故意躲开不见,让这股能量能够更持久的影响教育孔子师徒。
虽然没有遇到老人家,但子路还是说了一席话。这段话可以看作儒士对隐士的反击:“不出仕为政为民是不道义的。长幼孝悌的礼节是不能废除的,君臣之间的道义怎么能废除呢?只想要洁身自好,却违背了人伦大道。君子从政,就是要行道义,即使早已经知道大道不能实行。”儒家是出世的,他们面对问题不是逃避,而是想办法解决。他们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关系,一是建立在政治秩序上的君臣关系,这两种关系覆盖所有人。在儒家看来,隐逸之士只想洁身自好,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和改善社会与人群的努力,是违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公理,更像无父无君的禽兽。当然,这也是一种傲慢。孔子和子路当然知道恢复东周、建立大同的理想已经不可能实现,历史正从春秋滑向战国进而滑向帝国,但他们仍然要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进行挽回,这也是儒家最可贵的地方。
十二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卫灵公》)
虽然子路豪言:“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残酷的现实面前还是有过一丝动摇。孔子师徒一行在卫、宋、陈、蔡等国游历,却屡屡碰壁。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楚国攻打陈国,他们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断了炊烟。因为多日没有吃的,跟随的人饥困交加,以至于几乎无力站立了。这时候大师兄面带怒色来见孔子,据说这个时候孔子正在彈琴。他问了一个被无数代人反复提问思考的一个问题:“君子也有穷困潦倒的时候吗?”(这个问题也可以简化为更为大众熟知的问题:“好人必然要受苦吗?”)以他跟随孔子几十年的学识经验、所见所闻,当然知道君子大几率是会穷困潦倒的,他跟随他的老师已经多次经历体味了“别是人间行路难”。
但这次情势是如此危急严重,以至于“不忮不求”的子路都对原来的信念产生了一丝动摇,他悲愤的不是自己的饥困潦倒,而是连他最尊敬的老师都要面临生死之考验,都要被他平日最轻视的物质资料所折磨。对于很多人来说,世间最大的悲剧不是恶人享福,而是好人受难。“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是大众的普遍愿望,是理想状态,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好人未必有好报,恶人也未必有恶报,所以人们才生出此一强烈愿望。如果我们把愿望当作现实,难免要受挫沮丧。在日常生活中,德行低劣之人较少法律、良知的束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从而可以掌控利用更多的资源,往往可能比较容易“富贵”乃至“寿延”。与此相反,好人往往更容易碰壁潦倒。
孔子给因绝望而愤怒的大弟子泼了一盆冷水,指出了世间一大真相——君子本来就安于贫困,普通人甚至很多读书人贫困潦倒了就会放弃操守原则随波逐流。对于孔子和古典哲人们来说,终极的目标是改造自我而非外部世界,他们倾向于独立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其价值评价体系。“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社会常态。大众期冀得好报就是希望有利益交换,实质上是商业行为,得之也如梁武帝“全无功德”;失之则怨天尤人,好人不得好报返身做坏人的也比比皆是。但对于孔子来说,做好人是自我的内在需求或者说追求,没有目的。也可以说,德行高尚的人致力于一个伟大的目标并非是籍此为自己谋福利图回报,相反而是为其贡献牺牲。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好人就是上天对自我最好的奖励。任何追问其原因的提问都是“不合法”的。做好人就是为了做好人,并非其他,更不是为了得好报。可以说,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好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并不需要在此生、此身之外再寻一个来世或者天堂。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孔子刚到卫国的时候,卫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灵公的太子蒯聩看到南子弄权,所以计划除掉她,失败逃亡到了晋国。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卫灵公去世了,卫国立太子蒯聩之子辄,即卫出公,赵简子则派人护送蒯聩回国,卫出公拒绝让位,联合齐国派兵把他父亲围困在戚邑。新君继位,自然要任用新人。子路跑来问老师:“如果卫君让您来主政,您先从何事入手呢?”子路的这一问首先就有问题,不问老师愿不愿意蹚这个浑水,就来个预设。孔子不理会子路的冒失,回答:“首先应该正名。”“正名”就是根据道义遵循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辨析去除围绕在事物本质周围的各种浮词虚言乃至大话谎言,还事物的本来面目。孔子一句话点破了卫国局势症结所在:卫国自灵公以来,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卫国为政之要,确在先正卫辄与蒯聩父子之名。子路知道孔子所指为何,心里热腾腾的愿望被老师一盆凉水浇透了总是很难受,于是又忍不住顶嘴引来孔子一顿大骂。孔子“正名”的观念在战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专门的“名家”,研究名实逻辑之辨。子路不好学,未能深入理解名实之辩,又急仁好义、勇猛刚劲、爱惜名节,很容易被各种打着诸如“仁义道德”之类大旗的宏大叙事所吸引、裹挟,献祭自己的性命。这是孔子的担忧,很不幸,这也是子路的宿命。
十三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乡党》)
孔子无时无刻不在教育、纠正子路。在远游的路上,师徒看到路边有彩色羽毛的雉鸡在飞翔,然后看到孔子诸人无伤害之意就慢慢落下来聚集在一起。孔子不禁感慨:“那山梁上的雉鸡啊,它们知道审时度势啊。”子路看到老师赞赏,就拿了一些吃的喂雉鸡,雉鸡小心地嗅了几次才吃掉。孔子被孟子称为“圣之时者”,知时之圣人遇到知时之生灵,难免不有所感慨。所谓知时,就是知时代运行的节奏,也就是“知命”。孔子的感慨,或许也包含着对子路委婉的教诲。子路可能对此有所感应,所以上前供养雉鸡。但老师的深意,他懂了吗?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
所以,孔子抒发了自己的大感慨:可以与他一起学习切磋,却未必可以与他共同向道;可以与他共同向道,却未必可以与他强立不变(所谓“立”大约相类与《学记》的“强立而不反”的“立”,也就是孔子“三十而立”的“立”);可以与他强立不变,却未必可以与他权衡轻重。子路作为陪伴他时间最长的大弟子,大约是可以与他风雨同舟强立不变的。但很遗憾,却无法与他一起斟酌历史隐微处看似无关紧要却性命交关的细节。在求学问道的路上,与他一路走下去的人注定是原来越少的。这是孔子的大悲哀,也是子路的大遗憾。因为有些东西,终究是老师无法教会的。这是教育的局限,孔子也无可奈何。
十四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
子路有一次外出办事,晚上投宿在鲁国的城墙外门。负责早上开启城门的官吏问:“您从哪里来?”子路回答:“从孔老先生那里来。”晨门回答:“难道就是那个明明知道不可做却一定要去找的人吗?”这位晨门大约也是一位隐者,隐身为从事具体事务的小吏。他的话里面有赞叹,有感慨。“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孔子非常精妙的评价。但是在孔子看来,自己一生所为,皆是可为之事。隐逸之士,对于孔子的汲汲于世事,终归有一些偏见。“知其不可而为之”,逆流而上,横而不流,的确是很多儒士的风范,其中就包括子路。
子路后来又回到卫国,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鲁哀公十五年,灵公的太子蒯聩与孔悝勾结,与他的党羽攻打儿子出公,在动乱刚发生的时候,子路在外面办事,听闻之后马上去赴难,正好遇到同在卫国为官的师弟子羔。子羔告诉他:“出公已经出逃了,城门也已经关闭了,你可以回去了,不要空受其祸了。”子路回答: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拿他的俸禄,就要不逃避他的苦难艰险。子羔说服不了大师兄,只好一人离开了。子路径直去找蒯聩,蒯聩和孔悝登上高台躲避。子路说:“您怎么能用孔悝这样的反复小人?请让我杀了他。”蒯聩自然不愿意,于是子路准备放火烧台子。蒯聩恐惧,于是让石乞、壶黡攻击子路,子路年事已高,已经六十三岁,抵不过二人,被击成重伤,系帽子的缨带也被击断了。子路说:“君子死而冠不免。”系上缨带死去了。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动乱,预测了两位高足的结局:“子羔会活着回来,子路则会因此而死。”听说子路死后被砍成了肉酱,孔子马上让人把肉酱盖起来,不仅不想吃了,看也不想看到了。可见师徒二人感情之深厚。
從“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到“结缨而死”,在追随孔子的一生中,子路完成了从武夫到儒士的转变,并一直在朝着君子的目标努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用君子的风范要求自己。虽然因为心性的原因,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是他努力的痕迹。他虽然有血气之勇,但却讲求以义为质,用生命践行孔子的教诲,无愧为孔门首徒。在战国两汉的著作中,子路是孔门弟子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唐玄宗尊之为“卫侯”,宋真宗加封为“河内公”,宋度宗又尊之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
责任编辑:弋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