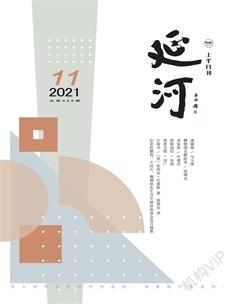美如斯
叶德庆
访千年古树群
九月的天总是高一些
深山在云的下面
一只自寻短见的青蛙
在水涧的石头下安排好自己的子女
跑到乡道上来,蹲着
挡住我的去路
耽误了几分钟
不知这只青蛙有何冤屈
千年古树群,像一群隐贤的乡绅
看我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是一个浮躁的人
刚才上山的路上遇见一位僧人
驮着一大包衣钵
我停下车,打开车窗,想搭他上山
他摆摆手,算是谢绝
刚刚经过一个叫学堂的地方
对面有一个私塾的遗址
我说这些充满灵性的字眼
很容易和千年古村树群套上近乎
千年古树群等了一千年
见面时一句话也没有说
原来,每棵树都隐身在我去的路上
山里风大
隐贤的消息来得很快
人生大别
秋分这天去大别山
可以说母语,草木皆懂
早晚凉,白天热
北边开始霜白
南边的落叶追风而去
大自然懂得轻描淡写
天高云淡
晚上月隐星疏
形单影只
大别山是个故事
河流往南北
山脉问东西
秋分这天,做一次人生大别
我去的地方是主峰白马尖
听说那里有一棵松叫矮人伞
很有意思的名字
是不是到了山顶,要
矮人一等
远走高飞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远行
鲜衣怒马,从容,且歌且行
去陈桥斟酌一二
与岁月杯酒释怀
我计划走水路,沿运河北上
天水一朝,一段宋的静好
泊瓜州,渡口有不可言传的故事
算了算,到达北方可能已经
大雪,说书人围炉讲咸平之治
好长的水路,日头升到一竿高的时候
船工换过一根长篙
一只雁从北往南
泄露了赵匡胤与赵普雪夜之后
灭南平和楚,灭后蜀、南汉、南唐三国
从南到北
经常有人问我老家是什么地方
很突兀。楚早灭了
唐、宋、元、明、清、民国
算不算故乡
没有走出运河
不算走出故乡
船头上有秋水,解绳的人
和昨晚来接我的是同一个人
何时启程,黄历上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我想天亮就走
我关注过一棵石榴树三次
邻居家贴水,灰白的墙,上覆黑瓦
一棵石榴树,半隐在墙内
半倚在河边。邻居家,极少出入
是从外地来隐居的
可能无人
我认识这棵树的时候是冬天
除了几片没有落尽的败叶
还有一两颗瘦得皮包骨的石榴
枯枝上挂满冷风,据说,是一位先生
住在里面
有朋友自远方来,划船至
石榴树下的时候,正好花开
有几朵落在水面,有人触景生情
没有人修剪蓬勃的树枝
又到秋天,石榴压弯枝头
始终没有人摘
院墙外的人也摘不到
一天一天,听着秋风
把石榴吹老
风不识字也读书
房子是有故事的,南北通透
书房在南面,窗下和阳台是
读书处,两边整墙齐的书柜
新开了一间画室,在北边
冬天画画会不会手冷
安排这些事的时候,可以
从中找到母语和词根
我站在画室,确实
秋天在北边,夕阳西下
画架温和起来,天色一边挥手
一边拉开
夜幔
在书架上摆了几把紫砂壶
几包茶叶
那些书本中的人物有一些是喜欢
喝茶的。还有围棋、象棋
一副缺子的军棋
几枚硬币
画桌上有一头牛,有所隐喻
有一尊金菩萨,尼泊尔的
一尊铜菩萨,藏传
隐于市
我经常坐在北边的椅子上
剪指甲。然后把为数不多的指甲屑
包在纸里,放一段时间
孝之始也
香炉里的灰满了,拿纸包好
找个地方,好好埋着
有时候,倚着回忆打瞌睡
发呆是另外一种睡眠状态
胡须始終在生长
风不识字也读书
遗憾的是,我打碎了一只貔貅
神兽肚子里空空的
也不知道饿了多久
生辰不详,卒于2021年9月1日
君子不器
天太高,云和雨分不清楚
雁阵借着气流南下
和我同居的一只葫芦
在屋檐下,镇邪
门牌上2-22几个舶来品
阿拉伯字
沾满灰尘
我叹了一口气,无吹灰之力
长袖善舞的草叶集
出版在春天
用秋色做了封底
如期去三秦
蜀道难,我取道青天
戒烟七年,痒啊
在火锅中加几根折断的罂粟杆
和几片完整的叶
一想到充满野性的花就上瘾
我在江南,君子不器
才子佳人,居有竹
飞蛾记
是夜,一只飞蛾入室
准备扑火。这里没有华丽的照明
只有一盏旧白炽灯
飞蛾在一张旧报纸上
产下一群孩子
卧蚕不知道茧缚
蛹不懂得蛾的高度
秋风萧瑟,飞蛾入室
发现早已经没有前朝的烛火
淘汰的白炽灯钨丝断了几次
但,还是有一些旧事如初
读书的人青丝变成白发
多了一副老花眼镜
岁月改变命运
我还是挽留飞蛾
躲过外面的秋雨
飞蛾借宿一夜
冒险与飞蛾玩类似猫捉老鼠的游戏
等我找到飞蛾的时候
飞蛾趴在玻璃上睡着了
像极了我趴在床上张开翅膀的样子
美如斯
我画了八位僧人,身披袈裟
推开风,沿着山路,走在钛白
黑色和紫色混搭的石块上
这个色调有点冷
我有意把山门画在画框外
空门。白天和黑夜
僧人和俗家弟子,季节
可以自己进出。在画中
达不到隐喻的作用
石块是搬不动的
对垒的石块隔着山涧,无人探索
僧人们不打算征服什么
江山如画。僧人云游的地方
此刻静止在画中,山高
水长,都是有雾的地方
适合神仙居住
适合转世
八位修行的僧人
走在最前面的,画的是我最小的师弟
今年七岁,瘦小,单薄
走在后面的是大师父,稳重
本来应该是七个人,有一个胖胖的
是我。这是迟早的事
楚河汉界
楚河汉界,我被划分为南方人
老家被长江划开,一座城市
分为几个镇,我的性格偶尔
也会分裂
我更喜欢老家的山,流水薄情
山不走
江中有豚寻欢,山上的桃花洞
有白鹭求偶
江底有一条手腕粗的铁链
锁着三国的故事
老家的山不高,有神仙
一位道人,有缩骨术
睡在无水的缸中,真的永垂不朽
另一个山坳,有一间凉亭
有一个疯子,有一年大雪
冻死在这里。那个年代
老家唯一的变化是挂出了许多遗址
招牌,都是我小时候
打着赤膊,穿着一条蓝色橡皮筋短裤
乱跑的地方
如果有一天,我住过的旧居废墟上
挂个招牌
也不稀奇
对于大海,我一无所知
把手伸向大海的腹部,触摸
鲸鱼如文身在海的私密处
我左手戴着藏传的念珠
右手串着印传的佛珠
海太大,我罩不住
交给神灵
在距离公海二十海里的地方折返
有的地方不能去
但不妨碍我,放下一个漂流瓶
太阳一定会落在穹顶之下
那个海钓的人正好收竿
互不相识的两个人,从芦潮港
出海
又回到芦潮港
一转身,背后的灯塔老了
我买了几只横行的梭子蟹
海钓的人一言不发地拎着
鱼篓里的虚无
对于大海,我一无所知
壳
金蝉脱壳以后,没有什么内容
很难想象这里住过的灵魂
曾经热烈地歌唱过夏季
下塘街的一个老剃头匠
走了。很久,一件衣服还搭在椅子上
一把刮光头的刀在暗处割开一小块
光明
石缝中的小草毕其一生
寻找与花的幸福
忽然发现,一群蚂蚁像抬棺的人
举着昨晚脱壳的金蝉
去废墟那边
后来有人把剃头匠的衣服拿走了
说是烧给剃头匠
这一夜,我失眠了
还能念出这么多名字,蝉、灵魂
夏天、剃头匠
光明和小草
吴楚留香
在天堂寨门口,我突然决定
不上山了。所有的选择是可以溯源的
昨晚我在寨口借宿,万物皆安
吊锅的铁钩
在风中轻微地晃动
不要再去打扰这个世界难得的
安宁了
自古以来,这里兵家必争,帝王巡幸
名人登临
不缺少我这样一个寒门
发现旁边草丛深处有一座老邮局
这么僻静的地方,已经十分神秘
還有更神秘的
需要寄到远方
听指示牌讲故事
这里的纸包着的是火种
在天堂寨的门口,我没有上山
最难的几十里山路我走完了
最后的一段路我没有走
大山与我,一个是四处漏风的
山崖和流水
一个是吴楚留香
海盐掠记
潮水遥远。海盐的滩涂上
唐宋元明清来过,早已经
没有痕迹。朋友不停地介绍
有一位小说家叫余华
我告诉朋友,他曾是海盐的一位牙医
与莫言在鲁迅文学院同室
我更早知道海盐是《搜神记》
有神的地方当然人杰地灵
藏龙卧虎。还有鬼、妖怪
杂糅佛道,民间传说
听说海盐上了年纪的人早晨四五点钟
吃烧酒,当地人叫吃早烧
我赶去的时候接近尾声,沟通太难
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吴语
不会普通话。这样的宗亲会长久
我还不知道喝早酒是什么味道
老海盐人,抿嘴咂舌的样子
一边喝酒,一边望着海上赶路的云团
他乡遇故知
美酒河今年水浅
临河的吊脚楼很单薄
对面的摩崖上,有些隐忍很深的文字
白色的、褐色的、红色的
会飞
有的从很远的地方归来
这些灵魂傍晚回家
一只找不到母亲的鸟,从摩崖那边
借着灯光,飞到吊脚楼的檐下
一只鸟的命运是一个人一生的形容词
把夜光倒满吧
把河水隐藏在黑夜中的声音
表达出来,把山影移至杯中
山里的风雨,一会儿有,一会儿无
风雨会不会遇到旧故
他乡遇故知,宋朝人说话
文绉绉的
形容在异地他乡遇到自己的老乡
老乡拿了一瓶十五年陈酿的老酒
有什么隐喻
和我背井离乡的日子一样的漫长
黔北一日
紫云是黔北一个小山村的名字
牛肉有名。一年四季有围炉
经过马桑坪,由一种花的名字命名
繁花落尽,盐帮在这里不止千年
当年马夫扶着骡马走古罐子口
从四川翻山过来,再走水路
这些很小的山村是不是这些人种下的
抵达美酒河,顿时浮想联翩
再走一步是川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不去了。天色渐晚,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两江村的灯火暧昧
山里传统的舞蹈和篝火一起
寂静的地方有昆虫闪光,还可以
闪光的是天上的星星和美酒河的水
好日子和苦日子在山里都很干净
一只脚站在四川,一只腳
在贵州的地盘上,摩崖连天
石刻是怎样刻上去的,是不是
真的有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