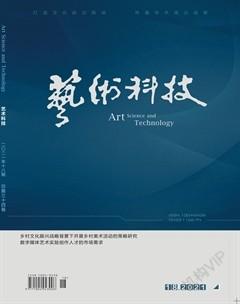地方集体记忆在乡土空间的再生
摘要: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对过去的记忆,始终是人们从群体性视角出发所共有、传承以及一起架构的事或物。受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城镇文化建筑风貌变得千篇一律,许多乡土空间消失在城乡改造中,这也导致居民出现记忆断层、文化自信缺失及归属感、认同感消散的恐慌。文章以赣榆区青口镇牌坊街社区礼堂改造为例,旨在让废弃的礼堂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使主体(记忆者)、客体(记忆对象)、时间三者形成交联的纽带,期望通过深挖牌坊街社区的生活,重构礼堂空间。以简洁的几何形体介入旧建筑中,用嵌套的方式加强新旧建筑之间的联系。通过对尺度的调节唤起人的身体在空间中的记忆,是一个渐渐理解原有“秩序”并逐渐建立新“秩序”的过程。
关键词:集体记忆;乡土文化;地方;禮堂;嵌套结构
中图分类号:TU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8-00-03
R.E.帕克曾经说过:“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1]同理,集体记忆对乡土文化空间维系自身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地位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集体记忆的存在,乡土空间才具有特色与吸引力。乡土空间中文化趋同的现象,不仅会导致乡土空间外部形象的雷同,还会使乡土空间中的居民未来的生活方式、行为与心理产生断层。
1 乡土空间中集体记忆的认知危机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构建的概念”[2]。集体记忆要与个人记忆区分开,集体记忆具有普遍性、共识性。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集体记忆中,记忆主体以时间为轴线与记忆客体(集体环境中的人、事)之间发生联系,作为记忆的共识成员,除了有着个体生理与心理的差异外,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集体环境的制约。
集体记忆作为虚体的隐性存在,往往依附于各种实体的媒介载体。通过各种不同种类形态的载体,人们的记忆被唤起、被激发,其记忆要素包括区域要素、空间要素、文化要素、生产生活要素、文献资料等等。而乡土文化是在原乡原土内发源流行、长期积淀演变并逐渐发育形成的,是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及生态文明的总和。乡土文化中集体记忆客体的空间就是其地区中历史事件、生产生活发生的场所。当今中国乡土空间的集体记忆的载体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频繁更新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中也加速了自身的生命流失。乡土空间的独特性和场所感渐渐消逝,乡土空间的集体记忆因此中断,城市化的城乡规划使得许多乡土空间从“零”开始。
城市化高速进程中,城镇建筑文化风貌趋于同一,被规划的“美感”缺乏当地独有的情感认同。因此,如何延续集体记忆成为城镇在城市化历程中应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根植于民众生活进行城镇建筑改造,集体记忆才会得到良性的循环与发展而不至于消亡,才会成为联系集体成员的纽带。
2 集体记忆在当代乡土空间的设计案例解析
集体记忆是一个乡土空间的灵魂和生命,当乡土空间的集体记忆发生断裂的时候,其与市民的有机联系也会随即消失。中国千百年来的寻根思想和对现代新生活方式的要求的矛盾,使保护历史遗存和生活更新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乡土记忆在当代空间中的呈现方式有空间形式呈现、视觉符号呈现、场景呈现等多种类别,其中杨梅竹斜街的改造、浙江省文化礼堂视觉符号系统设计与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你的地方”三个成功的方案呈现出集体记忆实现的几种不同的特点。
2.1 空间矩阵:杨梅竹斜街大栅栏项目
在对杨梅竹斜街的改造中,设计师以空间矩阵的方式在居民腾退的场所引进文化创意机构,实现了杨梅竹斜街街区的复兴,并且在街道、地面铺装、街区设施、空间分布的改造与更新中提取了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据点。例如,正门入口以历史悠久的杨梅树为中心,周边建筑对杨梅树呈簇拥和环抱的姿态进行自身的空间叙述。对于原本地标、公社、居委会等公共空间的改造形成矩阵,点动成线,线动成链,链动成面,形成了“一村、一树、一井”的杨梅竹斜街文化氛围。将胡同生活融于公共空间中,利用街道的铺装和绿化将原本街道建筑的文化和历史保存下来,又起到了串联街道空间的作用,实现了对北京胡同集体记忆最大限度的保留和升华。乡土空间的乡镇文化与胡同文化一样有着自己完整的体系,在本次设计中,笔者将吸收空间矩阵的思想,对牌坊街礼堂进行空间串联。
2.2 视觉符号系统: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
中国美术学院韩绪教授在对浙江省农村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后,带领其团队设计了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意象维度图。其设计将模型分为天地、人生、作为这三个维度,展示了文化礼堂活动内容,并且以浙江乡村最具礼堂集体记忆的承载符号——大樟树作为形态的支撑,对文化礼堂的复兴计划在视觉上进行梳理。将松散的集体记忆脉络重新凝聚,并且设计出普遍适用的中国农村文化礼堂的视觉形象模型[3]。乡土文化礼堂的空间建设离不开对视觉形象的概括与梳理,只有构建文化体系,才能支撑集体记忆持续发展。
2.3 共情桥梁: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你的地方”
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你的地方”提示人们认识身边的环境,擦亮由自身主体意识形成的镜子,重新找寻生活的意义。“你的地方”是一个由专业与非专业人士共同搭建的城市历史讲述平台,成功地还原了各地的乡土情感、乡土肌理、乡土传承、乡土记忆、乡土风貌,与观者共振共情。其中嘉定老城河道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其对嘉定各个街道的道路、城市肌理、每一个场景中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进行了梳理,还原了嘉定老城河道的风貌。环境场景是集体记忆载体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的记忆往往由一面墙、一块砖、一条河这一个个小点展开。乡土空间的集体记忆的客体也一样,人们所居住的环境空间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存在,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温度。人们通过自身的行为参与到乡土空间之中,扎根于出生的土地,在汲取营养的同时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是一个双向的体验过程。
相比之下,某些地方的街道规划不清晰,一些建筑和街道景观并没有注意细节,反而千篇一律,让人感觉处处似曾相识。在建筑的立面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广告,大量的信息输出让人目不暇接,同时也丧失了地方特色,更谈不上对集体记忆的保存。
3 以“牌坊街计划”为例试论集体记忆在空间上的重构与转译
“其东南十里,为青口镇,县舄奕殷阜胜处也。车来贿迁,盖无日无之。圩曰和安。”[4]这是光绪年间对二道街的描述,描绘了街道的繁荣景象。二道街与牌坊街是青口镇历史最悠久的两条街道,赣榆区青口镇牌坊街军人礼堂的集体记忆正是依托于这两条街而生的。
3.1 实践对象:赣榆区青口镇牌坊街社区军人礼堂
人们在乡土空间中居住、生活等一系列行为活动构成了乡土空间的环境和存在意义。人们在扎根的基础上也生长出自己的枝丫,传承着地区特有的语言、习惯,创造出属于集体的历史。
每一个小镇都有它深埋记忆的地方。赣榆作为一个沿海的小镇,有巷子,有码头,每个角落都藏着属于它平凡而不平淡的故事,欲说还休。对老巷的赣榆人来说,老式的建筑、蜿蜒的巷道、错落的堂口组成了对赣榆老街最深的记忆。赣榆青口镇牌坊街与二道街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老街,烙印着每一个老街人的生活轨迹,静静地见证物转星移。老街的巷道蜿蜒曲折,砖瓦的墙面由于城乡建设翻新被抹上一层又一层的白漆,但白漆并不能永远留存,时间的洗礼会让其慢慢剥落,于是老巷又露出了原本的模样。
老街的建筑有两种形制:第一种是传统的狭长的民居,独门独户,但紧紧相连,细长蜿蜒的巷道将老街的民居串联起来;第二种是前店后院的建筑形制,便于居住和店面经商。由于赣榆区青口镇二道街与牌坊街城乡改造,二道街由老民居开发成为商业街区,因此牌坊街居民社区建筑全部推翻重建。在这一次城乡建设的大改造中,横跨牌坊街和二道街的军人礼堂由于用地归属的问题幸存了下来,也使笔者生发了此次设计的动机。
赣榆区青口镇牌坊街社区军人礼堂的整体空间位于二道街和牌坊街的中间,军人礼堂是1950年至1960年间建成的,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礼堂在周边环境的变迁中大体保持了其原有的空间形制,只是在近些年的城乡建设中逐渐被淘汰而后被遗忘了。特殊的位置却没有发挥其文化中心的作用,着实令人惋惜。因此,激活礼堂空间,优化空间布局,让礼堂不再闲置,成为城市建设翻新后乡情的归处,让原先的街巷居民重拾在老街生活的感觉,并且拥有新的活动场所,让新搬入的居民融入老街的文化环境中,让开发后的新二道街的游客了解老街的历史迫在眉睫。
3.2 设计思路:嵌套结构转译集体记忆
嵌套式结构是叙事学的术语,指的是一环套一环、结构严密的叙事结构。其特点是多个事件之间相互串联、事件的目的有相同的主题、两个事件内容相似相近。而在建筑学中指的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相互重叠与交错,形成一种多变的空间嵌套结构。
笔者吸收了嵌套结构的经典案例,即藤本壮介的House N设计方案中的空间思想[5],对嵌套结构的含义进行了延伸,希望用嵌套结构转译集体记忆。在空间规划方式上,空间的最大限度利用和合理组合放置,嵌套是一种必然的处理方式,它将各种不同的区域结合在一起,并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公共性态度。交错暗示着一种公共的空间属性从一个点辐射开,这是一个交流与聚集产生的地方。在生活方式层面,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交叠与共享;在精神层面,是居民的关系、生活习惯、生活态度、故事的相互重叠交错嵌套。
3.3 实践方案:牌坊街计划——军人礼堂空间的重生
第一,空间形制上。笔者在空间形制上对赣榆街道空间进行分析,将赣榆巷道的特点植入礼堂空间的外部空间中。采用扭转角度的方式将巷道空间与礼堂外部结合生发出新的空间,再一次为废弃空间赋予意义,使生发出的空间有赣榆老街的影子。利用新旧材质和体型的对比,凸显历史文脉感,传承赣榆建筑的文脉。因此形成礼堂空间形制再生公式:军人礼堂空间形制再生=(空间扭转+空间赋予+空间新旧材质对比+……)×历史文脉
第二,文化图形符号填补肌理。利用文化图形符号还原城市片段与立面材质肌体。爬山虎作为赣榆随处可见的植物,大量覆盖在礼堂空间的建筑立面上,是笔者童年最深的回忆。爬山虎将建筑包裹的同时,也忠实地反映了建筑空间的起承转合。因此,笔者以爬山虎为视觉元素的形象提取,将爬山虎从建筑中抽离出来并运用到空间的串联和进入中,以还原较为形象的礼堂外部空间印象,用爬山虎包裹的形态塑造出虚体的外部空间。
第三,由场景引发共情。笔者经过多次田野调查,结合在赣榆老街生活十多年的经历,得出牌坊街居民以老人居多的结论,因此在空间设计中充分考虑牌坊街居民的日常活动,如品茶、晒太阳、聊天、遛鸟等,也充分考虑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孩子们的需求,进行合理的空间分布。通过立面改造、插层策略、结构策略、加固设计、聚落利用再保护,使老树发新芽。保留历史肌理,通过改造重新梳理赣榆地域文化,保留原先的建筑形制、空间分布和行为习惯,促进废弃礼堂重生为便民的城市社区文化活动礼堂,成为文化复兴的据点,辐射周边的环境。希望在不改变空间大体布局和形制的情况下对空间进行二次分配,对礼堂外部空间进行改造[6]。
4 结语
劳伦斯·哈普林认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城市,应该是新旧建筑并存,使人们可以体验到和过去、未来的种种联系。”乡土空间亦是如此,集体记忆联系了人与时间,将人们的过去、现在、未来串联在一起。乡土文化的集体记忆就像血液一样奔涌在每一个成员的身体里。那些保留下来的乡土文化空间、藏在意识深处的记忆片段和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念念不忘,正反映出乡土文化对人们精神与情感的重要性。笔者作为其中的一员,有着深切的感受。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赣榆区青口镇牌坊街礼堂空间的再生与激活,唤起人们身体里的集体记忆,让集体记忆得以保留与再生。
参考文献:
[1] [美]R.E.帕克,E.N.伯克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2.
[2] [法]M.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4.
[3] 韩绪.为中国农村做设计:谈《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视觉形象及符号系统设计》[J].美术,2015(2):92-93.
[4] [清]王豫熙,张謇.光绪赣榆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877:16.
[5] 贾蕊.藤本壮介的House N引发的住宅室內模糊空间构想[J].创意与设计,2016(6):102-104,17.
[6] [美]劳伦斯·哈普林.城市[M].许坤荣,译.台北:尚林出版社,1986:9.
作者简介:廖文慧(1997—),女,江苏连云港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传达。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2020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地方感理论视角下城市遗产图形设计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JCX20_0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