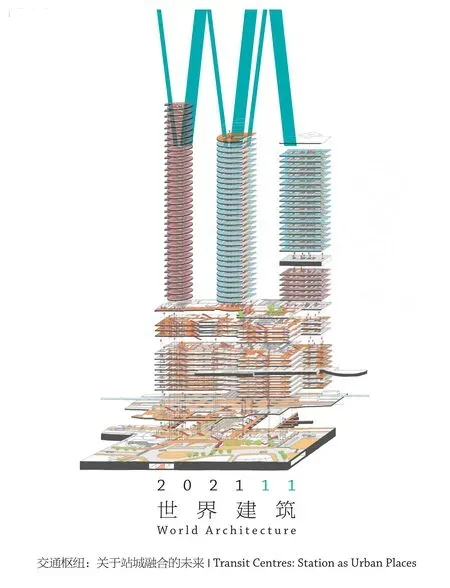结构真实性与欺骗性的分离和叠加
张思慧
1850年代,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建筑真实性的讨论逐渐趋向一种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结构真实性原则。虽然这一转变引导建筑脱离了传统原则的束缚,同时促进了结构效率与经济性的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建筑和结构之间的整体性,使得结构逐渐发展为仅提供支撑功能的技术要素。本文将讨论如何在结构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对真实性和欺骗性的重新审视,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结构真实观,达成建筑与结构的整体建构。
1 真实性和欺骗性的分离——结构作为支撑工具
1.1 16-18世纪中期的建筑真实性与欺骗性
在二元对立的理论里,真实与虚假通常被视为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在16-18世纪中期,建筑领域里的真实性与欺骗性是可以共存的。这一时期,建筑与结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划分,结构真实性的观念尚未形成。受到新柏拉图主义以及维特鲁威建筑理论的影响,建筑的思想家和写作者提到的“真实”,都是指对建筑的自然范本的真实再现[1]275。这种再现自然的活动既包括石材对木构建筑的直白模仿,也包括建筑对自然之物的秩序与和谐原则的类比模仿[1]206。例如,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认为建筑是模仿自然的,不能背离自然本身所允许的做法,而古代建筑师刚开始用石头建造过去用木头建造的房屋时,就是以自然树木为范本确立了柱子形态的基本规则[2]。
尽管如此,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建筑师都充分意识到:“建筑制造的是一种人为的现实,它关注的主要是建筑看起来怎么样而不是它实际上到底如何。因此,他们根本不觉得在这种虚假与所谓的真实性之间有什么冲突之处”[3]40。17-18世纪,真实性不仅可以与虚假共存,“甚至人们普遍接受建筑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假的艺术”。意大利建筑师瓜里诺·瓜里尼(Guarino Guarini)曾写道:“建筑,尽管它依赖数学,却是爱与风采的艺术,其中感官不想被理性厌恶”[1]275。
1.2 结构真实性与欺骗性
建筑真实性和欺骗性分离的根本原因在于“真实”的重新定义[1]275。18世纪中期,随着科学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哲学概念中美与真的分离,人们开始尝试通过理性的方法建立一种新的建筑观念。对于建筑真实性的讨论逐渐转变为以理性与逻辑原则为基础的结构真实性,即“结构外在形式的表现与它内在的结构体系一致,或符合它的材料的性质”[1]271。相对应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对结构欺骗性的定义是“提示了某种并非真正方式的结构或支撑方式”[1]282。其中包括:结构的构件形态不遵循其内在的力学机制和材料特征,或者在建筑外在的表现形式中刻意暗示其他的支撑模式,以及为了达到审美的需要将部分或全部支撑手段与方法隐藏起来等违背结构真实性原则的做法[4],例如,虽然圣保罗大教堂通过采用悬链线的做法,创造出古典建筑中质量最轻的穹顶结构,但由于真正的屋顶支撑体系被隐藏在由木桁架搭建的虚假外壳之内(图1),而被新哥特式和现代运动的理论家谴责为违背了结构真实性原则的“赝品”[5]。

1 圣保罗大教堂屋顶结构与覆层的关系(图片来源:参考文 献[14])
结构真实性的探索正是出于对“建筑是欺骗的艺术”这一观点的挑战。卡罗·劳杜里(Carlo Lodoli)是发展出这一新的建筑真实观念的第一人,他试图通过科学理性的思考方法,将力学与材料特性作为石构建筑与装饰的形式来源,以摆脱维特鲁威所谓的古希腊与罗马石构建筑与木构建筑之间的形态模仿[6](图2)。劳杜里将这一理性原则建立在将建筑二分为“功能”1)和“再现”的基础上,认为没有任何在功能上不真实的东西应该被再现。在劳杜里的理论中,建筑美只能从真实中产生,而“真实性”是指功能与再现的统一[1]277。该真实性原则在之后的建筑理论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地继承与发展,并在19世纪由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提出系统的结构真实性理论[3]44。勒·杜克以中世纪哥特建筑为范本,指出科学与几何应该作为建筑真实性的标准,“提倡建筑形式是结构材料的受力性能的真实表现,那些经由静力学得来的规律,自然会促进建筑的真实表现——忠实性”[7]。奥古斯都·佩雷(Auguste Perret)、尤金·弗雷内西(Eugene Freyssinet)和其他人将维奥莱·勒·杜克的这种真实性观点与预制混凝土技术结合在一起,使其影响了1920年代的法国和意大利的现代主义建筑师[1]281。在这一过程中,结构逐渐发展为效率与经济需求下的支撑工具,在勒·柯布西耶的多米诺(domino)体系中,建筑成为两个独立的系统——结构被简化为纯粹的技术性问题,美学系统被提升为一种抽象的形式组合,包括自由的平面、自由的立面、材料的肌理和色彩的表达[8]。

2 多立克柱式的三陇板和托块的手法源自对木构装饰的模仿
2 结构真实性的纯化——结构作为独立的艺术
1950年代,随着钢筋混凝土材料和静力学理论的发展,结构的真实性原则更加精准地指向数学和物理的“真实”,这一时期“建筑的形态几乎就是力的图解,形式可以在建筑的内外同时被阅读”[9]。一些工程师开始尝试将这种更加趋近客观“真实”的结构与审美需求整合在一起,形成一门独立于建筑之外的结构艺术。例如,由皮埃尔·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设计的都灵劳动宫(Palazzo del Lavoro)的夹层采用梁肋屋面系统,其梁肋的形体与结构内部的等应力线2)保持一致,反映了双向混凝土板真实的结构行为,同时这种由力的图解自然生成的有机形态又赋予结构艺术性的表达(图3)。以及罗伯特·马亚尔(Robert Maillart)设计的塔瓦那萨桥(Tavanasa Bridge),大胆地去除了一切的装饰面层,真实地反映力学作用的结构形态,创造出简单、明朗而轻盈、飘逸的结构形态[10](图4)。

3 都灵劳动宫(图片来源:参考文献[8])

4 塔瓦那萨桥(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0])
除奈尔维和马亚尔之外,结构师埃杜阿多·托罗亚(Eduardo Torroja)、菲利克斯·坎德拉(Felix Candela)、海恩兹·伊斯勒(Heinz Isler)等都在这一时期创造出很多兼具结构真实性与艺术表现力的设计作品。这一类以工程师为主导的建筑作品,充分利用混凝土的塑性与结构找形的方法,突破了多米诺体系的结构范式,使得结构的设计和思考从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美学高度。但也不乏在一些情况下,由于过度追求力图的表达,导致结构真实性需求与建筑整体需求之间的矛盾,最终偏离了结构经济性的初衷[11]。此外,这种致力于结构表现的作品大多属于桥梁、仓库、体育场馆等以结构占主导且功能和空间较为单一的建筑类型,而在更为复杂的建筑需求下,力与美的完美契合总是短暂的。
3 结构真实性和欺骗性的叠加——建筑与结构的整体建构
这一真实性逐渐纯化的过程,引导建筑脱离了文艺复兴的古典建筑原则和巴洛克建筑的随意性,同时使得结构的效率与经济性获得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这种更加客观、绝对的真实性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结构在技术体系之外的丰富性,进而导致了建筑与结构在设计层面的分离。尽管这一时期的工程师们试图重新为工具理性的结构赋予审美价值,但最终只是一场在理性主义孔径之下,由结构工程师主导的独角戏,难以形成结构和建筑的整体思考。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结构真实性的发展与纯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与反对。但无论如何,真实性始终是结构设计的重要原则,比起对结构真实性彻底地否定,更有价值的主张是通过真实和虚假的叠加,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真实观来调和这种对立的矛盾关系。例如,建筑理论家奎特雷米尔·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曾试图维护两者的统一,反对这种新的更加绝对的真实[1]276。拉斯金作为表现真实性3)的支持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对结构欺骗性的接纳。他认为“如果结构能在感观和头脑中引起审美反映”,那么这种欺骗性就是合理的[1]282。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写道:“如果始终被捆绑在所谓结构诚实性上,并且其含义不过是任性地坚持建筑中结构和艺术的需要只能由单一和统一的手段来满足,它就会步步受限制,以致无法追求结构的美”[12]48。
真实性和欺骗性的叠加在建筑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立足于建筑整体的真实观。其所强调的结构的“真”不是对力学逻辑与建造原理的精确再现,而是在尊重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欺骗性的叠加,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感知层面的“真”。例如,瑞士结构师约格·康策特(Jürg Conzett)曾借用地图学家爱德华·因霍夫教授(Eduard Imhof)的观点表达他对于结构真实性的看法。因霍夫教授支持数学的理性,但认为这一切要建立在人感知的基础上。例如,在他绘制的地图上光线是从北方照射过来的,即便在现实中这从来不会发生,但更好地表达光的印象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合理的 (图5)。他认为:“决定把什么去掉与把什么留下同样重要,人们无法看到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呈现出来,宁可这里的本质是要意识到被欺骗的可能性”[13]。在康策特的设计中也没有按照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结构真实性原则理性地呈现每个细节,而是更多地聚焦于那些可以被观者理解的有意义的因素。例如,在奥托广场大楼(Ottoplatz Building)的设计当中,为形成建造底层的大跨度空间,通过斜向的拉筋与预应力楼板形成高达3层的巨型桁架剪力墙(图6、7)。从立面上看,可见的墙、板等结构要素与真实的受力部分是一致的,但承担主要结构功能的预应力筋是隐藏的。奥托广场大楼没有全依照结构真实性的原则将内在的力学机制完整地表达出来(图8)。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通过立面上对角线的关系感知到一种隐含的斜向作用,可以说在感知的层面上,整个结构是真实可信的。

5 爱德华·因霍夫作品(图片来源:https://www.atlasofplaces.com/cartography/kartograph-und-kuenstler/)

6 奥托广场大楼(图片来源:https://divisare.com/projects/17916-jungling-und-hagmann-ralph-feiner-ottoplatz-apartment-and-office-building)


7.8 奥托广场大楼结构示意(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7])
尼迈耶设计的卡瓦内拉斯别墅(Cavanelas House)也存在某种结构真实性的偏差。这座建筑看似清晰的结构语言其实是一种欺骗性表达,与其内在真实的力学机制并不一致。从外观来看,屋顶部分似乎是悬空的,倾斜的扶壁就像房子两侧的桥墩,拉紧的屋顶结构似乎是锚固在其上,它柔和的曲线轮廓暗示了垂直支撑点之间的重力向下拉的印象(图9)。同时屋顶纤细的桁架呈现出轻盈的状态,加强了这种预判的视觉效果。但真实受力机制却要复杂得多,屋顶结构由4根主纵梁和15根次横梁组成,受力状态混合了梁、悬链线以及拱的作用机制。中间2根纵梁为三跨梁,所承担的荷载比边缘梁多1倍,但为了保持屋顶结构在视觉上的连续性,边缘的主纵梁和横向次梁也统一处理成相同厚度(图10)。可以说,尼迈耶利用丰富的材料使用经验,通过各种伪装使得他想要的视觉形态和空间效果打破了静力学法则的束缚[14]278,内在的力学差异与结构的复杂性都被一种简单、纯粹、充满欺骗性的形式语言所掩盖(图11)。然而,比起单一层面的结构真实性,这种让人产生“误读”的结构“欺骗性”更好地实现了结构和建筑形态、空间需求之间的平衡,形成一股盘旋于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张力。

9 卡瓦内拉斯别墅(图片来源:https://www.skyscrapercity.com/threads/mid-century-modern-architecture.1733581/)

10 卡瓦内拉斯别墅(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4])

11 卡瓦内拉斯别墅(图片来源:http://architecture-history. org/architects/architects/NIEMEYER/1.html)
路易·康的金贝尔美术馆(Kimbell Museum)在多个方面突破了固有的结构真实性原则。首先,这座建筑所呈现出来的结构形态与其内在的力学原则并不一致。其屋面的拱顶并不是真实的拱结构,而是由混凝土梁内置预应力做成的假拱。其次,拱形屋面的顶部的天窗使得拱形梁在应力最大的区域减少材料,违背了结构内在的力学原理(图12)。虽然最终拱形梁的结构形态按照结构师奥古斯特·克门丹特(Auguste Komedant)的意图呈现出与力学逻辑一致的变截面形态(图13),但依照康对于线条和比例的感觉,他想要的是一个更为简洁、具有均匀厚度的,可以忽略受力特性的轮廓线[15]。他曾经对结构设计师奥古斯丁说,“在当时部分完成的博物馆里,光线和空间的质量足够漂亮,以至于在那一刻,他愿意牺牲结构的真实性”[14]162(图14)。金贝尔美术馆的结构形态并没有完全地遵循内在的力学机制和材料特征,康是用一种非常人文主义的方式来回应结构的真实性问题——“它拥抱结构真理,但同时意识到人对表达的诠释掌管着结构”[14]162。斯科特也曾从心理体验的角度对结构中的欺骗性给予肯定:“对于那些未被觉察的欺骗,对那些不涉及稳定性及体量感的事物——这些欺骗的心理效应是可忽略不计的,即使在这里也是可允许的”[12]67。

12 金贝尔美术馆(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8])


13.14 金贝尔美术馆(图片来源:https://www.kimbellart.org/)
“完整意义上的结构”包括可知与可感两个部分,可知的部分“只能服从机械法则”,而可感的部分“服从于心理法则”[12]51。18世纪以来结构可知的部分在科学的发展下得到充分的发挥与表达,而可感的部分时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在结构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结构真实性与欺骗性的叠加重新把结构的“可知”与“可感”整合在一起,将数学与物理的结构转变为重力与几何的结构。
4 结论
绝对的结构真实性通过力学原理的物化,获得了结构效率与经济层面的最优解。但完整意义上的结构,除了真实性主导下的技术属性,还包括欺骗性所指向的非技术属性。相对于单一层面的、确定的真实,我们更需要一种多元与开放的结构真实观,来平衡技术与情感需求之间的矛盾。诚然,真实性是结构效率与安全性的基础,但真实与虚假叠合的部分,赋予了结构在技术理性之外的生命力。正如康策特写道:“想象的承重关系叠加在了对真实承重关系的理解之上。不同感知方式的共同作用创造出一种和音——这种和音令人神迷”[16]。□
注释
1)劳杜里的“功能”借用了数学里的“函数”(function),他想表达的“功能”是指“存在于建筑构件里的结构作用力与材料的综合作用”参见参考文献[1]159。
2)具有相等应力值的点连接起来的线称为等应力线。
3)表现真实性是指,“一个作品的感觉忠实于它的内在本质或它的制作者的精神”参见参考文献 [1]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