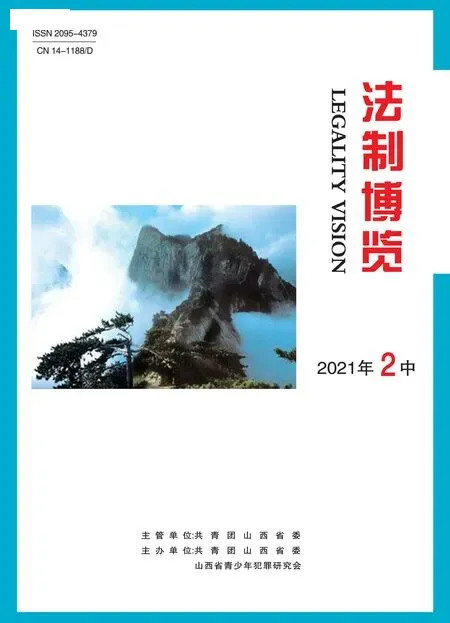法官的调查取证权研究
鲍玥萌
(海城市人民法院,辽宁 海城 114200)
法官在哪种情况下具备调查取证权,会对于案件真相的了解产生直接的影响,也会对于实体正义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实际运作来说,则时常形成了对于某方当事者的帮助,所以又和法官之中的程序正义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性。另外,证据主要是由当事者加以收集,或是法官进行收集,通常被判断为职权主义和当事者主义二者之间实施区分的关键标志。以调查取证权本身来说,不管是在实务之中,抑或是在理论之中,都难以合理处置程序主义以及实体主义二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因而容易陷入至这方面的困境之中。因此说,值得对于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调查取证权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一、两难处境之中的调查取证权
(一)调查取证权的实体正义之维
在我国2002年所颁布的《证据规定》之中,限制了法院的调查取证,而在实务之中则体现出了此种限制损伤到了实体公正,如认为在限制调查取证权之后,会产生诸多的消极问题,当事者在诉讼中会更易说谎话。不服事实认定已然成为当事者不服从判决的重要因素之一,还有法官认为由于当前当事者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在取证方面也较为困难,这样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法官的调查取证权,不利于保护当事者的权益[1]。该种对于限制调查取证权的判断以及批判,也获得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响应。李浩则认为,此种限缩所产生的后果会使得法官对发现事实真相方面产生消极影响。而肖建华认为,在证据规定之中彻底否决了法官职权调查,导致法官失去了发现案件事实的条件,致使产生审判权缺位的情况。上方评论内容是针对《证据规定》的,但在最新的《民事诉讼法解释》之中,对于调查取证权的界定,对比于《证据规定》之中的内容,还不存在本质方面的变化,在立场方面更是具备一致性,所以上方批评内容就算用在当下也较为适用。
(二)调查取证权的程序正义之维
调查取证权不单单在实体正义维度方面受到批评,在程序正义维度方面也是一样。张卫平认为,在最新的《民事诉讼法解释》之中,对于法官调查取证权予以了限制,在民事诉讼体制层面虽说获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还不是十分完善,因此其强调只需留下对程序事项的调查取证权,针对可能损伤到我国的利益等方面,就无需具备这一权利,这主要是由于法官的调查取证会虚化当事者的处分权以及辩论权,导致裁判失去中立性[2]。再者,法官还难以保障自身所调取的相应证据是绝对具备真实性的,所以也难以确保案件具备真实性。会损伤到我国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情况通常需由刑事诉讼来加以解决,所以不处在民事诉讼的范围,在上方批判原因之中,关键点在于中立问题。
在实务之中,法官调查取证权的主要运作形式,能够划分为事实调查及证据收集模式,以及庭外证据收集模式。以庭外证据收集模式来说,则是法官了解某一证据处在特定性的证据源范围之内,进而就会对于向个人,或是单位的取证产生影响。而事实调查及证据收集模式,则是指法官通常并不根据某一确定的证据实施收集,在案件事实未能了解的情况之下,先去案件现场开展走访调查工作,在此期间试图发现真相,并认真的收集相关的线索。本质目的在于探明事实真相,但不管是上述哪个模式,均很难满足于程序正义之中的相关标准及要求。
二、德日语境之下的调查取证权
(一)辩证主义之下的调查取证权
在德国法之中不存在和中国法绝对一致的法官调查取证定义,意思较为接近的术语则为法官证据提出以及证据调查,而这为法官所具备的重要职权。德国法之中的证据调查和中国的调查取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其是指法官根据之前对于相应的证据方法实施判断及审核的一种行为,以表层的意思来分析,即为提取证据,而以深层次内涵来说,则主要指的是法官对于证据方法的感知,并在此期间提取证据的一种行为。在德国法之中,证据主要包括证据方法,证据资料以及证据原因[3]。以证据方法来说,其主要指的是实际的人或物,通过其的帮助而加以证明,更为精准的来分析,则为传递或是观点的重要载体,主要涵盖鉴定人,勘验物以及证人等。证据资料主要指的是证据调查的最终结果,对于证据方式实施调查而获知的信息。证据原因则主要指的是证据资料以及辩论期间被认作为事实的内容。概括来说,证据方法与证据提出之间相对应,而证据资料与法官判断方面相对应,证据原因则和法官心证方面相对应。
(二)修正辩证主义之下的调查取证权
为提高诉讼效率,尽快发现案件真相,在当前的德国民事诉讼中,虽说在整体方面上坚持辩证主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也具备着许多修正内容,这主要是指运用修正辩证主义,表现在内容与修正辩证主义之原则,法院能够在不经过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之下,为职权证据进行调查。一方面在当事人未能够提出有效的证据方法时,那么则能够将此证据方法引至诉讼之中,如职权勘验。另一方面对此种证据方法命令以及证据调查和辩证主义的证据调查实施对比,发现和修正辩论主义的职权证据调查所存在的不同则通常表现在第一层次上,这主要是指法院能够根据职权提出证据方法,不需要当事者加以举证,但通常来说,法官须先以释明权的运用,对于当事者提出建议,让其能够提出证据申请,唯有在怀疑可能会违反实际义务的情况之下,才会应用职权证据调查[4]。
(三)否定主义之下的调查取证权
对于一些程序事项来说,在德国法之中法官能够依据职权加以审查,进而则能够形成辩证主义的一种例外体现。上述事项通常牵扯到合法性要件方面的内容,许多观点均认为法官能够为了自由证明,可不进行严格证明,这主要指的是不受到证据调查程序以及法定证据方法方面的约束,而这主要是由于自由证明倾向证明的迅速性、简洁性,防范产生诉讼拖延的情况。自由证明的主要方法,为立法人员假定的是对于证人的调查补充或利用电子邮件以及电话等形式来开展补充调查工作,而调查的主体则为鉴定人[5]。除却在事实提出方面上充分按照辩证主义理论加以践行,在其他方面上的处理则和辩证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则能够被作为辩证主义的局部否定。
在德国法中,法院有权基于构成裁判基础的证据以及事实实施收集这一原则,此原则和辩证主义原则之间处在对立状态,其核心内容在于法院应依据职权来衡量当事者未能够主张的一些事实内容。再者,当事者无争议的某些事实,法院能够不当作裁判资料,法院能够以职权调查证据,通俗来讲就是法院能够为证据调查以及职权事实调查。
总而言之,以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调查取证权来分析,尝试将法官在证据以及事实方面上的权力回归至司法权之本质层面上,此种论证途径强调于程序的理性化以及细致化,满足于现阶段程序主义以及实体主义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利于应对法院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并且在理论层面上,这种论证也尝试确定我国法官调查取证权,在对比法的参照定位之下来体现的缺陷以及特殊性,强调于解除一些对于职权主义以及辩证主义的错误性认知,以及偏差性想象,从而为民事审判的革新提供重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