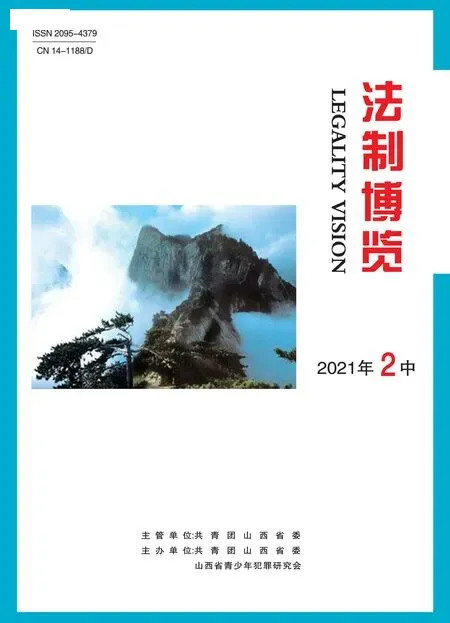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解释
——解读《公司法》第十六条
刘 健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300202)
一、《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性质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在向外部主体承担担保责任时,需要履行一定的决策形成程序。然而决策形成程序是否会影响对外合同的效力,这一点是存在争议的。在《九民纪要》出台之前,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决策形成程序不会影响对外合同的效力,其主要依据是将《公司法》第十六条定位为“管理性规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决策形成程序是否会影响合同效力需要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具体要考察合同债权人的主观状态,即审查债权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这种观点背后的支撑是“代表权限说”。
为了进一步分析《公司法》第十六条背后的法律属性,理论上出现三种学派,分别是“法律规范属性说”“法定权限限制说”和“内部管理规范说”。[1]法律规范属性说认为,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决策处理程序的担保合同,合同将不发生担保的法律效力。该理论目的在于强化对中小股东与公司的保护,实现对法定代表人的严格管控。内部管理规范说则恰恰相反,该理论认为该法律规定属于任意性规范,不否认未进行内部决策对外担保的合同效力。该理论认为,在《公司法》作为组织法的大背景下,《公司法》第十六条也当然不具有强制性,第三人也不会受到公司内部决策的影响与约束。
在2019年《九民纪要》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并未对《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法律适用达成一致,常常发生同案不同判的结果。《九民纪要》出台之后,则明确支持“法定权限限制说”理论。顾名思义,对外担保权属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权利,甚至对于关联担保来说,仅仅股东(大)会才有权决定是否对外担保。法定代表人排除在担保权利主体之外,法定代表人未经过公司内部决策作出对外担保决定的,属于未取得授权的行为,构成越权代表,合同效力将会对接《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审查债权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进而判断合同效力。
二、“善意”债权人的界定
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问世到《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再到《九民纪要》的出台,我国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权责配置规则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债权人在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时,法定代表人未取得授权的担保行为,符合表见代表的构成要件,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善意”,鼓励商事交易安全,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倘若债权人存在过错,此时站在利益平衡的角度上,公司则无须为他人的过错买单,不再承担法律责任。
《九民纪要》第十八条规定,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的,为善意债权人。同时,法律因担保对象的不同,对债权人善意的判断标准也进行了区分。一般来说,债权人对公司内部决策的审查要求较低,只需尽到一般的、必要的、合理的谨慎义务就可以。债权人审查义务较轻,仅仅是合理的注意即可,不需要审查决议的真实性、决议程序的合法性等等。但对于关联担保来说,债权人需要更高阶的注意义务。[2]例如在吴文俊与泰州市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文英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对公司是否有效,取决于担保权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已经超越了代表权限。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属于特殊担保、关联担保、对内担保。担保权人或债权人不仅需要审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及加盖公司公章的事实等代表权特征,而且还需要审查为股东借款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决议等程序性事项。
在2019年度人民法院公布的十大商事案件中,亦明确了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的,债权人不但要审查公司是否提交了股东会决议,还应进一步审查决议中签章的股东是否对应于公司章程的记载,检查股东签章或签字的一致性,另外还需计算签章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比例。当公司章程中对担保数额有限制的时候还要审查担保的数额是否已经超出章程规定。《公司法》的法律宣示效力,进一步扩大了债权人应当知道的内容范围,也进一步拓宽了债权人“善意”的外延。
实际上,债权人是否“善意”属于主观范畴,《九民纪要》也将该主观范围概括为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范围。然而,要计算债权人的“善意度”,还需要相对客观的标准来界定,使善意值得以量化。债权人的注意义务主要来源于两部分:法律规定与非法律约定。对于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应当采用“理性一般人”标准,推定债权人知晓公司法的法律规定。法律具有宣示效力,行为人不能以不知道法律来降低自己的注意义务。况且,作为商事交易的主体,很难在缺乏专业知识或行业背景的情况下去从事相关的行业。对于交易规则、当事人约定等非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则应采用合理的、一般的形式审查标准。人类是复杂的生物,每个人的注意角度与注意高度是不一样的,过高或过低的注意义务都不利于社会发展。因此,法律应拟制理性的第三人去规制当事人的审查义务,以一般的、大众的角度去看待商事交易。
在实践中,为了保护自己最大利益,债权人与公司签订合同时不仅要看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文件,更要关注公司决议与章程,审查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从公章主义、法定代表人至上论逐渐过渡到全面审查观,做好担保合同的事先审查。
三、越权担保的法律效果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法定代表人违反法律规定,未经授权对外担保的,其所签署的合同应无效。但是《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规定,存在下列两种情形的合同有效。一是法定代表人虽然没有取得授权或者超出授权,但之后经过决策机构追认的,担保合同发生效力。二是债权人为善意的,通过主张表见代理,担保合同发生法律效力[3]。
若法定担保人提供越权担保,决策机构并未补强追认或者债权人非善意的,被越权公司由于不存在可归责事由,从而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善意相对人在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后,会拥有双向救济的权利,既可向公司行使债权,也可要求法定代表人承担法律责任。公司以法定代表人越权为由提出的抗辩理由,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若债权人为非善意的相对人,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类推适用无权代理制度,公司可以行使追认权直接承认担保合同的效力。公司不追认的,行为人则需要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债权人的恶意程度较高时,例如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等,人民法院直接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然而《公司法》第十六条是不完全法条,缺少法律效果的部件,只能援引其他法条进行补充。例如当决策机构决议被撤销时,担保合同效力如何,法律并未完全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