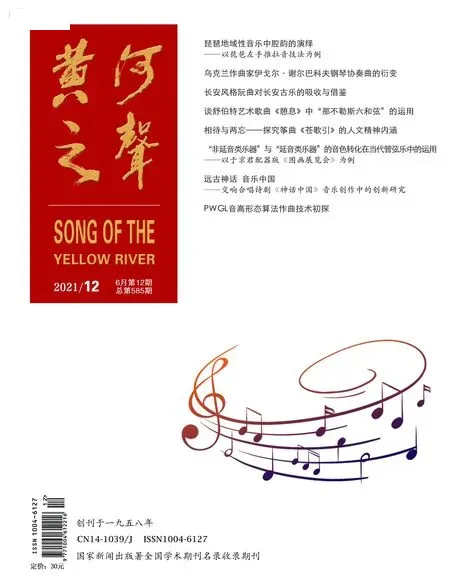蒲剧的唱腔艺术研究
王蓓珍
蒲剧,也称蒲州梆子,因发源于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而得名,是我国梆子声腔剧种中产生较早的一种,广泛流行于山西及周边省区。作为山西四大梆子之一,蒲剧与晋剧、北路梆子同根异枝,既有山西梆子声腔剧中的共性,也有独特的地方魅力,尤以独特的唱腔艺术而闻名[1]。永济南依中条山,北靠台垣沟壑区,西临黄河滩,位于黄土高原上,唱腔艺术具有黄河奔流的雄迈之风,以音域宽、用调高、跳动幅度大为特点,具有高亢激越、雄浑奔放的审美特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蒲剧的唱腔也在变化,呈现出了新的艺术形态与审美特征,因此,深入研读蒲剧的唱腔艺术,就成为感受蒲剧魅力的重点内容。
一、蒲剧唱腔的分类
唱腔为戏曲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器乐伴奏音乐共同构成了戏曲音乐,指由人声唱出的戏曲音乐旋律。线性分类是蒲剧唱腔最主要的分类方式,从线性分类的角度来看,蒲剧唱腔包括四种类型,一是平线唱腔。平线唱腔由两个以上同度音的横向连接,低音区、高音区有着不同的美学特征。二是斜线唱腔。斜线唱腔为两个以上连续音符的级进,并且,受乐音进行方向的不同,斜线的形态也有所差异。三是弧线唱腔。弧线唱腔由三个或以上乐音沿着同一方向级进或小跳进,再向反方向级进或小跳形成,包括上、下两种形态。四是折线唱腔。折线唱腔与弧线唱腔大体相同,区别处在于折线唱腔顶部有一个五六度以上的跳进音程。
除了线性分类外,板腔与色彩也是蒲剧唱腔分类的常见方式。
从板腔的角度而言,蒲剧唱腔包括行腔型唱腔、数板型唱腔两类。行腔型唱腔字少而腔多,又分为散板行腔、整板行腔两种,多用于抒情性较强的旋律,在综合板式唱段中,散板行腔多位于“起”与“合”的部位,而整板行腔则位于“承”的部位[2]。数板型唱腔与行腔型唱腔恰恰相反,字多而腔少,包括散板数板、整板数板两类,多用于表现唱腔的语言美。
从音乐色彩的角度而言,蒲剧唱腔包括苦音唱腔、欢音唱腔两类。苦音唱腔多用于表现悲伤、惆怅、愤恨的情绪,最大的特点在于唱腔中所用的“7”为“降7”,并在主音上方形成了一个小三度的音程,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欢音唱腔多用于表现欢快、喜悦、爽朗的情绪。无论是苦音唱腔,或是欢音唱腔,均是以“5”为主音的徵调式,二者的区别在于旋律中所强调的音不同。苦音唱腔、欢音唱腔主要由角色决定,同时,也受到行当的影响,如“净”行当以欢音唱腔为主。
二、蒲剧唱腔的发展历程
(一)建国以前的蒲剧唱腔艺术
蒲剧是山西四大梆子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推测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靖年间。清代,蒲剧艺术逐渐发展完备,而传统蒲剧的唱腔艺术便形成于这一时期[3]。抗战爆发后,大量蒲剧艺人从山西西渡黄河,进入广阔的西北地区,并组建了许多有名班社,比较有名的有华晋舞台、兴云学社等,其中,兴云学社在蒲剧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兴云学社首次提出了蒲剧的概念,而这一概念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并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兴云学社的重要艺人,如杨登云、筱九娃等多有唱片传世,而这些唱片正是今天我们研究蒲剧唱腔艺术最为原始、最为宝贵的资料。从整体的结构而言,蒲剧唱腔属于板体,以对称的上下句为基本腔,并且带有不同节奏、板式的变奏形式,而在调式的采用上,则是以“5”为主音的徵调式。建国前蒲剧的调门比较高,相当于Bb调的“二眼调”一直是蒲剧的定腔调。高调门对蒲剧演员有着不小的要求,因为建国前,蒲剧演员生角均采用真声发声,但并非所有演员均具有良好的嗓音条件。一些隐喻不宽的演员在高音演唱中,极易出现喊嗓子的情况,既会影响戏曲唱腔的美学效果,也会损伤声带。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男性反串的旦角中。高调门以及喊嗓子的发声方式使得蒲剧唱腔旋律形态多为平斜、连结形态。
(二)建国早期的蒲剧唱腔艺术
建国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趋稳定,蒲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在创作、演出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建国前,蒲剧中的旦角多为男性反串,女性演员极少,而建国后的蒲剧则逐渐取消了反串,女演员的数量不断增加。演出队伍的变化对蒲剧的唱腔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男女演员同台而带来的音区统一的问题,戏曲工作者引入了转调的方法,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当属移植于越剧经典曲目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该剧中,男腔用1=D,女腔用1=G,为蒲剧唱腔旋律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建国后,蒲剧唱腔的调门也有所降低,特别是低音区的加入,有力地拓展了蒲剧整体的唱腔音域,同时,音区的扩大也促进了演员发声方法的变化,真假声混合成为蒲剧发声的常见方法,提高了音色的圆润效果。新的配器手法的引入,使得蒲剧伴奏音乐更为丰满,而这也客观上促进了蒲剧唱腔的变化。文革期间,文艺创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戏曲成为革命宣传的工具,最为典型的便是京剧中的样板戏。蒲剧同样受到了样板戏的影响,具体到唱腔层面,便是新的大甩腔的形成。传统蒲剧中,大甩腔多见于“快流水”末尾的随板行腔,而对样板戏的借鉴则使蒲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甩腔,即在二性、紧二性等大段唱腔后甩的一个总的唱腔。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蒲剧唱腔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制约文艺事业因素的消除以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蒲剧迎来了新生,不仅大量传统的蒲剧作品重新被搬上舞台,也涌现出了许多新的蒲剧作品。同时,蒲剧唱腔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4]。首先,广泛汲取其他剧种的唱腔因素。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剧种间的交流、互动,蒲剧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与兄弟剧种,如晋剧、豫剧、眉户戏、碗碗腔、秦腔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并汲取了其他剧种中的唱腔艺术。举例而言,《土炕上的女人》中的“我时长萦绕心间间”的唱段就吸收了秦腔的唱腔,而《关公与貂蝉》中貂蝉的唱段则受到了评剧的影响。其次,演唱方法的改变。以往蒲剧表演场地条件较为简陋,缺乏现代化的设备。为了保证演出效果,让每一个听众都能听清楚,演员必须咬字坚硬,并形成了铿锵有力的发声习惯。改革开放后,蒲剧的演出条件大为改善,大量现代化的设备,如扩音设备等被应用于舞台表演中,传统的发声方式已经不再适宜,因此,演员们逐渐改变了蒲剧的演唱方法,从流行音乐中戏曲经验,由此带来的效果便是唱腔更加地优美自然。不仅如此,演唱方法的改变对蒲剧唱腔旋律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蒲剧唱腔艺术的特征
(一)富有变化的调式调性
蒲剧的调式调性主要分为两类,第一、五声调式变化。五声调式变化共有两种,均以三个骨干音为支柱。一个是多羽音的五声徵调式。这一调式在三个骨干音的基础上,添入了羽音和角音,能够体现出蒲剧婉转、流畅的特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唱段为《苦炕上养孤儿苦度时光》。唱段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全部出现,类似的还有《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等唱段上。另一个是中立音的五声调式,这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五声调式。中立音的五声调式在三个骨干音的基础上,加入了清角和变宫两个音,审美特征和多羽音的五声徵调式有很大的差别,具有非常浓郁的晋南风情。中立音的五声调式的代表性唱段有《对神灵不由我血泪滚滚》等。第二、七声徵调式。七声徵调式是传统五声调式与中立音结合的产物。在此类调式中,一个八度内会包含所有的自然音程,而在两个八度内,一些音程会反复出现,当然,这些反复出现的音程主要影响的是音域而非音响效果。七声徵调式的代表性唱段主要为《猫猫莫悲伤》。调式调性对戏曲的审美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蒲剧的调式调性既有严整性的一面,也富有色彩上的变化,具有民族性与区域性统一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蒲剧唱腔艺术的魅力。
(二)丰富多样的润腔技巧
润腔是戏曲唱腔中的一种美化、装饰技巧,我国地方戏曲众多,几乎所有的地方戏曲均有润腔技巧,并且,受区域差异的影响,不同戏曲的润腔技巧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5]。从大的角度而言,蒲剧的润腔技巧共有两类,首先,唱腔中的润腔。滑音是蒲剧唱腔中最为常见的润腔方式,在快速演唱中,滑音一般用于丑角演唱,且以装饰音的滑音为主,能够形成诙谐、幽默的效果,而在慢速演唱中,滑音一般和哭腔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形成悲戚、哀伤的效果。可见,作为主要的润腔方式,滑音产生的效果和演唱的速度快慢有很大的关系。除了滑音外,倚音也是蒲剧唱腔中的主要润腔方式。蒲剧唱腔中的倚音有很多中,尤以小六度的徵---变宫下行倚音居多。这种倚音完美地体现了蒲州方言的语言音调,具有婉转、柔和的特点。蒲剧《黄鹤楼》中也有一种不同的倚音润腔方式,即以骨干音为倚音的润腔。其次,念白中的润腔。念白中的润腔主要为单子的语调变化,最为常见的便是拖腔的使用。拖腔的使用使得念白中的单字具有了旋律化的特点。念白中还有一种连调的润腔方式,这种润腔方式是对念白音乐旋律起主要制约作用的润腔方式,和戏曲演唱中的旋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多样的润腔技巧极大地提升蒲剧唱腔的艺术表现力。
(三)高低起落的唱腔旋律
蒲剧唱腔艺术旋律具有高低起伏的特征,而高低起伏的唱腔旋律也是蒲剧唱腔艺术独特审美效果形成的重要因素,使得蒲剧在具有慷慨激昂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具有跌宕起伏的艺术魅力。以经典曲目《白蛇传》为例,唱腔第一句为蒲剧慢板最为常见的开头,以宫音起唱,而实际的音高则在小字二组的g音上,并跟随着骨干音下行,至于第二个字,则落在了骨干音徵上,实际上的音高则为小字二组的d音。第三字移高八度,后面的字则在此基础上,围绕着八段上下旋绕,形成了跌宕、婉转的效果。蒲剧唱腔艺术虽然总体上以高亢见长,但起音并不一定高,而在后续的发展中,也会呈现出高低起伏的特点。比如《黄鹤楼》。《黄鹤楼》起音不高,第一字为小字一组的d起音,但第三字则快速大跳到小字二组的g音上,同时,在第七字后,有做了再次的大跳,将蒲剧唱腔艺术中慷慨激昂的艺术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高低起伏的唱腔旋律赋予了蒲剧以慷慨激昂为主要特征,又具有百转千折婉转之美的品质。
(四)鲜明浓郁的方言特色
地方性、区域性是我国地方戏曲最为显著的特征,蒲剧作为地方戏曲的一种,同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蒲州方言对蒲剧唱腔的影响。声腔与语言的关系历来是戏曲届讨论的最多的内容,一方面,地方戏曲的声腔以语音的自然属性与形成基础,另一方面,语言结构也会对戏曲的唱词结构产生影响。念白是一种独特的唱腔形式,介于唱和读之间,蒲剧中的念白为蒲白,最能体现方言与唱腔的关系。并且,与其他剧种的念白相比,蒲白具有更高的乐音高度,也更能体现出念白的音乐特点。蒲白采用的是蒲州的方言,在发音吐字上与日常生活相似,但在调上却有一定的差别。受蒲剧自身整体调门较高的影响,蒲白的调也高于日常生活中的方言。声调是蒲州方言和蒲白声调变化联系的媒介,根据传统音韵学的分类,音节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大要素,其中,演唱的唱腔多和声母、韵母关联,而声调则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规律性。蒲白的声调与日常生活中蒲州方言的声调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许多字在蒲白与方言中,读音相近乃至相同,但调高与调值却不同。对此,韩晓丽将蒲白视作夸张化的方言,这种夸张化的方言既保留了蒲州方言的基本特点,具有地域特色,也具有戏曲艺术自身的音乐性[6]。
结 语
唱腔艺术是蒲剧艺术的精华内容,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和民族风格。蒲剧唱腔艺术在传承中既有延续性的一面,也有变革性的一面,而对唱腔艺术的深度解析则是把握蒲剧艺术审美风貌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