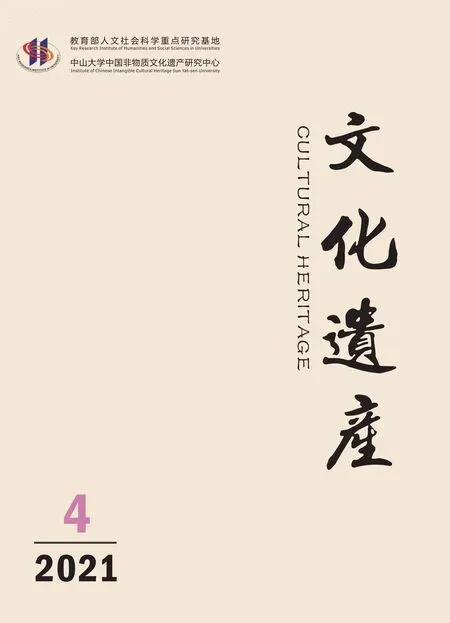论《格萨尔王传》中藏族先民的生态意识
方玮蓉 马成俊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生态文明观念的塑造愈发成为世界性的重要课题。自古以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民族都要面临来自极寒天气和高海拔地理环境的巨大挑战。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先民通过反思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繁衍的关系,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这种纯粹朴素的意识奠定了万物有灵论的基础。被称为藏族百科全书的《格萨尔王传》正是藏族先民生态意识的重要载体。它通过英雄的视角描绘藏族先民对自然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认识,记录他们的生存智慧,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想,值得我们作深入挖掘。
一、问题的提出
藏族先民的生态意识是部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群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平衡部落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产生,进而成为藏民们长期的一种生存模式。这引起了人类学者的极大兴趣。
基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既往学者关注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态保护区理念中的体现及其实践研究;(1)李然、李兴军:《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与实践研究——基于云南省环州大村的人类学考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有学者从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出发,审视人类与环境的重构关系,意识到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路径;(2)马莉:《审视与重构:人类学生态进路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20 年第 1 期。也有学者进一步深入到藏族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开展环境保护观念的相关研究;(3)曹津永:《生态人类学视域中的藏族垃圾观念与垃圾处理——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还有学者从非遗保护的视角,审视《格萨尔王传》的文化意义,通过对比其与《荷马史诗》中先民对牛神崇拜的不同方式,挖掘自然和文化生态在东西方区域的差异与不同。(4)刘代琼、张云和:《生态人类学语境下古藏族与古希腊的牛崇拜——基于〈格萨尔王传〉与〈荷马史诗〉的表述》,《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但是,这些研究均未意识到《格萨尔王传》中蕴含的藏族先民的生态意识。
本文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对《格萨尔王传》中关于生态保护意识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梳理,以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开展理论分析,进一步阐释藏族先民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万物有灵:古代藏民生态意识的源起
万物有灵蕴藏在古老藏族先民朴素的生态意识表达中,这一观念在《格萨尔王传》中得以传承,这种稳定的部落文化以文学创作和世代传唱的方式保留下来。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广泛流传在青藏高原。藏族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从古老先民开始积蓄了很多生存智慧,这个古老的民族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万物有灵”是这一套地方性生态知识的核心。苯教和藏传佛教作为藏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中的思想观念,认为山川河湖树木都是有生命和灵魂的,把自然物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量的对象而加以崇拜,客观上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
“万物有灵观”起源于藏族先民对自然界最初的认识。这种信仰从内心外化为对身边一切事物的崇拜,如对日月星辰的膜拜、雷霆发怒的恐慌、山川大河的敬畏、还有对虫鱼鸟兽的呵护,等等。先民们认为世界万物都有主宰,不能冒犯这些寄托于万物之上的神灵,对这些灵魂信仰的崇拜,逐渐演化出对自然的崇拜,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崇拜之神是和平的。另外一种意识是将自然界视为强大的威力,在这种充满不可制服的力量的环境中,人们为了规避风险,平安地生存下去,认为所有的大山、河流、风雷霹雳等都必须敬畏,如有冒犯不敬,便会受到雷神、水神和山神的惩罚。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屈从于万物,因为在那时的人们看来,万物之灵盛怒,便会导致族群甚至人类的整体消亡。这种纯粹朴素的原始认知,正是后来生态保护意识形成的根源。
万物之灵不仅具有上述“自然事物之灵本来有之”的特征,而且具有“英雄神灵附体于万物”的特征。这在《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中有较为深刻的表达。如姜国的屈拉大将,便是将自己的灵魂寄存在一头野牛身上,从此牛便成为了这个大将军的守护神;萨旦王认为,将自己的灵魂寄放在一间铁屋里,这间铁屋便会保护他的灵魂。灵魂外寄于这间铁屋,外寄之物常常受到当地群众虔诚的保护。因为在他们看来,保护该物就是保护本体,如果寄魂之物受到侵害,则英雄生命必将垂危。为了不让寄魂之人的主体受到损伤,当地群众总是将那些被赋予了“灵性”之物保护得很好。此二逻辑相互交织,使得人界和神界也有了参与自然的能力,客观上使 “万物之灵”的存在空间变得更为广阔。
三、藏族先民生态意识的主要表现
《格萨尔王传》享有“东方荷马史诗”的美誉,它以宏大的历史叙事,细致地刻画了格萨尔从降临、称王、降妖到圆寂的传奇一生,在全面展现藏区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的大环境中,表达了藏族先民惩恶扬善的基本价值观念。它基于万物有灵观,演绎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原则、对神山圣湖崇拜的生态表达意识、以及反对不义之战的安宁生存诉求。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
神山圣湖崇拜的直接影响是对生态保护意识的接受和对破坏行为的拒绝,内心行为外化于行,从客观上达到了保护藏区生态环境的目的。英雄史诗对生态保护的意识,并不仅仅局限于神山、圣湖,也不因为品种珍奇与否而选择是否对动物进行保护,可以看出,藏族先民生态保护的原则具有普遍性和全局性。在这种系统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则影响下,形成了人与草山共生、人与动物共生的整体性地方生态保护知识。
1.人与草山共生
自古以来,草山与藏族部落的生计与生存都密切相关。人与草山和谐共生,这种生存智慧自古有之。《格萨尔王传·英雄诞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格萨尔7岁时与母亲一起,被叔父(超同)驱赶到黄河上游的一个叫玛麦的地方。但当格萨尔母子俩来到玛麦之后,发现这里的山上不像家乡那样富有生机,而是黑土一片。看到此番景象,格萨尔才意识到,玛麦遭受了严重的鼠害,山腰的茅草被咬断,大滩的草根被啃食,没有充足的食料牲畜被饿死,这是在草山被破坏后的生灵哀嚎之景。正是这番破败不堪的生态环境,让觉如有了坚强的毅力,他意识到必须战胜一切困难,打败破坏草场的鼠王,让渺无人烟的玛麦变成水草肥美、牛羊肥壮的草原。格萨尔看到这番景象之后,便有了人与草山共生的意识,必须保护好这块处女地。游牧民族以草为生和藏族先民世代生存于青藏高原,使得草山对于牲畜养殖和人居生存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性,直接关系着藏族先民的存亡。史诗不仅记录了藏族先民对草山生态意识的重视,同时也讴歌了保护和拯救生态的英雄之力。除此之外,在《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中,从另外一个侧面记载了先民们深深地懂得人与草山共生的道理。霍尔在部落出兵之前,都要告诉自己的子民,不允许破坏沿途行径中的一草一木,除必要的交战之外,也不允许破坏当地的林草植被。在他们看来,不论是岭国的树木,还是霍部的树林,都必须受到绝对的保护,部落之间的征战不足以成为破坏草山的理由。在人与草山共生的理念下,发展出森林资源是维持藏族先民生存基础的地方性知识。
2.人与动物共生
英雄史诗中有各种珍奇动物与史诗的故事情节相随相生,这些动物的特点是具有人的品格,是某些人物形象的化身,在史诗中融入此类情节的确增添了不少灵动的画面和温情的色彩。在《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中记载,霍尔国白帐王的妃子去世,以辛巴为首的大臣们开始商量如何给白帐王寻找更美貌的妻子。他们将寻妻之事分别派遣给三个小动物:红嘴鹦鹉小银鸽、花孔雀和黑老鸦。黑老鸦在岭国发现了如花似玉的珠牡(格萨尔之妃),便回来向白帐王禀报。白帐王欣喜若狂,乘格萨尔赴北地降魔之机,动兵入侵岭国,逼迫珠牡做霍尔的王妃。这时候,珠牡的三只仙鹤历经千难万险,血书格萨尔,与主人珠牡生死共存,这是万物有灵观在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正是因为动物有灵性,激起了人们保护它们的决心;同时动物的灵性也传递给人类,成为保护人类的使者。人与动物共生的观念,在格萨尔史诗中有着深刻的描绘,在万物有灵的驱使之下,神山圣湖被赋予灵性、动物与人也互通有无,二者之间并非主人和寄养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灵魂相应的两个主体。
(二)神山圣湖崇拜规则
在藏族先民看来,山乃万物之本,水乃生命之源,清清的雪山雪水养育了格萨尔岭国的臣民。这种朴素的生态意识在英雄史诗的吟唱之中世代流传,神山圣湖的保护内化为人们对生存的感激,通过人们对家园的热爱表现出来,这是藏族先民古老的生态意识的朴素表达。
1.神山
青藏高原地势雄伟,山川河流均有滂沱气势,为古老藏族先民所崇拜。在青藏地区的古老传说中,一共有9座神山,其中有4座分别位于卫藏(西方)、库拉日杰(南方)、沃德恐杰(东方)、羌塘(北方)四个地方(5)卫藏地区的雅拉香波、北方羌塘的念青唐拉、南方的库拉日杰、东方的沃德恐杰。,另有5座神山在外围呈环状保护着青藏地区(6)即玛沁蚌日(阿尼玛卿)、党沁顿日、冈巴拉杰、党沃月杰、雪拉居保。,这九大神山成为青藏地区的保护神。其中,阿尼玛卿雪山是青海省境内最高的一座。据《格萨尔王传·英雄诞生》记载,格萨尔的母亲有一夜熟睡于深山之中,忽然梦见自己与一个“黄人”交合,不久后觉如诞生,这便是一代天骄格萨尔诞生的故事。自此之后,生活在青藏地区的藏族先民认为,根据传说相仿的地理位置,把最高大的阿尼玛卿雪山奉为神山,而那个“黄人”便是阿尼玛卿雪山的山神,阿尼玛卿成为了岭国的保护山。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代藏族先民神山崇拜的生态意识。
2.圣湖
扎陵湖、鄂陵湖和卓陵湖在《格萨尔王传》中被描写成为“像三颗碧绿的松耳石镶嵌在滚滚黄河上游”。根据神山圣湖的自然崇拜思想,藏族先民形成了“不渔而食,不污染水源”的生态意识,可以说除了神山崇拜之外,圣湖的膜拜也成为藏族先民最原始的生存智慧。英雄史诗从天界篇开端,中间历经了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霍岭之战、姜岭之战、白岭之战等篇章,直到地狱圆满结束,几乎每一篇章都或多或少地对各邦国部落的山川河流进行赞美:
六条神河源于诞生地,象征六大福庆永不息。十大吉庆汇集在一地,人杰地灵谁人能与比。(7)徐国琼、王晓松翻译整理,降边嘉措、耿予方审核:《格萨尔王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53-54页。
黄河是岭国的生命之源,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岭国人民:“清清的雪水哺乳着岭国的臣民,淙淙的溪流浇灌着肥沃的草原”,“黄河是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源泉,岭国格萨尔大王和百姓,饮水就靠这水源。”(8)徐国琼、王晓松翻译整理,降边嘉措、耿予方审核:《格萨尔王传》,第127页。
《格萨尔王传》中有各个部落都以水美为荣耀,尤其是格萨尔部落所在的岭国,对其玛域水源做了充分的赞美,也对世代养育岭国臣民的黄河的生态地位有了朴素的认知。
(三)反不义之战的生存诉求
《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以下简称《姜岭大战》)讲述格萨尔称王之后,水草丰茂的盐海被姜国强占八年之久,格萨尔绝地反击,最终收复失地。在《姜岭大战》中,从天界到下界一共塑造了十位女性,这十位女性有的是岭国妃子,有的是姜国女子,也有的是天上神灵,但是这十位女性身上都拥有着渴望和平、和谐与敬畏自然的共同品格。
1.敬畏自然
阿尼玛卿神山是格萨尔岭国的守护山,外敌既不可以参拜,更不可在神山上设立祭坛。在《霍岭大战》中,就记载了霍尔部落与格萨尔岭国部落之间因祭祀供奉阿尼玛卿山神一事而引起的战争。在《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的藏族先民看来,祭祀神山意味着战争的胜利,神山是权力的象征。基于此理念,霍尔部落在阿尼玛卿神山上设立祭台冒犯了格萨尔。格萨尔立刻率兵封锁了所有通往雪山的道路,出兵捣毁了霍尔建立的祭坛,同时声明不允许任何部落在神山上设立祭坛,以武力的方式表明不允许阿尼玛卿神山再遭到任何破坏的立场。
2.对自然的赞美
从英雄史诗《姜岭大战》出发,以史诗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为视角,分析她们在面对自然、人类和战争时的态度。史诗开首赞颂姜地的富饶与和平:
在花花岭国的南面,有个地方名叫姜地,人们又称它为穆布姜。姜地,天空无限广阔,姜地的山峦连绵不断。无垠的坝子前面,雪山犹如玉龙横空,终年不化,是个与仙境没有什么差别的地方:那里地下埋藏着无限宝藏,国土上生活着无数美女……叫人羡慕的稀奇珍宝,充满仓廪;肥壮的牛羊马匹,遍布草原。(9)徐国琼、王晓松翻译整理,降边嘉措、耿予方审核:《格萨尔王传》,第1-2页。
就连姜萨曲钟为代表的姜国女子,免使“雪域众生利益受损伤”,也忍不住高歌:
“玉龙宝露城”里花锦簇,天神的坛城难比这京都。国王的牛马布满大草原,羊群就像白云盖满山和谷。园中果树枝繁叶茂果累累,秋后鲜果丰收满仓库。(10)徐国琼、王晓松翻译整理,降边嘉措、耿予方审核:《格萨尔王传》,第36页。
女子们认为自己是生活在这种神仙世界的人,不欢迎没有道义的战乱。在《姜岭大战》中,女人的职责与“安分守己看好家园”相联系,若是家园异动,会自食其果,自找灭亡;这对于征战在外的男丁甚为重要,女人作为整个自然的一份子,守好家园不仅能使君臣同乐,平安无事,还会使富饶美丽的山川家园常在。
财务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财务人员在对企业资产核算时没有依法依规进行引起的。鉴于此,企业在清楚营改增给自身发展带来利好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控其给财务管理方面造成的潜在风险。有效防控财务风险必须建立在完善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上,只有通过制度的约束才能使企业财务管理进一步规范化。财务人员对企业的所有账目核算都必须亲力亲为,避免由他人代为核算带来的账目偏差。平日的财务管理过程中,财务人员要严格按照政策法规的要求来开展工作,熟悉所有业务流程,杜绝违法违规情况的出现。
四、藏族先民生态意识的客观作用
《格萨尔王传》展示了藏族群众对自然界的认识,从客观上塑造了藏族先民关于生态保护意识的观念,传递着先民们早期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11)李黛岚、白林:《生态美学下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研究》,《贵族民族研究》2014年第11期。这种古老而又朴素的生态意识,通过禁忌的形式口耳相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客观上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12)[英]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阎云祥、龚小夏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7-58页。。
(一) 山水崇拜,相对完整的小型生态系统
每一座神山都有自己管辖的区域,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存在的土壤,《格萨尔王传》的若干篇章,均体现出藏族先民山水崇拜的理念,这从客观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山水内循环,进而达到了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目的。藏族先民的生态保护智慧就在于,它并不是对某一项事物的刻意保护,也不是对某一项行为的单独强调,而是一种理念。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的保护。如神山圣湖的崇拜,就会拒绝对于一山一湖可能造成伤害的所有行为。在他们看来,山是神山,水是圣水,那么山上的花草树木,水里的虫鱼鸟兽皆为需要保护的对象。在神山圣水崇拜的生态意识之下,发展出一系列规范人类行为的禁忌规则。可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些禁忌规则,而非某一种宏观的叙事理念。如,藏族先民会教导自己的儿孙,不许将尿置于山泉之源,这样会遭到报应;更不能随意弯折树木,山神会大怒;开采矿山,人会遭不幸。
总之,山水崇拜是环境保护理念最直接的体现,也是藏族先民最直接的生态情感表达,这使地方性生态知识在维护小型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上有序地延续下去。这是藏族先民生态意识表达的关键。
(二) 万物有灵,通过禁忌达到环保目的
“万物之灵”是藏族先民对自然界生存法则的智慧总结,这种纯粹朴素的原始认知,正是后来生态保护意识形成的源头。在万物有灵论之下,草木虫鱼鸟兽被赋予了神性,这种神性或自天而降,或自地而来。正如前论,万物有灵之物要么被认为是自始神力,这种神性是人类所不能侵犯的,直接地达到了保护山川湖泊的目的;要么被认为是英雄之灵寄托于某物,这种灵性需要人类的守护,只有平静祥和的环境才能使得寄托之灵安详,间接地实现了保护生态万物的目的。这些神性形成了很多禁忌:比如“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上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13)梁艳:《论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中的地位及作用》,《甘肃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弗雷泽在《金枝》中强调:“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相互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14)[英]弗雷泽著、汪培基译:《金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6页。藏族先民生态保护禁忌中的万物有灵论观念的形成,正是弗雷泽所论述的相似律和触染律法则在生活中的实践。
总之,万物有灵是藏族先民生态意识表达的源起,基于此发展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引发出神山圣湖崇拜的生态保护意识。万物有灵论指导人们行为,最终通过禁忌的方式形成地方性生态环境行为规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达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客观上起到了生态保护的效果。
(三) 众生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格萨尔的降临,在人界、天界、地界的关系中成为“三神”化身,但是实际上格萨尔与万物众生之间的关系,均可视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15)索南措:《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传播特征》,《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在传统的人界或天界之中,均存在等级和边界,只有在万物混沌之时才是所有生命的开始,也是众生平等之处。但是《格萨尔王传》通过万物有灵论,弱化精神、肉体和自然之间的疏离感,赋予自然主体性,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构造出带有青藏高原和藏民族特色的地方性生态知识系统,为生态环境保护营造出“众生平等”的良好氛围。(16)杨福泉:《〈格萨尔〉所反映的纳藏关系考略》,《西藏研究》2009年第6期。以生态整体理念来打造生态观,这与现代的理念是非常接近的,是现代生态文明观形成的基础。
总之,《格萨尔王传》表达的自然主体性,通过众生平等来刻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处模式,是提升地方性生态知识的重要阶段,生态美学理论由此升华,弱化人类主体性,在人与万物共生的环境中刻画生态文明思想,这也是从藏族先民的朴素生态意识表达中汲取的营养。(17)贾芝:《中国史诗〈格萨尔〉发掘名世的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五、救赎与惩罚:古老的地方性生态智慧
从地方性整体生态观念出发,敬畏与禁忌贯穿着《格萨尔王传》九十四部曲的始终,万物有灵引导下的自然崇拜让人们敬畏自然的山川圣湖,热爱家园的一草一木;反之,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些古老的生存智慧是藏族先民生态意识的体现,更是地方性生态保护知识体系的原则,但在处理复杂的现实社会与自然关系时,尤其是在处理冲突性矛盾时,演绎出以下两种特殊规则,它们共同组成了《格萨尔王传》中藏族先民生态意识表达的完整体系:
(一)年少无知,亦受惩罚
敬畏与惩罚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惩罚可能来自现世,无知与冒犯也要受到惩罚。比如在《格萨尔王传·英雄诞生》中吟诵的,忽然有一天,神灵附体于觉如之身,告诉他,选择帽子、衣服和靴子三样东西:
现在我需要一顶合我头的帽子,合我身的一件衣服,合我脚的一双靴子,得不到这些东西是不行的。(18)参见徐国琼、王晓松翻译整理,降边嘉措、耿予方审核《格萨尔王传》,第127页。
觉如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先到色玉日拉杀死了三只羚羊,用羚羊的皮毛做了一顶毡帽;到吉本犊牛场杀死了七只牛犊,做了一身衣服;最后,在马场杀死了白额妖驹,做了一双靴子。当时的觉如并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岭国神灵。无知的他欣喜地穿戴好得到的服饰,有时候去山上捕鹿摘取鹿茸;有时候到滩上用石头打黄羊。觉如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岭国部落的非议,因此遭受了惩罚,岭国国王把觉如母子从岭地驱逐出去。这便有了前述玛麦草场的英雄史诗。这个故事中的觉如是爱岭国的,同时也是敬畏神灵的,他的行为本意并非伤害岭国的一草一木,在敬畏之心与冒犯之举并存时,藏族先民的朴素情感选择了惩罚。
可以说,万物有灵的智慧是衍生其他生存智慧的第一层位阶,是元意识。在万物有灵观之下演绎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原则、神山圣湖自然崇拜的生态意识表达、以及反不义之战的安定诉求。这三项规则共同支撑起了地方性生态知识体系的第一层位阶。地方性知识体系中的第二层位阶,便要解决“敬畏之心”与“冒犯之举”并存时,该作何处理。《格萨尔王传·英雄诞生》这部曲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将年幼无知的觉如及其母亲赶出岭国,以此谢罪。
(二)因爱受刑,地域救赎
在英雄史诗中,八十八岁的格萨尔在闯了一百零八次磨难之后圆寂。流动的史诗是《格萨尔传》被称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神秘的地方。每一个地方的格萨尔藏戏在刻画和流传的时候,都有细微的差别;甚至每一名吟诵艺人、觉藏艺人都有不同的版本。在这一百零八次磨难中,耳熟能详的便是《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姜岭之战》《霍岭之战》和《地狱救母》等篇章。实际上,在上文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这些文本中包含着古代藏族先民朴素的生存智慧。但为地方性生态保护体系的完整构建,仍需探索《格萨尔王传》的其他篇章。
《格萨尔王传·阿德勒姆》记述的生态规则位于地方性生态知识体系的第二层位阶,揉合了爱、罪、赎三元素,填补了第一层位阶中规则与伦理冲突时不知该如何处理的漏洞。《阿德勒姆》是在整部格萨尔史诗的倒数第二章。阿德勒姆是跟随格萨尔征战沙场的唯一女将,她骁勇善战、对格萨尔忠心耿耿、对岭国热爱坚守,正是这样一位将领在跟随格萨尔征服各邦国的过程中,杀戮了很多生灵、也造成了很多地方的破坏,在史诗中,阿德勒姆一生追随格萨尔王征战沙场,战无不胜。可唯独这一次,阿德勒姆在格萨尔离开岭国之后惨遭杀害,这也是“常胜将军”一生中唯一的失败,杀戮与破坏之罪使其坠入地狱。
古老的藏族先民生态意识在这里彰显,即杀戮生灵,破坏环境,必将触犯神灵,受到地狱的惩罚。这是古老地方性生态知识体系的第一层次位阶。但是故事并非到此为止。当格萨尔征战归来,发现阿德勒姆不在岭国,派人找寻后才发现她已坠入地狱。此刻,格萨尔一跃快马,飞驰至阿德勒姆身边,经过重重磨难,格萨尔和阿德勒姆浴火重生。在古老藏族先民的生态意识中,处理复杂事务往往加入了英雄之力,这是一种以正义为导向的生态观,用正义救赎罪罚,成为了地方性生态保护体系的第二层位阶。
结 语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通过反思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繁衍的关系,总结藏族先民的生存智慧,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轴心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体系。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阐释古代藏族先民在人与自然关系时,包括均以“万物有灵”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性知识架构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本原则演绎出三条生态法则,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原则、神山圣湖自然崇拜的生态意识表达、以及反不义之战的安定诉求。这三条生态法则蕴含着反不义之战、众生平等和山水崇拜等生态意识,并通过禁忌规则,从客观上对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念是通过禁忌达到了环保的目的;山水崇拜的生态意识有益于塑造一个相对完整的小型生态系统;而众生平等的生态理念从客观上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这三条生态法则与万物有灵的基本原则共同构成了藏族先民在处理生态环境关系时的第一层位阶。但是,基本原则与普遍规则无法解决带有伦理冲突的生态关系问题。作为弥补,藏族先民的生态意识在地方性生态知识体系中聚焦于第二层位阶,则蕴含着古代藏族先民处理复杂事务的智慧,其中包括在主观不知和客观破坏之间,选择对破坏行为进行惩罚的法则,以及以正义为导向的生态观,救赎生态之罪的纠偏性智慧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