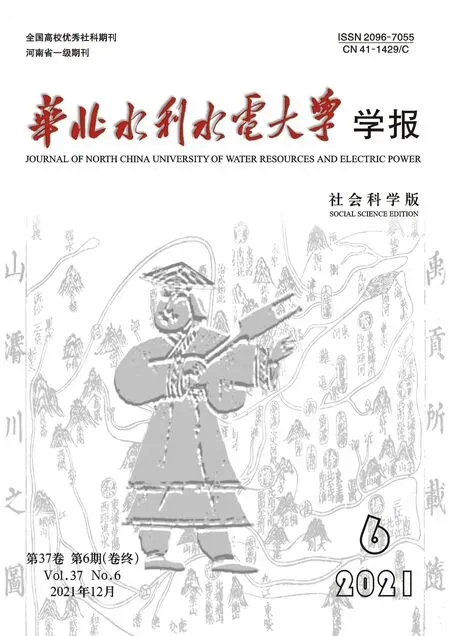翻译叙事不仅描述现实也在建构现实
——赵文静教授谈改写及其多种翻译形式
张艳波,赵文静,2
(1.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2.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赵文静教授的专著《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是国内最早研究改写的多种翻译形式和广义翻译的著作。她主持翻译的国际知名学者Mona Baker的TranslationandConflict(《翻译与冲突》)于2018年获得首届英华学术翻译奖。她对翻译中的改写研究很有建树。因此,张艳波采访了赵教授,请其详谈改写及其多种翻译形式,从而澄清翻译界对改写的误解。
张艳波(以下简称“张”):赵老师,在刚结束的第五届“理论翻译学及译学方法论”高层论坛上,您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分析Mona Baker主持的重大项目“‘知识谱系’的新视角、新方法”,并由此展望理论翻译研究的新动向。您提到,“知识谱系”的语料库收入了广义翻译的多种形式。20年前您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研究多种改写形式。然而,正如Baker先生在访谈中所讲,这些形式至今依然被忽略[1]。所以,今天主要想请您谈谈您的专著及改写和多种翻译形式。
赵文静(以下简称“赵”):好!很高兴有机会一起聊聊翻译研究。
张:您的专著《翻译的文化操控》荣获2006年河南省社科研究成果奖。这本书还被最具权威的《劳特利奇翻译百科全书》作为“rewriting”(改写/重写)词条的实例收入第二版及第三版的参考文献中。我们先聊聊这本书好吗?
赵:这本书基于我的博士论文。可以说它是国内首次将“rewriting”的多种形式纳入理论翻译研究的专著。Baker先生为我的专著所作的序对这项研究的独创性和研究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赵文静对于胡适案例的研究,从多个方面满足了理论翻译学研究的需求,为翻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首先,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极为重要的时代及其文化的精彩掠影。其次,它从历史的角度具体论证翻译的概念历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能与多种改写实践截然分开。此外,通过研究胡适因创作、改写和翻译而成名的过程为研究理论翻译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绝好的案例,证明翻译总是以多种方式植根于复杂的社会语境之中,并且受到一系列文化和政治势力的影响。该书在详细地描绘叙述一位极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对翻译学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2]。
张:这本专著研究多种翻译形式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变革的影响,是国内较早研究广义翻译以及翻译的社会性的著作,很有超前意识。当初您是基于什么考虑选定这个题目的?
赵:谢谢你的美言!我最初报考博士时递交的研究计划是从语言学视角来对比分析David Hawkes(大卫·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两个《红楼梦》译本。
在曼彻斯特大学读博期间,我逐渐感悟到:目前翻译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字层面的对应,而开始关注翻译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我陷入选题困境:是继续做准备了很久的课题?还是改题以便跟上研究的最新动态呢?那是2001年,当时国内外绝大多数翻译研究都仍在关注语言层面的问题,翻译与社会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很少。另外,导师也不大同意改题,提醒我改题风险很大。焦头烂额之际,我突然想起读博之前看过的翻译史研究方面的几本新书,马上让先生把书寄到英国。刻不容缓,等书的同时,我夜以继日地在图书馆查阅相关的理论资料,比如James Holmes(詹姆斯·霍尔摩斯)的宣言书式论文“The Name and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76),Theo Hermans (西奥·赫曼斯)主编的TheManipulationofLiterature(1985)和他的专著TranslationinSystems(1999),当然还有Andre Lefevere(安德鲁·勒弗菲尔)的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s(1992)。通过阅读这些文献逐渐形成一个轮廓后,我要改题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我把这些资料进一步分析、综述,把论文选题逐步锁定为“语际改写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变革”。
我向导师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这个研究在当时是颇具新意的:首先,大多数研究仍聚焦在语言的层面看翻译,而它开始关注翻译的社会效应;其次,所研究的翻译活动不再局限于狭义的翻译,而是 Lefevere提出的“改写”——翻译的多种形式,包括文学评论以及以创作的形式所做的隐性翻译,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易卜生主义”; 此外,所选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翻译活动最频繁的时段之一。)听了我的阐述,导师同意我更换选题,并决定提供经费让我回国查阅相关资料。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开题报告不仅顺利通过,还获得了曼大文科非常难得的奖学金。
从改题的经历,我总结出两点:第一,听讲座或与导师学术聊时要努力捕捉新信息;第二,研究离不开平时的积累,所以平日里一定要多读书并做好笔记。
张:您前边提到Lefevere的改写理论。您认为改写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赵:改写理论 “将多种文本实践形式归入‘翻译’名下并将它们放在更宏观、更复杂的研究背景中,这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3]。换句话说,除了狭义的翻译,“改写”将更多的形式纳入了翻译研究,比如我的专著中列举的文学评论、仿作、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选读、百科全书以及外国作家小传等。事实上,很多情况下,了解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恰恰是通过上面提到的这些改写形式,而不是原创作品。外国作家与作品的形象也是通过大量的改写形式建立的。文学史与选读就存在选谁不选谁、选哪些作品的问题。这些都会对翻译史有改写效果。
张:但这个理论曾遭到质疑或批评。他们认为:翻译就应该忠于原作,怎么能改写呢?他们担心这会误导译者“胡译”“乱译”。对此,您怎么看?
赵:我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对于学术理论持批评态度、有挑战精神值得提倡。Lefevere本人不擅长下定义,加上他英年早逝,这个理论的确还有它的弱点。但上述质疑说明他们对“改写”根本没读懂,只是望文生义。翻译理论分为规定性和描述性。规定性翻译理论是以原文为中心提出翻译应该遵循的规则或符合的标准,告诉译者应该怎么做。在这些质疑者看来,所有的翻译理论都应该富有指导意义,都要以能否指导翻译实践来评判其正确性和实用性。但描述性翻译研究则完全不同,它是从认知和哲学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不以原文为重心,而是以翻译的结果为研究对象;它并不制定翻译规范,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对翻译现象做客观描写和个案分析;它通过对翻译产品、翻译过程以及功能的研究,再现译者在翻译中的种种决策和选择,进而探索某一时期某一文化系统中制约翻译的因素。改写理论就属于描述性翻译研究。简单地说,改写是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将它置于目的语社会的政治、思想意识、文化等大环境中去考察翻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它的目的不是为翻译制定规范,做价值判断,而是客观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描述、分析翻译活动有哪些呈现的方式,阐释译作改动的缘由和作用。按照规定性翻译理论,这些改动显然不符合翻译规则。然而,改写理论的功能之一就是探讨这些“不合乎规则”是否合理。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称作“改写”的都有其原因,是译者有意而为,有些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译者在关注原作和原作者的同时充分考虑翻译所服务的另一端:功能和传播效果。同时译者也受到译入语政治和文化的制约。这与胡译、乱译完全扯不上。那些质疑者显然是在用规定性理论规范描述性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改写理论的质疑,更多的还是源于对“忠实”的误读。将改写与“忠实”完全对立起来,误以为忠实就必须使原文完好无损,改动了就必然不忠实。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就很难有合格的翻译,因为译者和译文受到来自新语境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如新的语言、文化和受众,特别是当今的网络文档。比如,在新闻翻译中,很难辨认出所谓的原文(original),我认为很多时候只有源文(source)。因此对等翻译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正如Bassnett在她的TranslationinGlobalNews中所说:……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只不过是语言转换这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包括编辑、改写、重组及整合——中的一个成份。可想而知,新闻经过这些过程进入新的语境时,原文和译文的对应早已荡然无存,所以才有transediting(编译)。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若是有强弱之分,也会出现改写。比如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因为文化优越感,在翻译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集《鲁拜集》时,就有些随意。即便是抛开政治和文化因素,译者也会受诗学的制约,面对新老受众不同的已知信息、阅读习惯与审美期待,对原文也难免做出改动。虽然大家都认可,翻译涉及原作者和受众,但一直以来过多关注的是原作者,而极大地忽略了受众。如果从忠实于读者,忠实于效果这个层面上看,很多改写就都可以理解和接受了。比如,翻译《骆驼祥子》的Evan King(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他对刚刚经历了二战的美国民众的心理非常了解,所以就将《骆驼祥子》改为喜剧结尾。但如果只顾与原文对应,机械地忠实于原文,像老舍自译的那样,翻译有可能根本达不到传播的目的。总而言之,改写与“忠实”并不冲突,更不是随心所欲地乱改,而是为适应新文化、新受众等需要而做出的必要改动。
其实,对原作改写从人类有翻译活动就开始了。无论是佛经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都无一不伴随着改写。林纾、严复的翻译也通过增加注解和评论为读者的解读作导向。凡事都有动机和背景,翻译也不例外。目的语社会的政治、思想甚至经济背景都会对如何理解和传播原文造成影响和制约。在翻译实践中,无论口译还是笔译,我相信,译者的初心都是忠实地再现原话或原作信息。但翻译也是在叙事,起着建构现实而不仅仅是描述现实的作用。正如Baker所说,因为“学问认识从来就不是客观的,毫无视角的,……所有的景象都是有观察角度的,完全独立和客观的叙事几乎不存在”[1],译者也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语境中。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你会发现,有诸多因素,比如诗学、思想意识、出版商或委托人的要求等制约着译者,使你不得不对原来的内容做改写。
张:也就是说,其实改写现象由来已久,只不过是Lefevere为它正了名,并将它作为了研究对象。这些现象只存在于文学翻译还是所有类型的翻译?
赵:为改写正名,to be legalized?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以往凡是对原文做改动的译作就一定会受到负面评判。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 受权力、政治、文化的强势和弱势等影响,文学翻译中历来存在改写。至于说是否只存在于文学翻译中,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翻译研究领域所说的“文学”不仅指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这样的狭义文学,还包括诸如宗教、新闻、法律、政治和学术著作等广义文学。改写现象不仅存在于狭义的文学翻译中,在广义的文学翻译中,甚至在科学文本的翻译中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颇多成果,比如Baker的《翻译与冲突》中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实例。
张:哦,原来翻译中有这么多改写啊,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今后就不必跟学生过多地强调忠实于原文了?
赵:问得好!但不能一概而论!给本科生讲翻译实践时,必须强调忠实于原作,因为这时候我们是在培训译者做翻译实践,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运用规定性翻译理论训练学生如何能够尽可能准确地把原文内涵展现出来。这就是翻译的初心,对吧?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翻译”和“翻译研究”是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不少学者在翻译的定义和定位问题上有分歧,有时就是因为所论及的对象并不同。这一点,我在《翻译的文化操控》(2006)书中做过较为详细的阐释。读博期间,为了理清改写理论的来龙去脉,找到它的源头,我翻阅了所有相关的英语文献。我发现,随着人们对翻译理解的加深,翻译和翻译学的定义就需要不断补充。实际上,对翻译和翻译学的再定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并越来越关注文化、政治与权力这些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再定义很有必要。Maria Snell-Hornby (2012)就曾经质疑,在充满了facebook、 twitter 和Skype的全球化的今天,Bassnett 和 Lefevere 在20多年前对翻译的预言(定义)还有多大效力?近几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柴明颎两位教授也在组织做这件事:为翻译和翻译学再定义、再定位。希望更多的研究参与进来。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再定义或再定位的复杂性,若不能评估到位, 则很可能会出现以点概面的现象。比如,改写理论提出的几种形式,如果都归于翻译,就很难被接受,会被质疑,翻译的概念是否太过于宽泛?事实上,这是对翻译学下定义,也就是说,对一个阶段的翻译活动进行研究还应该涵盖这些内容,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出这个阶段翻译的全貌。
张:这样说来,改写理论还需要更深入的理解。
赵:对。改写理论有其不可替代的贡献,但不能说是完美的。改写理论受到Michel Fucault(米歇尔·福克)的影响,把翻译完全看成政治和社会行为,看作是权力斗争的工具,Lefevere在“译介”中极大地拓宽了“介”的范围。然而,在关注翻译中的仿作、评论与介绍等形式产生的社会效应的同时,忽略了翻译自身的语言学和美学接受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受Fucault的影响,改写理论过多强调翻译的政治和社会属性,从过去翻译只强调语言这个极端,走到完全不看语言而只强调文化的极端,矫枉过正,有时甚至模糊了译与介的界限。同样是关注翻译的社会性,语言学出身的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就兼顾到二者的平衡。
张:经过改写的文学作品接受情况如何?受欢迎吗?
赵:改写后的译本多数接受效果还相当不错。当年Evan King改写翻译的RickshawBoy(《骆驼祥子》)一经出版,连续几周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反而是老舍本人与另一位美国人一起重新翻译的版本(当然是“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效果并不如人愿。莫言的小说进入英语世界之前在情节上也经过很多改写,有的甚至结尾都改了,但接受效果大家有目共睹。动画片《花木兰》也是个很好的证明,它是经过改写改编的,但在国外很受欢迎。正如 Lefevere所说,非专业人士大多不看written forms (原作),他们更倾向于看rewritten forms(改写形式)(1992)。这一点对目前提倡的“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策有诸多启迪。对外译介中国文化的形式可以更多样化,而不只是狭义的翻译。可以考虑采用改写理论所包含的形式对外介绍文学作品、文学史、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中国文化……另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传播方式与渠道的多样化,可以节译、摘译后做成链接,做成twitter, 或者改编成TV series,以便更受欢迎,效果更好。
张:除了您的专著,您主持翻译的Mona Baker的TranslationandConflict(《翻译与冲突》)2018年获得了首届英华学术翻译奖。这是值得祝贺的。咱们简单聊聊这本译著好吗?
赵:好。这部翻译学专著的中文版能够得到业界的高度认可,我感到很欣慰。获奖之前,这本译作在国内就已经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首先,谢天振和潘文国两位翻译理论家、国内外著名学者分别为这本译作做的内容丰富详实的序以及穆雷与王祥兵两位翻译学教授2013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文章《学术著作翻译的理想模式——以赵文静中译本〈翻译与冲突〉为例》都对这本书的翻译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Baker是语言学出身的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研究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这本书是首次将翻译叙事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它的出版引起国际翻译界对战争和冲突环境下翻译叙事的高度关注,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战争中翻译所起作用的项目研究。另外,这本书的分析模式、结构安排、论证角度以及所采用的理论框架、选择的切入点又充分显示出它的跨学科性:不仅涵盖翻译学,还牵涉到叙事学、国际政治、社会学、话语分析和语言学相关学科。这一切都加大了翻译的难度,对译者自身的知识背景有了更高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点,翻译这本书并非我主动请缨,而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申丹教授写信邀约我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量接受的。我见证了整个成书过程,深知它的学术价值,也知道这意味着挑战自我。翻译过程中我特别谨慎,尽量将Baker想要表达的思想及其语言的妙处展现出来。的确花费了不少精力,还好,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
张:说到谨慎,我能理解,受托翻译自己导师这样一部学术著作,一定非常谨慎。想必您是亦步亦趋,紧跟原文不敢有半点改动吧?
赵:说来你可能不信,情况还真不是这样。作为译者,我的初心正是像你说的那样,想尽量忠实地再现原文的一切。Baker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她的语言风格清新晓畅,措辞讲究,恰到好处,学术英语严谨地道。书中引用的实例生动、渠道丰富:除了书本引用,还有选自荧屏的字幕翻译、美伊战争中散发的传单翻译、法庭实况翻译以及直接选自互联网上的新闻翻译。原作引用了大量的实例,涵盖了至少14种语言,原文本的写作风格迥异,所以在语言方面比一般的学术专著更难一些。为了将语言的形式、风格和意义都尽量“完好无损”地译出来,还真是下了大功夫。
然而,译者毕竟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机器,而是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遇到原文中有些内容在认识方面与自己的思想尤其是与目的语受众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冲突时,还真得改写。比如,Baker在第六章第五小节讨论“副文本的再定位”时举的例子中,香港短篇小说(英文版)的主编,在前言中描述回归后的香港时叙事颇为偏激。因此,出版社编辑与我商量,建议把整个小节删除。但是,如果全删的话就无法展示所论证的那个学术观点。经过与出版社沟通,有些内容直接删除,有些内容做了改写。
张:这些改动与原作者沟通、商量过吗?Baker是什么态度?
赵:这个改动并没有跟原作者提过,因为这里面有委托者和审查制度的约束以及译者的无奈,想必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Baker教授应该能够理解。你的提问本身就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译者有权不经同意改写原作吗?我前边讲过,其实译者最初不是要改,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不得不改,下面的例子会说明这一点。对于改写,不同的原作者也的确有不同的反应。《中华读书报》上曾报道:华裔作者Amy Tan(谭恩美)的SavingFishfromDrowningFish(《沉没之鱼》)当年由出版社聘请蔡骏“译写”后出版。蔡骏是国内著名的悬疑小说家,自然了解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与爱好,因此,对原作章节的顺序以及部分内容做了大幅度改写。当时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争议。后来谭恩美本人来大陆时,有记者专门就这件事采访她,告诉她《沉没之鱼》是先找人匿名翻译,然后又由蔡骏在译文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甚至打乱章节顺序改写的。谭恩美则表示:我不懂中文,无法挑选译者,只关心译出来的这本书是否受欢迎[4]。很显然,她并不介意对原作的改写,她关心的是译作的传播和接受效果。可以说,她的反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原作者对译本的态度。事实证明,这本译作是谭恩美中文版小说中最受欢迎的(2006)。其实,在国外获各类奖的中文小说在译成英文时也有很多改写。我们都知道,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把莫言、毕飞宇、姜戎等很多中国作家介绍到了英语世界。而葛浩文多次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在选材和翻译过程中他首先考虑的是读者和出版商的需求(是接受方而不是忠于原作)(2015)。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时,他做了大量删减。莫言的几部小说在翻译时也做了大量改写,《天堂蒜薹之歌》甚至连结尾情节都改了。姜戎和莫言对译者的改动表示赞同。但也有反对译者改写自己作品的。Evan King把《骆驼祥子》悲剧结尾改成了喜剧结尾,原作者老舍就极为不满,甚至为此还闹上法庭[5]。然而,不论原作者是否接受,这种改写一直都存在,而且哪种文化中都有,因为我们在用另一种语言通过说或写转换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新受众的背景知识、委托人的要求以及译者的动机等。也就是说,像其他叙事一样,翻译叙事也不是完全中立的。
翻译作为特殊的话语不仅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还穿越性地指向未来,也就是对未来也有影响。探讨这些话语在旅行途中产生的微妙变化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义翻译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