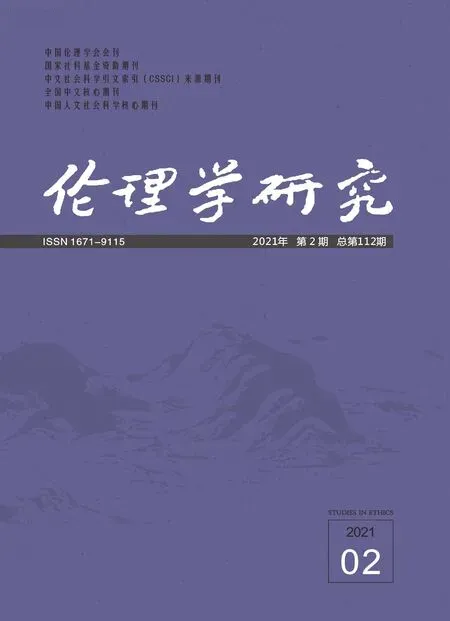朱熹浩然之气、道德认知与道德勇气述论
“浩然之气”是孟子人格修养论中的重要概念,孟子重“养气”工夫,其关于养气的言论在早期儒家中十分重要。朱子在《孟子集注·孟子序说》引程子之言云:“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1](P199)朱子对此章颇为重视,用力也较多,就此章“知言”“集义”“养气”等问题予以详细讨论,并将孟子所言诸多工夫系统化,使之与他所诠释的理学“格物穷理”的工夫相协调。同时,朱子对“浩然之气”的独特诠释也可以丰富对“气论”的认识,特别是他对“配义与道”的诸多论述,更是可以促进我们思考“气”与“德”的关系,探讨气的道德属性问题。
一、正气与浩气
《孟子集注》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言:“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1](P231)气,即是组成并充满人身体的物质构成,从质料构成看,“浩然之气”与“血气之气”只是一个气[2](P1237),并未有不同;从本来状态讲,它是“浩然”“盛大流行”的,但人若不加后天修养工夫,这气便会“馁”,也即“萎萎衰衰”[3](P654),孟子有工夫以养,才使此气“复其初”,恢复本来状态。
这里分了三个层次:本源上的浩然、失养后的萎衰、恢复浩然之气。关于本源上的浩然,《孟子集注》言:“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其体段本如是也。”[1](P231)从来源上看,人身上的气也即是“天地之正气”。《朱子语类》亦讲:“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盖天地之气,而吾之所得以充其体者也。”[2](P1241)这“浩然之气”与“血气之气”从来源上讲并无不同,这其实也即是《中庸章句》首章讲的“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1](P17),人之气从来源上讲是禀天地之气,“气,只是一个气”,只是从后天看,“从义理中出来者,即浩然之气;从血肉身中出来者,为血气之气耳”[2](P1243)。
此处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孟子集注》特将“浩气”与“正气”联系起来,与朱子所言气之偏正之“正气”有无关系,此“正气”当作何解?除“正气”“偏正”之气外,朱子对“正”与“气”还有一些表达,有时“正气”与理之常与非常有关,正乃常理之体现。这是从天地运化的角度讲气正,气正不正之与善不善可作好不好讲,亦可从“合理”与否看。此外,正气还与“生气”有关,正气是天地生生之气的体现,这可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角度看。这两种“正气”与禀气之偏正之正不完全相同。关于禀气偏正,朱子认为人禀正气,且“独得”,故全得天理,物不得正气,所以不如人“灵”。这里的禀气正与不正与禀气偏全意涵相同,而与讲理之常之正气、生气之正气不相同。但禀气清浊关系人的现实道德状态,而禀气偏正则与人物之辨有关,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全得天理而全具五常之德,纵使“枯槁有性”,但其所禀不全,故不似人为天地之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禀气偏正依旧具有道德属性。从这些来看,朱子处禀气偏正具有道德属性,他讲的“正气”都有一定的道德指向,“正气”与理的一些基本规定密切相关。偏正之正气与浩然之正气含义相似,浩然之正气其与“人”的禀气联系更紧。“至大至刚”是浩然之气的本来状态,而此“本”超越清浊厚薄等禀气状态,无论具体的清浊厚薄哪种状态,在本来状态上都没有差异,都是天地正气之分殊。
其二,朱子虽然讲“本自浩然”,但也讲“浩然之气,是养得如此”,不说“禀”得,《朱子语类》甚至有言“自不必添头上一截说”,“某直敢说,人生时无浩然之气,只是有那气质昏浊颓塌之气”[2](P1260),“本自浩然”与“养得如此”是否矛盾?其实朱子讲生时得此“正气”时,强调的是人一身之气的来源,浩气与血气自是人之禀气,当他讲“生时无浩然之气”,则从人现成之气的“体段”讲,从“现成见在”说,是为了突出“养”的工夫。讲人养得浩然之气,是突出工夫必不可少;讲天地浩然之气是突出人能养得如此,讲养的本来依据。故朱子讲:“至大至刚’气之本体,‘以直养而无害’是用功处,‘塞乎天地’乃其效也。”[2](P1253)
其三,此“正气”到得人身上就会“馁”,何以会“馁”?朱子特别强调“失养”,除此之外,还应看到“形”的作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时得此正气,缘何又“生时无浩然之气”。《朱子语类》讲“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衮来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盖气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恶也”[4](P68)。“衮来衮去”是指流行运化赋形成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气运产生不齐,故有昏明厚薄的差异。对于具体的人物来讲,必然有限定之形,在朱子看来,有形就有“美恶”,天地之正气“通”,而有形之气则“局”,理学常讲“形气之私”,朱子讲“气之体段,本自刚大,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蔽了他一个大底体段”[2](P1251),此浩气之所以馁,便是由于此形气的限定作用,正所谓“气只是身中底气,道义是众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气,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4](P1259)。而人之生必定有形,必定有昏明美恶之气,所以朱子就特别强调后天“养气”工夫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后天涵养澄治之功,人所具有的气就只是血气,而不能呈现出浩然的状态。
二、知言、集义与养气
人之气“善养”才能“复其初”,如何养得?孟子讲要“集义”。当然,孟子此章讲“知言养气”,“知言”与“养气”并列,赵岐注言“我闻人言,能知其情所趋,我能自养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气也”[5](P199),未将两种工夫联系起来,朱子《孟子集注》则明确认为两种工夫并非互不关联,而是密切相关:
盖惟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1](P231)
“知言”为“明道”,“养气”后可“行道”担大任,即所谓浩气“配义与道”。不明则不能行,不能知言则不能养得浩气,知言、集义、养气构成了工夫链条,而这其中以“知言”为主。朱子认为“知言只是知理”[2](P1235),“知言,然后能养气”[2](P1241)。《孟子》只是将集义与养气明确联系起来,朱子却认为知言、集义、养气在同一逻辑链条当中,故“欲养浩然之气,则在于直;要得直,则在于集义。集义者,事事要得合义也。事事合义,则仰不愧,俯不怍”[2](P1232)。朱子对《孟子》此章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断句,有其义理考虑。养气首先要以“直”养,此直对应“自反而缩”的“缩”的训释。而要做到“直”则须“集义”,做到“集义”,则需要“知言”,朱子讲“集义便是养气,知言便是知得这义”[2](P1245),他认为《孟子》此章的核心就在“知言”[2](P1270)。只有知道道理的虚实,“心”方可“帅气”而前。“知言”在本章的工夫链条中具有优先性。朱子认为做到知言,就可“浩气自生”:
若知言,便见得是非邪正。义理昭然,则浩然之气自生。[2](P1241)
浩然之气,须是识得分明,自会养得成……人自从生时受天地许多气,自恁地周足。只缘少间见得没分晓,渐渐衰飒了……若见得道理明白,遇事打并浄洁,又仰不愧,俯不怍,这气自浩然。[2](P1248)
人禀得天地之正气,若不得养,气便会“馁”,但如果能理精义明,血气便会转化为浩气。朱子讲知言先于养气,自然与孟子讲“志帅气”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孟子》的文本,而与其理学讲的“格物穷理”“已发未发”工夫有密切关系。《孟子集注》解释“知言”认为:“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1](P231)直接将知言讲为“穷理”,又讲“孟子论浩然之气一段,紧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学》许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2](P1241),直接将知言、养气对应到格致与诚意上。从朱子思想内在结构可以讲,知言可以对应“明善”“择善”,而“集义”则是积善、行善,是“固执”。当然,包括与《大学》工夫的对应是否严格等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可以看到,将“养气”对应“诚意”,是因为意是心之所发,朱子更多的是在“已发”层面上讲“养气”工夫,而知言则难应未发工夫。《朱子语类》讲“志动气,是源头浊者,故下流亦浊也。气动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浊了上面也”[2](P1240),此上流、下流当对应未发、已发。而这些工夫的对应,尤其是已发、未发的引入,则可提示我们来从新的视野理解血气如何转化为浩气、浩气的自生究竟为何意思这一问题。
第一,讲此气是自内而生,而不是外来,“自生”与“义袭”相对应,朱子讲“自家知言集义,则此气自然发生于中”[2](P1243),“须是集聚众义,然后是气乃生。‘非义袭而取之’,非是于外求得是义,而抟出此气也”[2](P1259)。知言、集义所“生”之气不从身体之外而来,是身体内原有的气发生变化而“生”此浩气。
第二,此“生”当为变化、产生之义,而非“无中生有”之生,将血气养成浩气,其实就是“变化气质”。《孟子正义》讲“生即育也,育即养也”[5](P202),此对“生”的诠释实与朱子一致。
第三,还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此“自生”,理解所谓血气转化为浩气的意涵。其实,“已发未发”的问题可以引出我们对朱子“道心”“人心”相关诠释的关注,朱子经常将浩气之生与“义理”之发联系起来:
气,只是一个气,但从义理中出来者,即浩然之气;从血肉身中出来者,为血气之气耳。[2](P1243)
道心发于义理,人心源于形气。朱子讲气则以为浩气为义理之发,血气只是形气之气,不受义理宰制。浩气、血气是一气,因由不由义理之发而有分。这里不讲“浩气自生”,而讲气发于义理则成浩气。可以认为,所谓的浩气自生,就是自家禀得的形气能受义理宰制,经过长时间的集义工夫,而成为浩气,这也正是血气转化为浩气的变化气质。《朱子语类》解《中庸》之一条更可佐证我们的讲法:
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养得则为浩然之气,不养则为恶气,卒徒理不得。[6](P1486-1487)
形气之善出自道心,形气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善恶,由于所发而有善恶之分,以道心主气,则气善。此浩然之气之养得、生得,当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而似乎不必从“理生气”的角度讲此浩气之生。
关于知言与养气的关系,还需注意,朱子认为“知言”方可“养气”,但他并不是要取消“养气”工夫的独立性,这与“气动志”有关。朱子认为孟子“恐人专于志,而略于气”[2](P1240),于是讲两边工夫,朱子讲:
“持其志,无暴其气”,内外交相养。盖既要持志,又须无暴其气。持志养气二者,工夫不可偏废。[2](P1239)
持志属内,知言亦属内,而“养气”则均从已经发用的层次来讲。朱子认为要内外交相养,如果“外”得不到好的修养,“内”就有可能受到影响。朱子这里讲的养气则更多地侧重“无暴其气”,即“知言”是积极的工夫,“养气”是相对消极的工夫,他讲“今学者要须事事节约,莫教过当,此便是养气之道也”[2](P1239)。知言、养气抑或持志、养气要“相夹着”[2](P1238)。当然,知言在工夫上具有优先性。
三、浩气体段
以上我们讲如何养得此浩然之气,那么养出的浩气是何种状态,其“体段”如何呢?《孟子》讲此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孟子集注》言:
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其体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缩,则得其所养;而又无所作为以害之,则其本体不亏而充塞无间矣。[1](P231)
天地之气本即是“至大至刚”的,而人通过修养养得的“浩然之气”与“天地之正气”则无二致,这也即是“复其初”。对于此浩气,朱子特强调其“刚”的一面:
浩然之气乃是于刚果处见。[2](P1247)
朱子认为浩气最重要的就是此“刚果”“刚大”,因此他并不太愿意将此“刚果”之浩气与气的其他状态等同,特别是强调浩然之气与气的“清明”等状态不同:
浩然之气,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说浩然,便有个广大刚果意思,如长江大河,浩浩而来也。富贵、贫贱、威武不能移屈之类,皆低,不可以语此。[2](P1243)
从气之本然层面讲,“正气”超越气的清浊厚薄,朱子突出此气的“广大刚果”与“刚勇”。他也强调浩然之气也不同于“夜气”:
夜气者,乃清明自然之气。孟子示人要切处,固当存养。若浩然之气,却当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之语看之[2](P1247)
清明之气不等于勇气,朱子特别强调浩气“勇”的向度,当然,这种气由于是养得的,故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
然人所禀气亦自不同:有禀得盛者,则为人强壮,随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随分做得出。若禀得弱者,则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养成浩然之气,则却与天地为一,更无限量
只是一气馁了,便成欿然之气;不调和,便成忿厉之气。[2](P1247)
浩然之气与“欿然之气”“忿厉之气”不同,此两种气皆是无养之气。养则可将先天粗暴、不好的气,变为刚大的浩然之气,如果无养,即使先天禀得意气、盛气,终究会“馁”。养得的浩气不是粗的气,当是一种精细之气。由于朱子强调此气之刚,故常以“气魄”讲此浩气在人身上的状态:
曰:“只是这个气。若不曾养得,刚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气魄大底,虽金石也透过了!”[2](P1243)
“气魄”此二字用得活泼,可见人有此浩气之状态。这气魄可以穿过金石,可见其刚。此“气魄”即是“仰不愧,俯不怍”“睟于面,盎于背”的生命状态。
四、配义与道
朱子强调“刚”和“气魄”,其实突出了浩然之气的实践向度,他讲“浩然之气,只是气大敢做”[2](P1254),“此诸圣贤都是如此刚果决烈,方能传得这个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终不济事”[2](P1243),“道理,须是刚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2](P1243)。这与他对“配义与道”的独特诠释有关,《孟子集注》注此言: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馁,饥乏而气不充体也。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1](P231-232)
朱子认为,浩然之气养成之后可以与道义合,并且有助于道义的实现。有此浩气,则在道德实践时会勇敢果决,无此浩气则会有所疑虑、恐惧。朱子此注在《孟子》诠释史中颇为独特①。赵岐注“配义与道”言:
重说是气。言此气与道义相配偶俱行……道谓阴阳大道,无形而生有形,舒之弥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络天地,禀授群生者也。言能养此道气而行义理,常以充满五脏;若其无此,则腹肠饥虚,若人之馁饿也。[5](P200)
赵岐这里“以偶释配,又申之以俱行也”[5](P201),赵岐以气释道,此处“道气”连用讲“浩然之气”,突出一种由道德意涵的气,这就不是严分道气的朱子所能接受的了。而有此气之后,赵岐只讲与身体的变化有关,而未讲到道德实践这一领域;朱子这里,得此浩气后,强调的是此气对人实践状态的改变。这里也引申出“气”的道德性问题,即到底是气本身就可以是道德之气,还是其道德意涵不在于本身是否具有明确的道德属性,而体现在其对道德实践的作用上。在朱子这里,浩气若有道德属性,则体现在全具天理和“配义与道”上,而后者尤为重要。
以往对朱子气论的关注特强调气的消极向度,即气的清浊厚薄对“理”的遮蔽作用,如是,则气似乎只有消极的道德作用。但朱子对浩然之气“配义与道”的解释,则提示气在道德实践中也有积极作用,而且此浩气对一定的道德实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朱子语类》有:
道义是虚底物,本自孤单;得这气帖起来,便自张主无所不达。如今人非不为善,亦有合于道义者,若无此气,便只是一个衰底人。[2](P1245)
道义是公共无形影底物事,气是自家身上底物。道义无情,若自家无这气,则道义自道义,气自气,如何能助得他。[2](P1255-1256)
这里朱子认为道义“虚”,道义“无情义、无计度、无造作”,也就是道义本身并无直接的道德实践活动能力,但若得浩气贴合起来,则可完成道德实践,“道义”与“浩气”要一起“滚发出来”,道义的实践力量来自浩气。若没有气,道义就无法展现,直理的展现需要浩气[2](P1257)。“气者,道义之成质”[2](P1257),也即是气是无形的道义的有形的载体。朱子强调此浩气对道义的实践作用,特对应现实层面的一种现象,即有些人不是不知道理何在,然其却不能行道,也就是对道德的认知无法转化为实际的道德活动:
有人分明知得合当恁地做,又恧缩不敢去做,便是馁了,无此浩然之气。如君有过,臣谏之,是义也。有到冒死而不顾者,便是浩然之气去助此义。[2](P1246-1247)
若个人做得一件半件事合道义,而无浩然之气来配助,则易颓堕了,未必不为威武所屈,贫贱所移,做大丈夫不得。[2](P1250-1251)
人能以道义为主,得义理相助,就能做得成事,尤其是“死谏”等舍生取义的行为,更需要此浩气去助道义。有些人知道应舍生取义,然而正因无此气,故不能落实于实践。所谓“大丈夫”所为,均与浩气相关,“气配道义。有此气,道义便做得有力”[2](P1254),而无此浩气,正义则会遭受霸凌。浩然之气是一种道德实践力量的展现。朱子思想中有“理气强弱”的问题,而在道德实践领域,如果能养此浩气,则可“理强气亦强”。这里朱子对自己的解释颇为自信,当学生怀疑其阐释时,他甚至对天发誓。
当然,朱子在讲浩气“助”道义的时候,也特别强调“集义与配义,是相向说。初间其气由集义而生,后来道义却须那气相助,是以无所疑惮”[2](P1258),那能配道义的浩然之气,恰是道德实践所养成的一种由义理而发的气。可以认为,道德实践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一为“知道”,一为“行道”。“知道”并非单纯的认知,其中也包括“行”,但朱子有时讲,“方集义以生此气,则需要勉强”,“集义”过程中的行可能还不是自觉自发的道德实践(“行仁义”),抑或其道德挑战性还不十分强,而得浩气相助之“行道”其实践难度往往较大,而此时“道义之行愈觉刚果,更无凝滞,尚何恐惧之有”[2](P1256),此种“行”可谓之“由仁义行”。
这里也留下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浩然之气,则可能出现道德实践上的知行不一现象,也就是知道未必能行,按照朱子学自身的理论构建,则此不能行的知不是真知。但不产生“真知”的行为可以是“知言”或者“集义”吗?浩然之气配道义,可以视作知行合一、真知必能行,但“集义”过程中的知行如何理解呢?知言、集义可以视作“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或者是持续的明善、行善过程。但何时会有能配道义的浩气产生呢?似乎朱子认为“致知”而非“知至”就可产生此浩气,而不必等待豁然贯通之后,才会产生此浩气。虽然朱子教导我们不要“期必”(勿望)此浩气的产生,但这里道义与浩气的知行向度还需要我们多留意。
结语:浩然之气与道德勇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浩气具有道德实践能力,即在朱子的思想当中,气不是纯然消极的,它可以有积极的面向,这也是“浩然之气”道德性的重要展现。
儒家自先秦以来就重视“勇德”,《中庸》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强调“勇”作为一种美德,指向道德的“实践性”,通过“勇”将其他美德落实到具体的道德处境之中,一方面要突出道德困境当中的行动力,一方面亦要对峙道德麻木。同样,西方哲学也重视“勇”,如柏拉图特别强调城邦护卫者的“勇敢”。晚近西方伦理学家拉什沃思·M.基德尔(Rushworth M.Kidder)就特别重视“道德勇气”的价值,认为勇气自身并不具备道德价值,只有“道德勇气”才是道德意义上的美德。基德尔区分了“血气之勇”(physicalcourage)和“道德之勇”(moral⁃courage),其中“道德勇气”是为一定的道德原则所驱动的,是以实践道德原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为了维护美德与核心原则,而非维护身体。将physical courage 译为“血气之勇”、moral courage译为“道德之勇”,很容易将之与朱子所说的“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联系起来。朱子强调要抑“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1](P21),而“浩然之气”就是此种“德义之勇”,有此浩气,可以推动实践者对所知道德原则的维护,将之自觉呈现出来。基德尔从消极的不妥协和积极的选择坚守两方面区分道德勇气,亦可从朱子对“浩然之气”的描述中分析出,当然,此两重意谓在朱子那里还不是特别明显,朱子更强调积极有为的一面。
同时,基德尔将“道德勇气”定义为“心灵和精神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得一个人能够坚定而自信地直面道德上的挑战,而不会畏惧或退缩”[7](P74)。朱子则更强调浩然之气的“身体属性”,浩然之气作为道德勇气与“身体”的状态密切相关,“浩气”并不外于“血气”,而是通过集义将道德义理灌注于身体的内在,并将道德义理呈现出来,因此浩气作为身体性的特征,也具有了一定的道德意涵。
在基德尔看来,道德勇气具有如下要素:(1)应用价值,道德勇气更多的是实践道德,而非仅仅从思想上把握道德;(2)认识风险,道德勇气的发动会面临风险,而此种勇气的实践者觉知此种风险,并从良心出发展现勇气,而非经过计算;(3)忍受困难,道德勇气的实践者能够忍受风险,并自身具有坚定忍受困难的决心。基德尔作出的这三重要素分析,有助于扩展我们对“浩然之气”的理解,一个人具备朱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必定具备以上三重要素。从上述三重要素审视“浩然之气”作为“道德勇气”,其时代价值也就能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即今天依旧需要具有道德实践力、能抗风险、坚守价值的道德主体,此种道德主体必定是一身浩气。
[注 释]
①朱子这一独特的诠释其实面临着文本诠释的挑战。《孟子正义》引清儒毛奇龄、全祖望的观点(参见焦偱:《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01-202 页),都反对将“配”解释成“合而有助”,而是结合“直养”强调此气之生,如是诠释则两处“馁”意义一致,而在朱子那里,两处“馁”诠释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