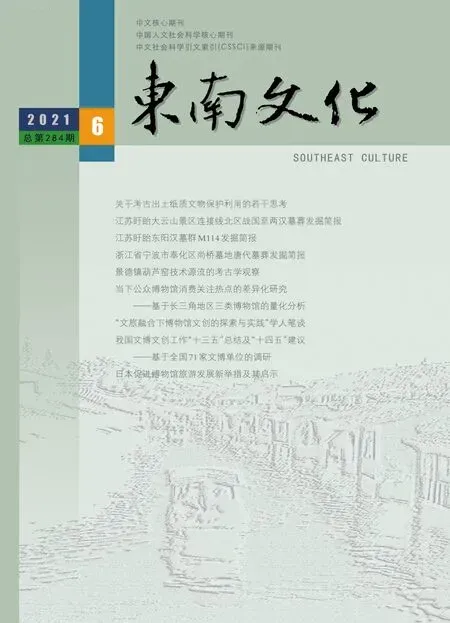论博物馆商标异议主要法律依据及关键证据
王月芳
(故宫博物院 北京 100009)
内容提要:博物馆进行商标异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博物馆商标的显著性,打击近似商标或其他对博物馆商标权益构成妨碍的商标。相比商标无效宣告等维权途径,商标异议有其特殊的优势。博物馆对不当商标提起异议,主要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关于“申请在先”“驰名商标保护”“在先权利”“不良影响”“恶意抢注”等内容的规定,相应的证据涉及博物馆作为异议人的主体资格证明、博物馆商标知名度证明、对方恶意抢注的证明、可能被异议商标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据材料等。
博物馆保护自身商标权益有多种途径,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通过注册商标取得专用权、对侵犯博物馆商标权益的他人商标提请异议和无效宣告等路径实现。其中,对侵犯博物馆商标权益的他人商标提请异议是最便捷的维权手段,具有其特定的优势。本文通过三十余件博物馆商标异议案件的实践,梳理异议结果,并结合商标维权领域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明确商标异议对博物馆的重要性;同时总结博物馆商标异议的主要法律依据和关键证据,以期对博物馆维护自身商标权益的具体实践和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一、博物馆商标异议及主要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商标指“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1]。博物馆商标的主要功能是标示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博物馆,明确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2]。从组合形式上区分,博物馆商标以文字商标、图形商标和文字图形组合商标三种情况居多。从注册类别上看,博物馆商标主要涉及与提供教育、培训、文化服务相关的第41类,与餐饮食品相关的第29类,与博物馆经营活动相关的第35类,以及与博物馆文创产品相关的第16类、第20类、第21类、第25类等。而在个别博物馆的商标注册中,几乎涵盖了第1至45类全部类别,例如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商标权被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河北博物院国宝级文物“长信宫灯”图像被社会企业抢先注册[3];浙江宁海县“十里红妆”婚俗博物馆与浙江诸暨“裕昌号”民间博物馆为“十里红妆”商标陷入七年纷争[4];2010 年,“明孝陵”等商标被杭州某公司注册并拍卖[5];2020年,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申请注册多个名商标权益。博物馆在陷入商标纷争后再维权,往往容易陷入被动。通过商标异议程序,博物馆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不当商标注册成功,保护博物馆注册商标权益。
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通过初步审查的商标予以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商标异议即公告期内由社会公众对公告商标提出反对意见,经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是否予以注册的决定。设置商标异议程序,旨在通过社会监督保证商标审查的质量,充分利用社会监督解决潜在的商标争议,减少商标注册成功后再被撤销的混乱秩序[6]。简而言之,博物馆商标异议指博物馆作为商标权利主体,对他人申请注册的、涉嫌侵犯博物馆权益的商标提出异议,以达到阻止其注册成功的目的。博物馆进行商标异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博物馆商标的显著性,打击近似商标或其他对博物馆商标权益构成妨碍的不当商标,防止博物馆品牌淡化,维护博物馆的相关权益。博物馆商标注册类别及具体的产品和服务通常限定了异议中获得支持的类别。例如,当博物馆商标注册类别为第41类教育和文化时,通常较难对注册类别为41类以外的他人商标提出异议。但因《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给予扩大保护,所以在博物馆注册商标曾获得驰名认定的情况下,双方商标近似但注册类别、注册商品或服务不构成近似时,博物馆依然可以获得支持。
二、商标异议对博物馆商标权益维护的重要性
博物馆商标保护重在避免两种情形:第一,他人商标与博物馆商标构成近似,造成公众对产品和服务来源的混淆和误认;第二,近似商标的使用削弱了博物馆商标的显著性。博物馆利用商标异议避免其他商标混淆、保持显著性,是博物馆商标权益保护工作的关键一环。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更多介入经济活动,而商标作为博物馆参与经济活动的符号和标志,商标权益维护愈发重要。抢注成本低、收益高,造成抢注博物馆商标的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商标注册的初步审查不能排除与博物馆商标构成近似或妨碍的全部商标。每年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的商标中,与博物馆商标构成近似或妨碍的情况并不鲜见,且呈增多趋势,这与每年申请注册商标总量的上升有一定关系,也与国家文化政策推动下公众对博物馆品牌认可度的提高有一定关系。如果博物馆未能认识到商标异议的重要性,使得他人成功注册了近似商标,不仅会影响博物馆使用自己的商标,还会对博物馆品牌形象和品牌显著性造成不良影响。从国家商标审查制度分析,商标初步审查和商标异议共同构成商标注册程序,因此商标异议程序是商标确权的重要步骤。商标初步审查主要排除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或者申请注册的商标存在法律上禁止注册的情况。在商标初审后通过异议双方举证,阐明事实、理由,提供有效证据材料,进一步审查注册商标初审阶段无法涵盖的商标知名度、商标显著性问题,其他在先权利如著作权、外观专利权、商号权等问题,非类似商品上的商标近似问题(如驰名商标权益),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问题以及关系人抢注问题等。由此可见,异议程序是对申请注册商标的第二次筛查,通过博物馆主动监测初审商标公告,筛查出可能影响博物馆商标权益的初审商标,再通过异议程序进行打击。
在博物馆可以采用的各类商标权益维护方式中,商标异议有特定的优势。商标异议属于非诉讼类维权,相比诉讼维权,操作便捷、耗时较短、费用较低;相比其他非诉讼维权,异议针对的是仅仅通过初审但是仍然处于公示期的申请注册中的商标。如果博物馆不在异议程序阶段进行拦截,申请注册的商标一旦投入市场,对博物馆商标权益必然产生不良影响。错过了异议期,不当商标注册成功,打击不当商标只能通过“无效宣告”或“撤销连续三年未使用商标”(通常简称“撤三”)等方式。届时,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时将考虑争议商标所形成的既定市场秩序,即如果争议商标在无效宣告审理时已经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该商标被宣告无效的可能性将非常低;已经实际使用的商标也较难通过“撤三”的方式进行打击。因此,商标异议无疑是现行法律下博物馆最便捷的商标权益维护方式。
三、博物馆商标异议主要法律依据
博物馆商标异议的法律依据也称异议理由,是博物馆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异议申请时书面陈述的相关法律依据或理由。《商标法》对“申请在先”“驰名商标保护”“在先权利”“不良影响”“恶意抢注”等内容的规定是博物馆商标异议的主要法律依据。其中,在博物馆商标异议的实践中普遍运用且较容易获得支持的是“申请在先”“驰名商标保护”和“在先权利”三项。
1.申请在先
我国商标注册实行申请在先原则,这也是博物馆提请商标异议的主要法律依据。如果博物馆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商标公告》中监测到他人在相同商品或类似商品上注册了相同或近似商标,可依据《商标法》关于“申请在先”的规定予以打击。“商标近似”是指商标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博物馆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有特定的联系。判定“申请在先”,以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申请书件的日期先后为准;同一天申请注册的,不存在申请在先情形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使用在先原则作出初步审定并予以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2020)商标异字第0000072809号异议案件中,异议人故宫博物院对被异议人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初步审定并刊登在第1635期《商标公告》的第33045332号“紫禁大婚”商标提出异议。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于第26类“绳编工艺品;头发装饰品”等商品上。故宫博物院引证在先注册的第6232977号“紫禁城;PALACE MUSEUM;FORBIDDEN CITY及图”商标、第13163037号“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及图”商标、第13162996号“紫禁城及图”商标核定使用于第26类“绳编工艺品;头发装饰品”等类似商品上,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认为:“紫禁城”是异议人故宫博物院的别称,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并且具有唯一的指向性。被异议商标与故宫博物院引证商标显著识别部分均为“紫禁”,双方商标整体含义区别不明显,易使相关消费者误认为两者系来自同一市场主体的系列商标或存在某种关联,若并存使用于类似商品上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误认,“双方商标已构成使用于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7]。
国家知识产权局(2020)商标异字第0000023710号案件中,被异议人注册了第28948648号“五千年良渚”商标。浙江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作为共同异议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异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被异议商标和引证商标的差异,注册类别、核定使用产品以及注册先后顺序等情况进行了审查,认为异议人引证在先注册的第6417920号“良渚古城 LIANGZHUGUCHENG”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馅饼、方便米饭”等,被异议商标“五千年良渚”指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咖啡、茶”等。双方商标指定使用部分商品在功能用途等方面相近,属于类似商品,且双方商标显著部分均为“良渚”,并存使用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两者为系列商标或存在特定联系,故双方商标已构成使用于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结合考虑被异议人在其他多个类别上申请的“五千年良渚”曾被驳回的情况,以及“良渚”易产生消费者误认其与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存在特定关系的情况,决定第28948648号“五千年良渚”商标不予注册[8]。
湖南省博物馆先注册有第3394672号“君幸酒”商标,浙江绍兴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注册了第33541538号“君幸食”商标。湖南省博物馆对该商标提出异议,引证了在先注册的第3394672号“君幸酒”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为第33类的“葡萄酒;蜂蜜酒;米酒”等。经审查,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双方商标主体部分均为“君幸”,且视觉效果相近。被异议商标“君幸食”指定使用于第33类“果酒(含酒精);葡萄酒;烈酒(饮料)”等商品上,与湖南省博物馆引证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类似,已构成使用于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并存使用易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因此决定第33541538号“君幸食”商标不予注册[9]。
2.驰名商标保护
博物馆对注册商标依法拥有专用权,非注册商标一般较难得到法律保护。但是,博物馆非注册商标如已经长期使用,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可通过复审、行政诉讼等请求认定为驰名商标,以获得法律保护。《商标法》第十三条就驰名商标保护作出规定,商标“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且“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可依法请求“驰名商标保护”。
是否“驰名”,其认定标准在于相关公众熟知的程度。“相关公众”包括与该商品或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相关人员清楚地知道该商标及其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即“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博物馆的相关公众包括参观观众、文化活动参与者、博物馆职工、博物馆志愿者、博物馆文化产品消费者、为博物馆提供配套服务的各类人员、博物馆合作方等。博物馆的相关公众清楚地知道某个商标属于博物馆,该商标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来源于博物馆,即符合法律规定的“为相关公众所熟知”。
博物馆驰名商标按照受保护的情况分为注册驰名商标和非注册驰名商标。博物馆已注册驰名商标,可依法获得扩大保护。扩大保护即在申请注册的商品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情况下也可获得保护,申请商标一旦构成对博物馆“已注册驰名商标复制或仿制”且“容易误导公众”,致使博物馆作为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便可依据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提出异议。若博物馆的驰名商标为非注册驰名商标,须符合申请商标申请注册的商品与博物馆未注册驰名商标的相同或类似,并且申请商标构成对博物馆“未注册驰名商标复制或仿制”,与博物馆未注册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情况下才可获得保护。
依据“驰名商标保护”提请异议,审查的标准在于后注册的商标是否复制、模仿博物馆的驰名商标,并在实际使用中足以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误以为使用了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与作为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博物馆有一定联系,从而损害该博物馆利益。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2019)商标异字第0000024230号案件为例,异议人故宫博物院对被异议人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第17968140号“流动的紫禁城 THE MOVING FORBIDDEN CITY”商标提出异议。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于第25类“婴儿全套衣;游泳衣”等商品上。故宫博物院引证在先注册的第6232976号“紫禁城 PALACE MUSEUM FORBIDDEN CITY及图”商标核定使用于第25类“帽子;袜”等商品上。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案件中被异议商标“流动的紫禁城 THE MOVING FORBIDDEN CITY”完整包含异议人引证商标主要认读文字“紫禁城”及“FORBIDDEN CITY”,且未形成明显区别于引证商标的含义,构成近似标识。异议人故宫博物院注册并使用于“组织和安排文化教育展览”“艺术品鉴定”及“观光旅游”服务上的“紫禁城PALACE MUSEUM FORBIDDEN CITY及图”经长期宣传使用具有较高知名度,并已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被异议人对异议人驰名商标理应知晓。因此,认定“被异议商标已构成对异议人驰名商标的抄袭和复制”,并行使用“易误导公众”并致使故宫博物院的“相关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因此决定该商标不予注册[10]。
3.在先权利
《商标法》规定任何人申请注册商标不得损害他人在先权利。“在先权利”指的是任何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与他人已经获得的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名称权、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用权等权利相冲突。如果他人申请的商标对博物馆已经存在的上述等任何权利产生冲突,则对方应合理避让。
国家知识产权局(2019)商标异字第0000028175号案件中,异议人故宫博物院院徽“宫”标识于2005年7月18日创作完成,并于同日在中国首次发表,异议人故宫博物院对该作品享有在先著作权。后经注册,成为注册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理后认为,被异议商标与该美术作品在构图要素、设计风格、整体视觉效果等方面相近,为实质性近似。且“宫”商标经过广泛的使用与宣传,已在中国市场为相关公众知晓,被异议人北京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有接触到该作品的可能。在申请异议的证据材料中,异议人故宫博物院提供了“宫”商标即故宫博物院院徽的设计确认函、委托创作合同、故宫博物院院徽标识诞生并启用的报告以及相关媒体报道等证据,上述证据材料皆可以证明故宫博物院的在先著作权。同时,被异议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异议商标为其独立创作。据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裁定,认为“被异议人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已构成对异议人在先著作权的侵犯”,被异议商标不予注册[11]。
4.恶意抢注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同时规定了任何人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如果博物馆商标未注册但已经使用,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使未能构成驰名或知名,他人也不得抢注。
未注册商标获得保护有两点要素:第一,未注册商标使用在先;第二,未注册商标应处于持续使用状态[12]。如果博物馆在未注册商标的使用上未能持续,中断期间由其他机构、单位或个人注册或持续使用了该商标,则无法获得有效保护。因此《商标法》规定的“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其中“在先使用”是指在先并持续使用,“使用”应为实际使用并在商品中能够区别商品来源。
判断商标具有一定的影响,应综合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使用范围、宣传时间、宣传程度、在相关消费者中达到的影响进行判断。在先使用和达到一定影响是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基础,两种情况同时具备才可获得有效的司法保护。注册商标到期未续展,但如果该商标持续使用,商标的影响力随着商标的继续使用而得到延续,则同样适用上述标准。持续使用既包括博物馆自身使用,也包括自己未使用而依法许可他人使用。在此种情况下,如他人注册博物馆的未续展商标,博物馆亦可依此进行有效异议。
5.恶意注册
“恶意注册”与“恶意抢注”的区别在于“恶意注册”中涉嫌侵犯博物馆商标权益的主体属于未经博物馆授权的代理人、代表人和其他关系人。上述人员注册与博物馆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博物馆提出异议且有证据能够证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注册。关系人包括与博物馆有合同关系、业务往来或其他关系,明知博物馆商标存在的任何个人、企业或机构,例如博物馆职工、拟与博物馆合作或已经达成合作的个人、企业或机构,均属于博物馆关系人等。
6.不良影响
《商标法》中“不良影响”[13]条款设立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商标标志对文化、政治、宗教、民族等涉及公共利益问题产生的不利影响。如果核准某商标可能损害公共利益,便属于“不良影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此理由进行审查时,也会着重考虑被异议商标是否存在涉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
国家知识产权局(2020)商标异字第0000000370号案件中,异议人故宫博物院对被异议人四川故宫御窖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6367617号“故宫荟”商标提出异议。故宫博物院作为异议人提交的异议材料证明,北京故宫作为明清两朝皇宫,在1961年3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都享有较高知名度。故宫博物院作为北京故宫的直接管理和保护单位以及综合性国家级博物馆,多年来为国内外游客及各国首脑、贵宾提供宫廷文物展示、文物收藏、文物和古建筑研究与修复、旅游资源开发等服务,“故宫”一词已在公众心中与异议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国家知识产权局综合考虑,除本案被异议商标外,被异议人后续还申请了与故宫博物院中的宫殿名称相同的商标,认为被异议人申请注册上述系列商标明显具有使相关公众将其产品与作为国家级博物馆的异议人产生关联的主观目的,并且在客观上确易造成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被异议商标由被异议人申请注册并使用会引发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决定依据“不良影响”等条款,被异议商标不予注册[14]。
前文所提河北博物院“长信宫灯”被抢注的案件,虽然异议程序未能获得支持,但异议复审依据“不良影响”条款予以认定。北京某图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在同类服务上在先申请了“长信宫灯”商标,河北博物院在43类申请的“长信宫灯”商标被国家商标局驳回。由于被异议人申请的第5795282号“长信宫灯”商标正处于公告期,河北博物院启动商标异议程序。因所提证据不足,河北博物院未获支持,被异议商标被核准注册。河北省博物馆不服并申请复审,提出被异议商标损害了河北博物院的在先著作权,如果被异议商标被核准注册并用于商业目的,将严重影响文物的严肃性和历史价值,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复审支持了河北博物院的理由,裁定被异议商标的商标注册和使用易产生不良影响,该商标不予注册。虽被异议人因不服提起民事诉讼,后经法院诉讼程序一审和终审,最终仍然认定不良影响存在,维持了异议复审的结果[15]。
四、博物馆商标异议关键证据
博物馆提请商标异议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是逐一对应的关系,既应根据提请异议时的法律依据梳理和提交关键证据,也应根据博物馆能够掌握的证据调整异议的依据,以使法律依据和证据在逻辑上形成较为严谨的证明关系。以相对应理由提请异议时,主体资格证明是首要证据。一般情况下,博物馆注册商标情况、博物馆商标知名度情况、对方是否存在恶意抢注的情形、是否造成不良影响是最为关键的证据。
综合全国博物馆提起异议的案例,提交的证据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第一,博物馆及引证商标简介,包括但不限于文字简介、宣传手册、商标含义说明等;博物馆引证商标在相关商品及服务上最早使用情况的证明。第二,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前三年,博物馆引证商标持续使用情况的证明,例如使用了该引证商标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合同及发票、相关国内经营网络、营业收入及财务审计报告等。合同及发票以能证明多省市地区销售了使用引证商标的产品或服务为宜。第三,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前三年,博物馆引证商标持续宣传推广情况的证明,包括但不限于电台、电视台、网络、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体形式的广告宣传合同及发票、宣传照片等。合同及发票以能证明引证商标在多省市地区的宣传推广情况为宜。第四,社会各届或上级主管部门对博物馆及引证商标的评价、行业排名,以及博物馆与该商标所获得的荣誉的证明。第五,博物馆是否与被异议人存在或曾经存在代理关系、合作关系的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被异议人知晓博物馆引证商标的证据材料。第六,博物馆引证商标受保护的记录,包含但不限于类似案件行政裁定、判决书,商标侵权行政查处记录等。通过对以往异议案例的梳理,可归纳出一般情况下博物馆提请商标异议时的关键证据,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
1.异议人主体资格证明
《商标法》根据商标异议的相对理由和绝对理由,对异议人主体资格作了明确的限制。博物馆以相对理由提出商标异议时,例如与在先商标相同或近似、驰名商标保护、在先申请、损害除商标权以外的其他在先权利、抢注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等,博物馆必须首先证明自己属于“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具有提起异议的主体资格[16]。证明博物馆属于“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证据包括:博物馆相关商标注册情况,例如注册证和初审公告;博物馆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案件记录;博物馆其他在先权利证明,例如相关著作权证明、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等。
2.博物馆商标知名度证明
博物馆商标知名度证明包括:商标使用的情况,例如商标使用的产品、包装、说明书、标签、网页、宣传页;商标使用在产品交易文件中的情况,例如商标使用的销售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商标使用在广告宣传中的情况,例如广告合同、发票、广告实际发布情况的复印件或者照片等;商标使用产品的产销量、销售额、利润及纳税等经济数据情况,例如审计报告、纳税证明等;商标或使用产品所获得的权威荣誉或者获奖称号;商标获得其他案件保护的记录,例如驰名商标认定的记录或其他被侵权胜诉判决;新闻媒体等对商标使用情况的报道,领导视察、知名国际友人参观博物馆的相关照片文件;博物馆赞助各类赛事、公益活动、捐赠证书等;其他可以证明博物馆商标知名度的证据。其中,商标或产品所获得的权威荣誉或获奖称号、媒体对商标使用情况的报道、驰名商标认定的记录等是非常关键的证据。
3.对方恶意抢注的证明
若要证明对方为恶意抢注,则应提供博物馆对商标实际使用并达到一定影响的证据、证明材料和证明对方为恶意的证据资料。达到一定影响的证据包括各媒体对商标的相关报道、广告宣传、行业排名、获奖证明等,“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检索的记录也可作为证据。对于他人以不当手段抢注博物馆商标,主要评估标准在于对方是否具有恶意,即他人对博物馆商标是否明知或应知,主要依靠明确告知、业务往来等证据推定。博物馆应在举证过程中尽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邮件、短信、彩信、微信等记录。
4.被异议商标注册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明
如前所述,关于不良影响是否存在,主要衡量被异议商标被核准注册是否足以混淆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是否混淆庞大的公众群体,足以形成对国家经济秩序的不良影响。当某一商标注册影响的群体足够大,以至于上升为公共利益问题时,才达到“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要件。商标实质上是进入市场流通的标志,市场是无边界的,因此博物馆商标涉及的不仅仅是博物馆这一特定民事主体的利益,还包括行业、广大消费者利益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难点在于,对博物馆而言,如何举证被异议商标妨碍了社会公共利益。在实践中,被异议方大批量模仿、抢注博物馆商标,从而可能导致公众对商品来源发生误认,进而产生不良影响,损害正常商标管理秩序的证据往往能够得到较好的支持。
商标异议中提交的证据并非越多越好,证据整理中应注意分清主要证据和辅助证据。证据的搜集和整理应根据异议时的法律依据而确定主次,并注意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博物馆可将适合多数案件的常规证据搜集整理,使其模板化,再根据个案有针对性地增减。
五、总结
明确博物馆商标异议的目标、重要性、法律依据和主要证据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参与经济活动更加频繁,商标权益维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运用好商标异议这一维权手段,能够促进博物馆的维权实践,打击不当商标注册,维护博物馆知识产权;同时,对构建、完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博物馆维护自身商标权益的角度,博物馆进行商标异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博物馆商标的显著性,打击近似商标或其他对博物馆商标权益构成妨碍的商标。相比商标无效宣告方式等其他维权方式,商标异议有特定的优势。《商标法》对“申请在先”“驰名商标保护”“在先权利”“恶意抢注”“不良影响”等方面的规定是博物馆商标异议的主要法律依据。博物馆作为异议人主体资格证明、博物馆商标知名度的证明、对方恶意抢注和被异议商标注册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明等材料是博物馆商标异议的关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