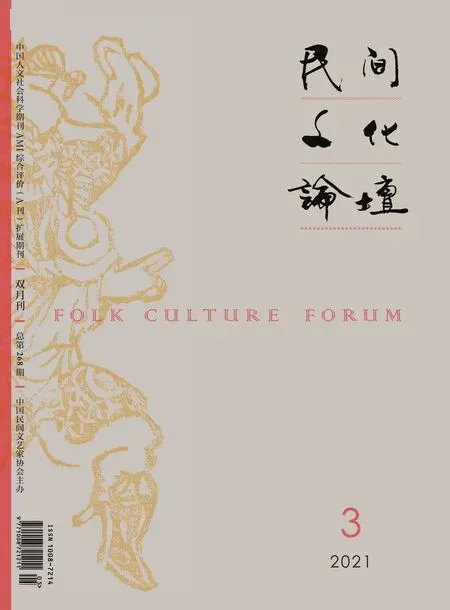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七十年
高 健
在中国传统社会,采录民间文学已成为一项制度,主要目的即采风观政。“五四”歌谣运动以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由原来的“风”之于“政”也更为突出地转向“风”之于“民”、“风”之于“学”。其中,“民”指民众或民族,即通过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来了解民众生活文化与民族历史文化,产生出一种新的“民族的诗”,甚至是“向民众学习”;而“学”则指学术或民间文学,即通过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构建民间文学、民族文学的学科体系,为之提供研究文本。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跃进”“普查”“抢救”等话语的影响下,“大规模”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成为国家、民族、学界的共同诉求。所以,我们经历了多次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工程,这不仅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全国上下大批学者、搜集整理者、演述人持续参与,也需要一个能够动员、组织、协调各方力量的团体机构。
70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①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本文分别简称为“民研会”与“中国民协”。由于坚持学术立会、群众基础深厚、团体会员广泛等,一直深度参与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事业,仅从中国民协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可看出:1950年民研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扬、郭沫若、老舍的讲话都格外强调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并公布了《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事实上,虽然民研会第一届理事会下设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戏剧、民间舞蹈等七个小组,但是,“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各艺术门类的协会相继成立,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范围则缩小为以搜集研究民间文学为主。”②刘锡诚:《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26页。1958年民研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正值“采风运动”兴起,全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活动。1979年民研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讨论、印发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十年规划》《关于加强民间文学工作的几点建议》。1984年、1991年、2001年中国民协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正是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简称“三套集成”)启动、全面开展与陆续完成阶段。2006年、2011年、2016年中国民协第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密切相关。可以预见,在即将召开的中国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又会是一个主要议题。
一、从个体到共同体
搜集整理者是上述运动、工程中的主要力量。过往的搜集整理者基本上是“单兵作战”,如《歌谣》周刊的投稿者多为个人。1949年后,“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则主要依靠调查队、调查组等形式。虽然以集体的形式开展搜集整理工作,但这个群体内部极为复杂。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并非一项专职工作,即使在三套集成时期,中国地方各级政府都成立了“集成办”,但后期“集成办”相继解散,原工作人员被重新分配到当地其他部门。搜集整理者的自我定位往往也是多元的:文学的记录员、地方文化的传播者、文本阐释者、民族文化代言人,等等。所以,在具体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则需要搜集整理者有相对统一的认识论与工作规范。一个重要的方式是举办讲习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民研会云南分会分别在德宏、大理、昆明、丽江、楚雄、文山、红河、曲靖、昭通、思茅、保山、中甸、玉溪、通海等地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近20次。
这些讲习班一般分为三部分:首先,学员学习民间文学基础知识,如民间文学特征、民间文学各文类特征、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以及当地的地方文化与历史。当然,最主要的是学习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原则与技术;其次,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实践,或请演述人到讲习班上对其直接采录,或学员到民间进行实地搜集,有时则先在讲习班上采录练习,由授课教师指导,再赴实地搜集;最后,讲习班学员汇合,进行文本整理和工作总结。许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在讲习班上产生的,如在大理举办的讲习班,共搜集了二十多万字的民间故事以及八万多行的诗歌。
此外,中国民协及各地民协还翻译、编纂了《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民间文学实习手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民俗调查提纲》等论著与工作手册,用于指导基层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民研会甚至于1985年创办了民间文学刊授大学。
这些讲习班的主讲人、工作指导手册与调查提纲的撰写者大多为民间文学、民俗学等领域学者,中国民协虽为学术团体,但主要工作并非学术研究,所以需要联合大量学者开展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民研会云南分会刚刚成立,由于缺乏专业研究者,于是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合署办公,即云南民间文学界经常提及的“两所一会”,三者既分工又合作,“两所”主要侧重于民间文学研究与编辑《山茶》杂志,“一会”主要侧重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两所”的学者为搜集整理工作做了理论支撑,“一会”也为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的田野资料,《山茶》杂志当时主要稿源也正是出自“一会”所组织的搜集整理者。
所以,我们看到学者与基层搜集整理者这两个群体并非相互隔绝,而存在着诸多的交流——面对面或书面的——而中国民协正是二者之间的“中介机构”,二者在一定限度内达成共识与合作,从整个学科的角度来看,二者也共同组成了民间文学这个学术共同体。
二、从“十六字方针”到“三性”
在“规范”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各种手段中,最有效的方式应为制定与普及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原则。
1955年,民研会主办的《民间文学》创刊,除发表民间文学书面文本、个案研究与理论探讨外,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讨论的文章。1955年,董均伦、江源在《民间文学》上发表《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一点体会》一文;1957年,刘魁立发表《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一文与之争鸣,随后引发一场大讨论。此外,当时还有刘守华、李岳南、巫瑞书围绕着李岳南整理的《牛郎织女》的讨论。民研会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出版《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其中围绕着调查、访谈、记录、翻译、编辑、润色、出版等搜集整理环节以及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整理与再创作的界限等问题都展开了讨论。
这本论文集的首篇文章是《民间文学》1956年8月号社论,题为《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民研会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上的立场,文章总结了当时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存在“腐朽的学院气”与“庸俗社会学”两种倾向,并且认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危险不是一字不动论,这种迂腐的学院气倒还好些;而是庸俗社会学在作怪。庸俗社会学在‘左’的词语的掩护下,往往可以把读者唬住。而且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也是很容易产生的,它可以产生在‘词严义正’的教条主义者身上;也可以产生在仅仅是由于政治热情很高、而又对文艺缺乏基础知识的人们的身上。”①佚名:《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间文学〉1956年8月号社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5页。文章还强调“一起参加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人,应当把它们②指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笔者注看的像法律一样尊严”③佚名:《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间文学〉1956年8月号社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第7页。。
1958年7月,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同时也是民研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贾芝作了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大会报告,这篇后来被不断引用的文章确立了当时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基本原则: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这“十六字方针”也奠定了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基本范式。“采风运动”时期,各地搜集整理者并没有受过太多民间文学系统训练,但出发前大都知道这“十六字方针”。
1981年民研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贾芝代表常务理事会作工作汇报,提出在普查的基础上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中国谚语大观》。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与民研会联合签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文民字(84)808号],即学界经常提及的“808号文件”,这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正式启动。此时搜集整理者更多,学界对民间文学的认识论也发生了转换。所以,科学性、全面性与代表性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编选原则被提出与推广。
显然,“三性”原则是“十六字方针”的延续,全面性大致对应全面搜集,代表性大致对应重点整理,而被置于“三性”之首的科学性则代表着此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重要转向。正如云南民协的佘仁澍所说:“科学性是核心,这个基点解决了,全面性、代表性也就容易做到了。”④佘仁澍:《关于民间文学集成的“三性”问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通讯》,内部资料,第6期。
科学性不仅意味着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流程要符合科学规范,还意味着要加强对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更是在民间文学的民俗学转向背景下,强调民间文学与民俗、宗教、历史事件的关系。换言之,科学性在此更意味着新的学科性。甚至此后“‘搜集’‘整理’‘改编’等话语渐趋隐匿,田野研究逐渐取代采风模式”①毛巧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七十年》,《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1985年6月,民研会云南分会在昆明召开了第一次民俗学学术讨论会。江应樑在会上说:“搞民间文学的人不掌握民俗学,民间文学中的许多问题就无法解释。就是说,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它对民间文学起很大的作用。”②江应樑:《谈民俗学研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通讯》,内部资料,第6期。《白族神话传说集成》被作为三套集成工作的优秀范例优先出版,并获得一致好评,其中主要原因正是书中64篇神话传说作品均附有附记,还提供了27篇异文。这些附记提供了与作品相关的演述人、民俗、宗教、历史背景资料。如书中《狩猎神话》文末又描述了云龙白族祭祀猎神的流程与祭文,又如《绕山林》这个文本只占一页篇幅,文末的附记却占两页多。
当然,制定搜集整理原则本身就意在强调搜集整理活动的科学性,这些原则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制度化,并与其他领域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如作家、编剧采风)区分开来。这些原则的制定者与阐释者宣称搜集整理者只有依靠这些原则才能更加有效地、科学地开展搜集整理工作,而只有通过这些原则制作出来的文本才可被称为科学或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大部分搜集整理者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也是透过这些搜集整理原则达成的,搜集整理原则在此成为一个透镜,即通过这些搜集整理原则发现有价值的民间文学文本。
三、从“科学性”到“文学性”
然而,民间文学书面文本的价值从来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1922年《歌谣》周刊发刊词强调当时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20世纪50年代末的新民歌被认为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三套集成时期,虽然“科学性”被置于核心位置,但“可读性”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编选标准。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董森也谈到:“胡乔木同志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民间文学就像一枚铜板,一面是文学性,另一面是科学性,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离开了文学性就不是故事了,离开科学性就不是民间的了。”③董森:《阅尽千帆始识君,褪去浮华归本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学术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年,第27页。
中国民协在组织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也在不断探索科学性与可读性、资料与作品、学术与大众之间的平衡,“二者兼具”被认为是成功的民间文学书面文本。陶阳在评论前文提到的《白族神话传说集成》时说:“总之,‘云南民间文学集成’既有可读性,又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值得参考。”④陶阳:《一次成功的尝试——读〈云南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云南分会、云南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通讯》,内部资料,第9期。
为了使由口头文本转换过来的书面文本具有可读性,“采风运动”中各调查队的主要成员往往是高校中文系学生,他们被认为具有比较强的文字功底与文学素养。三套集成时期的搜集整理者中有大量的文学爱好者,甚至是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事实上,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看作是一种文学创作实践,想要从中寻找灵感与素材。陶阳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后来他又主动选择到《民间文学》做编辑工作,他说:“虽不是理想工作,但可下乡采风,有了生活也可创作,另外,还可像普希金一样运用民间故事素材创作童话诗。”①陶阳:《我与民间文学》,贾芝主编:《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09页。一些被认为重要的民间文学在整理的最后阶段甚至专门邀请作家加入整理团队,如《阿诗玛》1954年版、《梅葛》1960年版分别请来公刘、李鉴尧做了修改润色。
民间文学书面文本的文学性不仅指其语词达雅、情节丰富、结构完善,还需要将之传播到大众,以供民众阅读。钟敬文曾总结民间文学书面文本的功用:“首先,它是民间文艺学者、一般文学研究者、文学史家、民族学者、民俗学学者、文化史学者以及语音学者等的研究资料(全面的或部分的)。他们要从它上面发现各种人民所希望知道的规律。其次,它是提供编纂广大群众,特别是亿万青少年学习的文学读本的重要资源。再次,它是我们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家创作上取材的来源之一……”②钟敬文:《关于故事记录的忠实性问题》,《山茶》,1980年第2期。
作为学术研究资料的民间文学被书面文本化后,自有研究者主动查找、检索与使用,但作为文学读本的民间文学作品却需要对其进行推广与传播。中国民协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民间文学》杂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等曾经都是发表民间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民间文学丛书”“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等也集中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民研会分会也开始创办各自的民间文学报刊,如《民间故事选刊》(河北)、《山西民间文学》(山西)、《塞风》(内蒙古)、《辽宁民间文学》(辽宁)、《吉林民间文学丛刊》(吉林)、《黑龙江民间文学》(黑龙江)、《采风》(上海)、《江苏民间文学》(江苏)、《山海经》(浙江)、《乡音》(安徽)、《故事林》(福建)、《故事家》(河南)、《楚风》(湖南)、《天南》(广东)、《百越民风》(广西)、《南风》(贵州)、《甘肃民间文学丛刊》(甘肃)等。这些刊物都立足本地,兼顾民间文学作品与理论研究文章。而且,其中许多刊物与当时的三套集成结合,其主要稿源正是三套集成工作的成果。
我们会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形容民间文学的搜集路径,70年来,中国民协贯通了这条路径③仅从机构构成来看,中国民协现有团体会员32个,能够充分做到上下连接、通畅沟通,甚至地处中缅边境的瑞丽县1979年就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瑞丽小组。,通过民间文学将国家与民间、学者与基层搜集整理者、学术与文学关联起来,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成为了国家的公共文化,基层搜集整理者与学者共同组成了民间文学的学术共同体,民间文学书面文本既是学术研究的资料,又是大众的文学读物。布迪厄曾将知识场域分为“有限生产”与“大生产”,前者主要针对专业研究,后者则是满足政治、经济、大众的需求。④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4—265页。中国民协也在一定程度上连结了这两种生产,一方面,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既是一项技术性活动,又是一项学术性活动,搜集整理过程也是知识生产的过程,民间文学的若干学科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如书面文本的“格式化”、文类的模糊性、“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等等;另一方面,中国民协通过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民众的口头艺术被带入到更为广阔的现代、政治、商业语境中,从而被确立为“民族经典”,被命名为“非遗”,被跨文化重述,被跨媒介传播等。“‘搜集整理’是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彰显了民间文学文艺价值、文化遗产价值、社会认同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多棱面向。”①漆凌云:《新文艺·民族遗产·学术研究——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三重旨向》,《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从学术团体的角度观照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历史,我们更能发现这些价值的彰显。
本文作为一篇笔谈,无意全面梳理中国民协70年来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事件与成就,如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数字化建档工作等重要活动本文就暂未述及,但是通过片段性的采撷,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民协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学重要的学科传统,培养了大批搜集整理者,一些人甚至“搜而优则研”,成为专业的研究者,而积累起来的书面文本也成为学界与民众最为丰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