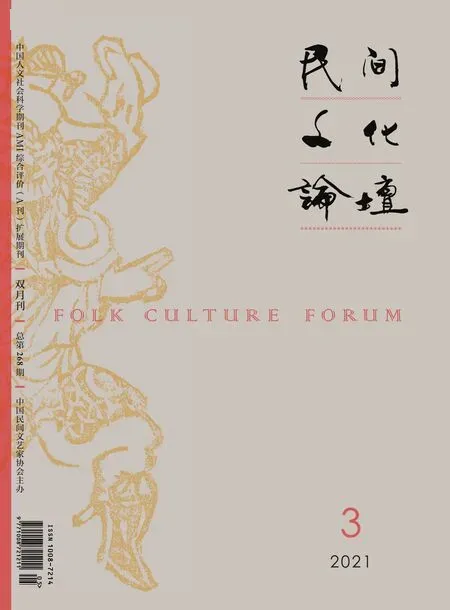作为反思共识的民族志电影
陈学礼
一、民族志电影作为反思共识的媒介
目前,不论是民族志电影的实践操作,还是民族志电影的理论讨论,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为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和影视人类学的研究者接受的共识。比如,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应该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民族志电影的摄影师应该和摄像机跟前人物建立熟悉的关系之后再开机拍摄;民族志电影的摄影师应该尽量避免对摄像机跟前人物造成影响,从而保证摄像机跟前人物像平时一样自然;民族志电影的剪辑应该做到顺畅平滑不留剪辑痕迹的程度,从而保证观众观看影片时的舒适度和愉悦度。
既然是共识,当然有支撑这些共识的论据和理由。比如,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能够保证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对于影片主题的理解;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人物之间具备了良好人际关系,其拍摄素材的可信赖程度就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如果摄影师、摄像机,以及拍摄行为没有对摄像机跟前的人物造成任何影响的话,民族志电影就能“如实”地再现曾经展现在摄像机跟前的一切。
不过,隐藏在这些共识背后的弊端和危险,也不容忽视。达成共识,意味着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守这些共识,以及共识之下实践路径和操作办法。对于初入民族志电影领域的新手而言,如果把这些共识奉为圭臬直接使用,虽不至于走入歧路,却可能灭杀其勇敢尝试放手实验的最初动力。为了保证摄像机跟前人物和平日一样表现自然,摄影师完全可以借助各种手段和技巧,把自己和摄像机对摄像机跟前人物的影响隐藏起来。不管是在足够长的田野调查之后才开机拍摄,还是在和摄像机跟前人物之间建立了熟悉关系之后才开机拍摄,都必然错过摄像机跟前人物初次接触摄影师和摄像机的反应和表现,也无法展现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人物之间建立关系的过程。
所以,有必要对业已达成的共识进行反思。此处所讨论的反思,是如何将民族志电影本身作为反思的媒介和载体,对民族志电影生产实践中已经达成的共识进行反思。如果没有开展前期田野调查,民族志电影会怎么样?如果把摄影师的拍摄痕迹、剪辑痕迹留在民族志电影中,民族志电影的观众会怎么想?如果不翻译摄影师拍摄时听不懂的话语,民族志电影在公开放映时将会有何种遭遇?历史以来形成的民族志电影表述模式的演进更替,是一种进步还是反思的结果或者反思的过程?
二、没有前期田野是否可以展开拍摄
为了民族志电影的拍摄而开展的田野调查,是指在实地拍摄之前对民族志电影的主题所做的调查研究。当然,除了民族志电影的主题本身,还需要了解拍摄地点的基本自然地理状况、气候状况、农作物经济作物种植状况、拍摄地点的民间信仰和仪式禁忌等。学习当地人的语言,详细观察并记录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参与当地人举行的各种活动,询问潜藏在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都是可能的方法。如果是民族志电影的摄影师在做调查,摄影师总是倾向于思考如何用一个一个的镜头去展现自己了解到的内容,而不是如何把这些内容转换成文字。
没有田野调查不能开机拍摄,这似乎已经成为无人能反驳的真理。因为有了足够深入的田野调查,才能保证民族志电影主题的整体性,才能保证其内容的可信赖程度,民族志电影才能作为文化解释的媒介。民族志电影的可信赖程度,也就是民族志电影内容的可信性,而可信性指向的是民族志电影中内容的真实性。只有具备真实性的民族志电影,才能作为影片制作者“向一个文化中的人解释另一个文化中的人的行为”①[意]保罗·基奥齐:《民族志电影的起源》,知寒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的媒介。
不过,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与主题相关的内容之后才开机拍摄,可能导致民族志电影被作为图解田野调查结果的载体。如果这样,民族志电影拍摄和剪辑过程,就变成了图解已经获得的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过程,而不是大卫·马杜格所言的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的过程。如果开展田野调查的人本身就是摄影师,调查之后才开机拍摄的做法将错过二者之间最初相遇的情景。如果摄影师不是开展田野调查的人,摄影师必须在开机拍摄之前就先入为主地接收调查者输送给自己的信息,并用这些信息来指导自己的拍摄。
不开展田野调查就直接拍摄的做法,早有先例。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河南的任村拍摄的段落,路易·马勒在印度德里郊区拍摄收集杂草的妇女,以及印度乡村的一场婚礼,都属于没有所谓的田野调查就展开拍摄的影像实践。在这样的影像中,观众不仅能够看到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的人物相遇的过程,还能看到摄影师如何在拍摄的过程中认识摄像机跟前的人物,以及摄像机跟前发生的事件。
安东尼奥尼和路易·马勒的影像实践,既可以理解为借助摄像机这个工具去开展田野调查,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开展任何田野调查就直接开机拍摄。从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书写的角度看,这样的操作方法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摄影师对摄像机跟前的人理解不到位,摄影师对影片试图表达的内容理解不到位。不过,这种判断暗藏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假设:没有开展田野就直接拍摄的摄影师,不会花足够长的时间进行持续的拍摄。
只要拍摄的时间长度有保障,不管是有了足够深入的田野调查才开机拍摄,还是没有田野调查就直接开机拍摄,最终都能够获得用于文化解释的证据。不过,没有足够的田野调查就拒绝开机拍摄的方式,是把民族志电影作为一个结果来看待;确定影片主题之后没有田野就开机拍摄,是把民族志电影作为一个过程或一种研究方法来看待。
三、让摄影师的拍摄看得见
之所以提出,应该让摄影师的拍摄行为看得见,是因为很多民族志电影中根本看不到摄影师拍摄的痕迹,或者说摄影师的拍摄痕迹在剪辑过程中被彻底清除了。为什么这些民族志电影要刻意掩藏摄影师拍摄的行为和过程?据我自己的理解,或者因为影片制作者严格遵守了观察式民族志电影的戒律,或者是担心观众看到摄影师对摄像机跟前的人物的影响,并据此怀疑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不过,此处强调让观众在民族志电影中看得到摄影师拍摄的行为和痕迹,目的也是为了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只有保障了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其内容才能用于文化解释。在掩藏了摄影师拍摄痕迹的民族志电影中,影片的制作者坚信,观众看到的是摄像机跟前人物的真实生活状态,或者文化的本真样貌。在倡导摄影师拍摄行为看得见的民族志电影中,影片的制作者希望观众看到摄影师对摄像机跟前的人物的影响,或者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影片中呈现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也就是说,观众看到的只能是摄影师出现在现场之后,摄像机跟前的人物和事物的样貌。
这里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操作方法带来的不同结果。在《上囡村影音日志》①陈学礼、岩上应、岩勐布:《上囡村影音日志》(97分钟),勐海深山老林茶厂出品,2018年。中,一个小伙子在火塘边,翻弄着铁架上的烤肉,一副专注的表情。待烤肉摆好,小伙子两手打开,朝摄影师看过来,并问道“好看么”,摄影师回答“好看呢”,两人随即大笑起来,之后是这个镜头的出点。这个出点是保证摄影师的拍摄可以看得见的出点。试想,如果把这个镜头的出点放在小伙子把肉摆弄好,尚未打开两手朝摄影师看过来之前,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民族志电影中的出点,让观众接收到的信息是,小伙子知道摄影师在拍摄,所谓专注的表情只是小伙子装出来的。如果像前文所述那样改变这个镜头的出点,观众得到的信息是:小伙子在专注地摆弄烤肉,并没有在意摄影师的存在与否。可现实的情况是,小伙子确实知道摄影师在拍摄。所以,观众应该根据摄影师在场,小伙子知道摄影师在场的情景事实,去理解小伙子摆弄烤肉的行为。在后期剪辑中,剪辑师应该根据实地拍摄的情景事实来决定一个镜头的入点和出点。
让摄影师的拍摄可以看得见,还应该往前推进一步:即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应该在影片生产过程中的不同时间节点、合适的情景状态、与被拍摄者不同的关系状态下,进入到自己的影片中”②陈学礼:《民族志电影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必要性》,《江汉学术》,2019年第5期。。负责民族志电影实地拍摄的摄影师,其身影、声音能够呈现在影片中,是为一种看得见;摄像机跟前的人物对摄像机、摄影师、录音师,以及其他在场工作人员的反应,能够被观众感受到,是为第二种看得见;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通过解说词的方式,还原拍摄时的情景事实,是为第三种看得见。而且,所谓“合适的时间节点,与被拍摄者不同的关系状态”,暗含的是一种历时的向度。随着民族志电影实地拍摄时间的不断增加,随着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不断推进,摄影师应该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和关系状态下,进入到自己的影片中,并让这种“进入”能够被看见。如果这样,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和摄像机跟前人物之间,从陌生到相互认识,从相互认识到逐渐熟悉,从逐渐熟悉到不再客套的关系演进过程,也成为了民族志电影中的一个内容。与此同时,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通过拍摄的过程逐渐理解影片的主题,对影片拍摄的内容进行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民族志电影的一个内容。如此一来,民族志电影所呈现的,既不是制作者完全了解了影片主题时所拍摄到的样子,也不是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和摄像机跟前人物关系熟悉之后的样子。
让摄影师的拍摄可以被看见,是因为承认摄影师和摄像机出现在拍摄现场时,一定会对摄像机跟前的人物造成影响,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事物的样貌,甚至改变事件的进展。所以,让摄影师的拍摄可以看得见,一方面,可以打消观众在民族志电影中寻找“原原本本”文化的执念。另一方面,还能为观众提供实地拍摄时的情景事实,以便其理解民族志电影中的人物和事物,如何在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的人物,以及其他外力的合力下,形成了民族志电影中的样子。
四、让剪辑师的剪辑看得见
在民族志电影的后期剪辑过程中,剪辑师在剪掉摄影师拍摄痕迹的同时,并利用精巧的剪辑技术把剪辑的痕迹也隐藏起来,实现了所谓看不见的剪辑。看不到拍摄和剪辑的痕迹,就意味着观众能够不受影片内容和情节之外的因素干扰,能够达成让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这正好与民族志电影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实质相矛盾。因为民族志电影是摄影师对生活现实进行第一次碎片化之后,剪辑师在第一次碎片化结果的基础上二次碎片化的结果。于是,民族志电影的剪辑,要么创造符合观众视觉经验的想象整体,要么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意识到影片的碎片化实质。
让剪辑师的剪辑可以看得见,就是无须刻意隐藏摄影师在实地拍摄中的选择行为,无须刻意隐藏剪辑师在后期剪辑中的选择行为。与拍摄和剪辑中的选择相伴随的行为,是省略。实地拍摄中开机拍摄的点和结束拍摄的点,后期剪辑中重新确定一个镜头的入点和出点,都是摄影师和剪辑师进行选择的痕迹。换句话说,让剪辑师的剪辑看得见,就是在打破剪辑规则的情况下,让剪切的痕迹显现出来,比如跳接(Jump cut)的剪辑手法。在同一个机位,使用同一个景别拍摄的同一个人物的访谈,或者在同一个空间,使用同一个景别拍摄的同一个人物的活动,只要剪掉其中任何一帧,或者任何一个段落,把留下来的两部分前后排列,都属于跳接的剪辑方法。剪辑师不愿意采取这样的剪辑方式,是因为影片播放的时候会给观众的眼睛造成不适的感觉。于是利用所谓的插入镜头,或者特效来消除这种“跳”的痕迹。
但是,如果让剪辑师的剪辑看得见,至少这样可以让观众明白两个道理:其一,民族志电影的实地拍摄和后期剪辑都在选择某些内容的同时,省略了另外一些内容。其二,民族志电影是借助这些选择的内容进行事件和文化事项的重构以及观点的表达。实际上,民族志电影的表述形式,决定了观众对影片内容的理解。比如,观众看到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借助摄像机跟前人物的言语和行为进行观点的表达;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把那些不利于影片表达的观点的内容省略了;影片中呈现的场景和内容是在摄影师和摄像机的影响之下生成的。观众看到哪一种类型的表述方式不重要,但是,如果剪辑师的剪辑能够被看见的话,至少能提醒观众,不要盲目地把影片中呈现的内容作为文化解释的唯一依据。让吕克·戈达尔使用跳接的方式进行影像叙事,其中一个目的在于反对好莱坞提出的影像叙事铁律。民族志电影中采用跳接的方式,目的在于唤醒观众的理智,在观影的同时认识民族志电影实地拍摄和后期剪辑的碎片化实质。
在一部民族志电影中,通过合适的方式,让观众不断地意识到:自己在看一部经过人为选择和省略得来的民族志电影,自己在看一部由制作者建构,并包含制作者观点的民族志电影。如此一来,观众就能在观影的过程中获得思考的空间,和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拉开距离来审视民族志电影本身,而不是和制作者站在一起来审视民族志电影中的人、事物和文化事项。另外,如果让剪辑看得见,就能消除某些设置在民族志电影中的悬念,让民族志电影以接近生活流淌的方式,呈现在观众跟前,促使观众以更加理性的心态和立场,来面对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在影片中做出的解释。
五、不翻译摄影师听不懂的对话
在后期剪辑开始之前,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个共识是,应该把拍摄的素材整理归类,并把其中人物的所有对话翻译出来,以确保剪辑时不遗漏任何重要的信息。共识归共识,但现实中的民族志电影制作者突破共识的情况不在少数。制作者或者懒惰,或者在尚未翻译对话之前就主观确定了重要的内容和可以舍弃的内容,或者因为时间和经费的原因,往往在完成初剪之后,才请懂得片中人物语言的人来做翻译,或者通过翻译确定重要的信息,或者通过翻译把某些遗漏的重要信息补充到初剪的版本中。此处不讨论如何翻译片中人物的对话,也不讨论翻译时保留本地方言的特色还是使用书面语言。而是对已经达成的共识做一些反思并提出可能性:即后期剪辑中不翻译实地拍摄过程中摄影师听不懂的人物对话,也不用字幕对镜头中包含的内容进行总结和概括。
不翻译片中人物对话的做法,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在《极乐园》(Forest of Bliss)中很早就使用过了。《极乐园》拍摄完成于1986年,而Timothy Asch 和约翰·马歇尔第一次在影片《爱,开玩笑》(A Joking Relationship)使用对白字幕的时间,是1966年。罗伯特·加德纳既不使用解说词,也不采取配音(把人物对话翻译出来,用观众能够听懂的言语配音)的方式,而是做了更加激进的尝试,即不翻译片中任何人物的言语。
对于片中人物对话翻译与否的反思,可以往前推进一步。比如,摄影师在实地拍摄过程中能听懂的对话和言语,就用字幕的形式呈现在影片中;如果摄影师听不懂的对话,就不翻译,也不用字幕的形式呈现对话内容。而且,如果摄影师既听不懂摄像机跟前人物的对话或言语,也不明白摄像机跟前人物行为的意义,这样的镜头不应该放进最终的民族志电影中。所以,最终进入民族志电影的镜头包含两类:摄影师既能听懂摄像机跟前人物的对话和言语,又能明白摄像机跟前人物行为的意义的镜头;摄影师不能听懂摄像机跟前人物的对话和言语,但是能够明白摄像机跟前人物行为意义的镜头。在前一种类型的镜头中,摄影师把自己的发现,自己对于被拍摄事物和主体的理解直接呈现给观众。后一种类型的镜头中,摄影师把自己能够模糊感知到的信息,通过镜头呈现出来,邀请观众和自己一起理解被拍摄的事物和摄像机跟前人物的行为。
不翻译摄影师实地拍摄时听不懂的人物对话和言语,这样的操作方法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民族志电影应该是摄影师拍摄到的,而不是摄像机拍摄到的;其二,民族志电影的镜头应该是摄影师对拍摄现场做出反应的一个结果。所谓的对现场做出反应,就是摄影师在听懂摄像机跟前人物对话和言语的情况下,在明白摄像机跟前人物行为的情况下,适时做出机位调整、景别变化、拍摄角度改变的决定。只有在此基础上拍摄下来的镜头,才应该是组成民族志电影的镜头。
余 论
民族志电影的摄影师在没有开展前期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就直接开机拍摄,在拍摄到的影像中,既能看到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的人物之间相遇的整个过程,也能看到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演进过程。在最终的民族志电影中展现摄影师拍摄的痕迹,也就是展现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的人物之间相互遭遇,相互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帮助观众理解民族志电影中的影像所对应的生活现实是如何被转化为影片中的样子。这样的尝试和努力,都是对民族志电影业已达成的共识所进行的反思,而且,这种反思既体现在民族志电影的表述形式中,也体现在民族志电影试图表述的内容中。
民族志电影的摄影师应该以非虚构的影像获取方式来完成拍摄,这种素材的获取方式,也可以称之为写实的方式。不过,这种写实不是机械地复制和记录,而是从生活现实中引用碎片来进行观点表达的过程。当然,需要进一步考量摄像机跟前的生活现实的实质,才能对“引用碎片”的过程有更好的理解。即,摄像机跟前的生活现实,是摄影师和摄像机出现在现场之后,由摄影师、摄像机、摄像机跟前的人物,以及其他可能的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现实”,而不是所谓的生活现实的本来样貌。所以,摄影师到底是要再现摄像机跟前人物原原本本的生活现实,还是再现摄影师带着摄像机介入之后创造的生活现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样的区分,有助于回应这样一个问题:民族志电影的写实,到底写的是什么“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