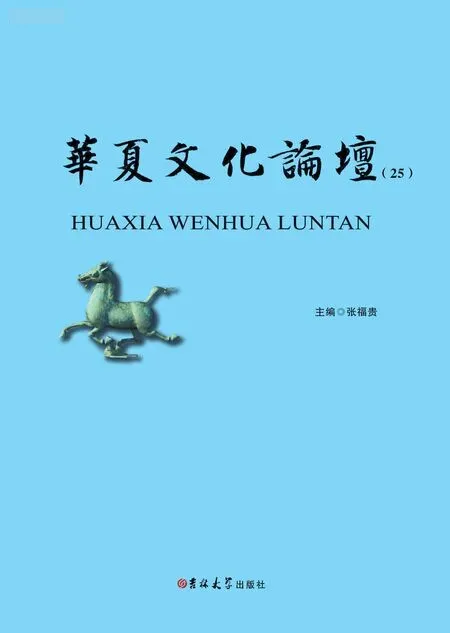女性主体言说的困惑
杨国颖 吴景明
一、女性主义理论的困惑:从“二元对立”到“辩证关系”
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及相关文学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兴盛至今,引发学界持久关注,其中关于女性主体的探讨尤为引人瞩目。然而由于这一理论本身隐含着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不仅女性文学在喧哗过后趋于平淡,女性主义似乎也陷入了一种两难处境。《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是女性文学研究学者戴锦华的论文,文章大致勾勒出五四以来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面貌,并指出:女性的真正困境是在“女奴/女战士”(秦香莲/花木兰)模式之间、在“女性特质”和所谓“与男人一样”之间徘徊。前者遮蔽了女性,而退回到后者,女性主体又往往要借助其他话语,被整合于其他话语内来浮出地表。当言说“女性”时,这个能指符号总是不经意间滑向她们所依赖的话语中的其他所指意义;而当女性言说时,她们发现自己陷于失语的尴尬境地。换而言之,女性建构自己的主体时,无法表述自己的本质。
戴锦华在论文中梳理了关于“女性文学”诸种的定义:第一种“女性创作的文学”,第二种“关于女性或以书写女性的文学”,第三种“狭义的、表达女性体验颠覆男权文化的文学”,并认为“关于女性”的说法过于宽泛,甚至包括了大量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反而构造和加固了本质主义的“女性”概念;而第三种最为激进的“女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是缺席者。所以她支持第一种界定。当然,戴锦华并非没有意识到第一种定义的缺陷,即以作家性别作为标准导致的分类的粗暴简约:“女性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写作是女性文学,因为她抒发了女性的生命体验;而女性以‘花木兰’身份,在男作家或普遍的‘人’的假面下写作,也是女性文学,因为她这一写作行为和创作理念(未必是作品本身)就是女性困境活生生的体现”——实际上,只要女作家动笔写作,无论写什么都跳不脱“女性文学”的圈子,只因为她是女人?
当然,各种概念界定都有其适用原则与范围,也都有其优势和不足,目的是达成共识以便思考与言说。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寻根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没有过多纠结于定义?为什么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没有以自己的命名建立一个“××文学”?其原因在于:前者以题材分类,后者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目的在于解读文本,从文本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而并不奢望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反观“女性文学”,其概念内涵之所以颇具争议,其原因在于“女性文学”迫切需要一个定义,以确立自己作为一种“文学”的地位。由此带来的,比概念内涵更有意义,也更尖锐的质疑是:“女性文学”到底想成为、能成为一种什么“文学”?是作为题材,还是方法论,还是全新的“文学”?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何在?
其实“女性文学”问题的实质体现在:“女性文学/男性文学”同样源自“女性/男性”这一根本性的二元对立。女性文学的问题也就是女性的问题,即女性主体性的问题。继“性别是被建构的”学术观点流传之后,美国朱迪斯·巴特勒的《消解性别》、《性别麻烦》等著作于2009年被陆续翻译出版,使学界系统地探究其理论全貌成为可能。而与她有过交谈的斯洛文尼亚的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理论更为抽象,他表述的不仅是女性的问题,更是关于象征秩序与不可象征的真实域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特殊”的辩证关系。从上述观点回望 “女性文学”,不仅对两性问题、性少数的问题、甚至更宽广的身份问题都展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二、权力话语与象征秩序制约下被建构的“女性”

实际上,关于女性主体性的问题确实无法回答。正如波伏娃“变成女人”的经典命题已然蕴藏着最激进的性别理论,同样,女性的失语和匮乏也已经暗示了这样的思路:不要试图在“男性/女性”二元划分的模式上寻求女性不同于男性的主体性。追问主体性或许不应被直接斥为假问题,但能得到的答案无非止步于“主体的匮乏”。为什么女性总是彷徨于“女奴/女战士”、“女性特质”和“与男人一样”两难选项之间的“无地”?为什么“先做人,还是先做女人”会成为一个类似鸡与蛋的难题?其根源在于因为学界相信有一个逻辑上在先的主体——“女性”的存在。她不同于另一个主体“男性”。千百年来“女性”被压抑了,被遮蔽了,被“男性”赋予了许多特质而成为客体,但这些特质却不是由“女性”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发展而来的。女性不仅要在现实生活中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更需要在理论上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发展一种全面或是足以再现妇女的语言”。“先做人,还是先做女人?”争论焦点的实质是把“人”放在比“男人/女人”逻辑上更优先、更纯粹的位置(这往往被斥为“抽象人性”),还是将其视为一个集合概念。
但先验的“女性”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从社会现实和文学艺术中考察“女性”的种种问题,并最终得出“匮乏”的结论,整个过程正揭示了权力话语和象征秩序运作的模式。如果女性的“无”是上述权力话语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上述权力秩序运行的机制,研究者还能奢望女性摆脱“无”,而以另外的身份加入其中吗?换言之,被压抑、被遮蔽、被误读,正是权力言说“女性”的方式;不仅如此,象征秩序也必须通过边缘化女性得以建立;在认可这种话语和秩序的大框架下,在不打破“男性/女性”二元模式的前提下,又怎么可能使女性成为这种话语和秩序中能够言说的主体?正如巴特勒所说的:“把妇女再现为女性主义‘主体’的语言与政治之司法建构,它本身就是话语建构的,是某种特定形式的再现政治的结果。结果女性主义主体成了那个原本应该是推动其解放的政治体系的一个话语建构……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加批判地诉诸这样的一个体系来‘解放’妇女,显然是自砸阵脚。”
上述论述显现了更关键的问题:其实“男性/女性”不是先于话语和秩序存在,而又被话语和秩序安排和塑造了的;恰恰相反,“男性/女性”就是话语的产物,这种二元模式就是秩序本身。也就是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不是一个自然的、纯洁的、没有被任何文化附着的、空洞而有待生成的本质,而“总是—已经”被权力生产和塑造的,总是处于象征秩序中的。当我们说“女性是匮乏”时,并非有一个本应该、本可能丰富的女性受到种种影响导致了匮乏,而是在这套话语中,“匮乏就是女性”。“女性”不是具有“匮乏”属性的一个主词,而是匮乏的同位语;女性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因果性必须被再次强调,这一黑格尔辩证逻辑的精髓贯穿在性别理论、精神分析、解构主义语言学等后现代诸多理论中。当我们谈及米歇尔·福柯的著作《性史》时,最常说的就是他的经典结论:“性不是被压抑的,而是被生产、被言说的”。并且“性别不是天然的,而是被建构的”这样的话也随处可见。但是,不仅仅要知道“什么都是被建构的”——这有把福柯的思想简单化,并沦为虚无主义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权力生产出“性”的概念,又将其隐藏,仿佛它是权力之前的东西,是需要权力来安排和管理的东西,这样就“合法化了律法本身的管控霸权”,即权力针对这个对象具有管理的合法性,被倒置了的“性”看上去也就成了原因而不是结果。当我们进行理论反思时,关键是要“倒因为果”,通过这个逻辑上的颠倒来勘破权力的秘密。这种逻辑学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特点同样体现在精神分析和其他理论中,正如Slavoj Žižek总结的:
原因并不先于它的结果,而是被它的结果自我反作用地设置的,这种作为原因的创伤是一个悖论,该悖论包含着一种时间的循环:正是通过它的“重复”,通过它在指示结构中的影响,原因反作用地成为它总是已经成为的东西。
这段晦涩的话更精练地表述了这种因果关系——它绝不能被“平面化”地理解为“因就是果,果就是因”的相互决定的循环,而是像莫比乌斯圈一样“弯曲空间的拓扑结构”,有一个要紧的“翻转”。并且“原因”和“结果”都不是自然科学那种线性因果论、决定论(否则也无法实现颠倒了)。回到女性主义,巴特勒的“操演理论”(Performativity)——源自“perform”一词,但巴特勒最不希望人们将她的意思理解为日常语言中的“perform”,表演,因为说“表演”,仿佛还有一个表演状态之外的“本人”,而这恰恰是巴特勒所要解构的。所以译者也专门选择了与“表演”一词不同的“操演”。这也就再次体现了这种因果性。她认为 “女性‘总是—已经’在操演行动中成为自身,仿佛总是戴着重重面具在表演”。既然我们意识到种种身份、种种“女性特质”不过都是外在“面具”,自然就容易认为“面具”底下还有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可巴特勒却说“面具”之下一无所有。并非“原貌” 被覆盖上面具,而是“面具”使我们设想并相信“有”原貌。那么,是不是本来什么都不存在?这样的设想是不是无聊的虚构游戏呢?当然不。巴特勒的意思是反对一种本质主义的原貌,但并不意味着有一种“使面具之为面具”的“某物”不能被设想。如果不假设“原貌”,“面具”又如何称之为“面具”呢?“面具”需要设定“原貌”来确证自身,但是当你想追寻“原貌”时,它却总是在一个又一个“面具”底下逃逸。“原貌”与“面具”之间不是线性决定的因果关系,而是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可以类比Jacques Lacan的“真实域”和“象征域”之间的裂隙。“原貌”是必须被设想的,是在理论上必须“存在”的,它是启动整个象征游戏的开关。象征秩序也正是围绕这样一个永远不可能显现、永远逃避着象征化、永远有意义剩余的“真实”才得以建立。只是,两者之间的分裂必须被保持,“真实”永远不能照进“象征”。
在解构主义的大潮下,“主体是被建构”的之类的表述往往有这种简单化的误读即反叛传统的主体性哲学,认为迄今为止所有主体都是被文化建构的。当然,这么说虽然没有错,但这种理解容易滑向将文化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视作决定论,一提到“前文化的主体”,就斥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主体,甚至可以说“没有主体”。然而这种“抽象主体/被建构的主体”的区分一般是精神性的和文化意义上的,当这区分遇到活生生的有差异的男性、女性身体时就束手无策了。因此传统女性主义只能说“存在着自然的、生理的女性,她们‘被塑造’‘变成’了社会的女性,妇女解放就是要颠覆既有的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为生理的‘女性’开出一片新天地,使她们能够自由发展,自我重构”——按传统的女性主义,现在的女性已经是被建构的,但是是被男权文化建构的,应该重新寻找自己的主体性。因此这里将传统女性主义的策略归纳为“重构”。这两种误读一是反本质到了极端,认为只有建构出的面具,而原貌纯粹是多余的假设;但这种极端很快就被证明行不通,所以只好想另一种办法:既然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普遍的、抽象的、具有某些先验能力的主体,那么就寻找一个被动的、自然的、纯洁而有待建构的主体——某种变形的“本质”又被偷运回自称解构的理论中,殊不知这个貌似“前文化”的自然主体同样是文化建构的成果之一!
只有通过米歇尔·福柯将权力视为生产性而非压抑性的理论,通过拉康对想象域和 真实域的区分,通过因果性的辩证“颠倒”,才能理解Judith Butler 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解构。解构生理性别,并不是对物质性的身体的差别视而不见,但这种差别或许也像颜色光谱一样,完全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在语言中被划分和命名;要质疑的是,为什么偏偏是“男性/女性”这种划分,这种语言的生产还被视作自然的、生理的、科学的?这一结果居然成了一切关于男性和女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女性解放的策略难道是返回生理性别的起点,再重走另一条自我建构之路?在Judith Butler看来,这显然是自砸阵脚,自相矛盾。福柯在《性史》中提出,“不仅社会性别是被建构的,生理性别亦然。它并非外在于权力建构的一片净土,而是权力话语引导我们产生的想象。它同样内在于话语和秩序中。”其实权力的特征之一就是“内在性”,不存在所谓的自然领域或中立领域,自然和中立的东西都是权力制造出来的,而对权力的反叛和颠覆也是在权力之中的。因此,挪用魏宁格(Otto Weininger)的结论:女性并不存在。——当然,不是根据他的论证,而是指作为话语中的、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女性”并不存在。但是,当我们发现了权力的秘密,发现了象征域的边缘,便可以知道仍然有一个使话语得以成立的“女性”(严格地说上不应该再用这个词,下划线以显示区别)存在,所有关于它的话语都是对它不断加以象征而总是失败的尝试。我们无法言说这样一个“女性”,我们只能在权力内部运用那些话语,然而保持这种清醒意识,拒绝使“象征域”与“真实域”短路,也许可能找到适当的解放策略,不会一再陷入诸如“女性”之类已经物质化、自然化的范畴。
三、从“女性主义”到“性别理论”“性别研究”
至此,上述关于“女性”的论述似乎已经过于抽象,离文学和社会现实渐行渐远。不可否认,在现实中呼唤女性自觉意识,树立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争取平等的地位和权力,仍然是十分迫切的任务,所以大谈“解构女性”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正如戴锦华所言,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女性早晚要走到自身匮乏和失语的窘境。并且——再一次运用“颠倒”的辩证逻辑——这最后的困境实际上是一早就埋下的原因。”所以,Judith Butler 的理论看似激进,却不乏现实意义。她已经看到,西方世界一次次的妇女解放运动走到“胜利”的尽头,都面临这样的“性别麻烦”,实际上这最后的麻烦却是所有麻烦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妇女解放、为女性争取权益的运动策略是错的,但Judith Butler 的理论却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促使我们在解放的策略上有新的设想。Judith Butler的这种后起的、先锋的理论,却将问题推到了最原初、最根本的环节,对“女性”解放乃至更大范围的性别解放运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既然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可与男性分庭抗礼的另一种“女性主体”已经不可能,既然也无法彻底颠覆原有秩序而建立全新秩序,所以Judith Butler选择了“戏仿”的策略,也就是在有意识地保持距离的前提下,重复操演那一套话语,践行那一套秩序。这样就会揭露“秩序”自身的建构性质,寻找到权力的裂隙。但另一方面,既然男性和女性并非在话语之先,而是生产出来的结果,或者说被塑造的、被赋予各种意义的范畴,既然我们对性别已经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那么选择做女人或做男人又有何不可呢?自觉地做“与男人一样”的花木兰,或者“认可女性特质”又有何不可呢?如果一个女人自觉地认可“被排斥”、“被边缘化”或“客体化”的处境,这又何尝不是女性自我选择权利的体现呢。
回头来看,女性主体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它之所以不能问,是因为“有待重构的女性主体”在权力结构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福柯在《性史》 中提出,权力的特征之一就是“内在性”,不存在所谓的自然领域或中立领域,自然和 中立的东西都是权力制造出来的,而对权力的反叛和颠覆也是在权力之中的。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要理解从Simone de Beauvoir开始回响了半个世纪的名言“女性是被建构的”,更应该进一步理解:“某物”是被建构的,建构的结果叫作“女性”,而这个“女性”又被当作是建构之前就存在着的,但实际上,作为结果的“女性”只在于其建构过程中显现本质,而不是先有本质存在。
如上所述,“女性主义”以“女性”为标签其中的“悖论”得以显现——“女性”正应该是此种主义倡导者应该打碎的枷锁,或许代之以“性别理论”“性别研究”更合适。至于“女性文学”,无论是划分出一些作品构成一个门类,或是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甚至建构出一部“不同于男性叙述视角”的女性文学史、一套女性的文学批评理论,恐怕会成为虚无缥缈的幻影。因为 “女性文学”建立的原初、这个概念的提法,以及其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无一不是最陈旧、最粗糙的二元对立模式。那些“女性创作的”、“关于女性的”、“颠覆男性的”说法,甚至远没有达到波伏娃“变成女人”的认识程度。“女性文学”注定不可能成功,它目前的存在与其说颠覆,不如说加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尴尬状况。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理论家都停留在最陈旧、最粗糙的二元对立模式上,她(他)们也在不断地学习、思考、推进性别研究。目前“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不乏最新最激进的理论。但理论虽然是前卫的,可是“女性文学”这个概念被提出时,是不是缺乏一种自觉的反思?是不是建立在无意识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在这样一个陈旧的概念框架下,试图不断拓展理论水平,进行突破性的创作实践,只会越走越窄。这个框架在发展中最终会被打破,还是顽固地扼杀自己,更应该成为学界深思的问题。也许放弃这种宏大的建构野心,以性别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文学批评的武器,在批评实践中不断丰富理论资源,倒不失为更实际、更扎实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