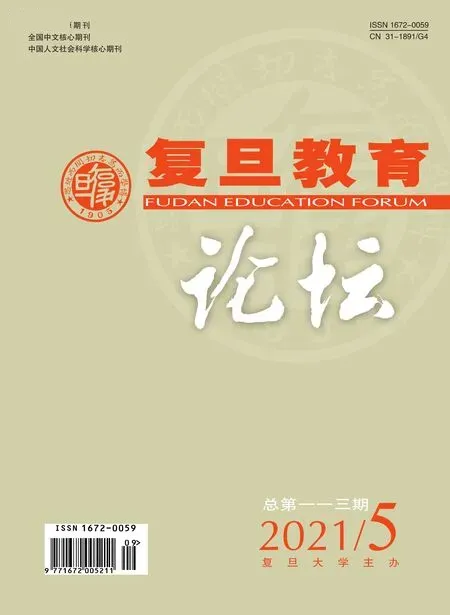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实证研究
——以我国东中西部10个贫困县为例
樊晓杰,林荣日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433)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改善民生是我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工作,改善贫困地区居民家庭的生存状况更是当前解决民生问题的第一要义。教育投入不足会导致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而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十几年来,我国教育投资体制在逐步转变和完善,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经费保障新机制,免除学生学费和学杂费,并给予寄宿生一定的生活费补助(即“两免一补”),以此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仍然面临教育投资十分有限的困境[1]。
2020 年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按照既定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将在年底全部脱贫。要真正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有许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包括家庭教育投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家庭教育投入或支出状况进行研究。本文将着重研究贫困地区居民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在这两种家庭资本因素中,哪一种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2)在贫困地区居民家庭子女受教育的不同阶段,这两种资本因素分别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教育阶段性差异?
二、核心概念
1.家庭资本及其分类
家庭资本的概念源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的社会资本理论,该理论不仅对个人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在学校建设、社会进步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2]。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首次对家庭资本作了定义,即可以为家庭成员的社会活动带来好处或影响的各种有用资源[3],其中,教育活动是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外学者对家庭资本给出了不同的分类。美国学者科尔曼(Coleman)将家庭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类[4];蒋国河等认为家庭资本主要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三类[5];李春玲[6]、薛海平[7]提出家庭资本可分为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以及家庭政治资本等四类。以下笔者仅对与本文比较相关的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两个概念进行说明。
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资本中最重要的资本形式,也是其他家庭资本的物质基础。家庭经济资本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与经济有关的资源总和[8]。家庭文化资本则是家庭及其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以及文化背景等资源总和[9]。家庭文化资本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自身所获得的学历和文凭证书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及教育期望等方面[10]。
2.家庭教育支出
家庭教育支出是家庭成员参加所有教育活动的年度经济投入,一般是指家庭对子女的正规教育所支出的各类费用总和,包括在校内的基本教育支出以及与课外学习相关的各种消费支出[11]。随着我国教育内容的日益多样化,家庭教育支出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它不仅包括学费、书费、住宿费、伙食费、校服费、交通费、择校费、补课费、兴趣班费用、家教费等,还扩展到了夏令营、暑假文化班、学习用品及电子产品、教育储蓄和教育保险以及其他类型家庭教育支出项目。为了更加客观地分析贫困地区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情况,我们的调研涵盖以上各类教育支出。
三、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研究
众多的研究表明,父母教育程度、教育观念、教育投资回报、个人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文化资本因素[12]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对教育的支付承受能力、地区经济状况等经济资本因素,都可能影响家庭教育支出[13]。
日本学者Hashimoto 等利用日本1989 年全国收入与支出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弹性系数为1.72,收入变动对家庭教育支出变动的影响显著[14]。张俊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学历家长倾向于重视孩子的教育,愿意给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15]。周强认为,随着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在相应维度下的贫困发生率会明显下降,而且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减贫绩效也越明显[16]。
教育观念反映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关怀程度和对教育行为的看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父母是未成年子女教育的主要决策者和支持者,父母的教育行为影响子女的学习绩效,而教育行为又决定于教育观念[17]。农村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决策出自他们在有限资源下最大化家庭预期收益的理性考虑[18],在多数农民的思想观念里,教育是“有用”的,它的有用之处主要体现在经济回报这一物质层面[19]。而对于贫困地区家长的教育观念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这一问题,尚未有明确的研究结论。
家庭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未来教育成就的现实性信念和判断。众多学者认为家庭教育经济支出、时间投入以及教育陪伴会随着教育期望的提升而增加[12]。崔超男对农村留守儿童家庭进行调查后发现,儿童学业成绩与父母教育期望呈相关关系,且低教育期望会促进儿童辍学率上升[20]。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子女就读的年级越高,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越低。由于经济压力与教育基础的限制,农村家庭存在着“高期望低支出、单项式参与”的特点[21]。
(二)有关贫困地区不同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我国贫困地区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在不同教育阶段存在差异。在义务教育阶段,张瑛根据四川省和湖北省2005-2006年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贫困地区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农户实际的经济承受能力[22]。楚红丽认为,中国初中阶段的教育投入会高于小学阶段,同一阶段城市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会高于农村家庭[23]。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任晓玲等研究发现,学前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对儿童发展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经费支出是关键影响因素,时间支出和文化资本是两个重要影响因素[24]。在高中教育阶段,雷万鹏对北京市等四省市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家庭年收入会显著影响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家庭年收入每增长1%,教育补习支出随之增长0.19%[25]。而周雪涵基于济南市高中生所在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高中阶段家庭经济收入与家庭教育支出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教育支出呈正相关,中考成绩与家庭教育支出呈负相关,农村与城市之间无显著差异[26]。
(三)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文献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均有研究。但是,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角度:一是多侧重于某类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较少将二者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二是多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前期我国贫困县的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情况,而对政策后期即将脱贫或刚刚脱贫的县的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情况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贫困县居民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均会显著影响家庭教育支出,而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更大。
假设二:贫困县居民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存在教育阶段性差异。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一)数据来源及基本数据特征
为了研究贫困地区居民家庭的教育负担和教育支付能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支付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课题组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了《2018 年农村家庭教育状况调查表》并进行问卷调查。该问卷分为贫困县居民家庭基本信息、家庭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内容五大维度。在问卷发放时,综合考虑了我国不同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贫困县为基本调查单位,分别选取了东部地区的福建平和县、江苏阜宁县,中部地区的湖北巴东县、孝昌县、大悟县以及江西吉安县,西部地区的甘肃秦安县、通渭县、临洮县、乐民县共10个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10 个贫困县13379 户家庭的基本信息。为了更好地分析基础教育四个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情况,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无效样本后,筛选出家庭子女均处于基础教育学习阶段的4939 户家庭样本,其中学前阶段样本1218 户、小学阶段2552户、初中阶段745 户和高中阶段424 户。同时,将“建档立卡户”作为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参考指标。“非建档立卡家庭”有2784 户,“建档立卡户”2155 户,详见表1。

表1 数据来源及样本量(单位:户)
表2具体呈现了本研究中贫困家庭和普通家庭各教育阶段人均收入和人均教育支出的统计结果。在被调查的10个贫困县中,2018年贫困家庭人均收入为16590元,普通家庭人均收入为17747元。当子女在初中阶段时,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最低,平均为14602元;当子女在幼儿园阶段时,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最高,为18210元。与之相比,普通家庭人均收入普遍高于贫困家庭。当子女在初中阶段时,普通家庭的人均收入最低,平均为16376 元;当子女在高中阶段时,普通家庭的人均收入最高,为22093元。
贫困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明显高于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高于同一阶段贫困家庭的支出。具体来看,小学阶段普通家庭人均教育支出最低,平均为8196 元,初中阶段为8500元;而贫困家庭在小学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为7087 元,初中阶段为7592 元;当子女处于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时,家庭的教育支出明显增加,普通家庭教育支出达到人均15016 元,贫困家庭为14087 元;幼儿园阶段的普通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为10127 元,贫困家庭为9452元。
(二)关键变量
本文的关键变量有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以及受访家庭基本特征。因变量是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即家庭教育总支出除以家庭上学孩子数量。在实证模型中,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取对数。
家庭文化资本通过父母的教育观念、教育期望及受教育程度这三个变量来测量。本文将父母教育观念定义为父母对其子女教育的态度和看法,通过“供养孩子上学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孩子不上学、没文化是不行的”等11 道问题和十分制打分量表进行测量。同时,对教育观念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进行检验,发现每个问题的α 值都在0.8以上,说明教育观念问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最后,运用线性综合法得出父母教育观念的最终得分。本文将父母教育期望定义为父母对其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以“您(父母)希望孩子的最高教育程度”来衡量,其中“9=能读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初中毕业,12=高中/技校/中专,15=大专,16=大学,20=硕士,24=博士”。父母最高学历根据“0=小学以下,6=小学,9=初中,12=高中/中职/中专,16=大专/本科,20=研究生及以上”来衡量。
家庭经济资本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子女教育对家庭经济影响程度以及当前家庭经济承受子女教育最大程度这三个观测变量进行测量,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的“2018 年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根据您(父母)家庭现在的收入,可以承受孩子教育的受教育程度”三道题目,家庭教育承受度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衡量标准相同。
同时,将受访家庭的基本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调查家庭的民族、户籍、子女数量、家庭所在地区等。其中,民族变量以汉族为参照,户籍以是否为农业户籍分别构建虚拟变量。
(三)研究思路
本文对调查数据进行多角度分析,以了解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具体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计算贫困县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差异,并利用方差分析结果来判断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显著性问题;其次,以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这四个基础教育阶段产生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研究发现,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建议。
五、实证分析
(一)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具体呈现了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各个因素、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分别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描述统计值和卡方检验结果。从父母教育观念的指标来看,子女就读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父母教育观念得分整体高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子女就读小学阶段的父母教育观念得分达到5.46,而高中阶段得分最低,只有4.61。家庭教育期望随着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略有提升:在初中以下阶段时,父母期望子女不仅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且可以接受高中以上的教育;在高中阶段时,父母希望子女接受大专及以上的教育。

表3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基于2018年10个贫困县的调研数据)
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指标来看,父母自身多为未完成高中教育的文化程度,但子女在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的父母,其自身受教育水平略高于子女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父母。从家庭教育承受度来看,子女在高中以下阶段的家庭可以承受子女完成大专以上程度的学习,子女在高中阶段的家庭可以支持子女完成大学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础教育各个阶段中,贫困地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低于家庭教育承受度。最后,通过相关数据的卡方检验得知,影响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因素在各教育阶段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二)贫困县居民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讨贫困地区居民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本文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对民族、户籍、所在地区、子女数量等变量进行控制的前提下,分别分析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影响。二是分析贫困地区居民家庭子女在基础教育四个阶段中人均教育支出的差异性。
表4中,模型1只考虑“家庭文化资本”变量对贫困地区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其结果显示,父母教育观念和受教育程度的系数和显著性方面均有较好的解释力,父母教育观念对家庭教育支出呈负向影响,而父母教育期望对家庭教育支出没有显著性影响。

表4 贫困县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2只考虑“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对贫困地区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该模型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建档立卡户和家庭教育承受度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而且普通家庭与贫困家庭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
模型3则综合考虑了所有变量。该模型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收入、建档立卡家庭、父母教育观念、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但各系数有所降低,而父母教育期望与家庭教育承受度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家庭人均收入(0.285)和父母受教育程度(0.015)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最大。
为了衡量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各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将模型3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得到模型4。该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家庭经济资本相较于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贫困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更重要的因素。具体来看,家庭经济资本中的家庭人均收入(0.230)和家庭文化资本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0.049)对于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普通家庭比贫困家庭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0.037),而父母教育观念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呈现了显著的负向影响(-0.049)。
以上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一的成立。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通过膨胀因子分析法(VIF)判断模型中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模型中各变量的容忍度的值介于0 和1 之间,VIF 均小于10,说明模型中各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这说明了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基本独立的,同时也说明了上述回归模型及其分析是有效的。

表5 多元回归模型中变量的膨胀因子
(三)贫困县居民家庭子女在四个教育阶段中的人均教育支出差异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和所在教育阶段的变化,贫困地区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那么子女就读年级的高低不同是否会影响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尚未达成一致。接下来本文将基于第二个研究假设,尝试探究各教育阶段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差异性。
表6 是多元回归非标准化分析结果。表7是对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同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所得到的回归系数。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消除了量纲、数量级等差异化影响,使不同变量之间更有可比性,所得结果也更有解释力。通常认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回归系数以绝对值大小来衡量,绝对值越大,它对因变量的影响就越大。本文采用标准化回归系数来比较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各教育阶段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作用大小。
在学前教育阶段,与家庭文化资本因素相比,家庭经济资本因素中的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根据表6 和表7 可知,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教育承受度是影响贫困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P<0.05),而结合表7 中标准化处理后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19和-0.075来看,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教育观念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影响的显著性降低(P<0.1)。

表6 贫困县居民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在各教育阶段的多元回归分析
在小学教育阶段,影响贫困县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因素相对较多。本研究发现,贫困家庭在子女就读小学阶段时额外增加的校外教育支出会使其家庭教育承受度和教育期望明显降低。在这一阶段,除了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教育承受度这两个主要因素外,建档立卡家庭(即贫困家庭)也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一个显著性因素,父母教育观念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均略有增加,而父母教育期望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却不显著。从表7 可知,在小学教育阶段,家庭人均收入的标准化系数为0.220,家庭教育承受度的显著性和系数仅为0.044,建档立卡户系数为-0.050;而父母教育观念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依然呈负向影响,为-0.060,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仅为0.034。整体看来,贫困县居民家庭经济资本整体标准化系数和为0.214,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文化资本整体标准化系数和为-0.021,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呈负向影响,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家庭经济资本比家庭文化资本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

表7 贫困县居民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在各教育阶段的多元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
初中教育阶段是决定子女是否继续接受教育的重要过渡时期。随着子女在校内外教育支出的增加,初中阶段的家庭教育投入明显高于小学阶段。本研究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初中阶段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两大显著性因素,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43和0.069,相较于小学阶段均有所提升,但家庭教育承受度、建档立卡家庭、父母教育观念和父母教育期望这四个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时期,仅有家庭人均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两个指标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其标准化相关系数为0.246和0.132。在这一阶段,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也分别代表了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在高中阶段,子女的校内学杂费和校外补习等教育支出使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大幅增加,加上新高考制度的调整给贫困地区孩子就读高中阶段的居民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等原因,使贫困地区高中阶段的教育收益率降低[27],进而导致贫困地区“新读书无用论”的抬头,这些都可能是导致父母教育观念、父母教育期望、建档立卡户以及家庭教育承受度这四个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的原因所在。
以上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假设二的成立。
六、基本结论与建议
经过以上研究,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果:(1)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均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较大,而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随着子女受教育阶段的提升而增大。(2)家庭经济资本中的家庭人均收入及家庭文化资本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贫困地区居民家庭在基础教育各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两个最主要因素。(3)在学前教育阶段,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教育承受度是影响贫困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结论与任晓玲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相吻合[24]。另外,贫困地区居民家庭在子女就读学前教育阶段时的教育投资负担率和投资能力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教育投资观念的影响,这一结论也印证了于冬青等学者的研究结果[1]。(4)影响小学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较多,除了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教育承受度这两个最主要因素外,建档立卡户和父母教育观念等对其子女处于小学阶段的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也存在显著影响。(5)贫困家庭在子女就读小学阶段时额外增加的校外教育支出,使其家庭教育承受度和教育期望均明显降低,这证实了早期学者提出的“贫困地区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农户实际的经济承受能力”[22]的研究结论。(6)家庭人均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初中阶段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两大显著性因素,但家庭教育承受度、建档立卡家庭、父母教育观念和父母教育期望这四个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差异。(7)在高中时期,仅有家庭人均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总体而言,贫困地区居民家庭的文化资本依然薄弱,父母的教育水平、教育观念和教育期望等对其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我国全面脱贫之后,国家仍需设法重视和提升相对低收入地区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同时继续加大为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良好教育机会的力度;学生家长也要有意识、有目的地提高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和合理的教育期望,并重视子女的非物质教育投入,从而以提升家庭文化资本为手段降低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