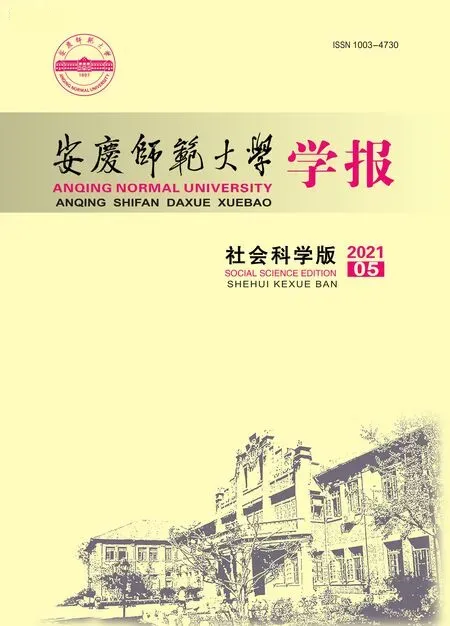俗字的“所指”及研究的两个“平面”
刘敬林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一、凡未被认定为正字的同词字均属俗字,可分“形俗”“音俗”两类
“俗字”这一概念的“所指”范围为何?
笔者认为当前研究俗文字的学者多把同音通用字排除在俗字之外的作法似欠妥。为了使讨论直观,请允许先引一组近年从海外回归的中医典籍中用来指称同一药物名称的同词异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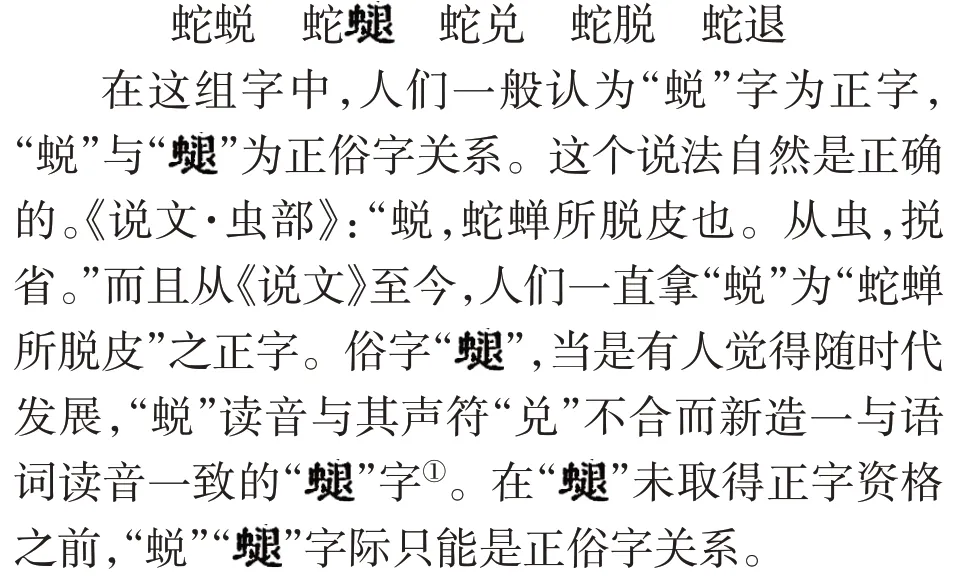
①《说文·手部》:“捝,解捝也。从手,兑声。”段玉裁注:“今人多用‘脱’,古则用‘捝’,是则古今字之异也,今‘脱’行而‘捝’废矣。”又《肉部》:“脱,消肉臞也。从肉,兑声。”段玉裁注:“消肉之臞,臞之甚者也。今俗语谓瘦太甚者曰脱形,言其形象如解蜕也。”由此我们觉得,《说文》将“蜕”释作“捝省”应是省声之意。若再拿“捝”“脱”为“兑声”字看,“捝省”或未安,因为直接释“蜕”为“兑声”而与“捝”“脱”一律,符合汉字构形系统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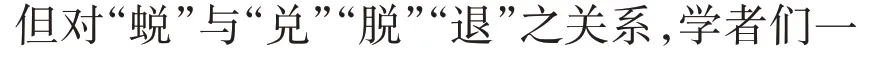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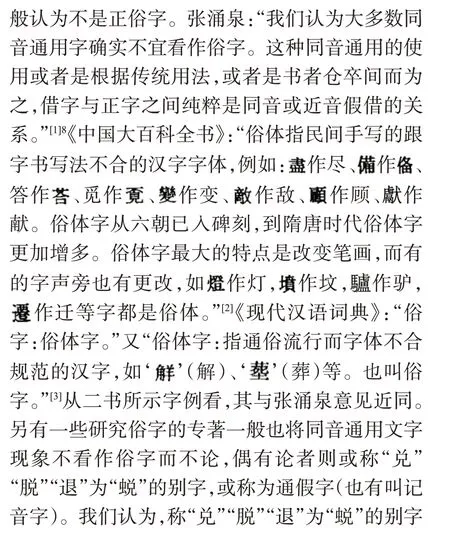

李运富在谈到用以表述汉字关系名称“异体字”“通假字”“正俗字”等术语时说:“这些名称所反映的汉字群组关系并不处于同一系统,它们是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的实用需要分别提出的,没有平列或对举的逻辑关系。如‘异体字’‘同源字’着眼于构形系统中对应词语的音义关系;‘通假字’(关联‘本字’)和‘古今字’都着眼于文献用字的职能关系,但‘本借字’指的是使用属性关系,‘古今字’指的是使用时间关系;‘正俗字’着眼于规范领域的地位关系;‘分化字’(关联‘母字’)着眼于字符职能的演变关系。”“这些术语各自立说,原本互不相干,但人们往往把本来属于不同系统的异质概念混同起来强加辨析,这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永远争辩不清楚的。”“‘正俗字’属于汉字的规范问题,应该放到规范领域去说。”[4]可见,在“正俗字”这一术语中,“正”的意思是“规范”字,“俗”则指相对于规范之“正”的非规范字,而与字的本用借用无关。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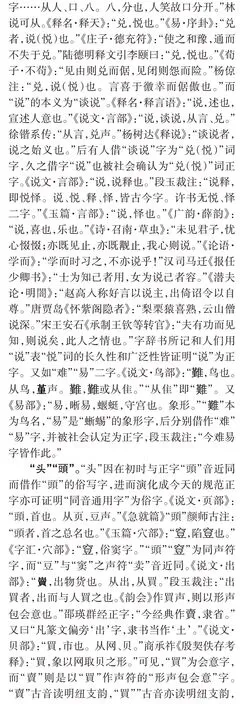

至于那些“或是书者仓卒间而为之”的“同音通用”字,因未被社会认定为是正字而确实存在着“借字与正字之间纯粹是同音或近音假借的关系”,但这个“借字与正字”关系是从字的“本用”和“借用”角度来说的,若从规范角度说,非“正字”之字,不称作“俗字”当名之作何?
其实,前人也多把书者仓卒间而为之的“同音通用”字称作“俗字”。《颜氏家训·书证》:
张揖云:“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汉书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谧云:“伏羲或谓之宓羲。”按诸经史纬候,遂无宓羲之号。虙字从虍,宓字从宀,下俱为必,末世传写,遂误以虙为宓,而《帝王世纪》因更立名耳。何以验之?孔子弟子虙子贱为单父宰,即虙羲之后,俗字亦为宓。或复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旧单父地也,东门有《子贱碑》,汉世所立,乃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是知虙之与伏,古来通字,误以为宓,较可知矣。
在这段文字中颜之推讲到了“宓”“虙”与“虙”“伏”两对字际关系。为讨论方便,先说“虙”“伏”关系。颜氏说“虙之与伏,古来通字”,这是就“古来”两字常混用不别即从同记录“伏羲”这一语词角度来说的。就字际形义关系言,“虙”应是“伏”的近同音借字,只是在颜氏眼里借字“虙”因社会承认而“转正”为“正字”而已。关于此,可从“伏羲氏”称名理据得知。晋王嘉《拾遗记·春皇庖牺》:“庖者包也,言包含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曰伏牺。”《说文·人部》:“伏,司也。从人,从犬。”段玉裁注:“司,今之伺字。”徐锴系传:“伏,伺也。从人、犬,伺人也。”王筠句读:“司,今作伺。”“伺人”必顺服人,故“伏”可引申为“屈服”“顺服”。《书·汤诰》:“罪人黜伏。”蔡沈集传:“故夏桀窜亡而屈服。”《淮南子·原道》:“海外宾伏。”言服从也。《后汉书·廉范传》:“世伏其好义。”言服其好义。《晋书·束皙传》:“时人伏其博识。”言服其博识。“民服其圣”为“伏牺”称名之由来,其本字必为“伏”字无疑。《说文·虍部》:“虙,虎貌。从,必声。”“虙”本义指老虎的体貌,用来记录原有本字“伏羲”的“伏”,当看作是有本字的假借。《素问·气厥》:“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虙瘕,为沈。”王冰注:“虙与伏同。”“同”是从“虙”“伏”同音又同为正字可用来记录同词来说的,若从字际形义关系说,亦为通假字,《汉语大字典·虍部》:“虙,通‘伏’。”当是对其形义关系的正确解释。
对颜氏所言“宓”为“虙”之俗字,可从两个角度进行讨论:一是从文字规范角度来说,在“虙(伏)”被当时社会认可为正字情况下,有人借与“虙(伏)”音近同的“宓”来记录“虙(伏)”词,那“虙(伏)”与“宓”字际当然是正俗字关系。二是从“本借字”角度说,“伏”是“伏羲”的本字,而“虙”“宓”均为音近同借字。《说文·宀部》:“宓,安也。从宀,必声。”《汉书·古今人表》:“太昊帝宓羲氏。”颜师古注:“宓音伏,字本作虙,其音同。”退一步说,即使颜氏将当时社会确认为正字的“虙”看作“伏羲”字的本字,则作为“虙”的俗字“宓”,与其本字“虙”之间也只能是同声符的“同音通用”关系——“宓”是“虙”的音近同假借字。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颜氏眼里的“俗字”“宓”与本字都是“同音通用”关系。
顺便补充一句:同词两字形同为“正字”的现象在古今汉字里都是存在的。《干禄字书》“并正”字例甚多,为节省篇幅,容不引。而这种文字现象在现代汉语文字里也是存在的,如“阎”“闫”。《说文·门部》:“阎,里中门也。从门,臽声。”《改并四声篇海·门部》引《俗字背篇》:“闫,与阎同。”“闫”字早见例为明佚名《吕翁三化邯郸店》:“向东华,上九霄,你到南闫走一遭。”清通俗文学作品亦沿用之,吕熊《女仙外史》:“第六十六回:谭忠又有家将二名:一闫细狼,一张黑胖驴。”后出之“闫”乃“阎”的俗字。在新中国“一简”时,古正字“阎”被沿用而为现代规范正字,而古俗字“闫”则作为异体被淘汰。但在2013年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阎”“闫”均为规范正字而与古代的“伏”“虙”并为正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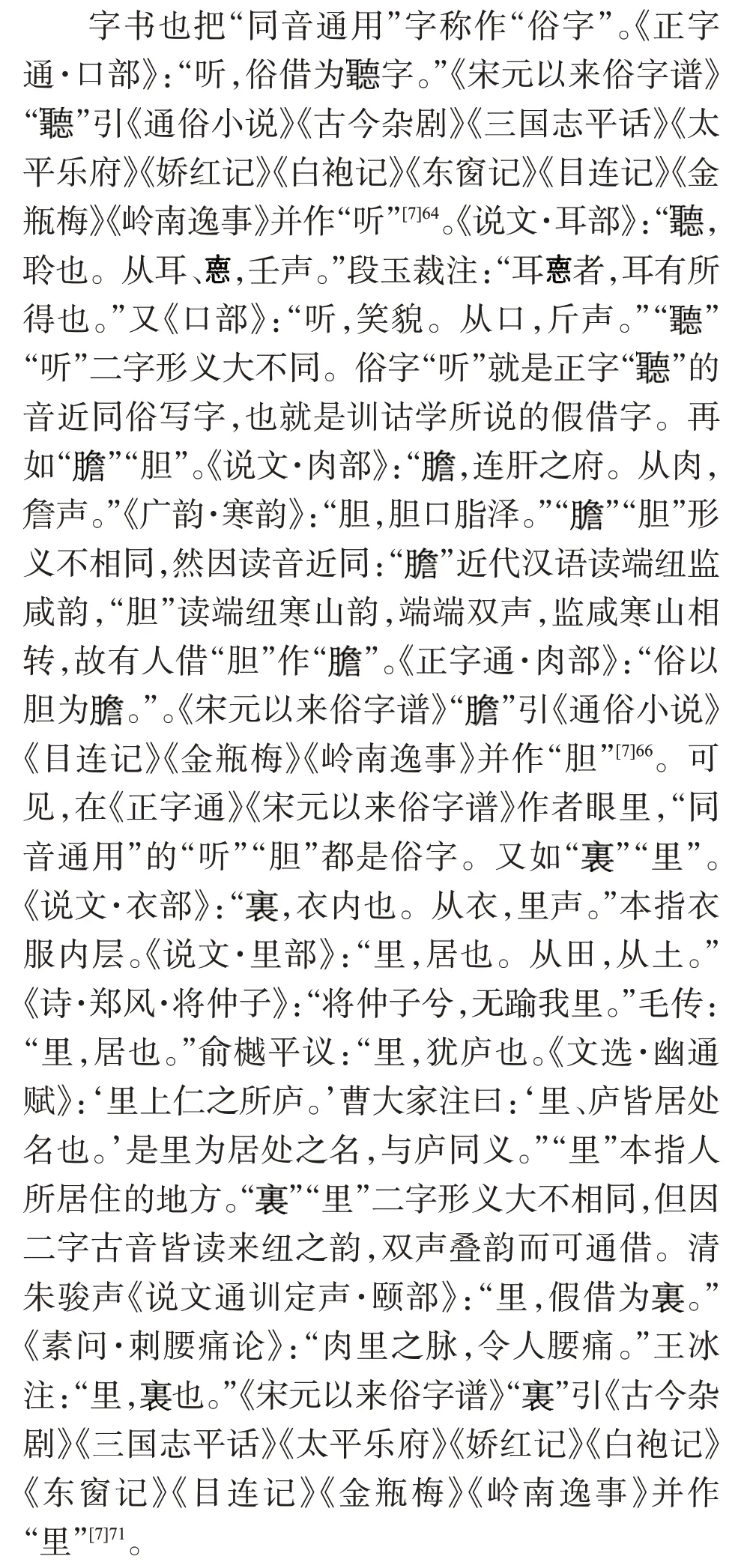
现代学者蒋礼鸿也认为“同音通用”字为俗字。蒋礼鸿说:“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区别于正字的异体字,都可以认为是俗字。”“简体字是俗字中的重要部分,但俗字不都是简体字,因为异体字也有比正字形体更繁复的,如。”“其实同音通用字在民间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例如敦煌写本的变文里交字通用作‘教’,由字通用作‘’,‘望’和‘忘’互相通用,歌字通用作‘哥’等。搜辑和归纳这些用例,也应该是俗文字学中应有内容。”[5]
此外,从各家对“俗字”的定义看,“同音通用字”应属“俗字:
《中文大辞典》:“俗字,谓通俗流行之字,别于正字而言。”[8]
《辞海》:“俗字,异体字的一种。旧称流行于民间的多数为简体的文字为俗字,别于正字而言。区分正和俗的标准,往往随时代而变迁。”[9]
《辞源》:“俗字,在民间流行的异体字,别于正体字而言。”[10]
《汉语大词典》:“俗字,即俗体字。旧时指通俗流行而字形不合规范的汉字,别于正体字而言。”[11]
蒋冀骋、吴福祥:“俗字是相对正字而言的。正字,指可在《说文》中找到依据,可用六书条例进行分析,并且可以在高文大册中见到的字。俗字指那些不见于《说文》,不能施于高文大典,民间所习用的字。”[12]
张涌泉:“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1]1
以上各家虽在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异,但都认为“俗字”是“别于正字而言”的一个汉语文字学术语。而“正俗字”所表述的字际关系又是从规范领域的文字地位角度来立说的,既然与“正字”相对的字是“俗字”,而由“书者仓卒间而为之”的“同音通用字”又不是“正字”,若不将其归入“俗字”,哪岂不成了非“正”非“俗”而“无家可归”之字?

总之,从规范文字角度将文字的地位关系划分为相对应的“正”“俗”,并进而将“俗字”分为“形俗”“音俗”两类,既符合事物分类同质的逻辑标准,也与汉字史上文字使用的实况吻合。对“正俗字”概念的定义,从着眼于规范领域的地位关系而可作如下表述:“正字”指汉字历史上不同历史阶段使用的规范字,“俗字”,则指与正字相对的一切同词字书写符号。因汉字为意音文字,故俗字可分“形俗”“音俗”两类。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所作的定义没有将“俗”释作“通俗”“民间”。因为此“俗”虽然与其常见义“通俗”“民间”相关,但它是与“正”相对的引申用法,这就犹如佛教、道教称未出家人为俗人之“俗”作“凡世”讲,而不能解作“普通人”“民众”一样。在“正俗字”这一概念中,按照颜元孙《干禄字书》的说法,“正”,指的是施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述”“文章”“对策”之类“高文大册”,以及“流芳百代”的“碑碣”中的“有凭据”字;“俗”则指“籍帐、文案、券契、药方”“表奏、启,尺牍、判状”等“非涉雅言”的实用性文体中的缺“凭据”字,而与“通俗”“民间”无必然性。关于这一点可从目前人们引以为说的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序》中找到答案:
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名曰《干禄字书》,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具言俗、通、正三体,偏旁同者不复广出,字有相乱因而附焉。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启,尺牍、判状,固无诋诃。(若须作文言,及选曹铨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张涌泉在谈到俗字的通俗性时说:“通俗性是俗字的根本特性之一,俗字之所以成为‘俗’字,便与它通俗的特点有关。”并在引颜氏“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后,说:“根据这一表述,俗字的通俗性可以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字体‘浅近’;二是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书。”[1]122我们觉得这个理解似与颜氏所言“俗”不相一致。张涌泉对“浅近”进一步解释说:“字体浅近,主要与俗字省减的特征有关。”[1]122但刘中富进行的量化统计似证明此说不成立:“《干禄字书》337 个俗字的总笔画数为3 991 画,平均笔画约11.8 画,与之对应的337 个正字的总笔画是4 186画,平均笔画数约12.4 画。从总体上看俗字笔画少于正字,但就一对一的情况而言,却并不是凡俗字都简化。跟正字笔画数相同的有62 个,约占总数的18.4%;比正字笔画数多的有107 个,约占总数的31.75%,比正字笔画少的有168个,约占总数的49.85%。”[13]而《干禄字书》自身所言“俗者”载籍似对“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书”说法也是否定的。“籍帐”指登记户口、田地、赋税等簿册,“文案”指公文案卷,这两种自然属于官方文献。“券契”“药方”也不独用于民间而与官方无涉。《说文·大部》:“契,大约也。从大。从。《易》曰:‘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徐锴系传引《周礼》郑玄注:“大约,邦国约也。”段玉裁注:“《小宰》:‘听取予以书契。’大郑云:‘书契,符书也。’后郑云:‘书契谓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书聚目,狱讼之要辞,皆曰契。’今人但于买卖曰文契。《玉篇·大部》:‘契,券也。’”《汉语大字典·大部》:“契:券证;文卷。古代把证明出卖、租赁、借贷、抵押等关系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案卷、总账、具结等均称为契,近世则只指前一类文书为契。”[14《]后汉书·百官志三》:“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至于“承用已久的俗字”——“通者”所涉的“表奏、启,尺牍、判状”等,除“尺牍”指书信,官民并涉外,余者皆与民间无关。“表奏”指古代臣下向君主进言的奏章。《释名·释书契》:“下言于上曰表。”《广雅·释诂四》:“奏,书也。”“启”指下达上的笔记、书启。《新唐书·百官志一》:“下之达上,其别有六:一曰表,二曰状,三曰,四曰启,五曰辞,六曰牒。”“判状”犹今之判决书,自然亦归官方之属。而颜元孙“所谓正者”下所言“碑书多作八分”亦是对“俗”指“通俗”“民间”的否定。“碑书”指书刻在石碑上的文字,而作为“碑书”的载体“碑碣”为古代官民并用来记死者生平功德以作为纪念物或标记的石头。《后汉书·崔寔传》:“初,寔父卒,寔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业。……及仕官……。”元白朴《墙头马上》第三折:“你不去望夫石上变化身,筑坟台上立个碑碣。”而《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的以“居士”“处士”等身份称谓的众多碑文,更是“碑书”亦流行于民间的明证[15-16]。可见,颜元孙笔下的“俗(通)者”“正者”不是从“官”“民”相对来说的,而是从用语平实的实用性文体中所使用的无“凭据”字,与“高文大册”中所使用的“并有凭据”的字来说的。
二、研究的两个平面:以构形学研究“形俗”字,用字用学研究“音俗”字


而对“音俗”字的研究,是借助于文字的声音所承担的该汉字在古代文献具体语境所适宜的词义,探讨的中心是汉字的使用,属于汉字字用学范畴。如近年从日本回归之明代医籍《济世碎金方》卷之一:“用上等真正油烟京墨,不拘多少,槌碎,入水少许,以瓦器乘之,火上温热,待冷可丸时,丸如梧桐实大。”其中,“乘”是“盛”的音近同俗写字。“乘”“盛”二字近代汉语均读穿纽青庚韵,双声叠韵,有通用的语音条件,故以“乘”作盛物字。同书卷之四:“先将锡称定,用铫子乘定,火上溶化。”又“用铁勺乘酒,将草、砒一同入烧酒勺内。”用法并同。这样,我们就会在了解“乘”字的本用、兼用基础上,进而明确其借用情况,以较全面的把握“乘”字的职能情况。
三、结 语
总之,“俗字”所反映的汉字群组,与“正字”所反映的汉字群组,为汉字规范问题系统中对举的逻辑关系。人们在研究俗字这一汉字群组字时,应该放到规范领域去讨论,从规范领域的地位关系角度以弄清楚与“正字”相对应的俗字的“所指”,并在理论方面给“俗字”以科学的内涵与外延,进而依据汉字意音文字的性质将其分为“形俗”“音俗”两类,使其既符合事物分类同质的逻辑标准,也与汉字史上文字使用的实况及人们的认识吻合。唯有如此,我们的俗字研究才能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的研究重点和方法,以准确地揭示汉语俗字构形规律及文字使用全貌。